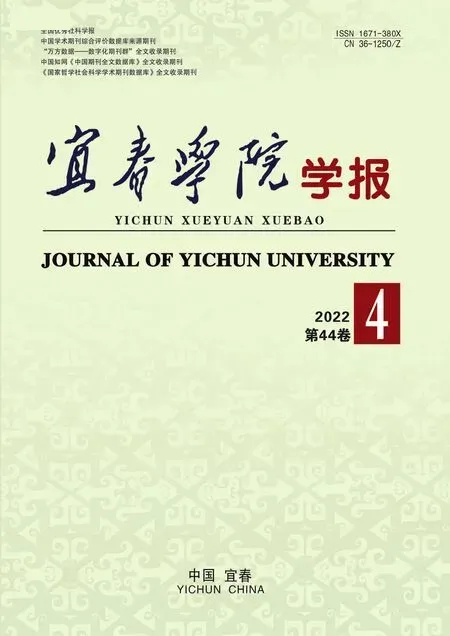经典符号学术语symbol名实探
2022-09-08徐结平王永亮
徐结平,王永亮
(1.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8024;2.河南大学 外语教研部,河南 开封 475001)
近代以来symbol一词在西方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艺理论等学科中用途广泛、内涵丰富、概念复杂,黑格尔、胡塞尔、弗洛伊德、荣格、弗雷泽、拉康、德波莱尔等都曾用做重要概念。在符号学界,皮尔士、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卡西尔、莫里斯、雅各布森、西比奥克、艾柯等也都曾专门论述。皮尔士曾言,“symbol一词如此多义以至于再添新解都是对语言本身的伤害”;[1](EP 2.297)艾柯曾言“symbol出现在于不同语境,单义性似乎不可能”;[2](P132)西比奥克则认为symbol是最被滥用的术语。[3](P57)赵毅衡“在西语的符号学著作中,这个问题弄得比其他学科更乱”。[4](P194)因此,作为符号学核心术语之一,我们有必要梳理重要符号学家对此术语的不同界定,厘清概念之实,总结该词内涵嬗变。汉语定名须兼顾西方概念之实,再探究翻译之名,“察其实”,“分其物”再“有其名”,以知实为先导,遵循同实则同名,异实则异名的原则。
一、索绪尔之symbol
索绪尔创建了semiology一词,其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语言范畴,应用于现代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无独有偶,以语言为中心的索绪尔及其后的叶尔姆斯列夫也都曾专门论述symbol,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又有区别之处。
在索氏的二元语言理论之中,symbol置于语言符号的对立面,二者区别在于: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联是绝对或相对任意性的,即理据也许存在,但绝非主要特征;symbol恰恰相反,它与对象之间有理据相连;语言是独立的符号系统,即它与所指称对象之间不具有任何可见性关联之特性,symbol则不然,它在能指与所指间存在一种自然联结,是一种并非完全任意的符号。索绪尔并未将symbol完全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semiology就是“研究符号存在的科学”,[5](P16)并认为“语言是一套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因此与书写系统、盲文字母表、象征仪式、礼仪客套、军事信号等等相当……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研究的一部分”,[5](P70)这与后来的结构符号学家的看法有所区别。
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向前推进的重要学者——叶尔姆斯列夫将自己研究对象定名为语符学(glossematics),“是关于符号一般结构的科学,对象为符号系统”。[6](P90)语符学将symbol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他将语言符号分为两个层面:表达层与内容层。两者的组成原则不同,比如“人”的表达层为“r”“e”“n”组成,而内容层为“人”的概念,与索绪尔类似,叶氏之symbol多指非语言符号,其表达层与内容层为同构关系(isomorphic relation),即两个层面在形式上不存在异质性,也就不存在类似言语符号的双重分节,叶氏称之为“可被阐释的非符号性的实体”,[6](P114)意为内容层与表达层之间不做区别。
无论作为研究对象与否,索氏与叶氏具有一定的共性,从他们论述与所举实例可见,他们的symbol概念蕴含皮尔士的像似符,即符号与对象之间具有像似性、相近性特质。索氏认为计时的钟声为symbol,因其数目(符号)与计时点数(对象)具有共性—数量相等。叶氏的系统性同构体,将棋子、交通灯、旗帜、徽章、绘画作品等都是symbol,因为都是“那些与它阐释同构的实体”。[7](P114)对于叶氏,语符学研究对象首先得有双重分节,内容层的结构法则是其主要研究内容,相当于后来1938年莫里斯符号学三分支中的符构学(syntactics),符义学(semantics)与symbol被他排除在研究之列以外。
二、皮尔士之symbol
皮尔士对术语有过更替,早期多用表征(representation)指代后来的符号(sign),symbol之前也用过type与general representation等,但一旦名称确定,就不会轻易改变。有研究认为,在皮尔士的语境中,symbol有两义,一为符号,另做icon-index-symbol三分之后者,但皮尔士一生孜孜以求“弄清困难的词和抽象的概念和方法”,[8](CP2.400)他的实效主义(pragmaticism)就是“一种弄清任何概念、教条、命题、词和其他符号的真实意义的方法”,[8](CP 5.6)一生自创术语过百,从《澄清概念》与《术语伦理》能清晰察觉皮尔士本人对术语要求极为严格,在sign与symbol同时出现时,不大会出现模棱两可或逻辑错层的概念混用。即便在早期,《目的逻辑》(1865)一文,就试将representation分为copies-symbols-signs三类,尝试将sign与symbol平行对待。同年在《科学逻辑》一文中将symbol定性为类符(type),表征的是一个对象的某方面特征或多个对象的某一共同特征,具有sign的假定与虚构性,但也可具备对象的实在秉性,此时的sign定性他后来思想出入较大,但概念上求精求实为他一生的追求。
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也是皮尔士的思想进化史,symbol的定性历程就是缩影,symbol论述之关键词变迁,可窥见他日臻成熟理论体系。1865-1867为icon-index-symbol三分野的萌芽期,在《范畴新篇》中最终定型。1894年为其思想的第二个分水岭,此时他认识到先前论述的局限,更为严谨也明确地将symbol与规约符号(conventional sign)区别对待。
(一)1894年前symbol界定
1894之前,论述symbol最常见有归属性(imputed character/quality)、规约性(conventional)与一般性(general)三个关键词,规约性与一般性学界论述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①第三类也是最后一类表征称为symbol或曰一般性表征,它的内涵属性决定延指。所有的单词与观念、大部分的词组皆归此类,一个命题,一则论证,甚至一整本书可能或应该是一个symbol。[9](W 1.468)
②诸如单词或观念此类一般性表征都是symbol。[一]symbol作为表征,两方面与对象在无法割裂:关键性的质与连接——归属的质与理想的连接。[9](W2.55-56)
③……三类表征,第一类为与对象的某特质类似的表征或称为类似符(likenesses);第二类为与对象之间存在事实相关,称之为指示符或符号(sign);第三类为与对象之间的关联基础为归属性,与一般性符号相同,或可定名为symbol。[9](W2.55-56)
④表征(即后来的符号概念)不但具有物质属性,还有(人为的)将某属性归于对象身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归属性。举例来说,词语“白色”出现在某本印刷书籍中,其相关的物质属性为黑色,但归属性是白的。[9](W 3.64)
以上皮尔士五段论述中,①symbol的内涵属性能决定它的外延所指,内涵属性(attribute)即归属性;②认为symbol除归属性外,还可见后来三级符号范畴划分的端疑,即symbol作为三级符号范畴是不可割裂一级符号范畴(quality)与二级符号范畴(relation),即后来普遍范畴理论的第一性(firstness)与第二性(secondness);③来自《范畴新篇》,此文为其本人的得意之作,是他三分的定型开端。④阐释符号的物质性与归属性之别,物质性为本原属性,归属性指符号依据借助思维体(mind)将某特征认为强加在对象身上,即symbol具有将某种属性归于某对象身上的能力,比如,symbol“甲”具有“x”特性,指称对象“乙”,可理解为“甲”将“x”特性归属于对象“乙”。[10]例如,“狡猾的狐狸”,这里“狡猾”就是归属性,其实没有研究能表明在动物界中,狐狸能比狗或其他某动物“狡猾”。归属性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个归属特性会发生改变,如在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前,普遍认为“男人阳刚,女人柔弱”,现在发现“阳刚”“柔弱”并非性别差异,只是强加在对象身上的属性。
早期皮尔士多用归属性,中期多用规约性,而一般性则贯穿始终,此三词有相通之处,不同点在于相对于一般性与规约性,归属性可能更侧重symbol的能动性而弱化了符号主体的作用,后代学者进一步解读皮尔士的symbol具有生命性、生长性与自主性,而符号主体比如人并不能随意改变它,只是符号生长或曰符指过程中扮演工具的作用。[11]早期皮尔士以语言文字为例作为symbol的实例较为常见(比如以man为例),认为symbol对对象的表征是归属性的,一般性的,类符,且存在于主体大脑中的观念,这与索绪尔所认为所界定的“所指”概念有惊人的相似,这也是许多后代学者将symbol与语言符号或规约符划等号缘由。
(二)1894年后皮尔士之symbol
1894年后,皮尔士对symbol的定性中,最为明显的改变为将规约性只作某些symbol特性之一,并渐渐被习惯(habit)所代替:
我认为我称它为规约符号,或曰依靠习惯(后天或先天)表意并非另生新义,而是回归源意……亚里士多德称symbol为规约符。在希腊语中,营火是symbol,即共识之信号;旗帜是symbol;口令是symbol;徽章是symbol;教会之教义被称为symbol……,戏票为symbol,任何能让某人获得某物的票据或支票是symbol。甚至某一抒情表达也可被称为symbol。此乃源语之要义,读者可看出我并未扭曲该词词义。[1](CP2.297)

①我注意到将自然症状即归为指示符又称为symbol,因此,将symbols限定为规约符号,是另一错误。[8](CP2.340)
②自亚里士多德或更早,规约符号就获名symbol,但是除了规约之外,还存在依赖自然倾向的symbol,他们就是自然symbols,所有思考都是依赖自然symbol与规约symbol的自然化的进行。[13](MS[R]450.6)
③第三类符号曰symbols,不但如同其它符号一样,如是阐释并产生如是功能,而且具有特别意指特征——即仅基于习惯、自然倾向或约定俗成上的意义。[1](EP2.274)
④symbol用做一类符号的统称,对于阐释者,它指称对象不考虑与它是否相似(尽管这些因素曾左右了当初对符号的选择),同样不顾及与此(对象)的实在联结与否(可能联结很近),只是因为阐释者的思维习惯,无论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习得,在任何时候将他们直接指向对象。[13](MS[R]638.20-21)
①写于1895年,在这段论述中,他反思在1867年《范畴新篇》中犯的两个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明确指出symbol的范围应该宽于规约符号。此后再论及symbol与规约性时,作者一定加上其他一些限定词。如1898年他用到了“规约性或准规约性”;[13](MS[R]484.7)1902年用到“自然习惯或规约习惯”;[8](CP 2:307)1909后甚至弃用规约一词,完全以习惯代之,并将自然倾向也归入习惯的一种,说明他意识到规约或语言符号只是symbol最为常见的类型之一,绝不是symbol之全部。Nöth认为,皮尔士将规约性作为symbol界定只是附和自《克拉底鲁篇》以来整个西方语言哲学史一直存在的二元对立(nomos/physis)传统,即语言规约论与自然论之争,“为了便于那些深谙规约符传统的人更好地懂得他的定义”。[14]故皮尔士在1894年后对symbol的论述更加严谨,从以上引述也可以看出,他是将symbol分为两类:自然symbol与规约符;其后认为symbol的指称的确定性取决于三因素:自然倾向、规约性与习惯性;并在1909年最终弃用,完全以先天或后天的“习惯”代之,这里面就包含了自然倾向与规约性了,表述更加科学。
三、后皮尔士时代之symbol
自从皮尔士符号思想在学界被发现并广泛重视,它的符号众多三分类中论及最多的还是像似符、指示符与symbol。伊始,对symbol以及符号分类,无论认同与否都绕不开皮尔士。
(一)莫里斯的界定
查尔斯·莫里斯的行为符号学受当时流行的美国实用主义、行为主义与欧洲逻辑实证主义三种思潮的影响,其中数现代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它的导师社会行为学家乔治·米德与语言哲学家保罗·卡尔纳普的思想的影响最大。在皮尔士理论的基础上他努力向前推进。譬如,在1938年在符号三要素(符号—对象—解释项)的基础上加入了阐释者,1946年再添加语境概念,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其实皮尔士的影响在他早期著作中清晰可见,如1938年的《符号理论基础》一文将符号分为指示性符号(indexical signs)、通符(universal signs)与描述性符号(characterizing signs)。
只要是某符号(如用手指示的行为)只延指某单一对象,它就是指示符;如果某一符号为复指(比如词语‘男人’),它就可以依多样方式与以解释或限制它的应用范围的符号结合;如果某一符号延指所有(如词语‘某物’),那么它将与每个符号都有关联,因此具有通用含意,也就是说,它在语言中它暗指所有符号,此三种符号分别为指示性符号,描述性符号与通符。[15](P31)
此时的莫里斯还是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理论,借用Andrade的主导符(dominant sign)与说明符(specifiers),他将解析句子基本结构为:主导性描述符号[说明性描述符号(指示性符号)]。在此,他基本沿袭了皮尔士对于指示符的界定,但在语义分析中,并未将像似符与symbol置于指示性符号同等地位,而是隶属于描述性符号的子分类:
总之,指示性符号实指某时刻它的指向物,但非为(对象的)的描述(仅大略暗示时空方位),也无需与对象相似。描述性符号是对意指的描述,此类符号可能具备所示对象的某特性,如像似符;若非如此,就是symbol。照片、星图、模型、化学结构式都是像似符,而词语“照片”,星星与化学元素的名称都是symbol。[15](P37)
其后,莫里斯意识到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片面性,“全面的符号学研究必须公平对待非语言符号”,[15](P272)并认为:“皮尔士符号学的长处部分在于应对非语言符号的能力,因为它未对任何(符号)媒介设限。”[15](P295)此时对symbol的论述也并非将symbol与像似符—指示符三分,而是采用二分法将符号分为信号(signal)与symbol两类,“symbol为阐释者所创造的能代替其他同义符号(来自不同类符)的符号,所有的符号要么是symbol,要么是信号。”[15](P100)在他的行为符号学理论中,信号与symbol的差异在于,动物只具备理解信号的能力,而人类具有思维,因此不但能使用信号,而且能创造、理解与使用symbol。“简单来说,信号而非symbol主宰动物行为,语言符号包括后语言symbol是人类主要或曰独有的技能”,[15](P131)他视为信号与symbol的差别所在。后语言symbol指被解释为阐释者所创造的,能代替语言符号表意的一切非语言符号,这种符号可以是个人专属性符号,如自我独白,也可以是人际间的交流符号,如手势。莫里斯还认为,symbol具备可替代性、可再造性、情境独立性等特征。相比而言,他们是更强的符号,但也正因如此,在行为过程中,信号的模态有限性、刺激关联性与情境依赖性使得它比symbol更可靠。
虽然限制在了语言层面,早期莫里斯的符号分类还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皮尔士的三分法,在他的行为符号学理论中,保留并详细论证了皮尔士像似符的重要性,并认为像似符可作为symbol下属类别,即iconic symbol,可见此时的莫里斯在内涵上改造了symbol,但在外延上认为symbol主要包含像似符、语言符号、后语言符号等,更像是sign的别名,只不过他有意识地区分了“符号”与“信号”。
(二)雅各布森界定
皮尔士如今在符号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和雅各布森的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他认为皮尔士是“美国有史以来创见最多,最为广博的思想家”。[16](P8)对于像似符—指示符—象征符三分法,他的最大贡献在于证伪了当时学界普遍认为的语言只是任意性的观点,“任何努力将言语符号仅作为规约性的任意符号都是误导性,都是过度简化。在语言结构的不同层级中,虽为从属,像似性扮演着纵多且必要的角色”。[17](P700)可以说,雅各布森是语言中的像似性的研究的开拓者,其后“音韵学、形态学、构词法、句法、语篇、语言变迁等各层级的像似性越来越多地被发现了”。[18]
同时,他还论证了语言中的指示性,借用了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的“转换项”概念,认为语言中存在“如在不涉及到说话人与受话人正在交际的信息时,其意义就不能确定”[18](P132)的元素。这些转换项就具有指示性。转换项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人称代词。正如皮尔士所言:“列举出纯指示符或者发现某一符号完全不具有指示性的例子都很难。”[8](CP 2.306)
在给三类符号定义时,雅各布森启用了源于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哲学signans与signatum两个术语,而非索绪尔的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尽管在细节表达方面有别,但在皮尔士的学说中,斯多葛派传统明显,将符号构想为signans与signatum相关联两部分。”[17](P11)在雅各布森基于结构主义思想,视归属性与事实性(factual)为两极,“此三分类(icon-index-symbol)是基于两类二元之对立——相似性—邻接性,事实性—归属性”。[17](P22)相似与邻接即像似符与指示符之别,而归属性与事实性为symbol与指示符之别。
(三)西比奥克的界定
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数理逻辑是其根基;莫里斯力图将符号学科学化,他的学生西比奥克则致力于将人类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生物界或更广的领域。关于分类,西比奥克曾言:“并非将符号做实际分类,严谨说来,分类的依据是符号的某方面性质,一枚符号的性质可能常常是多方面……”[3](P43)因此,并不能武断的将某一符号划归某类,只能说这枚符号的某方面是像似性、指示性还是象征性。他在吸纳了皮尔士的三分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信号、症状与名称三类。
他将symbol界定为“能指与实指之间不具相似性与邻接性,仅以规约相连,意指内涵为类指”。[3](P56)西比奥克的定义中借用了索绪尔的能指概念,但如同莫里斯,西比奥克将对象概念做了细分,一为符号意指,但并非都涉及到实在,一为客观世界的存在体。将指示关系定为邻接关系,是借用了雅各布森对皮尔士指示符的独特诠释。为明确符号之间的区别,在皮尔士的手稿中确有“(symbol与对象之间)非像似或外在物理联系”[8](CP5.73)等表述。但也不乏“不存在纯粹的指示符”[9](CP2.305)与“所有符号都或多或少的具备象征性”[13](MS[R]484:5)等说法,西比奥克的解释是每个符号不止具有一面,我们区分的不是符号,而是他的某方面特性。这是皮尔士三级符号范畴理论的简化,略去了他关于符号的生长性以及转化思想。在定义中,加入了内涵(intension)概念,如他本人所言,旨在区分于其后同样具有规约性与任意性的符号类型:名称(name)——只具有延指,涵指多是空洞的。
西比奥克对symbol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极大地扩展了symbol使用者的范围,在他之前,皮尔士认定的symbol隶属智力符号,同样莫里斯也认为symbol,特别是后语言symbol为人类专属。西比奥克证明在整个界都存在任意性的规约符号,一种食肉昆虫舞蝇在交配前,公舞蝇有“送礼”的习性,他还并发现雄性舞蝇甚至会为了交配权,欺骗性的送给雌性没有食物的空“包装”,趁母蝇费力打开“包装”之际行交配之实,这些在西比奥克看来都是具备规约性的symbol。[3](P58)
(四)艾柯之界定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受叶姆思维列夫的影响,对符号、symbol的界定以及他的符码理论(code theory)都以表达层与内容层的双重分节为理论基础,但艾柯的symbol与叶氏完全不同,并没有将symbol排除在符号学的研究的门槛之外。他曾专门就symbol在哲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等学科中的概念运用加以系统论述并形成自己观点。值得肯定的是,艾柯的符号思想在nomos与physics二元上实现了突破。他认为即使是像似符号也存在左右像似的文化单元或风格法则,如中国的山水画就存在特有的文化习俗(convention),反对将symbol任意化。“符号效应(sign function)就是表达层与内容层基于规约性符码(一套联结规则)的联结,如果存在与对象有某种程度的理据、像似、类似、自然联系的符号,符码能提供产生符号效应的规则。”[19](P49)他论及常见符号范畴时有独到之处:第一范畴指建立在推理机制上的符号与对象关系,为逻辑上的前件与后件,如“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第二范畴为普通语言,也包括旗语、信号灯、纹章、标签等,需预设符码的存在,这些符码是发出者与接收者交际的前提;第三范畴为symbol,他表征的对象是抽象的,具备第二范畴的任意性,也具有第一范畴的推理性,同时具有像似或类似的理据性,为人类所独有,比如用于逻辑、化学、数学的公式或图表等。[2](P16)艾柯界定的symbol与叶尔姆斯列夫不同,也不同于皮尔士:symbolic表意具有模糊性(vagueness)、无限延义性(艾柯称为content nebula)、情境性、阐释自由性。
艾柯认为“……一枚symbol依据它与对象之间任意性与规约性关联……symbol到底归于像似符号,还是任意符号范畴,他(皮尔士)需要二选一”,[2](P136)因此他将皮尔士的symbol界定为“一枚symbol依据任意性与规约性与对象相连”,[2](P136)因此依他所理解的皮尔士,他写道“奇怪的是,依皮尔士的理解,许多人将诸如旗帜、徽章、占星图、化学符号等称作symbol,其实如果是皮尔士本人会认为具有大量像似品质的符号”。[2](P136)艾柯推崇皮尔士的解释项理论,在symbol的论述中借用了他的无限延义思想,将symbol界定为具有模糊性、多义性与个人习语性(idiolectal)的符号,“symbol不具备既定的文化编码能力;它是个人习语性的,释义只能存在于它所在文本环境(否则只能视为既定symbol的不当使用)。”[2](P161)可见,艾柯并不认同他所理解皮尔士的symbol,认为阐释不具备模糊性与暗指能力,如在军旗中,狮子或鹰的图形是像似性的,他们喻义勇猛是有符码预设,不能称作symbol,艾柯对symbol的界定近似修辞学,并走向了语用学维度。
综上所述,后代学者有将皮尔士之于symbol的定义简化之嫌,无论是西比奥克所界定的“一枚符号不存在像似性与相邻性,只是在能指与指称物或指称项之间存在规约联系”。[3](P56)艾柯以“symbols作为规约表达”为章节标题界定皮尔士的symbol。克劳斯·厄勒(1987)认为“symbol是这种符号,由对象决定,对它的阐释就是如此,因此,与对象之间完全独立于相似或物理联系之外,比如旗帜”。[20](P6)厄勒之意为symbol与对象之间不存在内在相似性(像似符)与外在的物理相邻性(指示符),没有理据可言。
五、国内符号学界symbol翻译与问题
在学理过程中,我们出现了某些误读与曲解,“一直以来,国内符号学术语译名混乱、意指含糊乃至误译,这势必影响思想传播与学科发展”。[21]国内目前针对符号学术语symbol的翻译常见的有“规约符”“抽象符号”“象征符”与“常规符号”等,有认为“象征一词体现不了人类在常规符号加工中的独特的约定性”,[22]显而易见,“常规”的定名也是来自于conventional,与“规约符”实无差异。王亦高认为symbol的翻译应该依据是否理据、是否抽象、是否能指消融来确定是“象征”还是“符号”;[23]胡易容坚持在三分法中symbol应翻译为规约符;[24]彭佳论述过symbol的建立基础为习惯,论述了从规约与习惯差异。[25]
如同后皮尔士时代的众多符号学家,国内最大的误解还是在于对皮尔士之symbol概念的翻译。“抽象”一词非皮尔士symbol属性,首先,三分法里抽象与否并非的symbol的主要特质,其次,如果symbol是抽象符号,受众可能认为icon与index就会是“具体符号”,事实上,icon或index也可以很抽象(比如在一些西人的眼里国画很抽象),而symbol也可以很具体(镰刀与锤子代表工人阶级),且抽象与具体之间不是绝对的。
“规约符”是将conventional sign与symbol直接划等号,如果仅从皮尔士所举实例,1894年之前他本人的论述以及概念的明晰化方面考量,此译不失为一种便捷之法,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此译难言准确,皮尔士之symbol翻译,我们应该更加依据他后期的论述,即“习惯(habit)”,皮尔士认为“习惯”有天生习性与后天习性两种,主体可以是人类和可以是其他生物,甚至器官,细胞、分子等,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并可进化,此外还有个体习性与群体习性之别。“规约”多是后天的、人为性的、群体性的,意义相对狭隘的多。总结说来,首先,“规约”在皮尔士的原稿中只是1894前的界定,其本人也认识到此界定的局限性,在1985—1903年前后,更多的是将“规约”“自然倾向性”与“习惯”三特性并列,其后更是遗弃该词,以“习惯”待之,因此不符合作者原意;其次,“规约”按照汉语词典的释义为“经协商确定的共同遵守的规章、条例”,绝大多数的symbol不存在协商,而是依据皮尔士所说的自然倾向性。因此,译为“规约符”会缩小symbol的意指范围,如前文所译的皮尔士实例“某生理症状”也可是symbol,就不可能有规约的成分;其三,限定为只具有任意性的规约符,会有陷入自柏拉图《克拉提鲁斯篇》以来,长期困扰西方语言学史二元对立的危险中,皮尔士在symbol定性中挣脱了任意—理据、自然—约定二选一的尴尬境地,因此,翻译为“规约符”无疑是掩盖了皮尔士的理论深度。
“象征”在《大辞海》中有两条释义:①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如鸽子口衔橄榄象征天下太平,具有一定的理据性,更具偶成性。②通过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如海燕象征勇敢,舞台上的4个人象征千军万马等,多指以具体指代抽象,具有一定的理据基础,此译适合前皮尔士时期的symbol界定。如果依雅各布森的看法,类似即像似性,联系即指示性的话,也能传达皮尔士symbol作为三级符号的包容性(既包含像似符的质(quality),也包含指示符的二者关联(relation)。因此,余红兵也认为,“该词内涵同时涉及了约定俗成性、后天习得性、文化性、文艺象征性等多个方面,考虑到这个特点,译为‘象征’和‘象征符号’”。[26](P32)
综上所述,以皮尔士思想为参考点,symbol概念在现代符号学中大体有两端,一端以索绪尔为代表,包括其后思想一脉相承的叶尔姆斯列夫,索绪尔与叶尔姆斯列夫的symbol近似皮尔士的像似符,艾柯以叶氏分节为基,他的symbol界定近乎修辞学定义,事实上走向了符用学。另一端以莫里斯、雅各布森与西比奥克等人为代表,将皮尔士的symbol解读为任意符号,这些后皮尔士时代符号学家都或多或少地简化了皮尔士原意,在symbol与规约符之间划等号,甚至认为语言就是皮尔士的symbol,或symbol就是语言。这两端看似矛盾,究其原因还是没有走出西方语言符号思想中长久以来的nomos与physics二元对立思维。皮尔士后期的论述证明规约符只是symbol的常见一种,以“习惯”为纽带界定符号与对象之间关联的走出了机械的二元观,使得作为三级符号的symbol即可包含语言等人类世界中的规约符号,也可指宇宙一切具有规律性,连续性与重复性的自然符号,将symbol与规约符甚至语言划等号,实则误读。
注释:
①遵照皮尔士作品引用的惯例,《皮尔士全集》(The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Peirce)、《皮尔斯基要文集》(TheEssentialPeirce)与《皮尔士著作集》(WritingsofCharlesS.Peirce)引用格式分别为CP,EP与W,首次引用加CP,EP,W,其后加卷数与段数,理查德·罗宾整理的皮尔士收稿引用格式为MS[R],其后为手稿编号与段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