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抽象艺术发生的心理分析
2022-09-05李晓峰
李晓峰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抽象的上海》,主要指涉的是上海与抽象艺术乃至与抽象的关联。
的确,谈到上海现当代艺术,肯定离不开抽象艺术,甚至往往还是核心。由此,谈中国现当代艺术,也肯定不能离开上海抽象艺术,而且,它们之间还常常构成了耐人寻味的互文关系。
抽象艺术在上海当然是突出的,某种意义上,上海就是中国抽象艺术的主场。
1981年,中国当时最高级别的美术期刊、也是今天被称为核心期刊的《美术》,刊登了吴大羽先生题为《滂沱》的作品,作品因显著的抽象面目开了一时的风气之先。那时的官媒能刊载这样的作品已属开禁,事实上,吴大羽先生绝大多数的抽象作品都是在其一生蜗居的上海斗室内完成的,却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艺术先河,并被公认为“中国抽象艺术之父”。
2021年,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大展“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展出了吴大羽先生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两件藏品《无题》之一、之二,与一代大师林风眠先生的《独立》、徐悲鸿先生的《鸡羊图》、关良先生的《献花舞》、刘海粟先生的《复兴公园》交相辉映,三四十公分的小画幅,却也暗含着上海抽象艺术进程的艰难与尴尬。
伴随划时代的“八五美术新潮”,上海现代艺术活动也如雨后春笋,著名的“80年代的美术”“83绘画实验展”“85现代绘画六人联展”“凹凸画展”等现代派画展,此起彼伏,蔚然风气,形成了一个上海现代艺术活动群体,其中抽象艺术很快占据了主流,并出现了一批名声鹊起的抽象艺术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余友涵、周长江、丁乙、王劼音、申凡、黄渊青、陈墙、曲丰国、秦一峰、倪志琪、胡伟达等人,以及早期的陈创洛,阶段性的陈箴、李山、孙良、宋海冬、赵葆康,留美的张健君、赵渭凉、查国钧,留日的范钟鸣、潘微,还有与抽象艺术关系紧密的水墨圈的仇德树、王天德,雕塑圈的杨冬白,装置圈的施勇等人。尤其是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海艺术家余友涵、李山、丁乙、孙良、宋海冬等人的参加,使上海当代艺术包括抽象艺术走向了国际舞台。

1999年“都市抽象”展的策展人李晓峰与参展艺术家合影
引发世人瞩目上海抽象艺术如何发生,本文试图以心理分析维度从五方面予以分析与反思。
第一,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兴起的一个重要形式,抽象艺术在上海的心理诉求,首先涉及的是身份认同。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后的上海艺术家,希望摆脱“具象”身份,“抽象”成为身份改变的重要形式和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那个时期摆脱“具象”身份呢?因为那个时期的极“左”现实主义与“具象”紧密相联,而且专横独大,排斥视为异己的非具象,特别是抽象。所以,摆脱具象的抽象,便成为打破“具象”专制的重要手段与方式。这样一来,对一元僵局的打破,既是一种出走逃离,也是一种叛逆抗争。这恰恰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风潮的始基。

《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 陈钧德 布面油画 1977年
比如,发生在1979年岁首的“上海十二人画展”,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抽象艺术,但有了非具象、变形、表现,与当时的革命现实主义主流完全相悖的一种倾向,比如“去主题”。
“去主题”隐含着什么样的心理?就是要离开“具象”,要离开那种主题化的、单一化的、一元化的身份界定。我觉得,这是理解抽象艺术在上海发生的心理基础与思想前提。
上海现代艺术的肇始期(也是“文革”后的中国现代艺术肇始期),有一个承上启下的标志性人物,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陈钧德先生。那时的陈钧德还是位年轻教师,还没有去过外国,居然画出很印象派的绘画。
在“上海十二人画展”上,陈钧德的一件作品引起轰动,就是《有过普希金铜像的街》。这个长句子标题有几层意思,一是“普希金”,一个浪漫主义的俄国诗人,居然在上海艺术家心中那么重要;二是“有过”,这个普希金铜像那时没了(后来又复建了);三是“街”,他画的是街,那条曾经有过雕塑的街,有过外国人头像的街,有过诗人塑像、浪漫主义塑像的街,那是城市的街道,洋气的林荫街道,那是城市的风景……这里可解读出许多潜台词。
有一点特别重要,这件在那时出现的风景画,不再是政治化主题创作,不再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风景,而是“去主题”、无政治的风景,而且,艺术家使用的不再是一统天下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法国印象主义的色彩笔触,进而,显露了相关抽象的最初迹象。
当然,当时的表现、变形,都是针对具象、写实的主题创作,意味着一种脱离、背叛。抽象化选择,是当时最重要的手段和形式,也是身份解放的必然选择,从具象的、专断的、单一的、固化的身份,走向轻松的、不确定的、开放的、抽象的风格,同步着城市的摩登(现代)、时尚,意味着一种貌似洋化、西化的(他山之石)改开倾向,一种改革开放的中国新艺术风貌。
同样是1979年,岁末的北京,发生了“星星美展”事件,之所以说是事件,是因为其叛逆性,这个常常被视为中国“八五美术新潮”的起始性展览,所有作品其实都是有主题的,虽然,也是变形,也是表现,甚至也是具备了某种抽象因素,初显背叛极“左”形象的的新形象,却是主题鲜明的。涉及的多是“人物”,而不是“风景”,人物多是挣扎的,扭曲的,变异的,以及愤怒、压抑、反抗等等。这为北京后来的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埋下伏笔。更反衬出上海 “去主题”“无主题”的艺术趣味,成为上海抽象艺术滋生的先声。
须补充的一点是,不管北京、上海,乃至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新潮,一个共同点就是打破极“左”的写实手段,使用的多是走出具象刻板的非写实手段,即抽象倾向;另一个共同点是凭借外力,借用西方现代艺术包括抽象艺术,成为抽象艺术肇始期的一个最突出选择。换句话说,很多我们今天不认为是抽象艺术的现代派创作那时都被视为抽象艺术,甚至那时还会把所有偏离正统主流的艺术叛逆都笼统划归成抽象艺术,或叫抽象派。
第二,抽象艺术在上海的生发与上海人的受伤情结有关。
经历了“文革”,也包括新中国以来的各场运动,还有殖民地以来百年坎坷,让接触了现代文明的上海人变得越来越小心谨慎、谨小慎微。
分析和判断这种心理成因,我觉得须怀着一种客观的、人道主义的审视态度。我对上海人的心理活动一直抱有好奇与理解的愿望。上海人不论高低贵贱,几乎人人有天然的优越感,有自我良好的感觉。比如在上海人眼里,外地都是乡下,上海对外地人的强烈意识与上海人的“崇洋媚外”心理是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出国潮”,其中上海人最多,比如美术圈大名鼎鼎的陈逸飞、陈丹青都是80年代就出国了。那时的上海人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就是傲气又小气,精明又狭隘,还有一点令人惊异,就是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上海每年都为国家贡献六分之一的财政,这份敏感,又多是经济角度,而不太关心政治,又与北京形成反差。
是不是太势利了呢?尤其历经浩劫后,上海人“势利”的背后,有种强烈的“安全”意识。严阵以待的谨小慎微,怕被别人占便宜却总爱沾点儿别人便宜,以致落下自私、贪小便宜的不良口碑。其实,与他们紧张的“自保”心态有关,这种几乎严阵以待的小心自保,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上海人严重的受伤情结,从聪明到精明,到计较、小气、功利、市井,都可理解为受伤后的自我保护与疗伤策略。
这种受伤尤其来自于政治伤害。一个偏远地区,比如说青海,受到政治迫害的人的反应和上海人受政治迫害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应该有很大差别。相比较而言,自我意识与自理能力超强的上海人,内心更丰富、更有情怀、更有教养,特别由于受过西风东渐带来的现代文明的浸淫。因此,上海人对政治的敏感与在意,实际上不比任何“外地人”差。上海人之所以没有政治热情,之所以从理想主义化的政治热情变为现实功利的经济热情,源于对生存的不安与焦虑,正像沃林格的那个著名命题:“抽象源自巨大的不安和焦虑。”选择抽象的上海人对这个“不安和焦虑”有着深刻的感受。
余友涵先生,被称为上海现代艺术教父级人物,最著名的创作就是抽象的《圆系列》。余友涵先生谈他抽象创作非常有意思,他说自己因为不够“精明”而当了兵,不如他同学“门坎精”,因为怕去当兵,装视力不行,看测视表偏往错里说,向左偏说向右,向上就说是向下,所以就逃避了。余友涵当兵入伍的是通讯营,学发报,“滴滴答答”这个节奏给了他至深的记忆,成了《圆系列》的来源,滴滴是点,答答是横,发报层面的“滴滴答答”内化为他心理深层的潜意识并用升华了的艺术宣泄出来,他还补充道,当兵使他总有种来自死亡威胁的恐惧。
王劼音先生,曾为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资深教授,出生于很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住在上海“高尚”地段淮海坊,一生谨小慎微地待人。每个接触到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安分的好人。作品却非常不安分,甚至反叛,创作也很跨界,油画、版画、水墨、意象、表现、抽象混搭。王劼音自称是个“反技术派”,在一篇回忆自述中坦言自己“不太安分,喜欢搞点新鲜东西……好像生有反骨,带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不满足于美院的正规教育,喜欢非学院的东西。”并说:“边缘离开中心远,天高皇帝远,正可以自己‘乱来'一通。”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王劼音的艺术基调却是优雅的,被认为是上海艺术典雅的标志。
所以,源于受伤情结和自我保护意识的上海人,更具备一种觉醒的自我意识、个人意识。比如很懂得自我,懂得我和别人的区分,比如不太串门、不太群体。虽然多数上海人还是有着很浓的小市民气,但是,上海人的自我,又是一种文明,是一种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生出的现代文明,这个重要的现代品质,让上海人在文化上、生活中追求品质、品位、格调、腔调。只是残酷现实与世俗尘埃,往往使良好的品质变形变味,比如胆小、狡猾、小气。小气往好处使用,那是节俭,是懂得环保,呵护我们的生态资源,进而发展出具有公共意识的市民精神,就看如何表达,有文化是节俭,没文化是小气;有文化叫自我,没文化叫自私。
还有一点就是自恋,过度自我到敏感的防御,也会成为一种狭隘,行为上是自闭,心理上是自恋,往往走向偏执,对艺术有时却是好事,如孙良时而细密、时而舒朗的画面神话几乎就是一场自我救赎的献祭;丁乙精微抽象的“十示”系列用数十年坚守;还有秦一峰银盐摄影精益求精的灰调,申凡艺术制作一丝不苟的讲究。
第三,上海抽象艺术的理性、克制,密切关联着现代性路径。
我们知道,上海的抽象艺术,在风格划分上以冷抽象为主,理性抽象、几何抽象为主。为什么这么多的理性、冷静?当然与上海人文明、文化的内在品质相关联。
深怀受伤情结、小心谨慎的上海人,表现出异常细腻、敏感的心理特征。上海人的理性与克制,让伤害带来的“不安与焦虑”变成克制内敛的隐隐内痛,而不是呲牙咧嘴、张牙舞爪的外伤。
同时,克制内敛到外表冷漠的上海人,还成就了一种“旁观者”立场,这种旁观者立场带来的心态与身份定位,很值得解读,不愿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
比如王劼音的低调为人、不扎堆、不出头,悄悄地在个人工作室“乱搞”,又最终走向雅致的艺术品质,这条路径是耐人寻味的。我们常讲,上海艺术没有群体,唯独上海抽象艺术貌似存在一个群体,其实就是因为人多势大,是不约而同,并非有意约定的群体。90年代,上海《青年报》曾约我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分而不群”的上海艺术》。
记得1998年底,上海香格纳画廊的一个展览开幕聚了一大群上海艺术家,一看,绝大多数是搞抽象的。就是那一刻,我提出做个抽象艺术群展吧,得到大家积极响应,这就是1999年“都市抽象展”的来由。那时,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一批青年教师办了一个“上美沙龙”,百十平方米的白盒子展厅,调性挺高,“都市抽象”就在那里开张了!这是上海首次明确打出抽象艺术旗号的展览,有策展人、有画册、有海报、有研讨会,几乎也囊括了在上海搞抽象的全部艺术家,余友涵、周长江、丁乙、申凡、孙良、赵葆康、黄渊青、陈墙、胡伟达,包括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乐大豆,游走中德两地的刘广云等,开幕那天,活跃在上海艺术圈的艺术家几乎全到了,老炮和现在都成了老炮的年轻艺术家济济一堂。展览开幕的合影,中间唯一坐着的是我,严重表示出了艺术家们对策展人的尊重,也是上海艺术家聪明、理性、低调、旁观的一个侧面吧。我也是由此获得“尊重”走向了服务艺术家的策展人道路。
“旁观”,不同于围观,不是非理性的喧哗,而是冷静、理性,最终,“旁观”变成一种品质,一种聪慧与耐心,一种气质与格调,就如音乐,一定是有调性的。事实上很多抽象艺术家尤其上海的抽象艺术家都喜欢音乐,发烧级的爱好者,一直延伸到对音响器材的发烧。这调性,和倾听有关,不聚众,不狂躁,不表演,不沦陷。这种音乐化格调,让我想到中世纪的“七艺”,包括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数、几何、天文学、音乐,音乐列入其中的缘由就是对理性、秩序、克制、冷静的强调。显然,这种倾向不会冒犯、不会犯错,不会惹事生非的,禁欲的中世纪和90年代上海抽象艺术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内在关联。比如秦一峰的《线场》,又要自由,又怕“豁边”(上海话,跑偏的意思),如秦一峰所言,是“自动与控制间的一种平衡”。后来的秦一峰所沉湎的摄影方式,选用的就是最经典的拍照技术,不厌其烦到近乎乏味的拍摄一种精妙的灰度。
以精明闻名于世的上海人,精于计算,计算理性极为发达。我曾为此归纳为“四精”:精致、精巧、精准、精(经)典。精明虽常常成为说上海人的贬义词,所谓“精明不高明”,不够胸怀天下、高瞻远嘱,有工具化嫌疑,然而,上海人的埋头苦干,却发展出在中国十分需要的职业化、专业化精神。
所以,上海的抽象,既有疑似精神洁癖的自恋,也有疑似高冷的纯粹,是理性与狡猾灵活的同体共生。进而,生成的文化态度与艺术立场,不是激烈的批判,更是冷静的构建与完善,丁乙的《十示》、申凡的《标点》、秦一峰的《银盐》照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第四,上海抽象艺术的心理活动与上海都市空间密切关联。
上海抽象还具备着强烈的空间意识,空间哲学,以“互补系列”闻名的周长江就是最好的例证。周老师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上海抽象艺术的前辈,建筑工人的经历,成为他对空间、建筑、城市理解的最接地气的铺垫。长江家的墙角都是半圆形,不易破损,也不会伤人,讲究至如此,是上海艺术家的普遍现象。从申凡、秦一峰一丝不苟的精准,到施勇《让所有的可能都在内部以美好的形式解决》,空间设计的井然有序、精细入微,使用的物尽其用、一尘不染,践行了上海一句著名的话:“螺蛳壳里做道场”。
从物理空间到心理空间的转换,抽象艺术表达差不多是最得心应手的,从这个意义上将,上海抽象艺术所以发生、发展、经久不衰,和上海的城市空间关系显然密不可分,都知道丁乙对Art deco的欢喜,秦一峰对明式家具的沉迷,包括器物选取、陈设、认知、理解,上海艺术家对空间的经营、打造,常常巧夺天工,文化品质别具一格。所以,上海擅长设计,包括平面设计、视觉设计、商业设计、工业设计、产品设计、建筑设计,天生具有的设计感,构成感,来自这座城市培育出来的空间感、秩序感。进入到21世纪之后,空间恰恰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最重要元素,当代艺术表达越来越离不开空间的表达。
就像2016年在上海民生美术馆举办的“抽象以来—中国抽象艺术研究展”,展览总策展人王端廷先生开幕时特别指出,“抽象以来”研究展第二站,在上海民生美术馆呈现的效果更好了,因为抽象艺术作品和工业空间遗产是如此吻合。的确,空间化的工业遗产,是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甚至摩登时代的文明写照,与抽象艺术互文,王劼音的一个创作系列就叫“工业风景”,丁乙也说过,他的《十示》系列源于工业印刷技术的校准符号,当然也与工业文明强调的“精准”相关。
1999年“都市抽象”的研讨会主题就是“都市与艺术的现代性”,那时还很苦逼的一代艺术家,在之后的创作中,大都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都市的光亮。丁乙自己也承认,他后来作品的斑驳色彩,包括荧光笔的使用,与都市有互文关系。来自贵州的陈墙,奇诡图腾与上海城市表情的重合,还有上戏的曲丰国抽象中的光影、速度,还有施勇后来变得更为抽象的板材装置,从色泽到形态,与都市文明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就包括了与当代消费、娱乐、当代文明、当代理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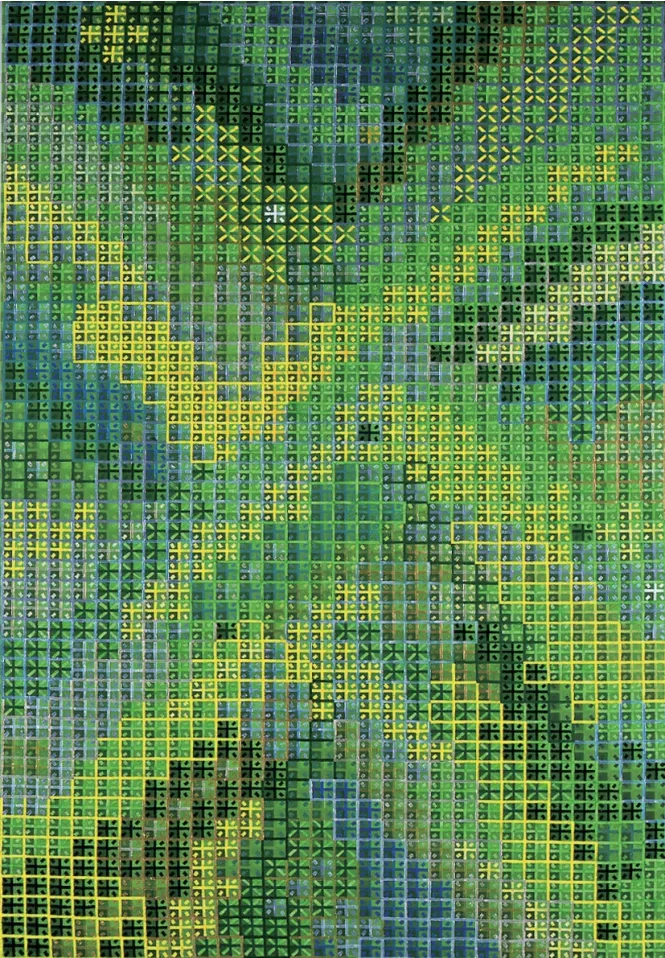
丁乙的《十示》系列
都市文明,往往更多体现为一种商业文明,当代人的智慧、思想、品质,有时在商业层面的表现度、实现度,甚于艺术。我们常常为了表达自己的高尚、清白,就不由自主、非此即彼的把艺术和商业对立起来,实为传统的局限。上海抽象艺术越来越显著的都市气息、摩登品质会令人想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纯视觉”。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艺术批评史家文杜里在其名著《西方艺术批评史》末尾提出了“纯视觉”的概念,就是对之前的“形式”“理性”“唯心”“古典”的时代更替,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兴起的视觉文化,恰恰是与都市文明、商业文化发生的深刻关联,比如刘建华的陶瓷装置,使用很中国、极工艺的陶瓷媒介,勾画出的却是很前卫、极观念的当代美学,近年的作品,从早期《日常·易碎》系列走向更为纯视觉的抽象观念。
第五,不避保守嫌疑的历史趣味与经典品质的文化诉求。
入选上述“研究展”的四位上海抽象艺术家,恰巧“四五六七”:40年代的余友涵,50年代的周长江,60年代的丁乙,李磊虽然也是60年代但年龄最小,又由于他抽象艺术创作时间相对晚些,可算成“70后”。这个虽不太严谨的描述,貌似巧合,却具有某种必然的暗示。四代抽象艺术家,隐喻了上海抽象艺术发展的四个代际,从情绪叛逆、心理疗伤、私人意识,乃至市民心态,走向思想意识、观念立场、身份重建的层面,进而形成精神态度、文化趣味、历史情怀,这个变化,既体现了抽象艺术不同代际上变化,也体现了艺术家不同的抽象阶段。
其中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回望、使用及认同,是上述变化中值得关注的一种倾向。走了三四十年,经典回望、文化认同,似乎成了一个显著情结,最早显现的是周长江的《互补》系列、余友涵的《圆》系列,都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了不约而同的关系。
余友涵曾说他的《圆》系列,是与陈箴的论辩中形成的,陈箴说他黑白两道无始无终,寓意无限永恒,说余友涵圆不行,是封闭的;余友涵说不对啊,圆是周而复始也是无始无终啊,然后讨论《道德经》,讨论完之后,余友涵说,我这是真正的永恒,近乎实用主义的百无禁忌,不等同于回归意识,更不是民粹主义的本土化倾向,谈到与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是古为今用的态度,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想到胡适先生的选择,其实胡适留学美国回来,带来的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也是今天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易于忽视的部分。这样的例子很多,尤其是留洋归国的海归派,在上海,中外东西两边游走的人很多。
上海抽象艺术,其趣味与品位,既离不开西洋文化的影响,也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基因。所以,必然会出现对本土文明的回望与追溯。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的抽象艺术,对于经典文化的钟爱,对于古典文明的钟情,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普遍。明明是搞现代艺术的,是叛逆、离经叛道的,却始终怀有古典与经典的情怀。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国艺术的书写性,余友涵说自己的《圆》系列笔触是因为当时在习练石鼓文,比如何赛邦对手感异乎寻常的强调,对书法有精深研习的黄渊青十分重视手的解放和自由,抽象视觉语言借助了传统文化资源,成为抽象艺术实践、探索、建构的重要补偿。
执着于抽象艺术的创作的这些艺术家们,到了今天已经从叛逆的心结走向了经典化的研究心结。甚至更自觉于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回望,余友涵、周长江、黄渊青、何赛邦的早期创作就十分明显了,王劼音、申凡、刘建华、陈墙等人近年有了更明显的倾向。
故此,可以认为,抽象艺术在上海的发生与发展,包括了三方面的转变:从手段化的叛逆阶段,走向主体化的研究阶段;从初级的形式模仿阶段,走向高级的精神原创阶段;从视觉化的语言实验,走向观念化的文化探究。
如今,我们不再把抽象艺术看成叛逆的艺术,看成离经叛道的武器,而是作为一种研究的形式、方法和手段。正如我们举办展览,命名为“研究展”,已罕见的达到了研究级,做展览是不会加研究二字的,可见抽象艺术在我们的诉求层面已经很高、很深了。
比如,从抽象语言表层形式的学习模仿,走向抽象语言内在逻辑的梳理建构,对抽象艺术的修辞语法的文化梳理。有学者认为,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语言的革命,对古代语言的改造,严格意义上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中国现代语言体系,就是说,现代中国话语还常常漏洞百出,所以我们经常遭遇语言腐败、语言暴力问题,因语言漏洞遭遇语言陷阱、语言忽悠。抽象艺术对中国现代语言体系建立应有所贡献。
再比如,从对抽象艺术的有形定义,走向对抽象艺术的无形命名,就是说,我们今天的抽象艺术,已从视觉形式的技术面解决,走向“大象无形”的哲学层次探究,我们引入古老的中国哲学思想的借用,不再是简单的符号化,也不是思想观念的倒退,而是精神资源的弥补与借鉴。中国的抽象艺术,从“去主题”开始,到本体化诠释,经历了从西方抽象、东方抽象、东西兼容抽象,到走向原创的、独一无二的抽象,更加个人化抽象艺术,在当代抽象艺术创作及研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抽象艺术是否东方化还是西方化,其实都不重要,仅仅是个过程而已。
抽象艺术的重要,当然首先已成为艺术史的阶段,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阶段,可能还是很多艺术家都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一个阶段。曾经,抽象艺术以其显著的形式语言的精彩纷呈,为现当代艺术构筑了不可撼动的经典类型。如今,这个经典类型,经历了我们从学习、模仿,到探索、创造;从现象、经验,到心理、知识结构的积累、沉淀、提升,已然成为我们今天仍能够继续面对的当代课题。
当我们把抽象艺术上升为现代主义的逻辑起点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抽象艺术成为现代艺术端始的重要标志的时候,正如今天中国学界越来越意识到的,在中国,一切后现代的、当代性的问题,其实还都没有走出现代性,其实还存留和滞留在现代性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仍然从事抽象艺术创作和探索的中国抽象艺术家们,在抽象艺术研究层面上的创作工作,表示诚挚的敬意和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