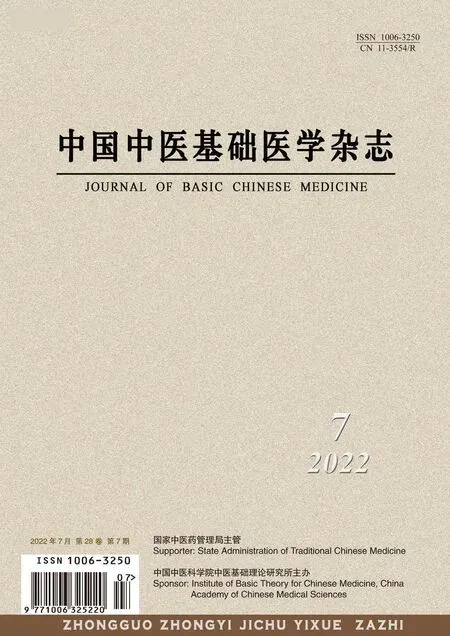历史地理学视域下的吴门医派学术探究❋
2022-08-17卞雅莉范崇峰
卞雅莉, 范崇峰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 南京 210023)
中医学术流派是在长期的学术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江苏中医发展历史悠久,医学流派纷呈,形成了以孟河医派、吴门医派、山阳医派、金陵医派、龙砂医派为代表的地域性学术流派,吴门医派是其中颇具地方特色的医学流派。吴门医派之称最早见于明·杨循吉《苏谈》,又称吴中医派、吴中医学,素有“吴中医学甲天下”之说。吴门医派历来以“儒医多、御医多、医学世家多、著作多、温病学说发源地”等特点而著称于中医流派之林[1]。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在历史发展中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中医学术流派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尤其是地域性中医学术流派。因此,将历史地理学方法引入中医学发展的研究中,有利于梳理地域医学流派的发展脉络,揭示地域医学流派的时空特征,澄清地域医学流派发生、传承与发展的相关因素,评价其时空属性及历史价值[2]。本文从历史地理学角度,通过历史传承性指标和地理区域性指标以考察吴门医派的学术特点和传承特色。
1 历史传承性指标
1.1 历史渊源
吴门是江苏省苏州地区的古称,又有吴中、吴郡、吴下、吴会、吴城、东吴等别称。公元前11世纪,周太王之子泰伯、仲壅来到“荆蛮之地”长江下游江南一带,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建都于此,始有“吴中”之称。秦始皇划苏州为会稽郡设吴县,到“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据《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引葛洪《神仙传》记载,最早的吴医是周代的沈羲,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沈羲者,吴郡人,学道于蜀中,能消灾治病,救济百姓。[3]”元末戴思恭师从金元四大家之朱丹溪,后至吴中行医,成为吴门医派的引导者,其弟子王仲光被称为“仲光之医名吴下,吴下之医由是盛矣”[3]。吴门医派鼎盛于明清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名医,“有闻名邦国者,有饮誉乡里者,有创造发明著书立说而成为一代宗师者,有精于脉理、善诊妙治而留范千百医案者,有广注阐解经典者,有专论克治时病者,有精通诸科者,有独善一技者。总观诸贤,不唯医道高超且皆医德隆厚”[4]。至此,吴门医派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令世人瞩目的地域性医学流派。
1.2 文化内涵
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一带,宋室南迁后,随着宋元经济文化中重心向东南转移,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日益繁盛,促进了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大批太医署的医官和京城的医学人才随之南迁,北宋范仲淹创建苏州府学,各地争相效仿,故有“天下有学自吴郡始”“苏州郡甲天下,而其儒学之规制亦甲天下”之说。明清时期,吴文化也鼎盛一时,丰富的吴文化底蕴给吴中医学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也为吴门医派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吴中地区儒学盛行,因此吴门医家中涌现了不少知名的儒医,如薛雪、张璐、徐大椿、缪希雍等,他们不仅医术精湛还善于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著作。
1.3 学术传承
家传和师承是吴门医派传承的主要方式。吴门家传世医颇多,有“以儒为医,而德被人者”的葛氏世医,自葛思恭起传葛应雷、葛乾孙等,被誉为“宋元吴中世医第一家”;韩氏世医始于元·韩凝,有“中吴卢扁”之号,其子韩奕与王履、王滨并称为“吴中三高士”,韩氏一族4代10多人业医,其中3人为太医;“以祖传医术与秘方要旨”著称的昆山郑氏妇科,郑氏始祖得其妻之外祖薛蒋仕所传医术,专精女科,流传至今二十九世,被称为世医之最;此外,还有金氏儿科、闵氏伤科、裴氏儿科、尢氏针灸等,这些家传世医具有鲜明的学术观点和特有的专科诊疗方式,充分体现了吴门医派的传承有序、各有建树的特点。
2 地理区域性指标
2.1 地理区域
“吴”原本是春秋时代诸侯国名,后来用以泛指长江下游的区域,因此“吴门”乃是苏州城及其腹地的古称。据《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吴门指出:“苏州的别称。或专指今江苏苏州市,或泛指平江府、平江路、苏州府”[5]。苏州地处长江冲击平原和太湖水网平原地区,运河贯通南北,地理位置优越,宋代以来苏州成为全国货物集散、转运和资讯中心,明清时期苏州地区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在江南地区大体上形成了以苏州为核心的各府、州、县体系。经济富庶,人口密集,促使苏州地区医学发展十分发达,人才荟萃、名医辈出、学术成就独树一帜,为吴门医派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2.2 地理环境
吴中地区位于太湖水系东部,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区,气候温和湿润,一年四季气候分明。吴中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属东南卑湿之地,河道纵横,水网密布,这种温热多湿的地理环境是瘟疫多发的自然条件,因此吴中成为瘟疫的多发地区。据史料记载,仅在清乾隆时期的60年间,太湖流域就暴发过40多次大小不等的瘟疫,大的遍及苏淞太杭嘉湖地区,死亡率极高,以致哀鸿遍野,民生凋敝。因此,吴门医家也有了更多治疗瘟疫的实践机会,瘟疫研究成为吴门医家关注的重点,从而成为温病学说创立于此的必然因素。
2.3 道地药材
吴门医派的兴盛也与吴中地区丰富的中药资源有关。吴中地区自然条件良好,气候宜人,雨量充沛,蕴藏着丰富的道地药材,主要分布在苏州的穹窿山、东山、灵岩山及常熟的虞山等,如苏薄荷、苏芡实、苏枳壳、蜈蚣、吴茱萸、玫瑰、灯芯草、荷叶等。如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薄荷,人多栽莳……吴、越、川、湖人多以代茶。苏州所莳者,茎小而气芳,江西者稍粗,川蜀者更粗,入药以苏产为胜”[6];吴茱萸在宋代《本草图经》中记载:“今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7];南北朝时《名医别录》中记载:“蜈蚣,生江南大吴,赤头足者良”[8];明·李梴《医学入门》中记载:“(蜈蚣)大吴川谷中最广,江南亦有之”[9];明·姚可成《食物本草》中记载:“(玫瑰花)处处有之,江南尤多”[10]。吴门医家对这些药材的使用颇有心得,处方用药注重实效,具有“轻、清、灵、巧”的特色。此外,吴门医家还善于利用本地资源和外来药材,加工制成各种成药制剂,如回生丹、人参胎产金丹、百花膏、肺露等,流传至今的有雷允上制售的六神丸、玉枢丹、辟瘟丹等。
3 吴门医派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传承特色
3.1 首论温病,开创先河

3.2 名医云集,医著荟萃
据统计,自周代至新中国成立前,有史料记载的吴门医家约1388人。吴门名医中被征召或举荐为御医者众多,仅明代就有御医70多位,如明代的卢志、钱瑛、薛铠等,清代的徐大椿、曹沧洲、潘霨等。从宋代起由于大儒通医的学风日盛,吴门医家中由儒转而习医者亦多,如葛乾孙、薛雪、缪希雍、尤怡、缪遵义等,推动了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渗透。吴门历代医家善于著述,据《吴医古籍存见录》统计,历代吴医古籍现存者有图书513部,专论110篇,涉及中医各学科,如宋·薛蒋仕的《女科万金方》,为现存最早的吴医古籍。元·葛乾孙的《十药神书》是我国第一本专治虚劳的专书;王珪的《泰定养生论》以道家养生观点阐述人生各阶段的生理调摄、疾病治疗以及五运六气、病因诊断等内容。明·王履的《医经溯洄集》阐发“亢害承制”理论,首创“真中”“类中”说;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用注疏的形式,对《神农本草经》药物加以发挥,考证药效,开本草注疏药理之先。清·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是一部论述方剂配伍意义的专著,选方300余首,为之“显微阐幽,申明其方之中矩,法之中矩”;张璐的《张氏医通》是一部集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的综合性医著,以病集方,被誉为“诚医学正宗也”;尤怡的《伤寒贯珠集》《金匮心典》深入探究张仲景学说,勘误删略,阐述张仲景原文精义,颇受后世推崇;王洪绪的《外科证治全生集》对疡科的论证与治疗有独到见解,书中所载犀黄丸、醒消丸、小金丹等经验方迄今仍为临床所用。吴金寿刊刻的《三家医案合刻》是医案著作中较有特色的一部,收载叶天士医案106则,薛雪医案74则,缪遵义医案141则,选录医案多撷其精华,便于后世研学,流传甚广;唐大烈编纂刊印的《吴医汇讲》汇编吴门医家的医学论文,被称为“国内最早具有刊物性质的医学文献集”[12],该刊“发前人所未发”,保存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医学文献,如叶天士的《温证论治》、薛雪的《日讲杂记》等,对当时的医学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3.3 学派纷呈,各具特色
吴门医派兴盛于明清时期,医家众多,在学术上包容广博,继承创新,既有尊古崇经的医经学派、经典伤寒学派,如陆懋修以训诂研究为主撰《内经难字音义》,并撰《内经运气病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疏解和注释;顾靖远撰《灵素摘要》对《内经》条文进行分类注释和摘要;徐大椿撰《内经要略》,摘引原文逐条注释。又有兼收并蓄的通俗伤寒学派、错简重订伤寒学派、易水学派、河间学派,如张璐父子等持通俗伤寒之论,提出一切外感热病均为广义伤寒之说,将温病学说融合于伤寒的论治之中;喻昌、周扬俊等持错简重订的观点,将《伤寒论》条文重行分类归纳,阐发三纲鼎立之说;葛应雷、薛己、缪希雍、蒋仲芳等继承张元素的易水学派,临床辨证以脾肾虚损为重点,多用温补之药并倡立脾阴学说,补充脾胃学说之不足;赵以德、王履、盛寅等以火热病机阐发药论,拓展“亢害承制” 理论,提出“百病不离火”之说。还有创立新说的温病学派、中西汇通学派,以陆渊雷、顾福如等为代表的吴门医家在学术思想上以“中西医汇通”而著称,“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论”,认为中西医应相互济用,这些学术思想流传甚广,推动了吴门医派的迅速发展。
3.4 重视传承,远播海外
吴门医派创立至今400多年间,一直传承不衰,与吴门医家重视医学教育密不可分。明·薛己“幼承家学,长而好学不倦”,从医50余年,又曾主持官学太医院的学校教育,因此其门人私淑者很多,有江南名医周慎斋等,他素以著述为志,注重实践,勤于临证,要求门人多读医案,通过师生讲论分析透辟,以利后学。清·叶天士在吴门医派的传承方面也有所建树,培养了众多学验俱富的弟子,如顾景文、华岫云、周仲升等,私淑叶天士者有吴鞠通、章楠、王孟英等。叶天士毕生忙于诊病,无亲笔著述,其医案均是其口传心授的临证经验,多由门人和后代整理,使其卓越的医学思想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得以传承。徐大椿认为医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传承“生人之术”,他在《医学源流论》提出:“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非虚怀灵变之人不可学也”“非勤读善记之人不可学也”“非精凿确识之人不可学也”[13],在医学传承中重视德、学、识兼备,重视经典,溯本求源。吴门医派的学术不仅在国内传承,早在元代吴门医派的盛名就已远播海外。《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吴门地区“医士甚众”“善能辨病源,投方药”。清·曹存心门人众多,琉球政府慕其医名,遣医人吕凤仪至吴门拜其为师,学成归国后仍以信函向曹存心请教。《琉球百问》即其回复其琉球弟子所提问题记录整理而成,该书是曹存心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吴门医派学术传播海外的历史性文献著作,曹存心也被誉为“德被吴中,名驰海外”第一人。
4 结语
地域性中医流派是依据地理范围而划定的医学群体,吴门医派作为地域性中医流派的代表,纵观其发展过程,苏州地区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包容性对其具有深远的影响。整理其学术脉络、学术思想的交融与创新是吴门医派在明清时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究吴门医派的学术特点和传承特色,有助于深入挖掘吴门医派的内涵和思想,为中医流派研究提供方法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