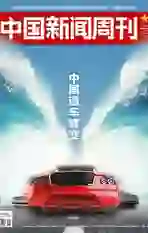ESG海外市场动荡,国内市场如何自处?
2022-08-16李权云
李权云
从2012年到2020年底,全球ESG投资规模从不到60万亿美元扩容到90万亿美元。国内投资市场也将ESG奉为“圭臬”,资管机构、基金公司言必谈ESG,ESG俨然成为被市场热捧的“新势力”。
然而,在ESG的繁荣表象背后,业界也陆续出现质疑的声音:先是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炮轰“ESG是魔鬼”,海外市场监管机构也撕开了企业“漂绿”的冰山一角。
今年5月,德国执法机构突袭德意志银行及其子公司德意志资管(DWS)办公室,针对其ESG基金“漂绿”的指控进行搜查,DWS首席执行宣布辞职。仅仅一个月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高盛旗下资管公司的ESG基金是否存在误导性描述展开调查。此前,纽约梅隆银行已经历过类似调查,并因多项基金未进行ESG质量审查、信息披露不足被罚150万美元。
在市场端,欧洲的ESG股票基金在刚过去的6月份平均亏损14%,美股市场ESG的ETF也遭遇2亿美元净流出。
业界质疑,资金出逃,业绩回撤,近几年在海外市场一路高歌猛进的ESG到底怎么了?国内市场又如何自处?
今年4月,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人类仍有一半机会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但要求确保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3年内,即2025年达到峰值,到2030年前该排放量要比2010年减少43%。
如果按照该报告来推算,临界点正在逼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该报告发表讲话,呼吁相关国家政府改变能源政策,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其中,E(环境)、S(社会)、G(公司治理)作为国际社会衡量经济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三个维度,成为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重要的非财务因素评价框架。
然而,以减碳之名,行“漂绿”之实,是当下ESG投资面临的问题之一。“漂绿”指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以绿色环保之名进行虚假宣传。日前,环保组织起诉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违反欧洲消费者法,用广告和碳抵消计划误导消费者,“对其航班的可持续性和应对气候危害的计划造成错误印象”。
在投资领域,“漂绿”更多地表现为某些资管机构发行标榜“绿色投资概念”的基金,利用相对主观的主题概念,以“伪ESG”吸引注重可持续理念的投资者。美国SEC加大对资管机构的ESG资产质量审查也进一步表明,遏制ESG“漂绿”是推动ESG发展的关键。
今年5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两项规则变更,就是为了提高针对ESG基金的披露要求,防止基金用ESG进行误导性或欺骗性声明。
视线转向国内市场。在“双碳”目标的引导下,绿色低碳转型正成为地方政府和各行各业的“必修课”。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助推器”,气候投融资被视为重要因素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副司长赵鹏高此前表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新增投资130多萬亿元。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我国绿色、可持续、ESG等方向的公募私募基金总数不足1000支,合计规模不达8000亿元,远低于潜在的碳达峰碳中和投资需求,需要引入更多的资本力量。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在媒体采访中坦言,由于当前绝大多数国家尚未就ESG投资中的“漂绿”行为处罚予以明确,ESG投资“漂绿”不受处罚或违规成本极低。少数基金经理人在隐性的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出现了实际投资行为与策略不符的行为。
比如,给产品贴上绿色标签,重仓股票与基金主题不符,基金管理人风格偏移,或对投资者夸大产品的环境效益、可持续发展及抗风险能力。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梁希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前一些领域的投资打着ESG的旗号去募资,相对能提高募资规模,但是投资的领域却不一定因为ESG发生改变。
“企业是否真正投入减碳或气候适应,关键看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目前碳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短期价格信号较弱,不足以让企业真正投入,所以中国企业现在口号喊得多,主要还是研究、宣传和示范,要真正大规模减碳还比较困难。”梁希说。
学术期刊《管理科学》曾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对比了签署联合国可持续责任投资倡议的几家美国投资市场的基金在签署协议前后六个月的变化。研究显示,签署倡议能够吸引额外4%的资金流入,但基金的ESG分数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此外,签署倡议后的6个季度与前6个季度相比,基金在ESG方面的表现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
也就是说,签署可持续责任倡议能够提升筹资能力,但在提升ESG水平和表现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一些责任投资还停留在统计层面,还没有真正发挥推动环境改善的作用。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丁辉认为,国内开展责任投资工作时,特别是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也应该谨防“漂绿”问题的发生,从标准制度入手为责任投资这项工作划好可操作、可量化、可检查的边界。
目前,国内市场ESG评价体系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企业自主披露的信息,二是企业被动披露的负面信息。
“考虑到我国企业ESG信息披露程度较弱,评级机构有时不得不以爬数据的方式对底层数据库予以补充,这也间接影响了相关数据的完整性和时效性,从而使投资者或投资机构并不能准确掌握企业的气候或ESG真实表现。”丁辉说。
2021年,A股约有26%的上市公司发布了ESG报告,从2009年的371份增加到现在的1125份,增速保持稳定。
王遥认为,SEC加强审查也会对赴美上市的国内公司产生威慑作用,敦促赴美上市的国内公司加强自身监管,做好ESG信息披露,真正践行ESG和可持续发展。
除了信息披露不足,ESG基金也在责任价值和投资回报率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而后者,是很多投资者所看重的。毕竟,业绩是硬道理,很少有投资者能“但行好事,莫问‘钱’程”。
俄乌冲突以来,随着供给收缩,油气价格暴涨,相关投资品的回报也水涨船高。而将传统能源公司排除在外并压仓新能源和科技股的ESG产品只能接受眼下的低迷行情。
这样的持仓结构也恰好是ESG产品前几年表现良好的关键因素。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之前ESG策略带来的回报几乎都要归功于相关基金对科技股的投资,并且避开了前几年表现不佳的化石燃料股。
梁希表示,ESG不需要一开始把资产总量做大,而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把ESG投资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环境影响最大化,“这方面我不担心ESG的资金流失,更多的是要看能否促进全社会的减碳工作做得更好。”
针对大部分ESG产品所看重的环境责任价值,梁希指出,海外市场的绿色金融发展是自下而上的,由一些行业协会发起并制定行业标准,主要是为了树立金融机构的绿色品牌形象,比如认证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这些只是统计性贴标工作,不是真正在促进大幅度减排。”
然而,投资者认为买了绿债、绿色基金就促成了大量碳减排,“其实投资者回报和绿债与非绿债并没有太大区别,投资行为对促成绿色项目有帮助,但不会特别显著。”
事实上,投资者的购买行为并不会带来直接减排。对于原本在商业上不可行的绿色项目,金融工具通过精准识别,引导政府和政策性银行给予优惠政策,使其在商业、技术上变得可行,这种能够产生增量或额外气候效益的金融支持更有意义。
“如果ESG想要兼顾回报和环境责任的话,只有从长期的视角出发才能看到足够的回报。”梁希坦言,长期并不一定是五到十年,一两年之内只要市场能够看到这个长期的假设成立,自然能夠形成较好的回报。
业内人士指出,当下政府、企业以及基金会的公益和公共资金大量投入碳中和领域,需要避免这些资金被投到商业回报已经很高的绿色项目,浪费公共资源。气候资金缺口需要弥补,也需要提升气候资金的使用效率。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双碳”目标是一项经济社会的系统工程,也是我国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的必然选择,气候投融资问题是其中的关键。因此,兼具评价体系和价值投资的ESG依然是为气候投融资和责任投资提供资源的关键性制度建设。
“从政府的角度看,我们要探索如何以目标引领的原则为责任投资设立标杆,立足中国国情,在实现国际国内标准同向并轨的基础上,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科学规范的指标体系,真正实现责任投资发展与我国宏观政策目标之间形成系统性响应。”丁辉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