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学记》与《东藏记》看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2022-07-23王雪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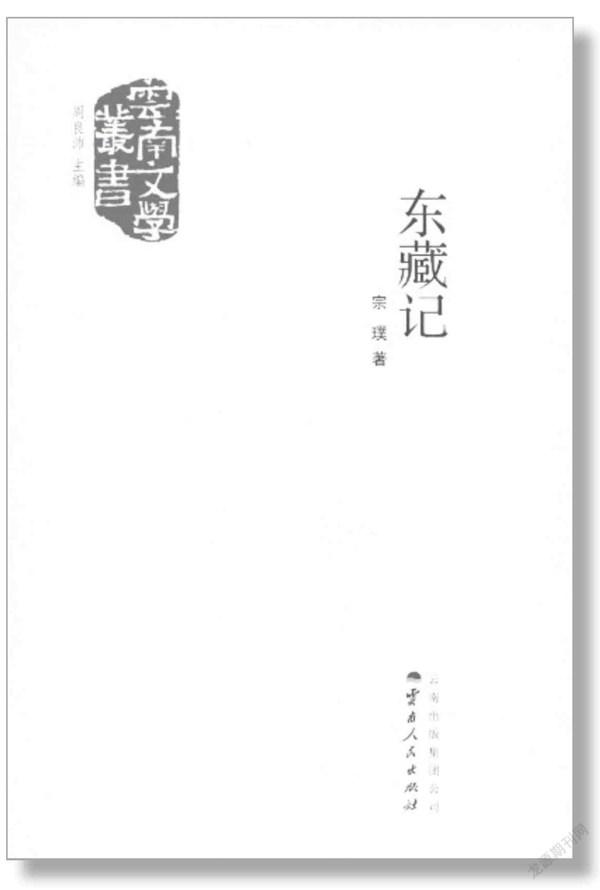
摘要:在借助历史创作文艺作品方面,学界一般有四种概念,即:实在的历史、记录的历史、陈述的历史、戏说的历史,这其中包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两大概念。从接受美学领域看,这两大概念经常成为文艺作品必须处理好的矛盾辩证关系。在 “记录西南联大往事”的文学作品语境下,何兆武先生的口述传记《上学记》和宗璞先生的虚构小说《野葫芦引·东藏记》为我们从其他维度解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提供了新视野、新途径。
关键词:西南联大;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上学记;东藏记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无论对于文艺创作还是文艺理论建设,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1]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普遍界定来源于文艺作品的选材和内容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件,这是一种借助外力的、外围的影响。笔者在查阅文献时发现,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本身,在创作过程中具有主观性,因而也存在一种内在的、以自我意志为出发点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即所谓的“实”与“虚”。这种内在的关系逻辑可通过《上学记》与《东藏记》进行比较研究。
一、选材之虚实
所谓选材之虚实,主要是指实际历史与创作主体受限于自身因素所选择的历史,也就是“陈述的历史”“个体的历史”。每个人的社会实践不同,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和呈现自然也大不相同。
通读《上学记》,最直观的感受是全书“宏大叙事”的艺术风格。相比《野葫芦引·东藏记》的含蓄,《上学记》实有壮阔之意。何兆武先生在开篇便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先生做了题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的开篇语:“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2]11从西南联大叙事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入手,为全书奠定了一个基本的严肃基调。在西南联大记忆中最主要的部分——知识分子/士人风骨的引领下,何兆武先生从“自由散漫的作风”“三个学校联得很好”“忆同窗”“忆恩师”等“普适”角度记录西南联大,其内容不外乎是先生如何讲课、学校是何种氛围、同学中哪些人当年努力,后来成了知名校友等。这些内容之所以“普适”,是因为大多关于西南联大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记录的。但同样的故事发生在《野葫芦引·东藏记》中,便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任的母亲和未来的母亲目光相遇,都十分感动”。[3]336
“女同学看到孟弗之的态度:有人恭敬地打招呼、有人赶快躲开、有人置之不理”。[3]16
“弗之一行人走回城内。经过小东门,见火已熄了。人们在倒塌的房屋前清理,有几个人呆呆地坐着,望着这破碎的一切。一棵树歪斜着,树上挂着什么东西,走近时才知是一条人腿。大人忙用手遮住孩子的眼睛,往路的另一边走,似乎是远几寸也好。嵋看见了,她像被什么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有些发晕。她尽量镇定地随着大人走,不添麻烦。心里在翻腾:可怜的人!一定是住这里的,没有跑警报去,如今变成鬼了。鬼是什么样子?鬼去打日本人才好,日本人太凶狠了。跑警报的也死了,不知死了多少人,有几个新鬼?可千万别到我家来啊。谁都没想到,他们已经没有家了”。[3]39-41
“随着警报声响,明仑大学的师生都向郊外走去。他们都可谓训练有素了,不少人提着马扎,到城外好继续上课。一个小山头两边的城上,很快成为两个课堂,一边是历史系孟樾讲投朱典,一边是数学系染明时讲授数论”。[3]73
“昆明不是日寇空袭的主要目标,但也承受着钢铁的倾污。积满了惊恐和劳累的日日夜夜,丝毫没有影响这里知识的传授和人格的培育。夜晚皎洁的月光和温柔的星光,与思想进出的火花相辉映”。[3]155
“生活对于同学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可你们要记住,你们背负的是民族的命运,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要靠诸君”。[3]187
上面列举的几个典型段落说明了两本书及其作者不同的选材风格。何兆武先生偏向选择印象深刻的“大”事件,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真实的部分,是为“实”;而宗璞先生则选择了贴近生活的小事件,如生活、生子、战争大背景中的小个体、小人物的爱恨情愫、先生们的弦歌不辍等。这些细枝末节的内容难以考证,且《东藏记》本身是以特定历史阶段为背景的虚构小说,笔者暂且将其归为“艺术真实”,是为“虚”。
探究两本书选材不同之根本,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何兆武先生与宗璞先生“身份”明显不同。简言之,何兆武先生是我们现在“百万高考大军”中的一个,是“百万雄师过大江”考上联大的,没有多余的身份,他所接触、了解的均是大部分联大学生都接触的、感受的、了解的,自然具有普适性。他在学校的生活,遠离家人,因而必然是由师德、师风、学风等环境记忆构成的。相对地,宗璞先生作为冯友兰先生之女,自然会接触到一些普通学生接触不到的,看见一些普通学生看不见的。比如书中写孟弗之(原型为冯友兰)一家生活拮据,碧初(孟弗之妻)整理金银细软典当以补贴家用,孟弗之仍在伏案;又写明仑大学(原型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长秦巽衡(原型为梅贻琦)在面临学校因战乱需要搬迁时,在校务大会上哽咽道:“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我们决不投降!”这些情节,或为历史真实,或为艺术真实,但如若没有“教授女儿”这个身份为我们“揭秘”,我们很难了解在那一段笳吹弦诵背后,教授们为坚守自己心中的理想、使命、清明与正义,付出了多少艰辛。
二是何兆武先生与宗璞先生的性别不同。尽管宗璞先生被各界称为“无性别作家”,但无可否认其女性身份。自人出现以来,性别差异所导致的思维差异、思想差异一直是左右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重要因素,人们对某些事情的理解角度、把握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性别中的“天性”。从女性视角出发,战火纷飞下的西南联大,不只有广为人知的、鲜活的、甚至是“模范”的一面,也有维系生存的艰难坎坷、家庭成员的复杂关系、青年懵懂的美好感情、母性特有的伟大光辉……这些都被彼时小小的宗璞先生收入心底。“看似‘卑微’的日常,就是他们的天堂”。从传统的教师、学生主体出发,增加了家庭、个性、心理等方面做考量,独特的关注点也为西南联大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东藏记》相比于《上学记》所增加的部分,或为历史真实,或为艺术虚构,但都服务于人物、情节,服务于联大岁月。
二、提炼之虚实
提炼与挖掘主题相关联,一个主题确定的背后是作者强大的主观世界在起作用。而提炼之虚实,也就是创作者在自己的世界中深化对主题阐释的过程。
在“西南联大留下了什么”等问题上,何兆武先生与宗璞先生有其各自的理解。
何兆武先生以为,平生最美好的读书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在西南联大的七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他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美好时光。[2]父亲从小教育他要远离政治,善于区分爱国运动和政治活动,避免陷入其中。何老一生谨遵父亲嘱托,远离政坛,潜心学术。而家中的姊妹却或多或少被政治风云牵入其中,结局令人痛心。
对于联大学生,何老将其分为三种: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了。比如四二级地质系,大约二十人,已经有了五六位院士。还有一种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新中国成立后大多在各地方、各单位任大小领导,甚至是级别比较高的领导。还有一种何老口中的“不成材”的,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何老说:“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可是我总觉得生活不应该过分功利,应具有一种内在的价值,所以一辈子一事无成也是这个原因”。[2]274
何老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联大学生风格,而《东藏记》中,宗璞先生则让主人公看到日本俘虏,发出“我们进行这场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不仅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也要将‘人’还原为人”的感慨;以艺术虚构的方式构建语言对话、描述心理活动;“爹爹,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我们的飞机呢,为什么不来?”“何曼身上常有一种气味,爸爸说那是油墨味。玹姑身上也有一种气味,爸爸说那是薰香味。我不喜欢油墨味。可是爸爸说:那代表一种理想,我向往那理想。可是我更喜欢衣香。”
这些对话看似是为了填补细节以刻画人物形象,实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象征,细腻的人物被塑造,真实的人物某种程度上被还原。宗璞先生在写作中强调着战争的大环境和人们的各类爱国、报国行为,也多次提到“牺牲”“参军”“轰炸”等事件,使得全书都很“重”——《上学记》主要塑造了战乱中西南联大的“世外桃源”形象,《东藏记》却诉说着离乱弦歌:复杂的人性、卑微的日常,教授的坚守、学生的韧性。
国难当头,硝烟未了,联大学子或加入中国远征军,担任翻译,为获得外援提供支持;或投身飞虎队,执行驼峰航线的生死飞行,以身许国;更多的人选择留在校园,续写弦歌不辍的教育奇迹,守护文化的火种,完成精神的自救,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祖国的崛起奋斗终身。而《上学记》与《东藏记》则借助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中不同的“虚”“实”方式为我们较好地解释了:在“人类的幸福”与“自身的完美”这一深刻命题面前,二者实现的先后顺序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本质上是殊途同归。
上文所述的“实”与“虚”,注重了创作者在文本选择、情节环境建构和主题思想表达过程中的“取舍”,即“我写什么”“我为什么写”。在此语境下,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被细化,由创作结果变为了创作原因,注重了“创作”这一核心行为,从宏观的大层面进入微观的小层面,使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达到了“统一”,更有助于贴近、理解作者和作品本身。
三、结语
总之,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并非仅由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作为唯一坐标,创作者自身因素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在“记录西南联大”这一问题上,《上学记》的“历史真实为主、艺术真实为辅”是何兆武先生个人思想情感与联大生活一定程度上的再现,而《东藏记》的“建立在艺术真实下的历史真实”,则为我们的西南联大记忆注入了新鲜血液。任何时期,文艺创作都不能与社会割裂,文艺理论都不能与创作者割裂。唯有将历史与艺术辩证地看,将作者与环境辩证地看,才能防止跌入“教科书”或“虚构品”的陷阱,从而达到“历史真实使人明理,艺术真实使人增信”的作用。
作者简介:王雪莹(2001—),女,汉族,北京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广播电视编导。
参考文献:
〔1〕郑铁生.沉重的话题: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J].文藝研究,2009(6):19-26.
〔2〕何兆武.上学记(第1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宗璞.东藏记(第1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