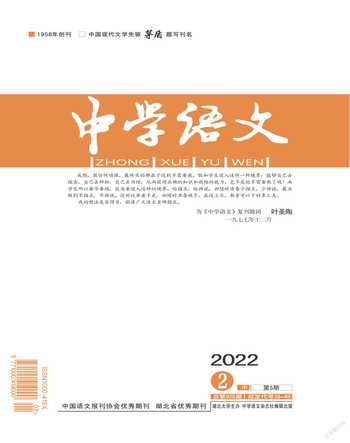略谈昌耀在中国新诗审美范式上的创造
2022-07-21李桃红
李桃红
摘要 本文以昌耀创作于1962年的作品《峨日朵雪峰之侧》为例,从意象的奇异与独特、语言形式上创造性使用“长句”、情感表达上与同时期的主流诗歌保持距离这三个方面来谈昌耀在中国新诗审美范式上的创造。
关键词 生命意象长句情感表达
近年来,对诗人昌耀的关注逐渐增多,他的早期作品《峨日朵雪峰之侧》也入选了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的第一单元。毋庸置疑,其具有鲜明个性和强烈创造意识的诗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纵观昌耀的一生,不难发现,他的生命体验本身就是一种不寻常的的独异和叛逆。尤其是二十多年在青海荒原流放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使得他的诗作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依然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体现着诗人本身的“自我创造”,形成了独特的“昌耀体”。
下面我们以《峨日朵雪峰之侧》为例,从“意象”“语言形式”和“情感表达”这三个方面来略谈昌耀在中国新诗审美范式上的创造。
一、意象的奇异与独特
《峨日朵雪峰之侧》开篇起笔不凡,“这是我此刻仅能征服的高度了”,“此刻”“仅能”,这两个词把一个历尽艰辛的登山者形象,非常突兀地呈现了读者面前。过去我们读到关于雪山的诗,大多都是描写雪山的雄奇或壮美,比如“青海长云暗雪山”(唐·王昌龄)。而诗人昌耀却创造性地描写了一位正在攀爬雪山的登山者,这位登山者之前经历了什么,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攀登,我们不得而知。诗人在这里也没有继续往下写,而是以一个冒号,引出了一幅宏伟、壮阔之景:落日的磅礴与决绝;山体滑坡的“嚣鸣”。这样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听觉轰鸣,却并没有带给我们“豪迈、激昂”之情,反而是全身心的紧张。因为,登山者是要想要向上继续攀登的,可是,眼前之景却带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向下的力量,似乎要拉动着登山者一起坠入深渊。
在这样岌岌可危的处境之中,诗人把笔触又收回到自己:“我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揳入巨石的罅隙。”“血滴,从撕裂的千层掌鞋底渗出。”这里对“指关节”和“血滴”的描写,再一次表现了此次登山过程中所体现的生命的艰辛。同时也以一种坚毅的姿态显示了登山者身处险境中的“意志坚定”和“顽强不屈”。在与山的不屈对峙中,登山者很自然地渴望能有诸如“雄鹰”或“雪豹”这样有着雄伟之力的事物出现,以汲取力量。然而,并没有。出现在登山者面前的,却是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这就与前面宏大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小小的蜘蛛能给登山者带来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吗?
且看昌耀对“蜘蛛”的进一步特写: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
此时,诗歌内在的张力陡然凸显,从“蜘蛛”上,我们看到:即使生命状态卑微,却依然执着于生命的这样一种昂扬姿态。此刻,昌耀将深刻体验到的生命理念、立场、情感,倾注、融贯到了这一精心选择的生命意象中,雕铸了一幅真实而顽强的生命图画。
1957年到1979年,这22年被流放期间,昌耀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都是以“地下写作”呈现的。他的名作《高车》《山旅》《良宵》等都写于这一時期。这时期诗作中的意象,以《峨日朵雪峰之侧》的“登山者”蜘蛛”为代表,俨然已成为生命形象的缩影,是诗人关照自我生命,烛照出来的生命意象。这些生命意象的共同特征都是:拼搏者、抗争者、创造者!是如昌耀自己在诗中所说的“生命意向”:我视生命为宇宙之诗,我视生命现象为宇宙原始诗意的冲动。
二、语言形式的“不合常理”
昌耀的诗,是一部个人精神传记,广袤的青海高原为他的诗作烙上了独特而强有力的象征语言。初读《峨日朵雪峰之侧》,我们一定会讶异于诗歌语言形式的“不合常理”。比如长句的运用:句子很长,且在句中分行;本该处在上一行的结尾,却出现在了下一行的开头。
比如这两句:
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
然而,我们仔细品读,却能发现这正是作者匠心所在:如果句子不分行,那这两个长句就没有了停顿,分别变成:“朝向峨日朵之雪彷徨许久的太阳正决然跃入一片引力无穷的山海。”和“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我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这样的改动,直接削弱了“日落”中诗人所着力刻画“落日”之“决然”。但对这个长句进行分行处理后,我们眼前似乎就浮现出了光明将逝,山海将暗的巨大危险画面。同时,诗歌以“山海。”这样突兀的形式出现在下一行的开头,就具有了极强的震撼。同样,对“蜘蛛”的描写句也被切分成了三行,最后以“快慰。”单独成句,戛然而止,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顽强的生命力”一下子扑面而来,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效果。
所以,昌耀诗歌中长句的普遍存在,“是诗人在诗艺发展中主动做出的艺术选择,目的在于寻找能与其精神强度相对应的诗歌形式。”
昌耀非常爱用长句,但也极其注重诗行的停顿。比如他同样创作于1962年的《良宵》中有这样的诗行:
这新嫁娘的柔情蜜意的夜是属于你的吗?这在山岳、涛声和午夜钟楼流动的夜
是属于你的吗?这使月光下的花苞如小天鹅徐徐展翅的夜是属于你的吗?
这几行诗都是长句,但是诗人处理的停顿就不一样。第一行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有一种款款而来的深情。第二句,在“夜”这里断开,前面对“夜”的铺排,让读者首先感受到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之后,才发出疑问“是属于你的吗?”第三句,还没有等到“夜”,写到“月光下的花苞”就停顿了,让读者在内心不自禁对“夜”产生了美好的联想,这时,诗人才接着缓缓写完后面的句子。
由此可见,昌耀诗歌语言形式上的“不合常理”,对“长句”的分行、停顿,甚至标点的运用,实际上正是他对于诗歌内在节奏的强力操控。“昌耀对于节奏的处理,正是要求诗句与散文语言、日常语言的无意识的节奏拉开距离,凸显独特性和陌生性。”
三、情感表达的“冷静、清醒”
《峨日朵雪峰之侧》创作于1962年,属于诗人创作的早期。如果把这首诗与同样创作于1962年的《甘蔗林,青纱帐》(郭小川),以及当时传唱于大江南北的《回延安》(贺敬之,1956年)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昌耀的诗歌与主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情感表达上,有一种独属于自己的“冷静”和“清醒”。“昌耀的创作一开始就卓然独立于时代的主流诗歌之外,显示出可贵的民间品格”(向卫国)。
50年代末、60年代初,诗坛呈现了一个从颂歌到战歌的变化,对新中国的热烈歌颂,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使主流诗坛的表现主题渐趋一致,却也使得抒写的空间日益狭窄。此时,被流放于边陲之地的昌耀,把个人身世和命运与这片砒砺、打磨他的广袤土地深深地契合了起来,把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和对命运的思考,以一种独特的生命景观和生存情状表现了出来。所以,在《峨日朵雪峰之侧》我们得以看到那孤独而倔强的“登山者”,看到那卑微却“默享”着生命快慰的“蜘蛛”。正如林贤治所说:“从早期的作品看,他已背向诗坛,完全无视时人的写作而独辟蹊径。”
纵观他这一时期的诗歌,比如传唱甚广的《鹰·雪·牧人》(1956)、《高车》(1957)、《良宵》(1962.9),他都是将视野深情地投向了他所置身的西部,投向了永恒的生命和蓬勃的生命力。这正是昌耀的独立之处。他带着这种时代情绪但没有完全被其吞没,“在取得与时代大合唱合拍、同步的同时,却又把诗歌视线抽取出特定时代的公共空间,投放到生命这一普泛领域。”因而,在裹挟一切的时代洪流中,昌耀以创造性的新诗审美范式,发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