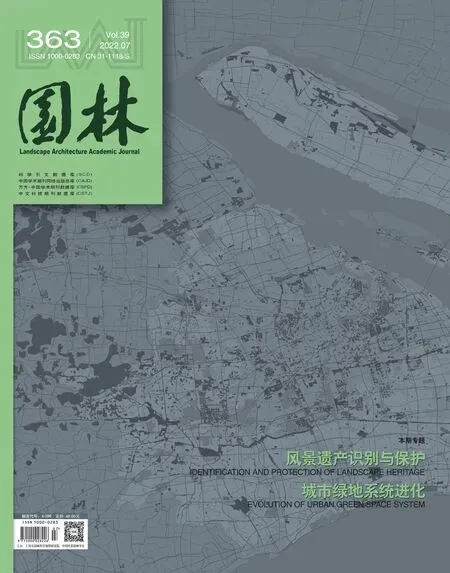风景遗产视角下藏羌交汇区聚落遗产空间特征识别与价值研究
2022-07-21孙松林
孙松林 宋 爽,2*
(1.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重庆 400715;2.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建筑与设计学院,重庆 401524)
风景遗产是具有国家或世界突出普遍价值的地域空间综合体[1],是自然和人文内涵高度融合的文化景观、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杰作,在《世界遗产公约》中主要被归为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文化景观两类[2]。而文化景观作为人与自然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驱动下产生的具有延续性与有机演进的景观,广泛分布于中国大地之上,成为风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乡土聚落不仅具有文化景观的普世价值,也拥有自然风光、景观建筑、乡风民俗、文化技艺等风景遗产资源[3],是风景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当下部分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乡土聚落已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制度下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如何进一步从量大面广的乡土聚落中识别出具有保护价值的聚落遗产,提出基于保护发展的价值传承与活化途径仍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4]。
1 风景遗产视角下的聚落景观
1.1 乡土聚落是风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通过不断地适应和改造自然,创造出具有突出特色与文化价值的乡土聚落景观,完美诠释了“有机演进的文化景观”这一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乡土聚落型文化景观也越来越受到遗产保护与风景园林从业者的青睐。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与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于2006年成立了ICOMOS-IFLA国际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和IFLA文化景观委员会,并在2017年底联合发布了《关于乡村景观遗产的准则》(ICOMOS-IFLA Principles Concerning Rural Landscape as Heritage),文件指出“:乡村景观是人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延续性文化景观中最常见的类型之一”[5-6]。自此乡土聚落遗产有了具体的评价标准,其景观价值也得到广泛认可,针对聚落风景遗产特征评估[7]、价值评价及景观资源保护[8]的研究也愈发丰富。学者普遍认为“区域景观特征明显、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并活跃至今、是特殊环境下人类聚居的典型案例”[9]是聚落风景遗产的共性特征,但如何划定遗产、阐释遗产价值仍是当前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10]。
1.2 藏羌交汇区的聚落风景遗产亟待发掘与保护
中国青藏高原东部的藏羌碉楼聚落群是乡土聚落风景遗产中的璀璨明珠,广泛分布于大渡河与岷江上游的丹巴、小金、汶川、理县、茂县、黑水、松潘等地区(图1)。由于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相互挤压,加上河流常年下切作用,使区域内沟谷纵横,谷底狭窄、谷坡陡峭,形成以V型河谷为主体的高山峡谷地貌。数条平行的南北向峡谷为民族迁徙提供了天然通道,成为中国西部民族交流的重要孔道(藏彝走廊),也是中原王朝与吐蕃军事冲突的前沿地带和征伐要道,还是汉藏之间茶马贸易的商贸通道[11]。藏、羌、汉、回等民族在此交错杂居,匮乏的生产资源、动乱的治安环境、复杂的民族与宗教文化[12]造就了此地区极其危险与脆弱的生存环境。藏羌人民为了生存繁衍,在这些纵横交错的高山峡谷中建造出巍峨雄伟的碉楼建筑群,探索出以种植为主、畜牧为辅的山地垂直气候环境下的立体农业,最终形成由碉楼建筑、碉房民居、陡坡梯田、高山牧场和高山峡谷组成的高原农业聚落文化景观,成为世界聚落遗产中一颗耀眼的明珠。2013年,藏羌碉楼与村寨(Diaolou Buildings and Villages for Tibetan and Qiang Ethnic Groups)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近年来,藏羌交汇区的乡土聚落逐渐受到学者关注,他们对其空间布局、生态价值[13]、景观特征[14]、建筑形态[15]、文化习俗等内容展开了研究,但针对遗产属性、遗产空间特征、遗产价值的研究仍十分少见,导致大量的乡土聚落被遗弃损坏或建设性破坏,逐渐丧失了作为文化景观的延续性与有机演进的活态价值,使未来的申遗之路更加困难重重。
2 藏羌交汇区聚落风景遗产空间特征识别
风景遗产为乡土聚落遗产提供了不同于以往聚焦于建筑本体、建筑群及空间格局等[16]内容的全新研究视角,它将乡村文化景观所处的大地环境、山水环境、景观符号等内容纳入遗产研究的范围,使乡土聚落遗产获得了更为宏观的整体视野,更有利于解析遗产的景观特征、生成机制及其独特的遗产价值。因此,本文借鉴翟洲燕[17]、周政旭[9]等人对聚落景观特征的分类识别方式,从环境本底特征、聚居建筑特征、人文景观特征三方面对藏羌交汇区的聚落风景遗产空间特征进行识别,以更深刻地认识该地区的聚落风景遗产,促进聚落风景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提炼。
2.1 环境本底特征
2.1.1 聚落选址
高山深谷的地貌特征导致本区域拥有沿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分异的气候、土壤、植被景观类型,由此产生了差异巨大的自然资源条件,影响着生存其上的各民族聚落的空间分布。基于30 m精度的DEM数据和2 059个1∶25万农村居民点数据(2014年),利用ArcGIS进行重分类、数值提取等处理后得到系列统计数据。从图2可看出,中起伏中山、高中山和大起伏高山是藏羌聚落分布最为集中的地貌类型,尤其以中山、高中山(当地称为二半山、高半山)分布数量最多。在海拔高程上呈现出随着海拔升高而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羌族主要分布在中海拔的河谷及二半山等地,藏族在低海拔的河谷和高海拔的高半山、高山均有大量分布。河谷聚落主要散布于支沟与主河道交汇处的冲积扇阶地之上,由于土地肥沃、交通方便,又是物资集散、信息传递的交通枢纽与战略锁钥,成为藏、羌、汉、回争相定居的叠合区,也是场镇、关隘等重要节点的分布地,聚落数量不多但密度最大。高半山地形相对平缓,临近高山牧场和森林,是典型农、牧、林交错地带,生活资源丰富且易守难攻,成为聚落分布最多的地带。半山和二半山为河谷和高半山之间的过渡地带,地势陡峭、水源匮乏、耕地稀少,主要是羌族聚落在此定居。
在坡度方面,绝大多数聚落位于15°~35°的中坡与陡坡之上,还有相当部分聚落分布于35°以上的急陡坡。稀缺的平地资源决定了聚落建筑必须充分利用悬崖、山麓、陡坡等不利地形,以将相对平坦的地貌留给耕地,因此大部分聚落处于中坡与陡坡等不适合耕种之地。他们紧邻溪流或山涧而居,以聚居村寨为中心,下方是相对平缓的坡耕地,背后是大片的暗针叶或针阔叶神树林,神树林之上有大片放养牦牛的草场,草场之上是神圣的雪山,整个聚落由折线式道路与河谷相连,并在河谷或沟口处由索桥与过境大路相连通。
2.1.2 山水环境
该地区年均降雨量普遍在450 ~700 mm之间,整体干旱少雨,因此水源成为聚落选址与生产的重要限制因素。图3-a表明,区域内绝大部分的聚落分布在河道3 500 m范围内,超过一半的乡镇聚落分布在河道500 m范围内。河流的大小等级也对聚落分布有重要影响,主河道两岸的居民点离河岸的距离一般在100~1 000 m,支流的聚落分布离河更近,多数在50 ~200 m之间,这主要和雨季河水的涨落情况有关。高山峡谷地区,江河水流湍急,时有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发生,聚落选址时故意避开大型的河流,而选择在小溪流、山涧旁,或离江河较远的河旁阶地。半山、高半山地区的聚落缺少自然水系,则人工修筑水渠将溪水引到村寨最高处,先为村寨提供生活用水,然后顺流而下依次浇灌坡地、农田(如色尔古与娃娃寨);而那些远离溪流山涧的村寨则选择在有泉水的地方聚居(如雅都大寨子)。寨神林或风水林作为聚落重要的信仰空间与生态屏障,往往位于村寨上方,具有保持水土、防范地质灾害等作用,也是村民在重要节庆活动中举行祭祀的场所。
相比较而言,藏族聚落更愿意在靠近水源且避开河口、谷口等容易遭受山洪等自然灾害侵袭的河谷地带定居。这些地区水源充沛、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用地相对宽裕,适宜发展农牧产业,具有较高的人口承载能力,成为强势藏族优先选择的聚居区域。而羌族长期受外部族群与临近村寨的侵扰,生存防御成为其首要考虑目标,因此舍弃缺乏防御优势的肥沃河谷,转向条件艰苦但生存更加安全的山地居住。这种长期的生存哲学也演化在藏羌民族的风水观念中,形成了大相径庭的山水文化[18](图4)。
2.1.3 生产资源
为了维持生存与发展,聚落必须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高山峡谷地带以种植为主、畜牧为辅的自给自足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资料主要来源于耕地,因此耕地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从图3-b可知绝大多数聚落位于耕地500 m缓冲区范围内。区域内耕地受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的限制,土壤瘠薄而产量较低,导致单位人口所需耕地面积较大,而现状适合耕种的土地面积小且分散,导致了聚落总体上分布较散、规模较小、密度较低。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地理空间狭窄且耕地资源少,斑块面积普遍较小。随着海拔升高,土地逐渐变得平缓,潜在耕地资源增加,聚落数也增加。但高寒地区受作物生长及产出的影响,需要更大的种植面积来满足生活需要,因此聚落密度逐渐变小,聚落斑块半径逐渐变大(图3-c)。受限于可耕地稀少,聚居建筑多集中建在耕地的边缘,以减少对耕地资源的占用,同时防止放牧的牲畜穿过村寨啃吃作物。
森林与牧草资源则为人们提供额外的生存补充,同时还具有生态保育功能,保障聚居环境的稳定。因此大片林地缓冲区内也有较多聚落分布,它们为农业产出不足的居民提供了进行森林采集、狩猎和放牧的多种选择,以补充生活所需并获得林下经济收入。区域内的牧场资源主要分布在亚高山和高山草甸,所以刚从西北草原迁入本地的传统聚落大都建在高山之上[19],后从中原及当地土著学习农耕技术后才逐渐往下迁徙。最终形成河谷主要为定居农业,仅养殖少量家畜,二半山和高半山为半农半牧的兼营方式,高山草甸为纯粹牧业的聚落特征。其中高半山同时拥有牧场、森林和耕地,具有丰富的食物来源和多种资源利用方式,因此在古代是最富裕的聚落所在地,也是藏羌聚落分布最为丰富的地区。
2.1.4 道路交通
由于高山峡谷不同的地貌条件与聚居情况,导致河谷地区道路最为密集,主要为单通道直线式道路,在集镇等地局部形成格网状道路;半山、高半山道路稀疏,基本全为单向折线式,并与河谷干道连接成树枝状拓扑结构(图5)。各沟谷中的山民与外界联系时必须要跨越沟谷或河道,在“村村通”工程以前,主要依靠位于沟口的溜索或栈道(当地称偏桥)进出,因此索桥可以看作是区分内外边界的标志与重要节点。同一地缘区域内的村民都将沟口作为内部势力范围的边界/起点,索桥或栈道则是象征村寨财产范围的实体构筑物,出山购货或外敌入侵都以是否过桥作为分界点。
聚落内部的道路则可分为直线式、格网式和狭窄街巷式,直线式多位于河谷地区的线型聚落中,格网式道路是河谷地区组团型聚落的道路形式,狭窄街巷式则是紧密聚合型聚落的道路形式,也是最常见、最有特色的道路形式。其道路一般夹杂在建筑之间的夹缝中,垂直或平行于等高线,并常和排水沟渠相结合,呈现出蜿蜒曲折的层次感。道路交通的便利性影响着聚落之间的信息交换与各聚落人群的自我认识与族群自信。往往交通条件越差的聚落人群信息越闭塞,对外界认识更少,与外界接触时常表达出一种莫名的自卑感,也加深了其对外界的恐惧心理。
2.2 聚居建筑特征
2.2.1 聚居结构
聚落空间结构与形态往往受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地形条件及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同处高山峡谷间的藏羌聚落在总体结构上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均分布较为分散,总体形态或顺应地形、依山就势而建,或沿等高线、河谷往两端延伸,无明显的几何中心或对称轴线。但在大体相似的结构下,藏羌聚落也有一定的区别性。藏族聚落受到的安全威胁相对较少,往往采用散点式的布局使各户获得充足的农牧场地,同时使耕作更为近便。但由于受土司头人及宗教信仰的影响,多以官寨或寺庙为核心或视觉中心。羌族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治阶级与宗教集团,故出于安全考虑,建筑多相对均质而紧密地聚集在碉楼周边,形成自由发展的密集型聚落。
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以碉楼为核心和以寺庙为核心的布局形式。以民居步行到碉楼的时间和距离为防御半径,以复杂多变的路网结构和水网系统为脉络,密密匝匝布置居住建筑,折射出人们缺少安全感,对外界充满恐惧的心理。而将宗教寺庙置于聚落中心或聚落附近山体的最高处,民居建筑呈环绕或朝向寺庙的形式层层布置,则表达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信仰寄托,是一种能够相互交往、共同祈福的理想居所。
当然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聚落也会有不同的布局形态。河谷与谷间台地一般地势相对平坦,耕地资源优良但无险可据,且河谷多为交通要道,故只有政治背景或族群势力强大的集团才在河谷安营扎寨,聚落多集结成组团以加强防御,形成组团聚合型聚落。近年来随着地区治安稳定,人们对交通、经济与信息交流的需求逐渐提升,部分聚落开始沿交通干线聚集,形成线性聚落(图6-a、图6-f)。山麓及二半山地区地势较陡,耕地稀少,为了节约有限的耕地,建筑只能建在耕地附近陡峭的山坡、山崖之上。同时由于仍在过往军队经常洗劫的范围之内,聚落建筑多紧密布置,形成建筑密度最大的紧密聚集型聚落(图6-b、图6-c)。高半山耕地充足,且由于地势与道路阻隔,生存环境相对安全,因此建筑间距较大,沿等高线松散分布,部分民居还带有院落,组团之间以耕地隔开,呈不规则分散状,为松散组织型或组团聚合型聚落(图6-d、图6-e)。高山多为林地及草场,资源丰富但条件艰苦,聚落多成随机散点式分布在绿色山野之中。
2.2.2 建筑形式
该区最具特色的空间特征当属耸立在高山峡谷间的藏羌碉楼,其中尤以石碉楼最负盛名。历史上也多有记载,《隋书·附国传》载有:“无城栅,近山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上方两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章谷屯志略》则记载:“石碉形制有二,或如方几,或似菱花,下宽上锐,自五六丈至十数丈不等,悉以乱石砌成,碉底六七丈,中栈以木,下卧畜牲,中置锅桩,上数层贮粮馍什物,远望轰如束笋,高出云霄。”石碉楼整体呈下大上小棱柱状,外墙面有明显的收分,窗洞狭小,常由片石、块石等天然材料砌筑而成,总体上与自然山岩浑然一体,气势雄浑粗犷、苍凉悲壮,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在缺乏石材的地区,则用生土夯筑碉楼,即为黄泥碉。黄泥碉一般以石片奠基,黄泥筑身,上作夯土平屋顶。墙身部分也常辅以片石、木料、稻草或竹条,以增加碉楼的稳定性和拉结作用。其建筑形态与石碉楼大体相仿,但平面多为四边形,缺少五边、八边、十二边、十三边等丰富的碉楼形态。
藏羌民居建筑的建筑形式与空间形态异常丰富,无法用一个标准的模式来概括,大体可以分为平顶石碉房、带坡屋顶的碉房、木质板屋、穿斗民居和黄泥碉几类(图7),但在各沟谷中散布有大量的变体形式,而同一沟谷之中的藏羌民居往往具有极高的相似性,与民族关系不大。碉房是分布最广的一种建筑形式,可以算作碉楼的民居版本。其内部一般由三层空间组成,底层为牲畜圈及杂物间,中间层为人的主要生活空间,由火塘、卧室等组成,最上层通常为半开敞的罩楼、经堂等神居空间,兼作储藏室,前半部多为晒楼,同时也是祭祀、敬神的场所。板屋即用木板建造的房屋,也是氐羌民族的传统民居之一,目前主要分布于茂县北部和松潘南部的羌族地区,以及平武一带的白马藏区。穿斗民居本是四川汉族地区普遍采用的建筑形式,但随着汉人大量进入本地区而在木材资源丰富的藏羌聚落和商贸古道沿线的场镇中得到应用推广。
在此相似的建筑形式中,藏羌之间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藏族民居以其更为强大的群体势力、更丰富的财富与更开放的性格,常修建更加大型、开敞的民居建筑,而羌族所处的资源条件、长年遭受战争的阴影以及更为保守的心态,使其民居建筑体量更小而密度更高。
2.2.3 细部装饰
藏族建筑细部装饰丰富,常在屋顶、墙体、门窗、梁、柱等部位进行浓郁的装饰,尤以彩绘和雕刻为主。其屋顶常装饰有煨桑炉、四角神、经幡等宗教物品,大门及窗框上部出挑有一至三层的小椽,每层出挑10 cm左右,最上一层再用石板做出挑檐,挑檐上放置白石、羊头或牦牛头骨,起到震慑妖魔的作用。在小椽上常装饰有彩画,有的门窗边框还雕绘有生动的八宝、莲花等宗教吉祥图案,门窗洞口的四周常用白灰涂成牛头窗框。
羌族建筑细部的处理要简单得多。平屋顶及罩楼上仅供奉白石,窗洞也基本是方形的斗窗,窗扇以木格栅及原木板居多,较少雕刻与着色,少数刻画有羊头、日月、山峰等图案。门头偶尔悬挂羊头骨或用白石镶嵌成羊头形象。部分靠近汉地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家庭则采用汉式垂花门的做法,门上常贴有对联、门神等装饰,个别还在大门左边设置泰山石敢当等汉族宗教形象。
如果将藏民比作高原阳光照耀下的雄鹰,羌民则更像是高山峡谷间的灵猴,不同的民族文化生长出大相径庭的色彩风格。藏族建筑色彩鲜艳,常用红、白、黑三种颜色装饰门窗洞口及屋檐脊线,总体对比强烈、饱和度高,和蓝天绿树形成强烈的对比,表现出豪放、彪悍、热情的民族性格,以及热烈、纯净、绚丽多彩的审美倾向。而羌族民居基本都是建筑材料的自然本色和质感,与大山融为一体,因此在崇山峻岭间很难发现羌寨的存在,从侧面提高了其隐蔽与防御性,也有部分靠近城镇的羌居外刷黄泥,但总体仍表现为自然、质朴、低调之美,体现出低调、质朴、内敛的民族性格(图8)。
2.3 人文景观特征
2.3.1 公共活动空间
公共活动空间不仅是村民社交活动的场所,也是民族文化、族群观念、宗教习俗等社会人文要素在物质空间上的反映。高山峡谷间珍贵的土地资源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大多数聚落缺少专门用于公共活动的实体空间,而是在田间地头、桥头道旁完成日常的交往,重要的集体活动则多是在神树林里进行祭祀或带上吃食去高山草地上转山野餐。相比较而言,藏族自信、开放、包容的民族风格造就出更多自信开放的公共空间,如屯兵广场、锅庄广场以及寺庙、白塔、转经廊、玛尼堆等兼具公共空间与社会交往功能,不仅数量多而且面积大。羌族拘谨、保守、内向的民族性格则衍生出封闭狭窄的公共场所。其聚落建筑密集而紧凑,仅少数羌寨有晒坝、寨门广场等明确的公共场所,大部分只能在过街楼、取水道、屋顶平台等狭窄逼仄的附属空间中开展公共交往活动。
2.3.2 文化景观符号
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景观符号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且其图案形式与制作工艺在不同地区又各有差异,但在同一沟谷中临近的藏羌村寨有时候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图9)。
藏族聚落中除了以牛头和白石为代表的文化标志外,最为常见的当属寺庙、白塔、转经廊等空间实体及狮子、佛教经文、吉祥八宝等平面图案。例如部分家庭在门上绘以日月、云纹、八宝等吉祥图案,或贴上“蒙人驭虎”“财神牵象”等图画,建筑外墙上还画有蝎子、雍仲等图案,作为驱邪镇魔、招财进宝的法宝。其聚落周边也常见有丰富的文化景观符号,如经幡、拉则石堆和玛尼石堆等,是嘉绒藏区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性景观。
羌族聚落中的景观符号以原始宗教符号为主,他们信仰万物有灵,并以白石为象征图腾,部分聚落也崇拜羊头图腾。由于受到藏传佛教、道教、儒教等影响,羌寨中还经常夹杂有道观、庙堂、寺院等宗教建筑,但规模不如藏族寺庙宏大,装饰也相对简单,民居建筑上也常附有门神、石敢当、天地君亲师牌位等内容,呈现出多种信仰符号杂糅的现象。聚落周边的景观符号较少,以白石和祭台为主,在村边、地头、神树林中常结合祭台构成山神、水神、青苗神、树神等宗教形象。羌族原先普遍实行火葬,后受汉族影响逐渐改为土葬,土葬坟场多位于村寨附近的山坡之上,靠近藏区的村寨也在坟墓周边插玛尼旗杆,挂彩色风马旗。
3 藏羌交汇区聚落风景遗产价值提炼
价值是决定风景遗产的标准和根据[1],也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灵魂,一个项目能否通过评委会认定,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因此遗产价值提炼是风景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20]。依据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2021),在综合考虑《巴拉宪章》(1999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等国内外遗产保护准则之后,本文尝试从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科学价值4个维度对藏羌交汇区的聚落风景遗产价值进行提炼总结,以为藏羌聚落风景遗产正式申遗奠定基础。
3.1 历史价值:族群斗争的历史见证
历史价值是指文物古迹作为历史见证的价值[21]。每个民族都用不同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历史,而羌族作为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其过往的民族经历与历史故事大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给当代的民族学研究带来诸多困难。而聚落作为特定土地上的历史沉积物,既是特定族群文化的产物,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代表,更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见证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及族群日常生活的展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聚落风景遗产是建构民族历史与记忆的重要历史素材,符合世界遗产OUV评估中第Ⅲ条的规定: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2]。
高山峡谷间部落繁多、互不统属,地方土司和中央政府对本地区进行轮番统治,加上自然条件恶劣、生存资源匮乏、匪盗纵横、宗教斗争激烈,使得此地的治安极不稳定,因此加强防御成为各个聚落安居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从各聚落的碉楼数量与密集程度、各民居建筑的组合形式与开窗方式即可大致判定出其历史上的战争与械斗情况,及本地区的生存空间与资源分布情况。而聚落选址与安全防御格局也可反映出该族群在历史上的实力强弱。只有势力足够强大的族群才分布于交通方便、土壤肥沃、水源条件更好的低海拔河谷地带,势力弱小的族群则分布于交通条件艰苦、缺少水源、气候寒冷的高山、高半山地区。或者选址于山脊、悬崖、坡脚等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以增强聚落防御性能。同理,势力强大的族群聚落分布于平缓坡地,建筑呈散点式布局,道路均衡布置呈格网状,部分还有锅庄广场、寺庙、转经廊等公共空间;而势力弱小的族群聚落则紧密聚合,高碉耸立,道路曲折而狭窄,没有开放的公共活动空间,整体呈紧缩的防御状态。
3.2 艺术价值:苍凉雄伟的生存艺术
在世界遗产OUV评估标准中,第Ⅰ条:表现人类天才创造的杰作,第Ⅳ条:是一种建筑、建筑整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这刚好是藏羌聚落风景遗产的艺术价值所表达的内涵。
高山深谷的地理环境、极度匮乏的生存资源、多民族杂居的文化现象赋予了地区独特而神奇的聚落景观,尤其是那些耸立在峡谷两岸,战时可御敌、平时可安居的各式碉楼,展现出雄伟壮观、苍凉悲壮的神秘魅力,给人以极大的视觉与心理冲击力,也反映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建筑艺术审美特征。而偏僻、闭塞的地理交通环境,落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又使得这些类型集中、数量巨大的民族瑰宝得以保存,成为青藏高原东部的壮丽风景与独一无二的风景遗产。
3.3 社会价值:冲突融合的民族记忆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指出:社会价值是指文物古迹在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文化精神的传承、社会凝聚力的产生等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价值[21]。聚落风景遗产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叠加而成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反映了聚落所处的自然环境、宗法制度、社会结构、生产关系、风俗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也是集体意志和个人记忆的载体[10]。在当代,它们与档案馆、图书馆等其他“记忆之场”一样[22],共同构筑起传承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在历史记忆的回溯、重构和刻写中起着重要作用。
藏羌聚落大多建筑密集,封闭内聚,缺少适度的公共交往空间,特别是羌族聚落,基本没有广场,只有街巷、过街楼等阴暗逼仄的交通空间,并修建有大量的碉楼,表现出很强的防御性,反映出当地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人际关系复杂的族群意识。而长时间的独立生活与阴暗逼仄的活动环境容易形成民族内向、保守的心理,甚至产生对外界事物的猜忌、恐惧与敌对情节,进一步加强了对坚壁高垒的依赖。
聚落遗产中关于空间形式、装饰符号的建构也是族群之间互相认同与区分的价值标尺。历史上,狭隘的族群认同与过度区分导致的紧张族群关系,使该地区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同民族内不同部族之间,常因争夺土地、家族仇杀等原因引发械斗与战争。而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原本各自独立的建筑原型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中进行了复杂的融汇创新,一方面衍生出多种不同的住居形式,另一方面也为族群认同与地区和平创造了条件。此外,聚落遗产也是民族节庆活动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丰富的民族活动与神圣的传统文化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生产生存知识,也是一代又一代藏羌人民对历史事件与经验记忆的沉积积淀,是联系各村寨之间的情感纽带。
3.4 科学价值: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
藏羌聚落风景遗产作为一种自然与人文的共同杰作,是先民们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代表着藏羌民族对社会历史和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符合世界遗产OUV评估标准第Ⅴ条“是传统人类居住地、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价值要求。
高山峡谷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给生活其间的藏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和心理压力,也迫使人们对变化莫测的自然界充满着畏怖与崇敬心理,并由此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天神、山神、水神、树神、青苗神等宗教禁忌,进而衍生出一系列的祭祀酬神活动。这种宗教信仰不仅保护了聚居空间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蕴含着与自然共生、与山水和谐的朴素生态观念,最终影响着聚落风景的构成与表达。动乱环境下的聚落人群多聚集在一起以增强族群势力,而当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出现“分寨”现象,以防止超过土地的生态承载力,减轻对聚落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保持人与自然系统的平衡。
藏羌建筑也在长期的试错—改良—调试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具有良好生态适应性的建造方式。例如聚落建造遵循靠近水源、依山构室、占山不占地等最大限度提高生产、保障安全的基本原则。墙体采用内直外斜、下大上小、下宽上薄的形态来增强整体稳定性;同时建筑开窗少,每层以木梁、木板拉接,增加整体刚度;厚实的墙体与较小的门窗洞口具有良好的蓄热和隔热性能,能极大地降低建筑的热能渗透,保持高原地区室内温度的恒定。以火塘为中心的空间布局解决了冬季室内的热能问题。建筑材料不拘泥于石材或木材,而是因地制宜、就地选择木材、石材、生土等进行建造,以最大程度降低建造成本与难度,进而深刻影响各地区的建筑形态,并使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优秀的生态适应性。正是这些适应生态的营造与生存智慧,才创造出今天独特的聚落形态与风景特征。
4 结语
复杂的地理环境、匮乏的资源条件与动荡的历史背景使藏羌交汇区出现了举世无双的聚落风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视觉冲击力。这些风景遗产既是藏羌儿女在特定历史环境中迫不得已的杰出创造,也是各民族融合迁徙的历史见证,是藏羌民族的智慧结晶与活的风景遗产。保护这些风景遗产免于破坏,使其所蕴含的历史、艺术、社会、科学价值得以长久保存,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当下,随着交通便捷、通讯技术革新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藏羌交汇区的聚落发展迎来重大转变,大量传统聚落被拆除遗弃或“风貌打造”,其延续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根本转变,聚落风景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要深入挖掘、提炼其遗产价值,尽快划定“应保尽保”范围,积极推动藏羌聚落风景遗产早日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名单。同时,积极利用其资源禀赋条件,结合地区发展与产业转型契机,将风景遗产保护融入藏羌民族的生存发展之中,使之得到活态、完整和永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