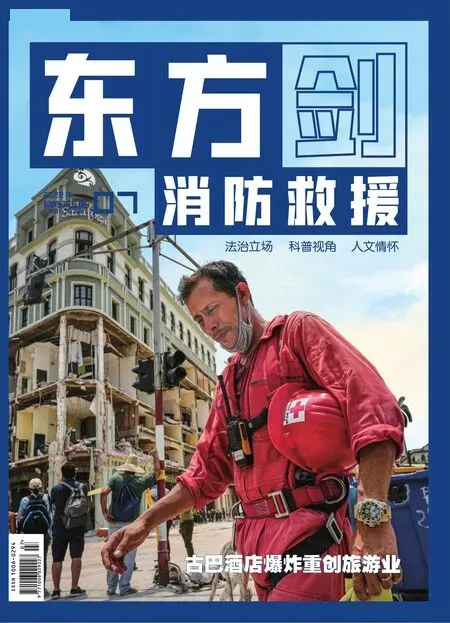鸿泥记(连载之二十四)
2022-07-16张晔/文
张 晔/文

七十九
“她没事吧?”
“她没事吧?”
“还好,我帮她换了件衣裳。伤口还挺长的。她的衣服,唉,你看。”陆秀英把团在手中的衣服露出了一角,血渍已经干涸呈现深褐色。
“等下,悄悄烧掉吧,”谷维新瞧了一眼,望了望虚掩着门的卧室,双眉紧蹙,叹道,“唉,这怎么回事呀?仲鸣到底怎么了,她有说吗?”
秀英连连摇头,轻声说:“作孽哦,看着像是刀劈的,大晚上的,不知道搞什么事情。我问问,你也别急。”谷维新点点头,低头望了眼自己这身随意的旧衣裳,想着出门还得注意一下行头,便让秀英进房拿件浆洗过的长衫。秀英刚进房门,就见满脸泪痕的陶小琴挣扎着要起身。谷维新和秀英两人见状忙关上房门,生怕惊醒了孩子们。还没待他们开口,陶小琴号啕大哭起来,带着哭腔嚷道:“爷叔,谷先生,你想想办法,救救仲鸣,他被,他被抓了。求求你!”秀英搂着她的肩说:“你别激动,慢慢说,千万别动,伤口又要渗血了。”随后,一点点扳着她的肩膀,扶她坐在椅子上。
秀英柔声安慰道:“小琴你慢点说,昨晚仲鸣怎么会被抓?在哪里被抓的?”陶小琴望着眼前的婶娘,见她身旁的谷维新眼神一改往日的温和,变得犀利又严肃。陶小琴支支吾吾了片刻,低声说:“昨天晚上,我们在,在,在纠察总队……没想到,冲进来一群人,穿着纠察队的衣服,我们以为是其他分区的同志,谁知道,他们见人就打,还开枪……我们从后门逃出来后,仲鸣让我先走,就……”
陶小琴失声痛哭起来,说不下去了。秀英问道:“那些是什么人啊?你认识吗?”陶小琴一个劲摇头,呜咽了会儿,断断续续地说:“不认识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之后,我想去找烟草工会的同志,他们的地方也被封了。我,我就,一路跑……”
谷维新恼怒地把头扭向一边,心想:真是瞎胡闹,现在哭有什么用。报纸上天天喊着精诚合作,可一边又限制罢工,果不其然,现在真的出事了。他沉吟了片刻,突然打断了陶小琴的哭泣,严肃地问:“小琴,我就问你。”刚脱口说出半句,谷维新内心又暗暗后悔自己太冲动,可转念一想,直接问比绕圈子好,便接着问道:“你说实话,你和仲鸣,是不是共产党?”陶小琴愣住了,房内的空气在此时陡然凝重了起来。
陶小琴收起眼泪,郑重地摇摇头,说:“不是,现在还不是。”听到这话,谷维新紧蹙的双眉轻轻舒展开,他如释重负般说了句“那还好”。他望了眼窗外,又听见楼下孩子们的动静,径直走出了房门,见秀英跟着出来,便拉着妻子到角落,悄声说:“你今天就待在家里,也别去阿爸店里了。几个小的也快要起床了,你在家看着他们几个。让老大去学校的时候给我请个假,就说我病了,请李先生下午帮我代节课。”陆秀英点点头,望着一脸严肃的丈夫,她已经快二十年没见过他这种神情了,忽紧张地拦在谷维新面前,问道:“你要去哪里?你,别是……”
谷维新勉强挤出了笑容,安慰妻子说:“看你慌的,我去找李之松。也只有让他看看有没有门路。”他回头看了眼卧室,正色道:“他们都不是,那还好。可我担心,之松也未必有门路。你看着她,别让孩子们进来。也别,别让她跑了。”最后几个字从谷维新嘴里说出来,在秀英听来别有一种意味,秀英瞪大眼望着丈夫冷峻的眼神,心中微微一颤。
租界内并没有丝毫的异样,谷维新拦住了辆人力车,开口就说:“去四川路。”车夫摘下毡帽扇了扇,喘了口气,拦在他面前说:“先生,你还是别去了,现在啊,也过不去的。”谷维新心中已知一二,仍装作不知,故作惊讶地问:“怎么了?我还想去老北门买点物什呢。”只见车夫扬了扬眉毛,像透露一件特别秘密的大事似的,说:“外头乱七八糟的。从昨天夜里到现在还不太平呢。”继而大声说:“先生,你不去嘛,我就走了哦。”谷维新笑了笑,客气地说:“去别的地方,走爱德华七世路,到圣母院路拐弯。”车夫一听,欢喜地大声应了一声,心想:那儿可是高档地方,说不定车钱还能多给点。
沿途点心店飘散出的蒸笼水汽、方糖糕的甜腻味,还有油滴滴的油炸桧让谷维新肚子里的馋虫咕咕作响,可他却懒得理会肚子的抗议,所有的心思都在想着董仲鸣和可能用得上的关系网:仲鸣这孩子,唉,太不懂事了。都是被他的家主婆带坏的。本来好好做点生意、读读书,现在不晓得在外面干嘛。李之松那么多年不问世事,虽然和洋人做点生意,唉,也只能姑且试试看了。董叔叔身子是越来越差了,哪里还能找什么人。再不行看看岳父在商会有没有门路……
还没理出个头绪来,车却已经停在了路口。谷维新下车后,没走几步就到了李之松的公寓门口。门房见是老爷的老朋友,也就让他直接进去了。谷维新刚踏进门厅,远远望见昔日冷清的客厅里坐了两个人,他自觉莽撞,赶紧退到了门外。却不想客人已经见到他,站起身向他走来。谷维新尴尬地退到门旁,可定睛一看,却愣住了,往昔的片段如黑白电影似的在眼前跳跃。
“啊呀,谷兄!真是相请不如偶遇啊!你看,刚想提起你,你就来了!”最先迎上来的是曾经的蔡翰林,如今国府监察委员的蔡民声。谷维新望了眼李之松忍俊不禁的模样,不得不感慨世事难料。还没有等谷维新反应过来,黄有尊不由分说迎上来抱住了他。紧紧的拥抱多少能感受到其中的真情,毕竟是曾经共患难的兄弟。谷维新轻轻拍了拍黄有尊的臂膀。
“来来来,别站着,”李之松走上前,招呼三人,略带深意地说,“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四人坐定,黄有尊开口问道:“谷兄,你这家伙,真是的,你跑哪里去了。抱得美人归就消失了,这也快十多年了吧。你说你。”谷维新的心思全不在叙旧上,望了眼李之松和眼前的两位故人,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自嘲道:“是呀,小弟当时,当时实在是儿女情长了,就,就不过问国事了。你们看李将军,不是也解甲了嘛。”
“这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啊,哈哈哈,哎呀,虽说没有‘二十载’了,但绝对是‘重上君子堂’。看来今晚我们要不醉无归了。”蔡民声笑着附和道。
“啊呀,两位如今都是国家的股肱之臣,岂敢岂敢。”谷维新连连摆手。这话恭维得漂亮,蔡民声忙拱手致意。
李之松见谷维新神色不定,插嘴道:“谷兄,你是有顺风耳呀,还是千里眼?怎么登门看望我这个闲人了?”谷维新松了一口气,瞥了眼李之松,见他狡黠地抿嘴笑,心想:还是之松明白我。又见黄和蔡都望着他,双手抱拳,对着李之松道:“今日,真是,唉,之松,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这……唉。”
蔡民声见他欲言又止,说:“要不,我们先回避下?”刚要起身,黄有尊倒心直口快地说:“谷兄,我们都是旧相识,有什么困难,我一定鼎力相助。你但说无妨。”谷维新望着黄有尊真挚的眼神,这个和他蹲了几年大牢的兄弟,说的这话着实让他很感动。他早在报纸上得知这位黄先生如今可是贵为先总理的托孤大臣,手握党政权柄,心想:如果黄有尊能开口,那董仲鸣自然是有救了。李之松催促道:“行了,你真是越来越婆婆妈妈了。怎么了?总不见得是借钱吧!哈哈哈。”
谷维新看着李之松,故作轻松地说:“这事情,唉,小弟的一个世侄,不知怎么的,昨天在街上,听说,听说,被抓了。你说,人家找上门来,我也没办法。”
“哈哈,”李之松仰头大笑道,“谷兄,你说你,真是糊涂,都进了庙,还拜错菩萨。”扬起手,指了指对面坐的两位国府重臣,说:“现在上海不就是他们的嘛,他们说一句话,可比我这个过气的李将军强。”谷维新见李之松这话意思,不知是嘲讽自己还是昔日的同袍,心里暗暗好笑,见他玩世不恭的模样,心想也许这也是一种大隐隐于市的本事。
听了谷维新吐露的实情,黄有尊却不吭声了。他把头歪向一边,瞧了眼蔡民声,见他也不做声,低头沉吟了会儿,叹了口气说:“谷兄,这事,我劝你,能不掺和就别掺和。”李之松权当没听到黄有尊的话,好奇地追问道:“谁啊,哪个世侄?”谷维新抿了抿嘴,说:“当年他爹救过我,这孩子,唉。我早骂过他了,不懂事,黄鱼脑子,跟着人家瞎胡闹。但,现在,总要有个办法。”听到这里,李之松坐直了身子,问道:“你说的,可是那起拳祸?那个人?”谷维新点点头。李之松对黄有尊说:“你看看有什么人要打点打点的?”黄有尊沉吟良久,叹了口气说了句“难办”。忽又问:“谷兄,难不成你也是?”后面三个字,黄有尊没有说出口,但在座的人都知道他的意思,谷维新冷笑了一声说:“多年不见,黄兄倒是有大胆怀疑的精神了。”蔡民声清了清喉咙,插嘴道:“黄兄又瞎操心了。谷兄,你别放心上。我们呀都是闲人一个,来和老朋友叙叙旧。你也是老同盟会会员了,现在是清党的关键时刻。只能……”
“报告!”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响声打断了蔡委员的话,所有人都诧异地回头望着客厅门口,只见一个精瘦的年轻人站在门口,身后跟着慌张失措的门房。李之松见来人穿着淡蓝色的军装,盒子枪明晃晃地挂在腰间,目不斜视地往里走来。
李之松心中陡然升起了无名的怒火。那么多年,还没有人敢如此张狂地拿着枪冲进他家。可见蔡和黄两人像是认识此人,也不便当场发怒。他冷冷地挥了下手,示意门房退下,倨傲地歪着头斜着眼睛看着来人。只见来人毕恭毕敬地对在座的人立正敬礼,正对蔡民声和黄有尊说:“黄主席,蔡委员,蒋总司令请两位速归,有要事商议。”又转而面对主座的李之松,敬了个礼说:“李将军,蒋总司令稍后会专程来拜会您。”李之松装作没有听到之前的话,漠然地坐在沙发上,岿然不动。
谷维新望着眼前的年轻人,见他肤色黝黑,但眉目清秀,颇为英武,脸也刮得干净,脚上的靴子像是新擦的。他定睛看了那人几眼,似乎像是在哪里见过,可他转念又笑话起自己:哪里认得现在当兵的年轻人,即使是当年巡警学堂的学生,那也都已过而立之年了吧。
黄有尊见李之松如此冷淡,忙介绍说:“之松,这位是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情报科股长罗文德。”李之松像没听到似的,眼皮都没抬一下,侧身拿起了边桌上的茶杯。
谷维新瞪大了眼睛,他不敢相信这个明晃晃佩着枪进来的人,竟然就是董叔叔一直念叨的小少爷,罗玉甫的儿子。黄有尊见坐在一旁的谷维新发呆,生怕冷落了这位老朋友,忙介绍说:“文德啊,给你介绍一下,你可别小看这位教书先生,他可是当年和我们一起刺杀摄政王的革命英雄。”
“谷先生,您好!家母时常提起您和董叔叔。”还没等黄有尊说完,罗文德已走到谷维新面前,伸出了右手。
“啊呀,啊呀,你们原来认识啊。”黄有尊惊叹道。谷维新缓缓地起身,茫然地伸出右手。眼神却停在了他的一身戎装上,心中纵有千言万语,一时之间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八十
阳光被梧桐树叶分割成一片片不规则的影子洒在柏油路上、车顶上,谷维新好奇地看着两边急速倒退的林荫道和煤气路灯。为了最后的一丝体面,他努力掩饰着自己初次坐轿车的窘态,眼神却不自觉地上下左右环顾。端坐在他身旁的李之松见谷维新左右张望的模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说你,怎么成了个教书匠,还不如,啊,像黄兄那样,一官半职总有的,再不济像蔡翰林,混个吃白饭的委员当当,也不错的。”
车子的反光镜上映出两人的影像,镜中的中年人早已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谷维新连连摆手道:“意兴阑珊,别提了。”李之松见谷维新虽衣着朴素,但眉宇间仍有英气,反观自己更像是个富态的商人,哪里有当年李将军的模样,不自觉地摸了摸脸颊。
“老黄,绕去苏州路!”李之松突发话。司机不发一言,抬头看了一下后视镜里的老爷。谷维新诧异地扭头看着李之松,见他神秘地笑了笑,扬了扬眉毛说:“去见识见识,看看黄兄他们能有什么雷霆手段去清党。”李之松见谷维新欲言又止,低声耳语:“你不晓得,他们老早就来了,一直躲在龙华的指挥部里,商量着清党呢。我们也去看看他们有多大的本事嘛。”
李之松本想送谷维新去董家,顺便兜兜风,散一散之前的闲气。轿车驶过赛马场,沿着西藏路一路往北去。还没过苏州河上的新垃圾桥,车窗前的景象陡然发生了变化,让车里的三人不敢置信自己身处的是上海。每个街口都有手持短棍的人逡巡四顾,敞开着的罩衫掩盖着腰间凸起的短枪。过往的行人和车夫都自觉地低头快步走过,唯恐避之不及。
李之松鄙夷地说:“打扮得倒像做工的,但这副架势,呵呵,不就是放哨的嘛。”谷维新早已收敛起他的好奇心,不屑地说:“怎么用起了地痞流氓?”
车外不远处传来一声声呵斥声打断了两人的对话。司机老黄放慢了车速。
“喂,侬只瘪三,覅动!做什么的?”
“上工去。”
“现在几点啊,上什么工!包里厢是什么?老实点!”
“做中班。”
“少啰嗦,侬包拿来!”
短衫人截住了一位手挽布包的年轻人。李之松在车里看得真切,轻蔑地说:“鬼鬼祟祟的,戒严就戒严,这种当街查问,像什么样!”
轿车缓缓地转向宝兴路,右前方的一排沿街店铺后方,乌云般的浓烟不断地升腾起来,烟气刺鼻的味道弥散在整个路口,司机老黄急忙把车停在路边,说:“老爷,前面烧起来了。过不去了。”
“掉个头,去后面瞧瞧。”李之松命令道。谷维新不知这位寓公今天怎么那么好兴致,想着事情也没办成,只能暂且陪他散散心。
轿车还没驶入后巷,只见陆续有三五个人被缚着押了出来,像一根草绳上绑的几只无法动弹的螃蟹似的,拎着这串螃蟹的人与街口逡巡的人一个打扮。“轰”的一声,一块招牌被扔了出来,“平民日报社”几个字无力地歪斜在地上。
李之松问:“怎么还放火烧报馆了?这是什么报纸?没听说过。”老黄说:“听说做工的有自己的识字学校,自己办报纸。”谷维新叹息道:“抓人封铺子,怎么还放火了?救火会的车子怎么还不来啊?”老黄说:“谷老爷,这里是闸北,救火会出水可是老价钿的。”
团团浓烟已包裹住了整栋楼,烈焰随之张牙舞爪地肆虐着,人们惊呼着四散逃跑,可路口的那些人并不为之所动,他们似乎另有目标。“放火烧房子,手段太卑劣,”李之松忿忿地说,“这种木头房子,火烧连营呀。可怜了周围的老百姓。”
“哔……”一阵刺耳的口哨声淹没了李之松的声音。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听到这一声号令,街口的短衫人像静候猎物多时的野兽猛地从各个角落窜了出来,他们狂奔的身影从车子旁擦过,吓得老黄狠狠地踩住了刹车。巨大的惯性让车内两人的身子不自觉地往前冲了一下。谷维新叹道:“啊哟,怎么这样呀,人性命也要被吓出来了。”
“砰!”
不远处的枪声又再次震慑住了所有人,旋即而来的尖叫和孩童的啼哭,让嘈杂纷乱的街道更平添了一丝恐惧和凄苦。谷维新见李之松的手微微发颤,自己的心也扑通扑通乱跳,毕竟快十多年没有如此近距离地听到枪声了。李之松气愤地说:“这是在干什么?都敢这样在大街上乱来了。老黄,快转回去,送谷先生去董家。”
李之松心急火燎地嚷着,抬头正看见后视镜中的自己,震惊、惶恐之色竟然毫不掩饰地流露在脸上。他不想多看一眼。车窗上,树影跟着汽车飞驰的节拍快速流转,映在窗玻璃反射出的人影上。李之松对视着自己影像里的眼睛,惊惧、疑惑,转而愤怒、后悔。他懊恼自己当年为何不敢背水一战,不和他们争个高下,为了所谓的“和平”和“戎马半生,李将军何不安享太平”的鬼话,竟做起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寓公。如今,真有人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满大街抓人、开枪,而此等荒唐透顶的行径竟是他曾经的革命同志干出来的。
回程的路上,两人相顾无言,谷维新心里无比焦虑:到现在都不知道仲鸣人在哪里,会不会就和刚才的那些人一样被绑走了?还是,被打死了?去董家也没有用,看这架势,哪里会放人。这可怎么是好,还不如直接再去找黄兄。可总不见得直接去他们的指挥部吧,真是上天入地都没有门啊。
“之松,仲鸣这事情,”谷维新不得不再次提起,“你说怎么办呢?”
李之松沉默了良久,说:“算了,你别管了。刚才你又不是没看到,我现在也只能去找巡捕房,可租界哪里管得了这些。你去跟董老爷说一声算了。对了,那个来传话的罗文德是什么人?他不是说要来探望你嘛?现在上海,哼,不就他们说了算嘛。”最后这句听着真酸,酸中带着苦涩。
谷维新诧异地扭头看了眼李之松,他都没有听到什么探望的话,忙说:“哦,是嘛,你说罗文德,就是罗教官的儿子呀!”
“难怪呢,总觉得哪里见过,像什么人,”李之松半晌又冒出了一声感慨,“呵,有趣。他的儿子!你知道这个北伐军蒋总司令是谁?”还没等谷维新开口,李之松就自问自答起来,冷笑着说:“当年不过是那短命鬼陈英士的参谋。罗玉甫的儿子给陈英士的参谋做什么股长,哈哈哈,真是可笑。”
谷维新对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陈英士印象颇深,他淡淡地说:“也是个能人。”谷维新内心总隐隐觉得罗教官遇刺与陈英士有种说不上来的关联。每当午夜梦回,他回忆起自己夜晚追凶的场景时,都坚信凶手绝非普通的土匪流氓,刺杀一定是军中人所为,开枪极其果断,瞄准也不差,而且枪枪致命。
“之松,罗教官当年,你觉得是谁做的?”谷维新的这一问倒让李之松沉默了,旧事重提总难免让人伤神。李之松心想:如果罗教官还活着,我们一定能干出点名堂,天下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不堪,可是,一切都不可能了。他压低着声音说:“就是陈干的,人都死了,也别谈了。”
轿车稳稳地停在了董家的弄堂口,谷维新下车后,脚上犹如绑着千斤重担,一步一步地挪到了董家门口。门敞开着,董仲月一眼就看到了他,嚷着:“姆妈,姆妈,爷叔来了。”
金氏听到女儿的呼唤,哗啦一声拉开了客堂间的门,迎了出来。谷维新跨进天井,还没说话,金氏就笑盈盈地说:“谷先生,老爷今天气色好了点,刚才起身喝了点粥。现在又睡下了。您里面坐。”又像想起了什么,放慢脚步,低声说:“怪了,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仲鸣两口子都还没回来,急死人了。”
谷维新一时不敢说出真相,灵机一动,说:“小嫂子,他们,他们昨晚到我家里来玩,没事的。”金氏听了如释重负,唠叨着:“啊哟,还好还好,这两个人,真是,也不是我说他们,心野掉了,小毛头也不管。你看看,这一大家子都丢给我。”谷维新敷衍着安慰了几句,刚跨进客堂间的门,却见穿着便装的罗文德坐在客堂间里。
金氏紧跟着跨进房间说:“谷先生,这位是罗少爷,来看老爷,已经坐了一歇。我都和他聊了好一会儿了。”
罗文德起身,欠了欠身子,谦恭地说:“董太太,您客气了,耽误您太多时间了。”又面向谷维新,伸出右手,恭敬地说:“谷先生,您好!家母时常提起您。”同样的话同一天听了两遍,还出自同一人之口,谷维新哑然失笑。
两人坐定,闲聊了几句,谷维新见金氏离开,心想:他应该已知道仲鸣是董叔叔抚养长大的,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还不如直截了当点,先把人救出来再说。便说:“文德,你都那么大了。董叔叔也一大把年纪了,他是一心一意为了这个洋货铺,仲鸣这孩子,也是一直在店里忙进忙出的。”
罗文德望着对面的谷维新,这位是他从小就听母亲提起过的叔叔、他父亲的爱徒、曾经的革命英雄,至于董二爷,母亲总说在分家时这一房只分得这间铺子,董家二爷是一心一意帮着父亲,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私家生意。可是生意、老交情和形象模糊的父亲,在母亲常年的唠叨中反而成了罗文德心中的一道坎,他极不乐意有人提起旧事,也看不上只有两开间门面的洋货铺,不,杂货铺。上军校、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成了他唯一能与家道中落的家族撇清关系的方法。如今,他快要实现了,可还有人要提起旧事。
罗文德听罢,礼节性地点点头,并不接话。谷维新无可奈何,往门外看了眼,见金氏还没来,便说:“文德,仲鸣他,他昨晚,你能不能帮忙。”话轻得像蚊子叫,可房间里就两个人,自然是听得真切。罗文德说:“上午,黄主席已经提起过。可是昨日被捕者,有上千人,一律都押在总指挥部等着讯办呢,如果董先生没什么问题的话,自然会放出来的。”
在谷维新的耳朵里,如此冠冕堂皇的话出自罗玉甫儿子的嘴里,他很失望,不过也算意料之中,他无奈地摇摇头,说:“他一直在店里帮忙,也算是店里的二掌柜,他能有什么事情。”罗文德收起了笑脸,严肃地说:“谷先生,有没有事情,那还要讯问过才知道。抓的都是匪首,他到底是什么人,你我哪里能知道呢?”谷维新一时不知该如何和这位新晋官僚说话,只能拱手道:“罗先生好本事。今天下午,鄙人同李将军在路上,撞见贵党当街开枪、焚毁报社,此种行径,想当年连清政府,连孙传芳都干不出来的。”
罗文德瞪圆了眼睛盯着谷维新,像受到了极大的诋毁,提高了几分声调说:“我们抓的都是匪首,哪里会焚烧报馆,即便是当街抓人,那也是负隅顽抗的匪类。”谷维新长叹了一声,从窗棂中瞥见金氏抱着董继林进来,也不再言语。
“来来来,叫人,”金氏抱着孩子,指着谷维新说,“叫叔公。”董继林两岁还不到,见客堂间里两个高大的人影,搂着金氏的脖子,嘴里喃喃着“阿奶”,缩着不敢说话。金氏边哄孩子边对谷维新埋怨道:“小毛头醒了,之前又闹了一阵。仲鸣和小琴怎么还不回来,他们俩小孩子都不要了呀。”谷维新心头一惊,可罗文德倒像没事人似的,笑盈盈地问:“小琴是仲鸣的太太呀,她怎么也不在家?”谷维新生怕金氏话太多,忙打岔道:“董叔叔是不是醒了,我们去看看吧。”
金水隐约听到客堂间里有声响,似醒非醒之间,见有人开门进来,他睁开眼,见到谷维新后面跟着一个人,朦胧间像是罗玉甫。他恍惚间以为罗老爷要带他走,惊恐地张大了嘴巴,可又听着有声响,像是他女人说的话:“老爷,您醒了啊,罗少爷刚回来,就来看你了。”听了这话,又见到小继林,金水绷紧的神经这才放松下来,像是重新活了过来似的,欣喜地咧开嘴笑着。董继林见到爷爷倒很亲热,急着要挣脱金氏的怀抱,嘴里唤着“阿爷阿爷”,要去金水的身边。金水见到孙子自然欢喜,可多年未见罗少爷,他总还有些许拘束,拱手道:“少爷,我最近总是起不来,感谢您还来看我。真是,让您见笑了。”
罗文德的目光被虎头虎脑的小继林吸引着,肉嘟嘟的小身躯扑向爷爷的模样更让他心生羡慕。他的童年没有父亲、没有爷爷,只有哭哭啼啼的母亲和冷言冷语的亲戚。罗文德略带感慨地说:“董二爷,您身体可好?家母还问候您呢。”金水尝试着自行支起身子,激动地说:“谢谢太太记挂。唉,我这副老骨头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现在店里,生意也不如往常,开不了几天又罢工游行了,生意难做啊。”罗文德并不关心生意,见金水这样年迈却对他这个年轻人如此谦恭,忙安慰道:“您费心了,生意好一阵坏一阵也是常有的,不打紧。您身体保重。”
谷维新见金水颤抖着嘴唇,说不上话,忙上前抚了抚他的背说:“爷叔,慢慢来,不要急,缓缓,喝口水。”小继林趴在床上,一刻都不消停,昂起头东看看西瞧瞧,见罗文德耷在床沿的衣袖是新鲜玩意儿,试图伸手去抓,一个重心不稳,头一股脑地从床上冲了下去。罗文德的目光在金水和孩子身上游移,见孩子跌下床,一个跨步,一伸手,稳稳地接住了孩子。
小继林被一刹那的失重吓得伏在罗文德的肩头哇哇大哭。柔软温暖的小身体在他臂弯中无助地大声啼哭,从心底油然而生的温情让罗文德情不自禁地生出爱怜,将孩子搂在怀中左右轻微摇晃。金水看罗少爷第一次来,就如此亲和,又生怕孩子打扰了他,忙说:“小孩子不懂事,罗少爷不要介意。”罗文德笑着说:“没事没事,我倒挺喜欢这孩子的。他叫?”金水道:“继林,这是仲鸣的孩子,少爷。”说起这个,金水心中想着要把店铺给仲鸣接管,眼神往外张望,心想着此时侄儿能进来那是最好的了。谷维新忙安慰道:“仲鸣在我那儿,还没回呢。”说完,他抬眼瞧了眼罗文德。金水尝试着坐直身子,可还是失败了,他鼓足勇气,哀求道:“少爷,我想跟您说,我老了,店铺以后,仲鸣会打理好的,他从小就跟着我,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跟着罗老爷是忠心耿耿,我永远都记得是罗老太爷救了我哥……”
上一辈的故事罗文德听过很多次了,可这次听起来却特别新奇,这位见素未谋面的老掌柜说得如此诚挚和详细,甚至琐碎,心中对父亲倒多了一分亲切。母亲口中的父亲是伟大的,冰冷的,就如同家中的牌位和墙上的夫子像那般,儿时畏惧,长大后又心生厌弃。
罗文德把孩子稳稳地放在床上,爽快地说:“董二爷,您放心,店铺的事情,家母吩咐了,您做主就行。”金水忙不迭地道谢,脸上的褶皱顿时都舒展开了。罗文德倒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情,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眼神从未离开过小继林。这孩子有一双透亮乌黑的大眼睛,像一汪清泉,透着晶莹的光芒,没有心机,没有忧愁,那是他从未见过的纯真。
出了董家,罗文德脸上还挂着笑容,想到母亲时常念叨的往事,又回头望了眼那条狭长的里弄。瞧见谷维新在他身后,他放慢脚步,待走出弄堂口时,罗文德开口说:“谷先生,我也只能打听打听,但是,您知道,如果他真是……我也无能为力了。”谷维新大喜过望,说:“那拜托了,你也知道他们家,董叔叔也不容易,仲鸣这孩子就是个看店的,怎么会呢。”
八十一
谷维新拖着疲惫的身子推开家门,他一路寻思着怎么和陶小琴解释,反复思量,还是不要多说。可刚进家门,就听见孟寅和女儿淑玲你追我赶的打闹声,就像家中并没有客人似的。秀英已经收拾好了碗筷,见他回来,对他眨了眨眼,谷维新心知又出变故,心情瞬间烦躁起来。奔波了一天,最后还是生出了些事端。
他随意吃了几口饭,回到卧室,径直瘫坐在藤绞椅上。待他闭目休息了片刻后,环顾四周,早上的痕迹都已收拾干净,桌上倒多了一张纸条,那是陶小琴留下的,上面只有一句话:“爷叔,我不(能)留在这,等(继)林长大了,告知他。琴”
谷维新把这张纸甩在了桌子上,脱口而出:“莫名其妙!”他打了个哈欠,奔波一天的他只求清静片刻。不知过了多久,他清醒了,见房里的灯已经点亮了,窗外全黑了,秀英靠在床边打着毛衣。
见丈夫醒了,秀英说:“她下午自己走了。小孩子都没见到。”谷维新不作声,想着仲鸣没有下落,陶小琴却自己跑了,恼怒地说:“这算什么?她到底什么意思?就扔下仲鸣和小毛头不管了?”秀英叹了口气说:“我也留不住她,问她去哪里,她也不说,只说不能留在这里,怕连累我们。”谷维新幽幽地说了句:“反正现在也就这样了,随他们去吧。”秀英听丈夫这么一说,感觉倒是事情有眉目了,问:“李之松倒还是有点门路呀?”谷维新摇摇头,说:“哪里,唉,说来话长。明天说吧,太晚了。”
“啪啪啪”几声极为蛮横的拍门声在寂静的里弄里显得极为不寻常,谷维新警觉地从椅子上直起身子,哗啦一声拉开房门,跨着两三节台阶跑下楼,一把握住门栓,阻止儿子恒明去开门。听见里面有动静,门外又传来几声敲门声。
谷维新站在天井里高声问:“谁啊,这么晚。”门外的人喊道:“开门,快开门,巡捕房。”谷维新心想:这可是奇怪了,巡捕房大晚上的来这里做什么?可巡捕房来了,他也不敢不开门,转身挥了挥手,招呼秀英带着几个孩子回房里。他缓缓地抽出门栓,打开门。
两位华捕颐指气使地走了进来,跟在他们身后的竟然又是罗文德。谷维新冷笑道:“罗先生,幸会啊。”罗文德阴沉着脸问:“陶小琴呢?”谷维新猜到了来意的大半,叹了口气说:“走了,我也想知道去哪里了。”
罗文德瞧了谷维新一眼,刚说了一声“搜”,谷维新张开手挡在他们面前,对着他吼道:“这里什么地方,你一个广州政府当兵的,凭什么进租界?”他瞪着两位华捕呵斥道:“你们凭什么允许这个人进租界搜查?”这两个华捕本就心虚,被这一问,互相看了眼,说:“我们收到情报,有人非法闯入民宅,要来查问一下。”谷维新指着罗文德说:“是呀,非法闯入的不就是他。”罗文德上前了几步,凑到谷维新跟前,低声说:“谷先生,你今天不把陶小琴交出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谷维新见他没多久的工夫又判若两人,气愤地说:“跟你说过了,人不在我这里,你这小子,好样的,带着人来我这儿搜了。”

两位华捕算看明白了,这两人原来是认识的,自己原本就是收了钱来撑撑场面的,犯不着掺和他们的事情,互相使了个眼色后,悄悄退到了一边。罗文德心知进入租界抓人本来就越界,也不敢太嚣张,换了个商量的口气说:“谷先生,我们敞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有情报显示,陶小琴有重大嫌疑,你还是把她交出来吧。”谷维新没好气地说:“跟你说了,她不在这里。”罗文德又凑到了谷维新面前,几近耳语道:“谷叔叔,我能进来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也不为难你,你今天不给我看一圈,大家都很难看。”谷维新见罗文德说话时手扶着腰,腰间鼓起一块硬疙瘩,心知无论如何是不能硬来,见他给了个台阶,只能说:“就你一个人。”罗文德点头默许。
来到卧室,罗文德见桌上的一摞书,都是些古文,随手拿起本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见书页中零星插着书签,微微一笑,放下了书。桌角的一张毛边的纸条吸引了他,罗文德用余光偷偷瞄了眼谷维新,见他僵硬着表情甚是紧张。
罗文德看了眼上面的字,思量了片刻,默不作声地把纸条揉成团,揣进了口袋。谷维新的心已提到了嗓子眼,心想真到了难以收拾的局面,最多跟他们走一趟,谅他们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下楼后,罗文德看了眼谷维新,冷冷地说:“谷先生,你可当心点。包庇匪类,可是要坐牢的。”谷维新还没有从应激的状态中缓过来,大笑了一声,斥道:“坐牢?小子,我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今天看在,看在,看在罗老师的分上,不和你计较。你,你别太过分了!”谷维新怒视着罗文德,双手握紧了拳头,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他浑身甚至都微微颤抖起来,说到“罗老师”时,他的心一阵阵揪紧。
罗文德不敢正视谷维新的眼睛,怕被对方看穿自己的纠结和犹豫,他招呼两名华捕摔门而去,似乎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两扇门板上。谷维新呆立着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听见轿车发动的声响后,他才稍许放松了点。坐在车里的罗文德揉了揉酸楚的眼睛,望着星光寥落的夜空,无奈地轻声叹息了一声,他也不曾预料到今天会以这种方式与父亲的故旧相逢,幻想中把酒言欢的场面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他失望地垂下了头。
罗文德的手摸到了口袋里的这团纸,“陶小琴是抓捕妇女委员杨之华的唯一线索,今天晚上一定要动手!”这是出发前上司下的死命令,他无法违抗。他不曾想到前敌指挥部门口架设的机枪真的会向手无寸铁的人开火,“清党关系到党国存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句话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心头。“为了统一,为了党国,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值得的!”罗文德喃喃自语着。他的拳头里攥着这张纸条,可该如何报告抓捕失败,他还没有想好。
就在这一夜,金水孤零零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罗文德出面为“董淦先生”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这个扛麻袋、跑单帮,曾被称为“金水”的年轻人,终于实现了自己成为掌柜、被人尊称为“董先生”的梦想。遗憾的是等不到他一手带大,视如己出的董仲鸣回来见最后一面。没有人知道董仲鸣在哪里,罗文德也找寻过,即便是电报发到南京第一监狱,依旧音讯全无。后续如何,且看下期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