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人傅元峰说一场“人话”
2022-07-14刘肖瑶
刘肖瑶

“流行词可能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进入一个稳定的‘公约过程’,在这之后,一个词就被装进了时代的词典。”
“但汉语的生命力恰恰是超出词典、在经验之外的,是从词典中走出来,又走回个体的过程。”
因此,傅元峰并不担心。
与学者对话,总是担心表述偏差,担心冒犯某些学派的自有边界。但傅元峰似乎不会给人产生这种担忧的机会,他会压制你。
一些“提纲”之外、“非主流”的观点和理论,傅元峰会在听者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忽然讲出来,不顾虑后果,叫提问者哑在电话那头。
这位让人猝不及防的学者—傅元峰,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南大学生称为“文字刺客”,著有《景象的困厄》《寻找当代汉诗的矿脉》等学术论作—这些可以从网上找到的信息,用傅元峰的话来说,属于信息的“工具性”部分,是“档案”和“百度百科”里乏味的东西。
而汉语和信息的生命力,藏在个体的、私人的、无法复制的表达里。
在采访开始前,我向南大的朋友打听了这位文学院的傅老师。有人说傅老师的“考试难得变态”,更多人则评论他“口语和书面语一样庄重、优美、简洁,像是凭空开放的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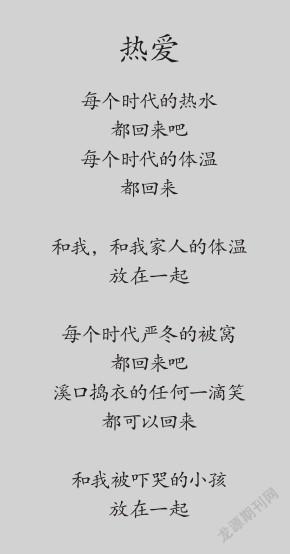
采訪结束后,我对后者的评价深以为然。傅元峰说话就像写诗,他的口语库里储藏着大量精准的词汇,辅佐观念自然流露,我不得不反复同他确认词语的字形,等到录音整理出来,就像是已经修缮过的书面表达。
前不久,在傅老师的一次网课上,有学生忘了关麦,与室友大声讨论:“你们看看,这傅元峰说的是人话吗?”
恰巧,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就是以“人话”开头的。
今年年中,一篇题为《中文已死》的文章在社交平台传播甚广。文章列举了当今盛行于社会的各式“不好好说话”的流行词汇,以证“中文”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污染和危机。
对于这种唱衰,附和与反调皆有,而在一片争议的喧嚣与嘈杂中,一本悄无声息出版的诗集《月亮以各种方式升起》吸引了我。准确地说,吸引我的是前言的一句话:“汉语在工具性盛行的年代依靠孤立的个体显现其美的本质。语言从来都不是一个集合体。从集合体出走的个体,调整其存在的精神格调并自愿成为汉语的安身之所。”
诗集的作者,就是“70后”文青傅元峰。
此前,他出版的一些文论、研究著作,大多被他“扔进了垃圾堆或塞进了储物室”,只有这一本诗集他爱不释手,即便它对一名大学教授评职称等无甚益处,甚至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
不止一个读书人需要这个“无用”的东西,每一个活在现代社会的具体的人,孩童、工作者、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需要。
傅元峰1972年出生于山东兰陵,十年前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后在文学院研究中文和文学,回家关起门来,却独爱写诗。
得承认,在今天,诗,对于公共社会的表达是小众,甚至被部分人视为空中楼阁。
《月亮以各种方式升起》是一位朋友主动提出要帮傅元峰出版的,一切发生得有些莽撞。在此之前,写诗一直作为他的一项个人活动,长久而私密地进行着。
诗写了十余年,傅元峰一度乐于使用“烟霞染月”这种词—好像是美的,但其实是套路化的,是“务虚”的青春抒情。而真正具有美感的写诗,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的否定”,是“成为自我的对立面”。
当“身边的事物都变得没有了名字,耳边的声音都是陌生的”,而后获得一种类似灵魂出窍的感觉,写诗,是为了重新捕获个体生活,为了给纯洁的自我表达“招魂”。
然而,对于我提出的“‘工具性’的反面是诗性”,傅元峰不以为然:“工具性包含了一种对于诗的拒绝,但人们将一些不属于自己表达经验里的事物笼统地称为‘诗性’,本身也是一种工具性的体现。”
在社会生活中,汉语的“工具性”主要体现为“信息过载”,“语言为了绝对的、完全的表意存在”,社会没有“小说”,只有“新闻”。
但真正的语言,应该包含一份孤立的自我表达。“有时候你甚至觉得不是像你自己说的话,这就是美学的、诗学的那部分功能。”傅元峰认为,这部分带来了语言的生气,让汉语成为“工艺品”而非“工匠品”。
此外,作为一名教育从业者、基础语文教科书编写参与者,傅元峰更关注学院里汉语言教育的“工具性”。
它体现为一种对技术性语言、历史学教育的过度倚重,从中小学语文课堂到大学的文学院,都爱强调罗列知识、记背,讲求历史学的物尽其用,但“在文学院,当你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时候,你的学问是最好的”。
比如,大学课堂对《世说新语》的讲授会强调故事里的人物、事件、线索,但在傅元峰看来,支撑《世说新语》艺术价值的恰恰是一种无形的“情态”,是文本里传递出来的“原汁原味的、未尽的日常生活”。他担心,绝对的知识性压制会拒绝美学,甚至拒绝生命。
因此,人们需要诗歌,需要文学,它们启自理性,诞生惊奇,超出文字之外,又最终回到文字上,且它们不受文化水平限制,一个文盲和一个三岁孩子一样可以写诗。
这是傅元峰的亲身经历。女儿三岁那年,有一天在家中阳台上,小丫头忽然对着盆栽冒出一句:“事实上,每个人都拿着花。”
一句无厘头的童呓触发了傅元峰,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悄然产生了,他随后隐秘地抒情:“我在语言中有了贪念,生动起来。”
还有一次,幼儿园老师教了“奶奶”“外婆”等亲属的称呼,女儿回到家后,看着奶奶的遗像,对傅元峰突兀道:“傅元峰,你妈给你写信了,让你多喝水。”这句话也成为了傅元峰的一行诗。
女儿的语言天赋就像一只精灵那样,游走于尚不设规则的世界,激活了一个成年人对熟悉世界的陌生感。
生活的神性,或许恰恰就藏在那些童年或暮年的呓语里,藏在那些人们平常不重视、看不起的罅隙里。
“中文已死”—这四个字简直老生常谈,年复一年,成为一种直指潮流语言的现代性唱衰。
对此,傅元峰只想用两个词评价:骇人听闻、哗众取宠。
平时在生活中看到“笑不活了”“绝绝子”“咱就是说”“yyds”,他不会摆出一个中年文学卫道士的姿态,而是观望,然后接纳。“每个人都有自由言说的权利,任何语言现象都是在语流当中自在形成,有它的合理性。”
不否认,一部分人呼吁警惕中文“濒死”,是一种从善意出发的危机意识,但傅元峰对中文的绝对信心,来源于汉字的“自在”和“忍受力”。
“汉字是一种很奇特的容器,携带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只要汉字在,汉语就形成了一个很难消除亚文化的区域。
”如何理解这种“亚文化区域”?比如,汉字在被文学化后会构成一个语篇语段文本,滋生出独特的有声力量,“如果遇到一个优秀的语言主体,它很快就可以复活”。
因此,“你可以把一本书损毁,可以进行一个写作和阅读的限制,但无论怎么样,汉字形成的亚文化区域实际上是很难被清除的”。
实际上,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词,不仅有形容词,也有名词,比如今天的“内卷”“996”“躺平”,比如上世纪末的“下海”“万元户”等,傅元峰蹚过它们,也见证着它们的批量复制与逐次消失,并得出结论:“词语的拼贴组合和流行方式都是社会的现状和思潮的一个言语的取样,是具有语言学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的。”
他曾经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流行网络词汇,比如“屌丝”,他认为这种词虽然携带了一些社会情緒,但对汉语的美有一种“降格”,有了一种污染。
如今,他的想法温和了许多。因为流行词不仅是一个名词、一个说法,同时也是一种信息传达。“它们实现了我们在(汉语表达)其他方面缺失的代偿,表达了一种默契,带来‘相视一笑’‘亲切感’‘熟悉感’,具有复杂的人类学研究价值。”
总之,“汉字就像一条生命力旺盛的大河”,在傅元峰看来,“可能会汇入污浊的支流,但它最终会澄澈回来”。
而真正值得担忧的,或许是当潮流词汇被更多人信手拈来,个体话语长时间被剔除于高效能的传播需求,逐渐会造成一种“自我话语结构”的消失。
当一个年轻人把自己的个性化表达都交给这些词语,看上去“他们有了自己的一个语言区域,有只有互相能听懂的潮流用语,几乎成为了一种方言,但本质上,他们还是被装填在一种‘可疑的恰当’中”。这也是一种去生活的、去个性的“自我迷失”。
2009年,傅元峰与诗人于坚在南京大学开了一场座谈会,叫“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现代化鼓励人们去过一种观念性的生活,文化、文学的神性被留在纸上,现实生活细节消失了。用傅元峰的话来说,是“被观念和意义的日常生活遮蔽与损毁了的语言的神性”,这是要不得的。
傅元峰补充道,随着互联网普及和传播方式的变化,潮流词汇的传播效率、拼贴组合的速率都在剧烈更新,逐渐可能会进入一个语言的“公约过程”,即一个说法被越来越多人使用,从小众到大众,最后被装入时代的词典。
但汉字的生命力,恰恰是超出词典以外的,是从词典中走出来,又走回个体的过程。在傅元峰看来,汉语之美是远离标准化词典的,是一个个体不可复制的声音、姿态,就像每一片树叶的不可复制。
真正的、有个性和自主意识的表达,就是要使用词典以外的,用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不属于经验里的事物”。
2016年,湖北女诗人余秀华凭借《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走红。傅元峰在朋友圈里读到了这首诗,读完第一遍,他立刻感受到一种撞击,“诗不错”。
不过,他不喜欢那篇文章的标题,将“脑瘫患者”“农妇”等标签都拼贴了进去,“强调了她的病痛”。
在傅元峰看来,余秀华的诗爱被人们谈及,根本上是因为她提供了一种“稍高于日常生活的、超越世俗性的美”,强调其生活境况形成的特殊性,不过是为了造成阅读反差,把诗人打造成“诗人商品”。
微信平台化后,公众号阅读成为国人阅读生活的重要形式,傅元峰曾在2017年一篇评论里谈“朋友圈阅读”的“文化延播效应”。
移动虚拟社区不再是简单的传播介质,而是具有了强烈的主体性,单向迎合或暗合偶然读者群阅读的惰性欲求,几乎不支持阅读中断以后才能发生的凝视和凝思时间,触发了艺术传播的变革,也是我们在争论“中文死不死”的今天,更值得警惕的。
现代生活充斥着碎片化的语义、影像,很繁复,但也很扁平。在高速运转的传播能耗当中,我们会警惕陷入某种“景观社会”,即一个人的生活被全面的表象支配,过量信息的无处不在,给孤立的现代人带来整合与统一的错觉。
如果一个人完完全全投入争论,投入了对概念、立场的争夺,它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心理问题,会让人陷入焦虑。傅元峰认为,这是一种对“人”的背弃。
“在对新闻的阅读中,人会形成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在旁观时产生了自己的情绪和表达欲望,偶尔也会参与讨论,甚至大声争辩;另一个自我则旁观‘自己’,不断撤离问题中心,将视域放长,看到更宏大的、外围的世界,达成一种对于世界和自我生存的重新确认。”
在傅元峰看来,无论是阅读新闻还是评论热点,创作或劳作,都得“允许更多经验之外的事物进入你的生命和生活”。
“哪怕看一个很熟悉的事物、很熟悉的人,也要尽量安静地停下来想一想、看一看,从普遍的潮流当中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应该待的地方”,在缓冲的片刻中,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有了“加载”和“内饰”。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对“经验”与“陌生”的距离进行拿捏与把控,正如我们开头所说的,需要对“工具性”与“诗性”进行平衡,对“自我”不断反复确认。读新闻如此,写作、教育亦如此。
从教十余年,目前傅元峰的学生以“00后”为主,他普遍感受到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局促的个性”:既是个性的,又被束缚着。
“他们普遍意识到,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个别的人,要保持自己的个性思维,不简单地认同家长老师;可能看起来与众不同,但本质上仍处于一种无头苍蝇的个性表达中,没有自己的判断力、思考力,没有风格。”
用傅元峰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技术化的个性”,个性的发展没有去向,思想的发展得不到交代,最终体现为“为了反抗而反抗、为了不同而不同”。
2019年夏天,一部院线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备受好评,傅元峰去看了那部电影,并觉得它恰好代表了“95后”“00后”年轻人那种“无处安放的个性”。
“哪吒是顽劣的、反叛的,但它最终被收束了,纳入了一个‘他者’的成长。反过来看哪吒的玩闹,发现就是一种很坏的玩闹,没有任何先锋价值,它不是‘文学’。”
“昔日顽童今何在?在我们的文化里,顽劣是需要被修改的”,因此,对于培养真正具有个性、具有思考力的审美,一代人还得继续跋山涉水。
至于当下能做的,可以从脚下的这一步开始。“不要陷入对知识霸权的迷恋,不必追求机械的博闻多识。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在泛滥的知识和经验中,你自己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