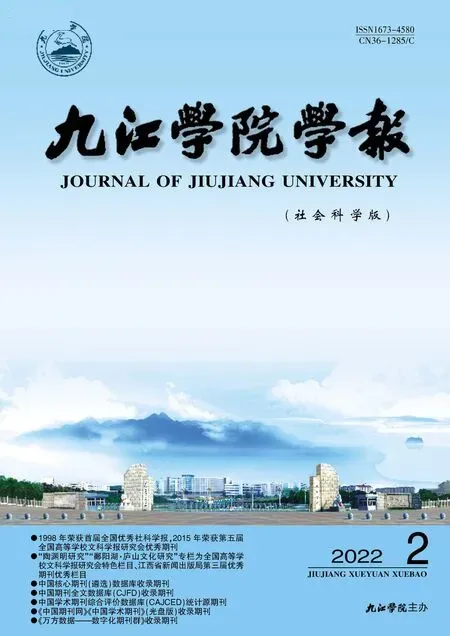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论宋元之际士人理想范式的生成
2022-07-09雍佳丽
雍佳丽 裘 江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隐逸或仕进的选择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文人心中,从《论语》之“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到苏轼之“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忘其君”[2],仕与隐相反相成且作为普遍存在的矛盾,在易代之际更为突出与特殊,宋元之交的士人此种矛盾心态尤为强烈。所谓“出处大节”,如何在保持士人气节的情况下消解仕隐矛盾,寻找精神寄托,便成了特定时代下群体的选择,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出”与“处”的仿效对象。
一、诸葛亮与陶渊明在宋元之际的并称现象
出仕与隐退向来作为士人的不同状态而存在,文人也在用来明志的诗文中寻找这两种不同行径的代言人,人们依照自己的需要去塑造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也就被赋予了特定意义,而进入文学乃至文化。宋末文人以诸葛亮与陶渊明作为自己“出”与“处”的典范与穷达观的代表,并频繁提及二人,于诗、词、文中将二人对照或并举。
元初虞集曾称:“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论者以为至当,信之不疑。”[3]“上配”指渊明功业不及孔明,事实上二人并提作为固定的搭配存在于宋元之交多位文人的笔下,最突出的例子是谢枋得。在谢枋得诗中,除“谁怜陶令分嘉饷”(《谢惠椒酱》其二)外,提到渊明时必以孔明相对,如“渊明岂但隐逸人,渊明素怀诸葛志”(《竹菊松扇四首》其二)、“靖节少陵能自解,孔明王猛使人悲”(《示儿》其二),而孔明未单独出现。与前人对渊明隐逸、孔明运筹帷幄形象刻画不同的是,谢诗着重于二人气节与“忠义”,以孔明与“贼”对立,又以渊明怀孔明志点出渊明之民族大节。谢枋得还取材于二人用以他人求字:“始渊明而终元亮,君子怜之。菊岂愿为隐逸哉?以靖节而隐,显之者亦靖节也。……孔明长笑隆中,时人皆以伏龙待之,宜以仲龙字。大丈夫生于乱世,消息盈亏,惟天所命。穷则晋处士,达则汉丞相。吾俯仰无愧怍矣。”[4]谢枋得还将自己对二人的追慕形诸于选本中,他以《文章轨范》为科举文章的范本,并在文中时有批注,选目中主要以唐、宋策论之文为主,皆条分理析。《前出师表》与《归去来辞》也被收录其中,并且是唯二非唐宋的文章。谢枋得未对这两篇文章作注,其学生王渊济洞察到这一点,于《跋》中谓“汉丞相、晋处士之大义清节,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会也”[5],谢枋得深意正是对二人“大义清节”的认可,以致选录其文供士人师法。谢枋得的言传身教,影响了许多后生,其学生魏天应亦为宋遗民,“吾翁铁脊文翁似,无愧渊明与孔明”(《和叠山先生韵》其一)以忠义为核心追求,以其师无愧于孔明、渊明为荣。以孔明、渊明为气节代表的观点在当时被广泛认同,宋末黄庚之“归来尚忆渊明菊,高卧谁知诸葛庐”(《孔明高卧图》)亦如是;文天祥有“世无徐庶不如卧,见到渊明便合归”(《宣州罢任再赠》),“孔明已负金刀志,元亮犹怜典午身”(《得儿女消息》)。文天祥与诸葛亮皆位至丞相而壮志难酬,一方面以孔明自比,昭示自己对收拾山河志向的辜负,另一方面则用“典午”表明自己对陶渊明归隐的向往;再有宋亡后隐居不仕的陈纪,其词曰“岁晚凄其诸葛恨,乾坤只可渊明酒”(《满江红·重九登增江凤台望崔清献故居》),皆是将诸葛亮与陶渊明并称为效仿对象,并突出二人的忠义与志节。
关于诸葛亮与陶渊明的联系与在诗文中的并称现象,可上溯至北宋黄庭坚的《宿旧彭泽怀陶令》,诗中认为陶渊明“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肮脏犹汉相”[6]。从黄庭坚开始,此诗认为渊明企慕孔明,并以未能恢复天下为憾,这便推出了诸葛亮、陶渊明两个本意都为出仕而结局不同的典范。从人品角度看,将诸葛亮和陶渊明设置为忠义与淡泊的结合,此诗双峰并崇,是为二人并称的滥觞。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没有掀起波澜,而在经历国家动荡的南宋被接受,诗人熊以宁有“肯荒元亮径,坚卧孔明庐”(《挽叔父二首》其一)之句,而与陆游、辛弃疾唱和的韩元吉之“元亮何妨慕孔明”(《病中放言五首》其五)亦是此意,将渊明视作仰慕孔明、希冀建功的人,至刘克庄称“千载英雄须冷笑,孔明回首学渊明”(《又真止堂一首》)虽反其语,将归隐视为孔明、渊明二人不得志时的无奈抉择,本质上仍用渊明效仿孔明之意。有宋一代,陶渊明不仕二朝的忠义思想得到了士人的强调,这恰与诸葛亮忠于蜀汉的思想是相通的。如果说把北宋作为二人并称的“奠基期”,那么至南宋则因韩元吉、刘克庄等人之诗则进入了“发展期”,而后又因宋遗民遇家国巨变,对诸葛亮与陶渊明的塑造与接受更进一步,故二人并称的理想范式定型于宋元之交。
二、“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范式的内涵及成因
诸葛亮与陶渊明的并称何以出现在宋并于宋末定型,关涉到二人形象在不同时期的塑造、接受与赵宋王朝偏安乃至灭亡的状态。
宋遗民在以诸葛亮与陶渊明并称外,还将二人设置为君子“出”与“处”的典范。宋亡几经征召而隐居不仕的于石有《述怀》诗:
孔明卧隆中,世事若不闻。草庐两三策,大义固已明。陶潜晋处士,束带耻屈身。浩然归去来,把酒惟长吟。潜鱼游深渊,好鸟鸣高林。是以古君子,出处各有心。[7]
于石认为诸葛亮与陶渊明是先人中的君子,这与谢枋得之“穷则晋处士,达则汉丞相”一致,将孔明与渊明的典范意义定位在二人对“出”与“处”的抉择。
抗元与不仕新朝外,保全自身的文人也将孔明与渊明并称为典范。戴表元晚年为稻粱谋而入仕元朝,心境以其诗概:“鲁女悲嗟起夜深,当年枉却泪沾襟。如今已免邻人笑,老大知无欲嫁心。”[8]在一生仕隐皆不遂意的境况中,孔明与渊明成为其精神寄托,《又坐隐辞》曰:“多金善贾,不如躬耕。……封侯万里,不如还乡。我观古来丈夫子,何用桑弧蓬矢射四方。苏秦生为六印役,主父死愿五鼎烹。不如诸葛草间谈管乐,陶潜醉里傲羲皇。”[9]戴表元认为苏秦、主父之纵横不足为模范,孔明与渊明之啸傲才值得效仿:虽于草野,所谈所念仍是出将入相之心。戴表元如何看待仕与隐,可审视其和陶诗:
贫贱如故旧,少壮即相依。中心不敢厌,但觉少光辉。向来乘时士,亦有能奋飞。一朝权势歇,欲退无所归。不如行其素,辛苦耐寒饥。人生系天运,何用发深悲。[10]
局势变幻而内心忧惧,并将人生归结为天运所命。戴表元对孔明与渊明形象的塑造与接受代表了宋元之际在抗元派外的另一种心态,面对新朝没有坚定的立场,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出与处,所以只能托志于孔明与渊明:穷时可隐,隐时也可不忘庙堂之事。
孔明与渊明并称且成为士人“出”与“处”的模范,就内因而言,在于思想情感方面。一方面,宋末文人认为二人的人品与行径正是古代士大夫的优秀典范,是儒家忠义之道的绝佳践行者与体现者;另一方面,诸葛亮与陶渊明的相似性也弥合了士人选择时的缺憾,如谢枋得,他将诸葛亮隆中之“伏龙”状视为天命下的隐,与陶渊明之隐无二,是“穷”时的选择,而诸葛亮入相则是天命使其“达”,二人最大的区别正在于“天命”。谢枋得认为陶渊明的“隐”正是为“仕”做准备,所谓“岂但隐逸人”“素怀诸葛志”即是如此。谢枋得曾亲身举兵抗元,后又拒蒙元朝廷征召并绝食而死,其抗元与绝食正践行了诸、陶二人所代表的穷达观的两面。陶渊明处于晋宋之际,诸葛亮立于三分天下的乱世,这都与家国巨变下宋末文人的境遇相似,而二人用不同的选择昭示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或是不书甲子,或是由躬耕南阳至位及丞相,这便在理想与现实的二重维度下为易代士人提供了范本。
就外因而言,在于偏安下“战”与“和”的宋代文化背景。一在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使诸葛亮与陶渊明的部分事迹被选择与典型化。从北方少数民族强权压制到宋朝彻底灭亡,疆土的缩小与北方异族的窥视使得宋朝不再有唐朝时大一统的国力与气象。而诸葛亮在宋代更有一层意蕴:北伐。即使是文官苏轼也有“西北望,射天狼”之语,诸葛亮之“北伐中原”正为宋代志士提供精神支撑,宋词“看木牛流马,恢复神州”(臧鲁子《满庭芳》)正是此意,姜夔也以“前身诸葛”赞辛弃疾之志在伐金。就诸葛亮的整个隐仕历程而言,卧于隆中可掌握军国大事,出仕后又鞠躬尽瘁、位极人臣,正是士人“穷达观”的最佳观照,故宋代士人抱有能似诸葛亮出草庐定乾坤之志;但有宋一代,毕竟以偏安为主,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用人政策下,在不可为之成为定局时,士人便或是效仿诸葛亮未出仕时隐于草庐,或是效仿陶渊明醉卧南山。二在于市井与书斋之间的文化互动对诸葛亮、陶渊明形象的塑造。文化方面,南宋时诸葛亮的忠义人格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而地位上升,又因诸葛亮所辅佐的蜀汉政权被认定为正统而得到当时社会的进一步认可;文学方面,如前所言,诸葛亮在宋代诗词中为志在“恢复神州”的代表,在话本中呈现出料事如神乃至“近于妖”的形象,市井与书斋间的诸葛亮形象相互融合,便呈现出一个能力与道德顶峰的悲剧人物形象。文化方面,陶渊明之“虽晋臣,未尝一食宋粟”(吴仁节《陶靖节先生年谱》)在宋朝被格外强调,又在论史方面被朱熹视为极重气节的典范;文学方面,陶渊明的松菊高节也在诗人诗文中多有咏唱,宋末,“陶渊明的精神情怀和行为方式深深地影响了特殊时代的士人群体。”[11]在朝或在野正是仕隐矛盾的具象体现,而宋代文人则在理学影响下,万物静观,以期至少能独善其身,而王朝覆灭之际,北伐恢复神州成了难以实现的愿望,宋末士人便转向诸葛亮之“卧龙”与陶渊明隐于南山的状态,以期保全自身气节。
总之,内忧外患的宋朝不复唐朝时国力强盛,宋代诗文中的诸葛亮与陶渊明形象也就随着时代需要而变化,在宋元之际的诸葛亮与陶渊明并称的诗文中,二人精神中“不仕二朝”的大义置于首位,二人无道而隐、有道则出的形象也被置于同一水平,诗人们将陶渊明之隐归结为没有诸葛亮的时机,又认为时运不济下诸葛亮不如陶渊明之归隐。此时二人并称,其为人处世中对儒家忠义的坚守与时运际会下的选择,正契合了宋元之际遗民诗人的内心需要。
三、“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范式的文化及文学意义
“出必孔明,处必渊明”在宋元之际文人的诗文中定型为一种人格理想范式,其意义在于三个方面:一,承接元前诸葛亮与陶渊明接受史;二,为宋元之际士人提供消解仕隐矛盾的手段;三,成为一种固有范式并影响了后世面对“出”与“处”两难的士人。
首先,“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范式构成了这一时期二人在各自的接受史上的关键一环,使得二人在文化史上的形象更为立体。就诸葛亮接受史而言,宋元之际士人渴望能有挽救山河颠倒局势的神人出现,对诸葛亮的这种崇拜也促使其形象在元话本中更具神异色彩,其神仙隐者的形象与“挥剑成河,撒豆成兵”的能力在民间深化、定型,直至进入小说中,为大众所接受。而就陶渊明接受史而言,陶渊明不仕二朝的行径被宋遗民放大并确立为士人在易代之际的模范准则。及至元初,遗民文人在忠义守节的情怀下因华夷之辨与社会地位、生存环境的窘迫彼此联系而寻求心理认同,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和陶诗呈现一定规模,对陶渊明人品的接受也甚于前朝,较陶渊明在之前淡泊隐士的扁平化形象更为丰富。元初文人陈旅《菊逸斋序》言:“然吾闻渊明中岁更字元亮者,慕诸葛孔明也。孔明与渊明出处不同,吾不知渊明所以慕孔明者何故?……盖尝思之,士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不于其迹而于其心物,非人而能与人同者不同乎?人而同乎,天惟其心之可以相感,则渊明何必不为孔明?”[12]此处陈旅直接将渊明视为孔明的追慕者,并指出“相感”之处,渊明即为孔明。元人刘岳申《张文先诗序》:“陶渊明本志不在子房、孔明下,而终身不遇汉髙皇、蜀昭烈。徒赋诗饮酒,时时微见其意。而托于放旷,任其真率,若多无所事者。”[13]则将陶渊明对诸葛亮辅佐蜀汉的追慕视为陶渊明忠义人格的投射。元初汉人征引渊明虽用其隐逸,而实际用其背后“为君谈笑净胡沙”的志向,因此二人并举时,常谓渊明有孔明之志。明清时期,士人已完全接受了忠义化的陶渊明,陶渊明隐于江州的面目也为其耻事二姓的儒家人格服务,施闰章“渊明仍纪晋”(《答叶蕃仙》其二)正是这种形象。直至清末,王先谦赞颂王夫之“恰比渊明题宋历,未防枋得作元民”(《题王船山先生书卷》),更是同时接受了谢枋得与他追慕的陶渊明。
其次,“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范式为宋元之际的士人提供了消融仕隐矛盾的办法,树立了模范目标。宋元之际仕与隐的矛盾到达了难以调和的地步,汉人入仕之难与易代之悲结合在一起。诸葛亮与陶渊明正以其“不仕二朝”的民族气节、穷达之时恰当的仕隐选择走进了士人的诗文中,构成了“出必孔明,处必渊明”的“仕隐”二元范式。事实上,陶渊明虽生于诸葛亮之后,但二人并称的范式以陶渊明为主角,将诸葛亮与陶渊明并称,是为将隐逸这一举动合法化的方法,将隐逸强化为爱国与报国的一种选择。陶渊明以隐逸终结一生,而诸葛亮的存在使得陶渊明的隐逸叙述更为完整,宋元之际的士人将二人并称,也正是想借此表明,隐逸并非单纯避世,而是一种守节的政治姿态,如谢枋得所言:“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庆全庵桃花》)在这种范式下,无论是对于坚定的抗元派还是选择边缘化的宋遗民,诸葛亮与陶渊明提供了一种进可仕、退可隐,既能坚持民族气节,留有报国余地,又能保全自身的处世模式,局势变幻下互转,这正符合宋元之际复杂形势下文人的穷达观。
最后,这种理想范式定型于宋元之际,也影响着后世仕隐两难或易代之际的士人。一元模范的崇拜容易使得士人在仕隐之间发生龃龉,“出必孔明,处必渊明”理想模式实际上是树立了二元典型模范,从而为消融“仕隐矛盾”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元末明初,胡奎有《题渊明抚松图》:“渊明与孔明,出处各有道。乃知归来辞,即是出师表。”[14]将渊明与孔明视作“出”与“处”的两种有道代表,这样的论调与观点几乎是宋元之际于石的再版。方孝孺有《立春偶题》:“万事悠悠白发生,强颜阅尽静中声。效忠无计归无路,深愧渊眀与孔眀。”[15]在报国无门且又归隐无路之际,方孝孺接受了谢枋得“无愧渊明与孔明”的隐喻,认为自己的处境是对渊明与孔明的辜负。而明人杨慎以“出必如孔明,处必如渊明”[16]对二人并举提出了明确的总结,后世士人又继续创作将二人并举的诗、文、绘画,更是对这种理想范式的进一步认同与演绎,明亡后,著名书画家、诗人陈洪绶更是挥笔画就《出处图》,以此劝好友周亮工能终止仕清,保全其最后的名节,此图以陶渊明与诸葛亮为核心,画中二人于松下对坐而谈,陶渊明一手抚无弦琴,一手向诸葛亮示意,而诸葛亮在陶渊明右方,身前有一案几,上置卷帙、纸笔等物,身旁盛有菊花,如图1:

图1 陈洪绶《出处图》
画像右侧卷首处有林宠楷书,林宠亦生于明,而入清不仕,其人颇有气节,其书曰“出则为孔明,处则为元亮”更是对“出必孔明,处必渊明”范式的认可,既是自己的志向,也是陈洪绶此图意义所在。卷尾,又有陈宠录诸葛亮《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与郭鼎京录陶渊明《归去来辞并序》,正与谢枋得《文章轨范》选目之“所深致意”相同。陈洪绶作此图的本意与林宠、郭鼎京题跋的结合,进一步深化了“出必孔明,处必渊明”的主题,也证明这一模式在明清之际的复兴。宋元与明清皆为易代,王朝更迭与民族政权的交替如出一辙,出与处之间的尖锐矛盾再度浮现,前人建构好的理想范式也就成了明遗民的最佳选择。
总之,黄庭坚看到了陶渊明对诸葛亮的企慕与二人之间的相似性、互补性,将二人并称,二人并称的现象在南宋被接受,到宋元之际定型,并被人们视为“出”与“处”的模范。一方面,宋人认为陶渊明有效仿诸葛亮之志,只是时运不济退而隐居,诸葛亮北伐的志向也代表了宋人的愿望;另一方面,二人忠义、正统的一面也在宋代被强调与确立,诸葛亮与陶渊明志向相同,只不过是不同时运下作出了不同抉择,但都没有违背“忠义”的本心。于是宋元之际在仕隐两难的状况下,士人纷纷将“出处有道”的诸葛亮与陶渊明视为理想前贤以消解仕隐矛盾,而“出必孔明,处必渊明”的范式也影响着后世面临着易代或仕隐无路的士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