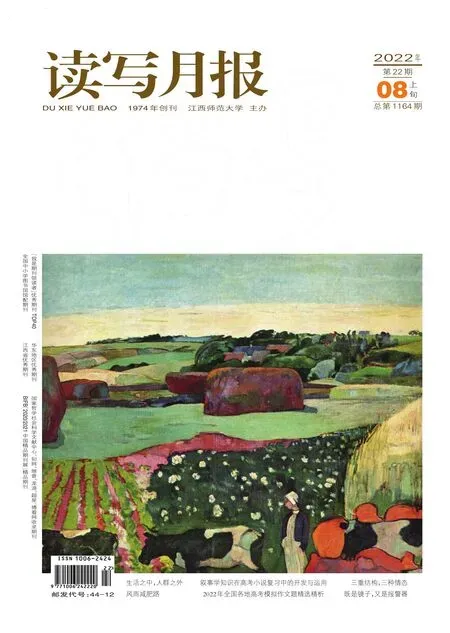生活之中,人群之外
——读王开岭作品有感
2022-07-06张婷
张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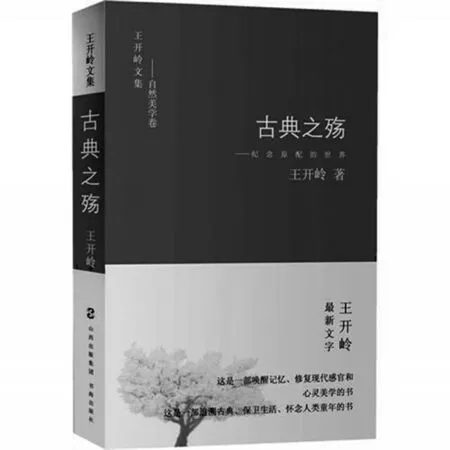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我觉得一个人活得诚恳,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王开岭便是如此。沉浸于生活之中,独立于人群之外,是我对王开岭作品的印象。
“生活”是什么?多赚点钱,吃点好的,穿点好的,买个大房子,再找个好点的伴侣……这些表面的相似是否足以涵盖生活本身?有时候,我们天真地以为生命在走向丰饶与饱满,殊不知一路走下去,一路在丢失:丢失童心,换取成熟;丢失单纯,换取生存手段;丢失幻想,换取实用技巧。我们就像一个懵懂的天使,“不断掏出衣兜里的宝石,去换取巫婆手中的玻璃球”。是的,我们舍本逐末却浑然不觉,我们把宝贵而庄严的一生活成了一份抄袭作业。
因此,为了让“生活”一词名副其实,我们必须留下点什么,尽量把“非生活”的东西剔除,以免当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未活过。正如王开岭在诗歌《不要以为这就是生活啊》中的疾呼:“不要让生活太容易了/不要以为这就是生活/不要以为你可以忘记/童年、诺言、十万个为什么/和英雄船长的故事……”
王开岭对生活的态度与众不同,那是一种交织着留恋、温情、伤感和疼痛的爱。《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这一书名便是极好的注解。他笃信“好东西都是原配的,好东西都是免费的”。什么是好东西?明澈的天空、有灵魂的水、情意绵绵的桥、敦朴浑厚的井、黑甜的静夜、微弱的虫鸣、消逝的地平线、粗犷的荒野……当这些寄托着人类美好情愫的事物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渐渐消失时,当每一次消失都能追溯到人的欲望、贪婪、冷漠、愚昧时,王开岭的文字,便成了“大自然的悼词和殇碑”。所以,读他的文字,时常会心情沉重。
于我而言,这份沉重带来的不是悲观,而是忏悔。因为,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超出所需地索取、浪费、挥霍,肤浅地把“活在当下”理解成了纵情享乐、肆意掠夺。我们自负地以“万物灵长”的身份剥夺了自然永续存在的权利,霸道而寡情。正如犹太作家以萨·辛格所说的一句话:“就人类对其他生物的行为而言,人人都是纳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对生活的“爱”是沉重的。
他试图以笔担荷人类自省的重担,怎能不重?
我们常被“热爱生活”的鸡汤灌得迷迷糊糊,但王开岭告诉我们:热爱生活是需要依据的。环境的恶化,公序良俗被破坏,权力肿瘤的弥散,自由意志被压抑等都会让“热爱生活”这句口号显得依据不足。这看似很“愤青”的话语背后,是他敢于刺破浮华泡沫的勇气,是他渴望加固生活台基的努力。他号召公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负起责任,期待政府以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公平,呼唤人人用只争朝夕、夜以继日的努力,去让一个充满仁爱、尊重、美德与光明的时代尽快到来!
所以,这份对生活的“爱”亦是滚烫的。
如果说热爱生活是他的通行证,那么独立不群便是他的座右铭。
在《人被占领》一文中,王开岭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人群是人的坟墓。”初读时,我便被击中。在这个“心灵屈从于感官的时代”,我们多么害怕成为那个不合群的异类,多么渴望一份让人感到安全的归属感。在人群中,勇敢成为了“战战兢兢的勇敢”,善良成了“心有余悸的善良”,高尚成了“如履薄冰的高尚”,我们活得太小心,以至于那个人之为人的东西被挤压到极小,乃至消失不见,人太容易从独翔九霄的鹰沦为用爪刨食的鸡群中的一只。
是的,他是犀利的;然而,他不仅是个批判者,更是一名灵魂庙宇的建构者。
这位建构者以审美和理性为基石,垫高你的立足点,让你感受什么是精神世界的壁立千仞、千峰竞秀。
“精神明亮的人”是王开岭的标签,“按时看日出”也已成为生命健康与心态积极的标志。但我更倾向于把“精神明亮”理解成对日常生活中我们视而不见、见而未察、察而不深的点滴细节的洞察。
例如,我们总是喜欢谈论梦想。王开岭在《海岛·寂静·居住》一文中却说:“比‘我有一个梦想’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任何梦想的实现都不能以优越和凌驾于大众平均福祉为前提。”追求梦想,哪怕只是追求富贵显达也无可厚非,然而没有把清白人格、敬人之心、利他因子注入生存,理性的富有和高贵注定孱弱苍白,不值得推广和炫耀。
生活中,我们多半忌讳谈论死亡。王开岭在《向死而生》一文中却引导你想象,如果你是一个濒死者,眼前会浮现怎样的画面。那个夏夜里爱数星星的孩子,那个英气飞扬的追梦少年还在吗?我们是不是把仅有一次的生命交给了世俗的游戏规则来主宰?我们是不是熟悉了圆滑世故、察言观色,习惯了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却唯独把自己给弄丢了?倒逼自己“向死”而思,才能让生命少一点负累,多一点轻灵;少一点浑噩,多一点清醒。
不仅如此,这位建构者还以大师的风采感染你,让你沐浴思想的明亮光芒而生出双翼,往更加澄明与辽阔的寰宇飞升。
《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是王开岭的文论集,从中我们可以追溯他深刻思想的源头。在《罪与罚》里深刻剖析历史英雄与杀人犯的区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生命维护“二加二等于四”的乔治·奥威尔;在纳粹战场当逃兵,却被誉为“德国良心”的海因里希·伯尔;为思考祖国命运而入狱,流亡海外20 年的索尔仁尼琴;明知世界冰冷,却要尽力燃烧、反抗绝望的加缪……这些姓名,也许在教科书里没有位置,却是王开岭精神饥饿年份里的光和盐。他说,这是一本献给青年和新人的书。他始终担忧呼吸着自由空气成长起来的青年,会忘却良知的分量,会精神缺钙、人文滑坡,以至于“对善与恶可耻地漠不关心”,于是他用这一本本携风裹雷的呕心沥血之作,为青年的生命做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
卡夫卡说:“好书必须是一把劈开我们内心坚冰的利斧。”王开岭的文字正是这样一把利斧,它敲击你的心灵,砸碎你的麻木、狂妄和虚伪,让你在震撼之余渐渐完成自我建构。
比如,我们习惯关心数字:新冠肺炎疫情患病人数增加了多少?东航空难遇难者有多少?王开岭《打捞悲剧中的“个”》一文,或许会让你震悚。冷静细想,我们所惊愕的也许只是表面的那个数字而已。但是,数字不是抽象、空洞、模糊的概念,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独立真实的生命个体,是一个家庭的晴天霹雳。数字抽空了悲剧的细节,减轻了悲剧的重量。只关注数字,会让我们养成一种粗鲁的记忆方式,无法唤醒同情和悲悯。而对悲剧没有丝毫共情,会沦为鲁迅先生笔下咀嚼他人痛苦的看客,一个麻木不仁的局外人,而麻木正是下一个悲剧的开始。
在人群中,我们不免常常要“鼓掌”,但王开岭对“鼓掌”的解读却可能刺痛你的神经。在《激动的舌头》中,他从苏联领导人讲话的记录稿上反复记录的“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读出了脆弱的团结、荒唐的民意、虚假的热烈和真实的狂妄。想想我们在生活中,又有多少次“鼓不由衷”的掌?出于礼貌无可指摘,然而如果人人主动交出自己的头脑,封闭自己的口舌,将一己之躯淹没在所谓的民意沸腾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只会愚昧和腐败下去,又何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
王开岭试图构建的是立体而坚实的精神大厦,而非虚假繁荣的海市蜃楼。他告诫我们,不要仅仅活在当代的截面上,要从人类的精神家园采撷丰饶的思想精华,搭建你心灵的谷仓,汲取梦想的甘露。权益被践踏后,你是否有勇气像86 岁的罗莎·帕克斯那样,选择有尊严地坐着,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千人诺诺之际,你能否像梁漱溟、马寅初、顾准那样,刚直不阿,发表异见?恐怖肆虐之时,你可有马克西姆·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那样的勇气和血性,保持清醒,捍卫良心?
踏上勇敢者的荆棘之路,注定是一场孤独之旅,但孤独能造就伟大,宣告生命曾经在场。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在我看来,王开岭始终在生活之中、人群之外。他站在思想的山巅,以峭拔的身姿、深邃的目光守望着良知的星空。
那么,就让我们用他给予的力量,对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报以汹涌的爱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