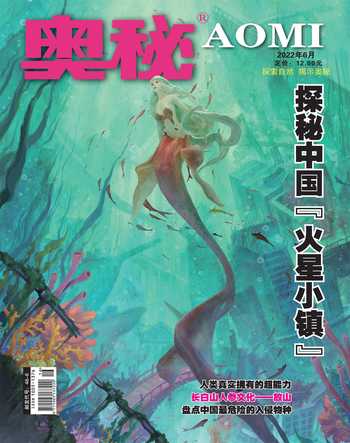童话是真正恐怖的故事
2022-07-02

每一种文化的人都会讲述童话故事,但相同的故事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往往体现出不同的形式。在欧洲儿童所熟悉的《小红帽》这一故事里,一名小女孩在前去探望奶奶的路上遇到了一只狼,并且告诉狼她要去哪里。狼跑到前面,吃掉了奶奶,然后穿着奶奶的衣服躺到床上等待小红帽的到来。你可能知道这个故事,但究竟是哪个版本呢?在一些版本里,狼吃掉了奶奶;而在另外一些版本里狼将她锁在衣柜里。在一些故事中,小红帽独自战胜了狼;而在另外一些故事中,一名猎人或者伐木工听到了她的哭喊,赶来救援。
这些童话故事普世的吸引力通常被归功于它们所包含的警戒信息,以《小红帽》为例,就是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故事有趣,可能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与生存相关的信息。”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家杰米·特拉尼说,“我们对故事讲述的历史以及史前史的认知存在着巨大的空白,尽管我们知道这一体裁十分古老。”但这并没有阻止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其他学者构建理论来解释童话故事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如今,特拉尼借用进化生物学家的方法,发现了一种测试这些观点是否正确的方式。
为了弄清楚生物群体的进化历史,发展历程与相互关系,生物学家通过一种叫作“系统进化分析法”的方式来比较物种特征。特拉尼利用相同方式来比较童话故事的关联版本,从而探询它们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哪些元素存留的时间最长。
特拉尼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小红帽》的多个版本上,这其中就包括另一个西方故事《狼与孩子》。在非洲、东亚和其他地区检索了这两个故事以及相似故事的变种后,他最终从口述传统中记录下来58个故事。一旦系统进化分析法证实它们确实彼此相关,他就利用同样的方法探索它们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改变的。
首先,他测试了一些假设:故事在演化过程中哪些方面改变最少(这表明它们的重要性)。民俗学家认为,与角色相比,故事情节对于故事而言更为核心。即拜访亲戚,偶然遇到带有伪装的可怕动物,比拜访者究竟是一名小女孩还是三兄妹,又或者动物是狮子而不是狼更为重要。
然而,特拉尼发现事件的演变速度与角色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由于特定的情节对故事至关重要,因而它们十分稳定,但也有许多其他细节可以十分自由地演变。”他说。他的分析也不支持以下理论,即故事的核心部分是留存最多的部分。他发现,与开头或结尾相比,该部分的事件灵活性并没有显著差异。
但他在研究该故事的警示元素时,真正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对狩猎采集者民间故事的研究表明,这些叙事中包含着有关环境以及哪里可能存在危险的重要信息,或者与生存相关的事项。”他说。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重要到,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不断再现呢?
答案似乎是恐惧,即故事中嗜血与可怕的部分(例如奶奶被狼吃掉)是所有内容中被保留得最好的。为什么这些细节能够在一代又一代的故事讲述者中留存下来,而故事的其他特征却没有呢? 特拉尼认为:“在口述情况下,故事不会因为一名伟大的讲述者而留存下来。当它由一个不一定伟大的讲述者说出来的時候,它还得有趣才行。”或许被一头狼整个吞下,然后切开胃部活着出来,这一情节如此扣人心弦,以至于无论讲述有多么糟糕,它都能保持流行。
明尼苏达大学的杰克·拉普斯不认同特拉尼有关童话的观点。“即使这些情节很可怕,除非它们确实重要,否则也不会保留下来。”他认为,在诸如《小红帽》这样的故事中,女性作为受害者这一反复出现的主题解释了它们为什么让人觉得与自己休戚相关。但特拉尼指出,虽然在西方故事中确实经常如此,但在别的地方却并不总是这样。在中国和日本通常被称为《虎外婆》的版本中,反派角色是名女性。而在伊朗和尼日利亚的版本中,受害者是名男孩。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马西亚斯·克拉森并不吃惊于特拉尼的发现。“习惯与道德会发生改变,但让我们恐惧的事情,以及我们寻求设计出来让我们感到恐惧的娱乐这一事实是永恒的。”他说。克拉森认为,恐怖故事让我们可以体会害怕的感觉而无需经历真正的危险,从而加强我们对负面情绪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