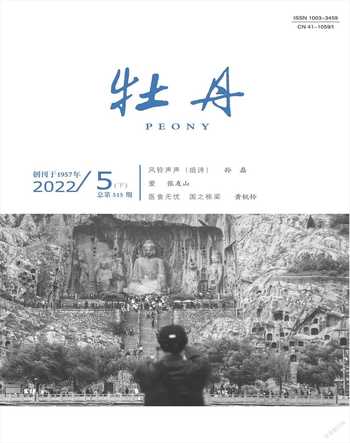两个我:拉康镜像理论视域下的《第十一回》
2022-06-30董喜梅
继执导电影处女作《一个勺子》后,陈建斌新作《第十一回》延续了此前悬疑、荒诞、黑色的影像风格,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与耐人寻味的黑色幽默。影片采用古典文学中的章回体结构,讲述了市话剧团以30年前的一桩拖拉机杀人案为故事原型,将其改编成三幕话剧《刹车杀人》,案件的当事人主人公平静的生活就此打破,三条叙事线索共时推进马福礼建构自我的过程。一是话剧团的排演。二是马福礼在三口之家的尴尬处境。继女金多多意外怀孕所造成的家庭矛盾推动着故事的演进与马福礼人物的生成与发展。三是导演胡昆汀与演员贾梅怡的情感纠葛。话剧团的排演引出了马福礼对真相的佐证,继女金多多的意外怀孕坚定了马福礼要翻案的决心,胡昆汀与贾梅怡的爱情映射着案件逝者赵凤霞与李建设的情感,二人的情感以“冒犯”之名引出马福礼对“自我”的审视,最后同化的三人在戏剧的舞台上跨越了想象界与象征界的间隔,和解他者与自我的对立,实现了自我的救赎与身份的建构,而戏中戏的故事架构也暗示着现实中马福礼从想象界到象征界再到想象界的循环往复。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电影第二符号学的基础。拉康在论文《来自于精神分析经验的作为“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像阶段》中提出了“镜像理论”,并划分了三个阶段:前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和后镜像阶段。在拉康看来,刚生下来的婴儿不能区分物与我,更没有主客体之分,只是一个“非主体”的存在物。这一时期即前镜像阶段。由于缺乏整体性的感知,镜子前的婴儿难以区分自我与他者,无法实现主客体的分辨。婴儿在6个月到18个月期间才达到生存史上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镜像阶段”。这一阶段是意识开始形成的阶段,是由身体破碎的意象向着整合完善的形象过渡的过程。拉康将这个过程称之为“一次同化”。这个时期婴儿第一次在镜中看见了自己的形象,并认出了自己,意识到自身的整体性。这种自我识别标志着“我”的初次出现。后镜像阶段期间,婴儿能在镜中进行自我识别,原有的自我被不断地予以否认,新的自我成像被不断刷新,从而获得全新的自我认知。
《第十一回》中的马福礼被镜像与他者左右,镜像下的看与被看、自我与他者的碰撞、凝视下的幻想与妥协、戏剧与现实的间离构成了主体内的自我混乱,以此构成自己的内心镜像。现实与镜像下的矛盾冲突必然造成自我主体的缺失与误认。但是,在误认与异化的过程中,最终完成了从“他者”走向主体生成的自我建构,从想象界到象征界再到想象界的回流。
一、镜像下的看与被看
拉康说:“人总是一个早产儿。”刚出生的婴儿尚未习得生活的能力,身体处于发展中。身体和心智以零的姿态降落人间,此时的婴儿不足以支配自身进行活动,脆弱的他尚不能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整体性的感知。这一时期处于前镜像阶段。这一时期是指婴儿的前6个月,婴儿没有自我的主体意识、不具备想象的能力,也无法从镜中识别出自己的镜像,处于一种混沌茫然的状态。在前镜像阶段,婴儿只能被动地接受外界给予的感知,缺少主体能动性,这种混沌、破裂的外界感知,拼凑起了婴儿对这个世界支离破碎的初始认识。
影片初期,马福礼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是模糊的,这一阶段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翻案,为什么要翻案。拉康指出,婴儿通过镜像以实现自我整体性的认知。影片运用“镜”这一元素折射出马福礼从自我混沌到自我确认的过程。相对于客观事物本身而言,镜中的像是一种幻想、一种虚无。但是,在影片中,镜像是抵达自我的重要途径、是照进生命的镜子。影片第一章中的舞台化妆镜、餐厅镜共同营造了虚空的环境氛围,暗示着胡昆汀、贾梅怡、马福礼各自的自我困顿与自我混沌。马福礼与金财铃母女的矛盾集中爆发在餐桌之上,这也体现了马福礼自身的空洞性,金氏母女的镜中成像与影片镜像的较量,与马福礼直视镜子相对比,凸显了马福礼自我的缺失与匮乏。影片共记录3次餐桌吃饭的场景,镜像的运用反映出金多多从本我叛逆到自我归顺的建构过程。
在看与被看中凝视着本我的快乐、自我的现实与超我的道德。看自身所带来的快感愉悦着演员、挑逗着观众、冒犯着他者、建构着自我。主人公马福礼在看与被看中挣扎,纠结案件当年的真相。影片共出现4次马福礼直视监视器与电视机的片段。从游乐园五光十色的灯光到电视机屏幕上的若干个自己,马福礼对街头电视屏幕的第一次注视暗示着他内心的混乱与茫然。在众说纷纭的现实中,马福礼不知何去何从,这个时期的马福礼是脆弱与空洞的。在马福礼偷听金氏母女争吵后,在金多多“他不是我爸,他没资格当爸,他是杀人犯”的喊叫下,马福礼第二次凝视着电视机中的自己,这次父爱唤起了他内心的果敢。他者的存在与变量推动着马福礼对自我主体的寻找与确认。而最为爆发的一次,即贾梅怡训斥马福礼后,贾梅怡以爱情的纯真性怒斥马福礼的木讷与冒犯,自我情感的大胆宣泄震慑了马福礼对世俗礼教的维护。由此,马福礼心中产生了疑问,他站在电视机前咆哮、复述与呐喊,这次意味着马福礼在自我怀疑中的自我愤怒,促进了自我主体的构建进程。最后一次,在白律师的“尊严”与屁哥的“浮云”中再次冲进虚与实、艺术与生活、真与假的漩涡里。影片结尾处,话剧公演的舞台上,混入拖拉机的马福礼在倒车镜内实现了自我的和解与主体的确认,这一次在被看中他救贖了自身、揭开了历史的真相。
二、自我与他者的碰撞
在镜像理论中,镜像阶段处于核心位置。镜像阶段是婴儿开始获得语言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个体开始与他者产生交集,他者以镜中像影响自我形象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关系总和的差异。在社会中,人无法在孤立的状态下获得全面的自我认知,社会中的我们是互为对象性的存在。拉康指出,他者可以划分为“大他者”和“小他者”。“大他者”指的是主体诞生的场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秩序,包括语言文化系统、社会主流意识等。“小他者”是“镜像”——别人的形象,代表的是理想的自我。这一阶段以他人的目光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随着分离的实现开始了自我的建构。拉康认为,他者是生成主体的第一步,镜像可以被视为他人的形象或者自己对他人的幻想。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环境中他人的认同充当了镜子中的反像,构成自我的主体。83F82672-524C-4726-961C-C7B8E1E62CB2
在拉康看来,自我在他者之中生存,自我就是一个他者。他者好似一面镜子,映射着自我的生成。他者之下的自我跳脱了实在界的本能与欲望,逐渐形成一个更为理性客观的自我形象。他者,既是与我相对立的客体,又是自我潜在的幻影,是另一个“自我”。在影片的第三回中,戏剧团傅团长向屁哥解释说:“舞台上他是马福礼A,生活中他是马福礼B。艺术源于生活,而不等同于生活。都是假的。”马福礼A与马福礼B镜像式的身份特征就形成了马福礼自我与本我的对立,互为镜像,彼此影响,模糊了马福礼本质性个体存在的自我建构与身份认同。同时,影片采用对照的人物关系,隐喻马福礼的A、B面。白律师与屁哥的人物设定更像是马福礼矛盾的两面,马福礼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拿起与放下、尊严与虚无之间反复试探。他在白律师与屁哥的三言两语之间改变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向,也在最后向他们反问意义的所在。白律師与屁哥价值观的对立设定,以他者的身份建构马福礼主体性的生成。
在戏中戏的影片结构中,角色以A、B面的人物设定进行内在的对话与博弈。现实生活中的A面与舞台虚构的B面相互碰撞,A与B假定着生活、戏谑着艺术。影片以时空结构的虚实对比照射出人性的多重维度,话剧舞台的戏剧性与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在交错与互证中,隐射着导演对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现实的理解与解读。贾梅怡主体性的建构也经历了一个从无我到“赵凤霞B”再到照见自我的过程。从最开始对于赵凤霞与李建设之间的种种不解到最后的寻找真相,从贾梅怡到赵凤霞B,从贾梅怡和胡昆汀到赵凤霞与李建设,贾梅怡不仅实现了自我的建构,也拯救了马福礼。在这个过程中,三人都在各自的他者中完成自身的蜕变与自我的建构。
三、凝视下的幻想与妥协
后镜像阶段是指婴儿在此阶段能够确认镜中的影像就是自己的影像,也就是说,这时期的婴儿已经能够分清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并且能清晰地分辨自己与自己的像,知道自己是谁,成功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这一阶段是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由镜像我走向社会我的生成,是主体演进史进入第二个转折点,即“二次同化”的结果。在这一阶段,通过“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幼儿既按照男女性别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建构人格,又在一个象征与语言的符号世界中建立主体与社会的关系。对于拉康来说,人类并非运用语言来指代缺失与匮乏的实在,而是“语言掏空现实,使之成为欲望”。凝视既是一种欲望的投射,本身又是欲望对象的缺席与匮乏。同时,凝视又是逃逸象征秩序的方式与可能。后镜像阶段中的凝视,是一种幻想,一种规训,一种妥协。
影片中,在话剧舞台的戏剧空间里,马福礼、胡昆汀与贾梅怡三人以他者的行为活动实现自我对象化的过程,而回归现实的马福礼,在凝视中走向幻想的世界,在屁哥对人生、生死的感发下,马福礼以一张死亡证明换取想象中的幸福,又由象征界回归到想象界。马福礼以爱之名的死亡证明是对世俗的妥协、爱的坚守。马福礼希望通过抹杀自我、妥协现实以抵达幻想的世界,三口之家荣升四口之家,对新生儿的迎接、对未来的幻想使马福礼由自我的生成走向自我的逃逸。幻想不是满足自身的指涉,而是以满足的形式完成对欲望的达成,欲望所追寻的是不断的满足,而幻想则是实现欲望的舞台。在幻想中,欲望的对象总是会从人们的凝视中逃离。影片最后,金多多瞒着马福礼与金财铃私下打胎。私人医生读诵着“庄周梦蝶”的选段,“就像梦一样,就像人生一样短暂,像梦一样漫长”,好似明喻多多堕胎如梦一般的过程,实则暗喻生命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就像蝴蝶飞过,庄周梦醒”,生活又回到了最初三人买早点的片段,此时的一家茫然无措,却又充满爱意。
影片曾多次提到“信念”二字。信念是基于一定认知后,所形成的成熟、稳定的思想态度。在影片的采访中,陈建斌说道:“必须要有信念,信念使爱情产生巨大的力量,也可以给你生活的真相,这是我想传递的。”信念或许是象征界里的执着与坚守。在约定俗成的规训下坚守着心中的光亮,在不得不的妥协中执着最初的坚守。马福礼以牺牲自己守护心中的信念,以此达成自我的和解、主体的生成与自我的建构。红色的光影下,伴着《甜蜜蜜》的歌声,三人一同坚信着幸福与爱、一同幻想着生命的下一段。
(长安大学)
作者简介:董喜梅(1996—),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影视美学。83F82672-524C-4726-961C-C7B8E1E62C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