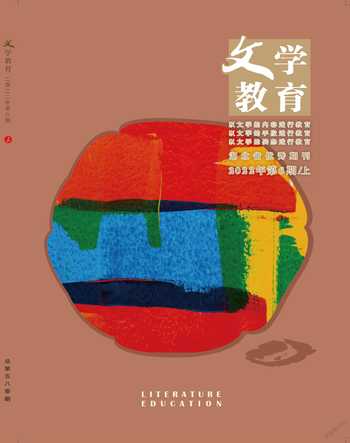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17年文学”中的女性英雄形象及其叙事
2022-06-30张倩
张倩
内容摘要:当代文学史上的“17年”是一个推崇英雄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英雄叙事是主流文学叙事方式之一。而女性英雄作为与男性英雄对立统一的存在形式,能更真实客观的反应文学作品的主流价值和审美走向。本文将尝试从“17年”时期作家笔下的女性意识着手,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英雄形象,探究“17年文学”的英雄叙事特征。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 “17年文学” 女性意识 女性英雄形象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学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基调基本确立。而此后的“17年”文学,其生态在主流意识的影响下具备了浓厚的时代气息,这种时代气息展现在文学作品的叙事特征上,即虚构和现实叠加的英雄叙事。英雄叙事从字面来看就是讲述英雄如何走向成功的过程,主人公一般是平凡的个体,他的事迹有可能是虚构的,也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但不管真实与否,在现实与虚构的交叉叙事中反映出英雄的共同特点就是坚定目标、勇往直前、一路披荆斩棘、可歌可泣,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17年文学”集中使用了这一叙事方式,甚至说“17年”是当代文学史上使用这一写作方式最鼎盛的时期,并为整个新中国文学创造出了一批具有现实价值的英雄形象。事实上,人物形象的塑造很大一部分要通过人物独立意识的觉醒、成长来刻画,因此我们尝试挖掘女性意识的觉醒,从作家们对女性英雄的形象描写来分析这一时期的英雄叙事特征。
一.意识形态引导下的虚构性英雄叙事
女性意识是女性拥有完整且独立的人格,在具备一定的思考力或在外界作用力的加持下,认同自身除性别特质以外的其他感受及价值后,而自我觉醒的非物化产物。从个体本身角度出发,它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从女性角度出发,不限于性别界限,看待世界的目光;二是从性别特质出发重新定义自己的审美角度,审视自身的目光。
(一)“17年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女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同时也无可替代的角色,然而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的生活方式被限制于男权创立的条条框框,女性的地位被男权弱化,女性的价值依附于男性,甚至仅仅体现在“传宗接代”。1916年启蒙运动的文化阵地《新青年》专栏探究了“女性问题”,大批作家针对“三从四德”等封建旧俗提出疑问。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思潮涌入,西方女性独立生存的社会现状与我国女性封建传统的压制产生碰撞,冲破旧思想和旧环境下的社会生活,塑造出一批新独立女性,在经济独立和社会责任方面都展现出同男性并肩而立的气概。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也能够较为清晰的反映出女性意识随着女性在社会事业的融入过程中开始成长。
文学作品能够较为客观的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革前后,也就是“17年”时期,在推崇英雄的“17年文学”中,女性渴望摆脱传统的约束,表现出同男性一般强烈的人格独立和参与社会生产的意识。如李毕的《李双双小传》中的主人公李双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杨沫的《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柳青的《创业史》中的秀兰等。
恩格斯说:“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才有可能实现。”[1]李双双是“17年文学”中一个较为出名的人物,如现代文学中大多数人评价的那样,她是个“铁一般的女人”,她的身上兼具男性的阳刚直爽和女性的温良敦厚。小说一开篇就写道双双是孙喜旺的爱人,仿佛她并不是一个拥有“独立”存在意义的人,甚至她的名字在村里也少有人知,而更多的是使用代称,比如“喜旺媳妇”、“喜旺嫂子”,丈夫在外对她的称呼也是“俺小菊她妈”、“俺屋里人”等,这一系列描述可以称之为是男权引导下的社会生活的最好体现,女性从属于男性和家庭,女性的价值仍然依赖于男性的存在而存在。在1958年的春天,大跃进开始后,双双的世界才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家务事,真心焦……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2]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的大字报让大家惊讶,这也是李双双作为一个家庭女性第一次突破家庭而表现出来的“叛逆”,这种“叛逆”不仅仅是对长久周旋于家庭事务的反抗,更具有一种“女英雄”的气势,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脚步而产生的迫切的想要参与社会生产的欲望。她不满足于日复一日的生活现状,主动打破传统,走出家门,上学识字,追求同工同酬,参与修水渠,研究如何喂猪,被评为模范…李双双这个人物越来越多的活跃在男性视野中,可以说在新的制度的发展阶段下,李双双的一系列事迹都能作为女性反抗从属地位的代表事件,同时也展现出她在追求自身存在价值的过程中,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不局限于性别特质,审视世界的女性意识逐渐被唤醒。
在专门解读女性文学的研究中,“17年文学”里的女性缺乏性别色彩,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女性意识或淡漠,或遮蔽,或潜隐。[3]意在指出女性的性别特征不够明显和突出,男女界限模糊,女性意识在关注世界这一层面被唤醒的同时,在关注自身的层面越来越薄弱,甚至瓦解。但是这一说法并不具有概括和代表性,如果说《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这一女性对世界的审视角度极大的被限制于女性在不同时代和特定环境下,那么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则能很好的展现对自身原始欲望的追求,比如林道静。
林道静是“17年文学”里极具个性的人物,在《青春之歌》里,她聪明、美丽、温婉,是充满活力和散发光芒的女青年,是成长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性格刚强,思想先进,不满足于被安排的婚姻命运,扔下一句“我宁可死,也不做军阀官僚的玩物!”[4]便与封建家庭决裂,抗婚后几经辗转只身前往北戴河谋生,此时的她作为一个女学生已经能够分辨女性的部分自我价值,她对爱情和婚姻有独立的思考和看法,可以说她已经是一个逐步走向思想上独立,灵魂上自由的新女性了;而后结识了那个有骑士风度的男人并与她成为伴侣,大胆的追求自己的爱情,从关注自身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她内心勾勒出的对于独立爱情的模样。但是她并非是典型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她不甘于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最终双方人生价值的不对等促使她离开了爱人,毅然决然投身于革命,关注政治局势,参与发传单、革命游行等活动鼓励人们积极抗日,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多次入狱遭受酷刑,这一系列的磕磕碰碰使她逐渐从一个知识青年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林道靜以最初的对婚姻爱情的坚守为契机,到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关注世界的角度,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不囿于性别界限,把自我融入家国之中,把女性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紧密联系起来。
(二)“17年文学”中的独立女性形象
从某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追寻这个时期的文学并不是一个新颖的方式。但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研究和把握却能很好的反映作品的风格和基调,挖掘作品的叙事方式,探究叙事特征。“17年文学”作品与其他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彭总,《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这些男性英雄,还是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李双双和林道静这两个女性,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带有传奇色彩,人物身上凝结着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在形象刻画过程中人物与时代相匹配的独立意识。女性相对于男性更直接打破了人们对于性别的认知,给我们开辟出一个全新视角,构建出一个理想主义倾向的女性生命情态。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处于弱势地位,一味服从的传统女性,而是勇于斗争、渴望平等的新女性。
李双双是一个泼辣、倔强的人,性格爽朗,敢说敢做。小说中描写的她在精神世界这个层面与男性一样,有着不可多得的干劲,而在外貌特征上也不是文学作品中一贯讨喜的“林妹妹”式女性,相反的从语言、性格特质、外貌特征都表现出了健壮、坚韧的特点。从小说中的具体描写可以看出她的形象符合社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她的形象与当时时代发展的需求,或者说在历史进程中女性角色的转变是十分匹配的;她是一个公正无私、大义灭亲的人。向老支书提出兴办公共食堂,为了办好它,尽心尽力,在丈夫不愿意成为炊事班的成员而撒谎自己不愿闻见蒸馍气时,双双揭穿了丈夫,并积极的自己加入食堂,做起炊事员,并和丈夫说道:“保护党提出来办的一切事情,谁破坏,就和他斗争!”[2]在挖出金樵家藏起来的水车时,双双“越想越气,睡不着”[2]孙有提出不入公社,商议着与双双家共同使用,却被双双立马拒绝,“布衫大衣一裹就冲出去了。”[2]立即汇报给了老支书。在得知丈夫喜旺帮助孙有做过寿的五碗大菜而偷偷挪用公共食堂的东西时,不顾私人利益和情分,毅然揭露这种不正确的做法,并让喜旺写大字报道歉……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下,作为一个家庭从属意义上的女人萌生出女性意识,敢于冲破男权的压制,并时刻表现出一心为公的思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从故事的一系列情节可以看出作者将李双双这个人物的形象有意识的进行了理想化和美化。
(三)理想性、虚构性的英雄叙事
李双双在形象上刻画的理想化和美化,实质上更多的是从这个人物如何看待公社的角度来写作的,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形象创造极大的限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公社正是需要双双这样思想的人,也需要通过双双这样的女性向社会传达女性在生产环境中的作用和地位。文学在“17年”时期被当作实现政治意图的传声筒,作家的文学创作自由得到了限制,极大的社会需求使得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或者女性形象都有清晰而模糊的“模板”,清晰在于主要人物的思想情感偏向都展现出一致的对党的拥护,对党领导下的事业充满希望和干劲,模糊在于这些人物处于不同生存状态下、不同情感经历成长中的各个阶层。在双双批评丈夫去道歉和想到金樵家藏着水车实际上是心不在社里,故而气急败坏睡不着这两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双双作为一个农村女性在维护公社利益也即国家利益时身上的不贪图小利,无私和高大,也许这与我们接触到的社会生活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说这个人物参杂一些假设成分,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存在。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还有《红岩》里的江姐,江姐被捕后被关在渣滓洞集中营,在狱里她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敌人妄图用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用竹签戳进十指的酷刑逼迫江姐就范,但江姐坚韧不屈,甚至高喊“共产党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5];林道静一个柔弱女子,两次入狱,受尽摧残,第二次被捕后,拒绝在《自首书》上签字,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在狱中待了一年,出狱后终于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论是江姐还是林道静作为女性承受的不单是与性别不相符合的身体痛楚,给读者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是突破人性所能承受的范围。
因此单单从女性的人物形象去窥测这个时代以英雄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关于英雄叙事的写作方式我们可以进行大胆的推测和判断,就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虚构艺术意味的写作。
二.现实环境引导下的真实性英雄叙事
“十七年文学”的英雄不论男女,总是带有时代意味,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迎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产生一些夸张或隐藏的处理。为凸显人物形象背后的精神意义而稍显理想化,但是文学作品在离开现实的基础上创作是危险的。老舍先生说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6]。十七年文学的叙述是一定程度上的现实主义写作,作品诞生的写作背景为这一写作手法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时代的风云变幻会催生更多的时代故事的讲述者,也会影响讲述者关于时代的思考,这种思考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即叙述的变化。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大多亲眼见过战争的残酷,因此我们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见作家对于战争给人情感冲击的描述,比如杜鹏程在《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中他所要极力展现出来的正是自身对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宣泄,他说道:“难道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这不仅是创作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情感的需要”[7]怀揣着这样的创作冲动的作家在十七年文学作品流域中并不少见,也正是这样的义不容辞的冲动,使得作品塑造了很多,或者说真实反映了很多战争英雄。
《红岩》的作者杨益言和罗广斌都曾是战争中摸爬滚打过的人,经历了战火和血液的洗礼,在他们创作的《红岩》中,重点叙述了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出彩的狱中描写尤为牵动人心。小说中英雄层出不穷,女性英雄像江姐、双枪老太婆都是现代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形象。
(一)战争洗礼下的女性意识
双枪老太婆在小说第十四章中的描写是一个让人闻声丧胆的人,警察局长前一秒还威风凌凌,下一秒看见隔壁桌的老太婆“大吃一惊,朝后一退,把椅子也绊倒了”,“她仿佛看见老太婆的白太绸长衫底下暗藏的两支上了膛的快枪,只要老太婆的手稍微一动,子弹就会穿透他的脑袋”[5],以及后文写道他的一系列肢体动作,比如手脚发抖、连连哈腰都侧面展示出双枪老太婆在恶势力面前极大的震慑力。老太婆是战争年代一个独立、刚强、坚韧的女性,在李敬原告知她谋划营救集中营里被捕战友的事情上,她表现出急切又激动的心情,仿佛一个从未经历战争的战士一样拥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毫不退缩且坚定的说“多给点任务吧,挑的动的”,“我们保证完成指定的一切任务,尽量多救出一些同事来”[5]。大多数军事文学作品中,女性并没有作为主要人物在战争中被突出,这源于这一类型文学语境中对女性描写的局限性。但是《红岩》在描写英雄的过程中,并没有像其他军事文学作品一样,直面战争激烈的场面,通过渲染战争的属性,花大量的文笔和情感去描摹主要英雄在一场战争里的突出地位,而是从侧面切入,将文本所要传达的核心要义从精神折磨和信仰坚定这两个角度的冲突去对比反映。江姐被捕入狱,在狱中的种种磨难和隐忍就能充分的反映作者的这一写作特点,以及老太婆在营救被捕同志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关怀和对党的服从,也展示了她对斗争和解放的认识,这两个女性的共同之处都是对于信仰的坚守,坚定不移的跟随党的步伐,相信信仰的力量可以成为斩断一切苦难的利刃。在《红岩》中,凸显的女性意识所展現的角度不同于林道静和李双双,更多的反映了革命者对生命意志的思考,挖掘支撑生命意志生生不息的背后精神,把女性的独立意识发展融入到整个社会对信仰的认识发展之中,与中国革命一路走来的发展态势交相呼应。
(二)“十七年文学”中的传奇女性形象
十七年文学为女性立传的小说很少,女性英雄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双重局限性,很难成为战争的主角,但是在十七年文学所塑造的英雄群像中,女性的形象反而是多元化的,有饱受摧残还坚贞不屈的女英雄,有革命洪流中大义凌然的老母亲,有历史舞台中斗志昂扬的女知识分子…这些极具历史情感特征的女性类型在十七年文学中对构建故事的合理性、丰盈故事情节、推动情节张力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贡献。在《红岩》里,女性人物出现的不多,有沉稳机敏的江姐、有爱憎分明的双枪老太婆、有勇敢坚强的孙明霞、成瑶。江姐是推动《红岩》故事发展的主要人物之一,她是一个比较丰满的艺术典型,她是一个妻子,更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她拥有地下工作者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警惕沉稳的工作方式,在看到丈夫的头颅被挂在城头上示众时她悲痛万分,但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使得她不得不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故作镇静,化丧夫之痛为视死如归的勇气,担负起丈夫的那一份责任继续做好地下工作。在苦难的牢狱环境中,出于对社会制度的思考和不满,教狱友们新的制度思想,默写《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供大家学习研读;为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拼命努力学习三个月考上号称“民主堡垒”的四川大学;借着难友出狱的机会,带去家书教导儿子“盼教以踏父母之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5]江姐这个人物的丰满过程围绕着对革命意志的坚守,人物形象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逐渐明晰,一个坚韧、沉稳、勇敢的女性革命者跃然纸上。双枪老太婆不同于江姐的是她身上的革命气息不是知识分子的义愤填膺,而是从一个平凡的老百姓角度出发,让我们看到了普通大众对于革命的激情和奉献,她是一个传奇的女性形象,有些刚强如同男性一般,作为华蓥山游击队的队长,嫉恶如仇、手持双枪,让敌人闻风丧胆,始終保持对党和国家忠诚不二。在叛徒甫志高告密导致众多革命同胞被捕时,她毅然决然的枪毙了叛徒,为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绝不手软。赋予人物传奇和生命意义的是这个人物自身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在与封建礼教相对抗的过程中活出了一种英雄气概,这种气概是在革命年代十分难得的。
(三)写实性、真实性的英雄叙事
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的总的界说和规定提到文学是对生活的能动的反映。[8]也就是说文学事实上属于人的一种活动,从具体的性质方面来探究,或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存在和意识的这一基本理论入手探究,把文学活动看成作家这个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和反映。十七年文学中的关于战争的场面,以及塑造的英雄人物,或来自于作者宏大的模拟想象,或来自于作者的亲眼所见,无可厚非所有的叙述都有历史的影子,在作品中我们能找到被“塑造”的时代的痕迹,真实的人物事迹也隐藏在传奇、宏大的故事情节之下。《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先生曾经说,双枪老太婆这个角色有三个原型,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分别是邓惠中、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是一个在封建社会被裹脚的女性,但出于对革命的一腔热血,积极参与练兵习武,指挥军事训练,为起义筹备资金,联络武器和弹药,是华蓥山游击队的主心骨、领头羊,因上级发给她两支枪,而号称“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和刘隆华也是构成双枪老太婆的最主要原型,都曾率领双枪队参与华蓥山区的多次战斗,传奇经历家喻户晓。好的文学作品留给后世的不单是曲折离奇的情节走向和无懈可击的艺术结构,还有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历史文明和文学精神。《红岩》中的江姐,作者的笔下她是一个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影响和激励着几代年轻人的爱国情怀生生不息。她的原型是革命烈士江竹筠,曾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年少时的江竹筠认识到自立自强的重要性,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宣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奋不顾身投身革命事业,在遭受国名党反动派老虎凳、辣椒水、代词钢鞭、电刑等多种残忍迫害时,仍旧坚定不移。在文学创作中记叙真实人物事迹的故事更能激荡人心,写实性、真实性也是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红岩》中的女性形象看到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样式,是真实性、写实性的文学写作。
纵观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不难发现作家在刻画人物时有了与时代发展相照应的侧重点,女性形象相较于“养在深闺人不知”的类型,出现更多的是能与男性平分秋色的新女性,尤其在新思想大量涌入的历史时期,比如十七年时期。女性形象在介于虚构化和真实化之间,透露出时代嬗变的气息,文学作品的叙事样式也随之成型。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转引自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三联书店,1997:13.
[2]李准.李双双小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杨益言,罗广斌.红岩[M].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
[6]老舍.语言与生活[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
[7]熊坤静.党史博采.纪实(上)[J].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2):51-54.
[8]卢允庆,林志香.能动反映论的多维解读[A].太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
基金项目:2020年甘肃省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项目(2020A-121)。
(作者单位:陇东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