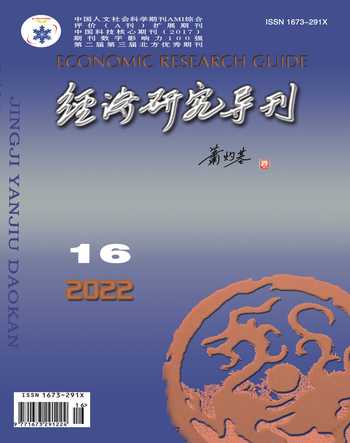生育激励下我国子女津贴制度的建构
2022-06-29李孟南
李孟南
摘 要:2018年,我国实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将子女教育纳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人口政策,全面开放三胎。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生育率却一直未得到提高,家庭生育受到经济方面的制约。个税子女教育扣除存在扣除方式单一、对象规定不合理等问题。因此,与个人所得税相配套的子女津贴制度亟待完善。
关键词:生育激励;子女教育扣除制度缺陷;津贴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3.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16-0064-03
引言
2018年我国进行了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将子女教育纳入可以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期望配合二孩政策来扭转低生育率状况,然而效果并不是很好。这其中固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经济压力一直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虽然我国步入小康社会,但日益衰老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让多数家庭经济压力巨大。
子女并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作为国家和社会一分子所有人都有义务维护子女的正当权益。另外,子女实际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费用,学龄前子女、未成年子女与成年子女均有不同需要,倘若一致对待,则可能造成贫困家庭的补贴不足,也会导致国家财政浪费。这样“一刀切”的规定也不利于单亲家庭等结构特殊的家庭。因此,可以填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漏洞的规定亟待落地实行。
一、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缺陷
2018年,我国改革个人所得税法,将子女教育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极大改善了以往国家在育儿这一重大民生问题方面的不足。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家庭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增加了这些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然而我国刚刚踏入全面小康社会,养育子女是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支出,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可以有效缓解人民日常生活压力,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进而提升生育率,缓解老龄化社会问题。如今,每个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孩子的父母可以享受每月固定1 000元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这样单一的扣除方式虽然能解决燃眉之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子女抚养费用的扣除额度难以统一
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的力度不够,也并未考虑到各地区的差异。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在个人和家庭的标准扣除额之外,规定家庭、教育、医疗等特别扣除。为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个人所得税在征收时不仅要提高标准扣除额度,还应根据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家庭的特殊支出要求来设计合理的费用扣除制度,结合家庭的收入与支出情况进行纳税能力的评估和考察,通盘考虑家庭负担的削减[1]。
(二)子女年龄规定不当
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孩子才能扣除,意味着位于0~3岁年龄段的婴幼儿是无法享受到这一项优惠政策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恰恰是最让父母劳心劳力的时候,由于子女不具备自主生活能力,家长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抚养费用以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更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会为这些婴幼儿选择早教机构进行教育,而这类支出在我国的已有规定中,并未被纳入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内。
(三)对不同结构的家庭政策单一
独生子女家庭和多子女家庭的负担明显不成正比。除了正常的婚姻家庭外,各种其他结构的家庭也不能忽视。较为常见的单亲家庭、非婚生家庭,甚至病残家庭和孤儿家庭等家庭类型也要考虑。而对于这些家庭中的青少年来说,他们健康成长和发展所需求的也不完全相同。现行“一刀切”刚性制度设计,不仅不利于这些家庭的日常生活,也会使制度僵化,失去效率。为保障制度的服务效率,提升制度弹性,可以采用分类管理的方法对不同情况的家庭条件下分类补贴。
二、我国子女津贴制度现状分析
我国目前关于子女津贴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对生理缺陷儿童和孤儿等特殊家庭进行补助。在家庭功能不全甚至缺位情况下,国家理应承担起子女保护和照料的责任,但是对于普遍且广大的未成年子女群体却关注不足。这是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谋求经济的发展,社会政策向经济政策做出的适当让步,制定政策一般以减轻社会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为主导思想,这就导致政府过于重视社会保障这一最后防护网的经济效率。
(一)子女津贴制度的法理基础和现实意义
1.维持生活家庭。早在2007年,陈清秀就提出“纳税义务人扣除其个人生活费用,与家庭扶养费用后尚有剩馀者,方需课征”[2]。课税禁区原则要求国家在征税的时候,应当将生活必需品排除在外。这就要求国家不仅需要保障纳税人的个人权利,也要同时保障纳税人所要照顾的家庭成员的权利[3]。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生育补贴、保育费等,包括之前实施的对独生子女补贴也与这项原则相契合。课税禁区所指向的对象不仅包括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也要求对个人所抚养的家庭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照顾。因此,确保最低生存是税法及社会法共同任务。
2.保障低龄子女生活与教育。早期教育对于子女的人生来说至关重要,它决定着子女的成长和日后发展方向,甚至子女的社会竞争力。很多家长望子成龙,为孩子选择了早期教育培训班,这与国家进行素质教育不谋而合。很多国家为了弥补因家庭困难而无法接受优质早教的子女在以后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先天不足的地位,同时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对家庭进行直接的子女补贴。为了给受教育权实现提供各种可行性条件,国家所承担的物质性给付义务主要有有形的金钱、实物给付义务和无形的知识、技能传授义务[4]。子女津貼主要以免除学费、实物补贴以及现金救助这三种方式存在,极大地提升了子女的入学率和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3.鼓励生育。子女津贴制度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多数家庭“不敢生”的问题。生育津贴,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母亲生育所需承担丢失工作的风险;设置子女养育津贴,学龄前子女的照顾成本由政府财政支持,很好地覆盖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所遗漏欠缺的区域。因此,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子女津贴制度来补充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不足将会有效地促进生育率的提升,解决现阶段社会所面临的低生育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子女津贴的局限性
1.子女津贴的模式单一。相较于各类服务型津贴,我国仍单一地以现金津贴作为子女福利津贴制度的主要形式。现金形式的津贴可以直接改善目标家庭的生活状况,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然而却无法保证所发的现金被直接用到子女福利之中,政策所针对的对象无法切实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实用性也就打了折扣。实际生活中,特殊家庭子女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困难并非现金补贴所能解决,需要专业服务项目的支持。并且由于服务式津贴如果不经过事先调查等准备,而仅仅是当作“面子工程”实施,就容易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并且对有需要的子女和家庭毫无帮助,本末倒置,极大地降低了服务效率。
2.子女津贴覆盖不全。子女津贴政策应该覆盖所有养育子女的家庭,而不是仅仅着眼于特殊的子女群体。我国现如今的子女福利对象大部分是针对存在生理缺陷的未成年人或者孤儿等特殊群体进行帮助,而大部分一般家庭无法享受到国家对于子女的社会福利,普通家庭子女长时间被社会福利体系排除在外[5]。在“三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应当将普通家庭的子女纳入子女津贴的补贴范围之内,如此才能进一步保障下一代的合法权益,减轻基层家庭的经济负担,改善生育成本高的社会问题,从而缓解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3.政府责任分工不明。我国现行的子女福利制度面临着严重的分割问题。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来看皆是如此。过多部门参与了子女福利制度的构建,然而过少的协作分工,使得这一制度变得杂乱无章。民政部门、教育部门、财政部门都执行相关的工作,可缺少明确的管理机制使得政府资金重复使用或存在缺漏,并且短时间内无法予以归责。此外,政府在与各方合作提供相应的服务时,相應的主要职责也无法确定。
三、子女津贴在我国的适用
我国构建的子女津贴制度应当分类补贴不同结构的家庭。子女津贴制度虽然是面向家庭的政策,但是家庭中的子女成长和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才是这一制度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应将这些困难进行分类管理,根据不同困难,设置不同家庭申报项目,对应不同的子女津贴类型。这充分贯彻了社会政策是对公民需要满足的原则,根据不同的需求类型制定相应的分类补贴措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提高了制度的效率。
(一)子女津贴的标准
1.基础性津贴。基础性津贴应该具有范围广和持续时间长两个特点,其中主要包括了子女生育津贴、子女抚养津贴以及其他对子女的优惠补贴。子女生育津贴主要针对现如今过高的生育成本制定。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对此类家庭进行现金补贴。我国目前生育保障中的生育津贴仅为128天单位平均工资,较之前的98天虽然有了较大提升,然而依然保障水平低、覆盖面窄,无法产生实质性效果。此项津贴应当与子女抚养津贴相衔接,保障孩子在学龄前能够正常生活。子女抚养津贴针对生育子女的父母。父或母一方不工作,专门照料或主要照料子女,并且另一方收入较低,才可以获得政府所发放的子女津贴。将子女托顾费用列于客观费用扣除的范畴,并仅允许双薪家庭适用,不论是将子女托予他人照顾或父母自行照顾,子女托顾费用属子女最低生存所必要费用之一皆应由所得税税基扣除获得满足。在单薪家庭情况下,父母一方选择放弃工作在家照顾子女所投入之劳动力应换算成相对应之费用报酬,并作为子女托顾费用之扣除依据。
2.特殊性补贴。特殊性津贴政策针对特殊群体而设计,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对针对失去父母,与亲生父母失去联络的孤儿,又或者父母入狱等是困境家庭子女,帮助其改善生活状况发放的基本生活津贴。第二类是对身患残疾的子女发放基本生活津贴,保障其生活水平。对于此类人员,应同时提供专门的津贴,以保障残疾子女的康复、功能训练和治疗。第三类是大病子女生活和医疗津贴,进行生活和医疗补助。
(二)子女津贴的发放形式
1.现金形式津贴。直接的现金形式津贴能够给予所有家庭选择的权利,让这些家庭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直接购买他们所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从而有效地提高补助的使用效率。因此,现金形式的补贴依然是救助的主要形式。当然,为了避免财政方面的浪费,最低生活标准应综合各方面因素后计算得出。
2.实物形式津贴。实物形式补贴的实现一般是通过费用减免的形式。由于不同的家庭需要多种多样,除了需要保障家庭最基本的生存以外,家庭成员医疗支出、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领域都会存在需求。
(三)子女津贴的管理方式
1.家庭分类。为实现让国家的财政支出物尽其用,实现相对应的目标,我国的子女津贴制度应当采取分类管理与分类补贴的设计思路。分类管理主要是对子女所在家庭进行分类,综合考虑不同家庭的生活需求。
2.管理机构及体系。社会福利资金主要有三种基本的获得途径:税收、自愿捐款和收费。我国需求的子女津贴制度应以政府为主导,政府承担起引领主导的责任[6]。因此,资金筹集应主要以政府提供和政府拨款为主导,政府仍然是子女福利服务资金的主要来源。而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央调控的同时也应当由基层来逐步实施。需要重点解决基层人手不足,人员不专业,兼职、兼任现象严重,办事职权过弱的问题。
总之,“三孩”全面开放政策不会不改变,要建立起完备的子女津贴制度,应先树立起子女优先的理念,贯彻政策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原则,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并与其他社会公共政策相适应,才能制定科学合理、符合我国国情的子女津贴制度。
参考文献:
[1] 盛常艳,薛兴华,张永强.我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探讨[J].税务研究,2018,(11).
[2] 陈清秀.量能课税原则在所得税法上之实践——综合所得税裁判之评析[J].法令月刊,2007,(58):66-97.
[3] 翁武耀.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的制定[J].财经法学,2018,(8):71-98.
[4] 莫静.论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J].现代法学,2014,(3):40-47.
[5] 金静,汪燕敏,徐冠宇.构建我国儿童津贴制度的思考——基于金砖国家的跨国比较[J].经济体制改革,2014,(1):161-164.
[6] 刘剑文.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法治成果与优化路径[J].现代法学,2019,(2):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