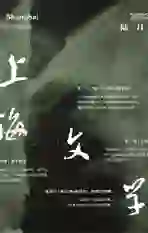寻僧记
2022-06-28王恺
王恺
我们的古诗词真是“一滴入魂”,比如听到“松下问童子”,就会联想到师傅肯定不会在现场,永远只在飘渺的山中。我们无法接受杵在山居等待来客的隐者,一般这样的人,都会被骂成“假隱士”,属于真名利之徒,这是传统。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又是极为驳杂的,本来按照道理,佛教道教里的高人都应该是真正的隐者,藏于深山,不露真容,但真实的高僧也未必符合我们的诗词想象,大德也和高官打得火热,受到皇上敕封的僧侣不在少数。这个传统一直也有,到今天也不例外,是另一个层面的佳话。
一方面我们有着近乎泛滥的文人之心,对假隐士嗤之以鼻,另一方面,还是趋慕名利,对名流们总是渴望的,名利场有巨大吸引力。外界说得再怎么纷纭复杂,亲眼目击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产生了动摇。我记得自己在某个近年声名鹊起的寺院的方丈室里,看着大和尚那些满堂“名物”的时候,内心波动的心情:硕大的翡翠山子,隐隐透露出青绿色的“华光”,其规模之大直追故宫,当然雕琢要粗糙很多,现代工匠未必有那么绵密的心思;随手递给我的檀香扇,释放着来自印度的植物的真实幽香;巨大的书法条幅,署着某某名家的名字,这个我倒看不出好坏,我是物质主义者,只对纯物质有鉴别能力,翡翠和檀香木,都是传世的好东西,今天在此地,明天又流传到了另一处,此刻,它们在这座深山里待得很安逸。
一边听大和尚叹苦经。大和尚面相就是当地农人,但出家久了,见过世面,多了些气派,憨直地瞪大双眼,说到寺院多年被当地的各种商人欺负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寺院刚出名的时候,各种人都来抢注商标,最早以寺名注册的商标,是一家火腿肠企业。我扑哧一笑,实在是可恶,依稀记得小时候电视里铿锵的广告音,明明知道寺院里不可能出品这种东西。也是那次聊天才知道,寺院周围的各种武术学校,也和寺院没啥关系,都是周围农民自己弄出来的,足足几百家,包括上春晚表演的那几家。真要去寺院习武,可能连这些学校的关都闯不过,基本被外圈就截留了——武侠小说里缺乏的一章。
“我们其实连门票都不卖,高价票啥的,是外面的旅游公司弄的,前一段还弄什么上市。”这些话,应该属实,寺里清规戒律并不少,这里属于禅宗祖庭,达摩老祖的出家所在地,禅堂规矩很多,比如凌晨三点就要起来坐禅,晚上七点就要入睡,行禅过程中如睡觉,会被板子打醒,所谓的“当头棒喝”。越是外界说得纷纷扰扰,内部反而要争口气,专门请来负责禅堂的师傅,像根清瘦的树杆,只是树杆,水杉被打去了枝叶,十分眼高于顶,见面过程中,眼睛不会看我们这些俗人,几乎永远翻白眼向天,据说打下来的板子,能打得贪睡的和尚头破血流。
大和尚算是有见识的人,网络上关于他的传闻太多,辩无可辩,索性走高层路线,也算是护身符。寺院里的高僧结交世俗高层,有时候也不完全是纯粹的贪图世俗虚荣。
中国的寺院是生活化气息浓郁的场地,走到哪里都逃不出“名利”二字,越是繁华,越是烦恼,出家人本来就是要逃离这一切,可是哪里逃得掉,说起来也是更深切的悲哀了。
民国的时候,中国的佛教界进行世俗化改革,要入世而不是出世,典型的就是太虚大师,这个可能也奠定了中国僧人们的某种进取意识。我所见过的国内僧侣们,基本上是积极向上,和一般人的想象迥异。
某一段我总是去景德镇,和大家混熟了,就能去各种场子。景德镇算是国内少见的好玩的地方,不仅瓷器山头林立,每个空间里,接待的主人们也各自不同,不仅仅是各路制瓷者,还有各种玩票的人:设计师、画家、当代艺术家,都转身而成灵活的小商人,看多了就觉得厌。走进湛云的小空间,眼前就一亮,怎么还有个小沙弥在景德镇坐镇?墙上挂着大红描金的瓷板唐卡,是他的合作伙伴的作品,桌子前面,清秀的湛云在泡茶,双手合十打招呼,正经的僧服,大夏天都要扣好领口的盘扣。景德镇那么酷暑,小师傅也不流汗,非常舒服。
屋子里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一桌几凳、一套茶具而已,端起杯子,方知道,喝的是几千一泡的名家岩茶。
名利藏在素朴之后,固有的章法。
混熟了,才知道十多岁出家的湛云小师傅是北京人,出家后落脚在江西的云居山,也是古中国著名的禅林。之所以长期在景德镇居住,得益于现在僧侣生活的变化——瓷器在当代的名刹生活中占了越来越重要的比例。古老的禅院,并不缺钱,要点缀装扮,最好的莫过于瓷器和书画。湛云等于成了他们寺院里的采买负责人,不仅仅自己的寺院要添置瓷器,送礼也需要,一些高僧做寿,常常需要几百只寿碗,绝对不能是世面上常见之物,最好带点宗教色彩的图案点缀,最好是名家手工,说法越多越好,这就需要有能力的僧侣在此地监工斡旋了。湛云年纪小,交际却是一把好手。顿时发现,素色僧袍下面的小和尚,有颗七窍玲珑心。
角落里有专门的柜子,放着各种奇技淫巧的瓷器。我算是有点瓷器常识,也觉得很多器物非常奇异,表面松石绿但加上扒花手法,做成细致花纹的小宝瓶;仿照乾隆的三清茶碗做的仿品,白底上朱红色的“三清茶诗”非常清丽;薄得透光的蛋壳瓷,拿着手机电筒一照,里面还有隐约的兰草纹,哪里是平常能见到的?因为少年出家,湛云的某些心性表达恰似少年,非常活泼,出家也没有收束,有时候觉得是和一个初中生在这里喝茶,北京口音,是再熟悉不过的嘎愣的声腔,但有时候,听他谈一两句佛教奥义,又觉得,到底是修行人。
贪图他的茶室在半山腰,难得的清净,每天晚上一起喝茶,喝着喝着,就熟悉了。湛云开着奔驰车,带我满大街逛瓷器店,有了这么一位司机,大家都觉得我也是迥异常人,也不知道我的来历,和陌生人见面,慢慢也是双手合十,不接触,倒是保持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景德镇因为始终以瓷器行走于世,所以这里各路人等都有,除了湛云,经常还能见到苏州来的一位尼师傅,穿着也是十分讲究,大夏天也穿着长袖的夏布长袍,手拿泥金折扇,挂着长长的沉香木串,有时候在路上见到,我们合掌行礼,几乎感觉自己不在今世,只如生活在明清的古中国里——不是说建筑和场景,而是这些人物,分明是在《醒世姻缘传》里的山东绣江县明水镇,大家终日在街道闲逛,看到陌生人就上去攀谈,从何处而来,到何处而去。
周围的风物也古老,没有高楼大厦,多的是旧时风光:田野里的宋代古塔,水面上缓缓飞过的一群白鹭,还有狭窄小巷里的古老吃食——麻花铺子、卤水瓜子,外加景德镇的名吃,糯米团包着油条,称为“油条包麻籽”,推着小车缓步叫卖,几百年延续的风光霁月,不让人厌倦。
景德镇凭陶瓷一脉传世,很多习俗就与外界不同。这里有陶瓷世家,子孙几代都以画某类图案行世;也有烧窑大师,靠瓷器进窑的位置摆放,硬生生成为点火圈的扛把子,成为非物质文化里的一项“把装师傅”;有仿古高手,造的假瓷器能够上拍卖会,蒙过专家的眼。湛云就是穿线人物,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人。越发觉得,当初第一眼看到这个年轻的小僧人,实在是走了眼——这完全是个可以进入小说的人物,机灵得落地生风。我们晚上喝着昂贵的岩茶,八卦景德镇,也八卦僧侣界,谁是谁的徒弟,谁传了谁的法,不少僧侣皈依了名师,日后作为就大,可以有更大的庙宇去住持。
湛云没有大的野心,也是年轻,他只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精舍,在山里,设计参考日本禅院,进门一处枯山水庭院,也有好处,往来人阶层比较单一,不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还是个中产审美系统的禅院。
他真正佩服的,是附近曹洞宗祖庭的一位当家师傅,说是中年出家,没几年就把本已落败的祖庭给修复了,整个庙宇颇为壮观。当家师傅在那里当方丈,据说风生水起,这才是大手笔。那名字让我狐疑,听起来总有几分熟悉,一看微信头像,更是似曾相识,再想想,这不是我朋友圈也有的出家了的名医?
当年在北京做记者,认识的名中医不止一位。这位雷医生印象深刻,是位爽利的妇女,出身针灸世家,据说小时候有特异功能。这种话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看到她之后,还是觉得生有异相,眼睛圆而硕大,住在SKP商场对面的豪宅,也没有专门的诊所,就在此地行医,可见客人的阶层。谈起医道,却颇为讲究。
顺手拿出一尺多长的针灸,就要给我扎针,我哪敢依从,赶紧逃开。结果徒弟拿去给另外的客人行针,从肚脐眼进去,我感觉都要把人扎穿,后来才知道,这针虽长但软,顺着经络走,并不会一针穿过身体,扎个透心凉。
可不就是她?雷医生几年前出家,没有几年就当了曹洞宗祖庭的方丈,修复了庙宇,和湛云同时接了佛教高僧一诚老和尚的法,俩人算是“法兄弟”。现在此地已经算是江西省的著名丛林,据说那里出家的全是女众师傅,奉行的是古老的寺院规矩,不劳动不得食,全部自己种田,自己做饭。我馋,看了看当家师傅的朋友圈,正是盛夏,寺院正在吃莲子饼,诱人。
想什么来什么,还是有心电感应这回事,晚上就收到当家师傅的微信邀请,说是知道我在江西,这么近怎么不去一次?其实宝积寺距离景德镇也不是很近,开车也要四个小时,加上天气暑热,七月的江西,整个地气蒸腾,人走在路上,都是暗黑的一道影子,我实在是犹豫。但归根到底,好奇心还是战胜了懒惰,湛云开车和我一起过去,一路上热得奄奄一息,就连在服务站上厕所,也是快速跑进去,瞬间汗流浃背。
寺院远在抚州城的远郊,这里有两座名山,曹山和洞山,成了曹洞宗名字的由来。最早的寺院遗迹都已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之后就要复建,可是一直没有建设起来,佛教的不少高僧大德希望能恢复此处,还是时机未到。直到前两年,新出家的这位当家师傅有能力,各处化缘,没两年,烂尾工程成了新的深山名刹,这方丈也就自然是由她担任了。这种故事在佛教圈并不少见,外人听起来,完全云里雾里,但是在他们自己圈子里,却有着种种考辨,比如经费从哪里来,当家师傅能力何在,各路护法怎么捐功德,包括她在欧洲得了“著名佛教人士”的称号,一堆的琐碎细节,热闹极,懂行的人,可以写成论文,至不济,也是能记载成某高僧复建祖庭记之类的碑文,只是我不懂其中关窍而已。
看到新修寺院的一霎那,还是吃惊了。寺院并非端正的南北朝向,而是顺着曹洞两山之间的河流走势而建。两山并不高大,但山谷之间夹一溪流,溪流涌出山谷,成一大池,被稍加改建,自然堆砌成了硕大湖泊,映衬着天上的白云。我们去时正是暴雨之后,山谷隐隐有彩虹,地上白气上扬,简直是可以传说的神话胜景——到了门口,层层关卡,登记车辆,清点人数,井井有条。看门的老太太说着北方乡下口音,倒让人疑惑怎么千山万水过来此地,只做了看门这件事——不过也可见这里的信众来源颇为广泛。
一个小尼师在门口等我们,每人递上一顶斗笠,正好避雨。我后来明白,也是某种风格。当家师傅是要求风格化的典型,给我们看的寺院宣传片里,近百名尼众前几年重走三藏法师的西行路线,人人都戴着同样的斗笠,在新疆的沙漠中行脚,宽袍大袖,几十人一队,非常美观。浅薄的我,顿觉是从《笑傲江湖》里来的意象。
旁边有跟拍的摄像机,头顶还有无人机拍摄,可见现代佛教的宣传已经到了高超的地步。我们戴上斗笠往寺院里行走,也是照例。
小尼师倒是江西本地人,一本正经的脸,一板一眼如同照本宣科介绍本院历史。其实不用她费劲介绍,已经能看出寺院的不凡,唐代建筑风格,进门处有两个高大台阁,往里走也是处处唐风,大殿里的佛像也是翡翠雕刻,说是泰国信徒奉献的,可是搬到这里来了之后,翡翠的纯质地开始变化,不少佛像有了深棕色的痕迹,“这是显圣”。我木无表情地听着,并没有配合她。这个姑娘塌鼻子,胖脸,非常严肃,有种县城文化馆讲解员的气息,挺符合这里的。
白天帶我们参观的时候,小尼师还是端着的,因端着,简直觉得她有点气鼓鼓,想聊几句,她一律板着脸,给予标准回答,也许是因为我对她的“显圣”说法不够热忱的缘故。晚上喝茶的时候,她已经放下了拘束,跃跃欲试地想和我聊什么的时候,就变了样子,一副小城姑娘的可爱。可惜,还没聊开,当家师傅就进来了,小姑娘立刻恢复到讲解员模样,话题也没有打开,我倒是对她印象更深刻了。
终于见到了当家师傅。她的私人茶室需要穿过一片小山,又到一片小湖,湖上远远漂来两只黑天鹅,一见人就迎来觅食。远处草地上,是树木枯枝搭建的卧佛,也是涅槃之像,并非一般寺院的繁华装饰。到了这一步,才明白湛云的这位法兄,我的这位故人,确是当今佛教界的翘楚,绝非一般僧侣可比。
当家师傅穿了灰色僧袍,旁边有几位侍者,用水煮陈皮老白茶,这仅是迎客之茶。我们找座坐下,却又没多少可寒暄的,这时候我才知觉,事实上,我和她也真说不上多熟悉。问她为什么出家固然不妥,生活细节也聊不出来,真的就成了套话,但套话也还有趣,毕竟是僧家生活。
比如书房里一把价值不菲的古董椅子,所有的客人都要坐在上面拍照,是她这里的网红景点,窗外是一棵传闻中唐代就有的古银杏;她自己每天换一副眼镜戴,因为出家后,没有别的装饰物,今天戴的是白色板材的GUCCI眼镜;这里的饮食都是自己按照中医方子规定厨房制作的,食材都是自己耕种得来,我们可以试试盐姜之类的,本地小黄姜,据说吃了可以精神饱满,“大清早一人要吃五片,放在舌头下面,整个人都会支棱起来”。
闲聊中看不出当家师傅的厉害,不过人家也不打算显示。窗外的唐代银杏树和游来游去的黑天鹅就是最好的布景说明,资深道具师的设计,反正我是想象不出来当代寺院会是这样。聊完了继续参观,才看到前面说的尼众的“大漠行走纪录片”,还有景德镇政府送的瓷烧匾额,原来她带领医疗队去景德镇支援疫情防控,这是政府的感谢匾。
一切都做得那般完美俏丽,如模范生。
晚饭被师傅安排和她一桌。僧侣们有专门的大厨房,我们这是小灶,一会儿工夫上了一大桌,显然是熟练极了的。当家师傅是西北人,这桌除了各种本地蔬菜,还上了极大盘的面条,撑得不得了,但寺院的規矩是不能剩菜。我一面勉力吃着,一面和周围人交流着,师傅轻描淡写地介绍着:这位是某地首富,来这里帮我在县城义务建医院的;这几位是省里来的,某领导的孩子走路不行,来求我扎几针;这几位是县城来的,我们寺院周围的村子,规划到了“新农村建设”系统里,我要去省里帮他们跑一跑。虽在山中寺院里,可是满桌子花花世界的众生,法师还真没有拿我当外人,我不由反思,大约还是我没有明显的文人气息。
突然想起来,《红楼梦》里的一章,王熙凤进了尼庵,可不也是拜佛烧香加上密谋要紧事?几百年中国的寺院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当家师傅有她可爱的地方。尤其是和身边众多尼众一起,像个大家族,她就是大族长,坐在饭厅旁边的另一间茶室。她一会儿不要开空调,要她们把门打开通风;一会儿又嫌风热,觉得不舒服,慌忙着急地让人关门,一刻也不停缓。周围的女孩子们被指使得团团转,嫌她烦,轻微地发脾气,被她看在眼里,也像贾母骂小丫鬟们,把你们惯的——有种特别亲昵的家庭风格。
如果是个朴素的小寺院,大概我会喜欢这里。
这里的排场,让见识颇广的我还是觉得有点太大。晚饭后和当家师傅坐着电瓶车去村里游览,周围的乡村建设,一大半是她的功劳,无论资金、规划还是专业支持,随手一划,就是某片的房子要重建,再一划,就是哪几间酒店要重新装修,颇有指点江山的气势。我突然想起来,类似的尼师傅,还不止一个。某年去台湾,是和越剧名家茅威涛的小百花剧团一起去巡回演出,逛了二十多天,到了中台禅寺,出面招待的当家法师是茅老师戏迷,据说看了茅威涛的《梁祝》当下流泪,从此成了知己。
她从前是台湾一个大糖厂的老板,和我们见面说话,绝无客气,意思是只有她和茅老师是主人,我们都是随从,眼神一瞪,随员们就该退下。有位茅老师的助理,不识好歹,在她们说话时,上前多说了几句,当下就被她呵斥而退,等级森严到了一定地步,从小接受新中国平等教育的我们不由侧目而视。
非常有趣,和心目中的出家人完全两样。
茅老师可能觉得我是请来的客人,不便那么斥退,老是把我往前面推,我也就和这位法师多见了几次。她是何等精明人,看到茅威涛总带着我,也就假以辞色,有时和我聊几句,包括一起吃饭。我们是餐馆点菜,法师面前是若干盘精致的素菜,也不让我们。席间也是挥斥方遒,非常有力量,谈世界经济和政局,谈中台禅寺在台湾的地位——寺院位置在台湾最中间,当然是顶天立地——颇为男性化的陈述,基本上还是当大老板的谈吐。据说她的糖厂是家族产业,台湾三大糖厂之一,也不知道是什么机缘出了家。
这两位当家法师很有相似之处,是我们想象之外的出家人,但又是当代出家人的某种典型样貌。
中台禅寺的大殿,有两根漆成红色的沉香木柱,顶天立地,说是东南亚深山运来的,印象中非常高大,现在想想简直匪夷所思,怎么可能有那么粗大的原始梁柱?大约还是拼接?而主楼,是一幢二十多层的高楼,是台北101大楼的设计师的作品,今日回忆都是前尘往事,完全是“梦幻泡影”般的记忆——在回忆中完成了佛教的教理。
当然百年千年之后,这些辉煌大殿,精致空间,还是归于空寂的可能性多。
世人对僧侣的想象,多半还是限制在自己的见识里,其实越是名刹,气度和排场越是不一般,这也是另一种法度,在佛家世界也能讲通,因需要大家见识到佛法奥义,不仅仅是深刻的知识,还有表面的繁华,所以需要大殿的庄严法相,万千繁华。
只要是建庙宇,就是功德一件,再怎么奢华,也不为过。
有一年朋友介绍,让我去深圳采访一位老和尚,前提也没说清楚,只是说老和尚年纪很大,功德很高。我完全是佛教的门外汉,去了才知道,这座寺院,是深圳当地最著名的一座,位于植物园的山顶之上。我们夜间到访,坐着车上山,沿途的上山盘道上,都是磕长头的年轻人,一路磕上山去,完全不觉得这里是深圳,和拉萨也没两样了,旋即明白,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对寺院之类的宗教系统需求越大。
到了山上被安置在寺院的别院里,基本上等于一个宾馆,早上在阳台上站着呼吸新鲜空气,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对面的楼里,一排排的灰衣尼众联队而出,十人一队,跟着又是十人,足足有三四十队,几百人之众。我和朋友感叹,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尼姑啊,这可是盛况,短裙的灰衣尼众,走动规矩,如同水中穿行的某种影子。
陪着我们的志愿者告诉我们,这是专门来给老和尚贺寿的尼众,过两天要在贺寿大会上表演合唱的。这时候才知道,我要见的老和尚本焕,是佛教界的高僧,已经一百零四岁了。虽是高僧,但是世俗礼仪上的供养,还是人间模样。这个尼姑歌咏队的盛况我没有看到,想来也是不凡的。
见老和尚不难。老和尚虽然一百零四岁,终日还是见人,在寺院传法。我们和一堆人排队进入,老和尚摸头,给几个护身符,说什么都是眯眯笑,几乎无话。前面一队人据说是某地领导,进门就跪地俯身,老和尚也不例外地眯眯笑,摸头,念佛,对他们并不例外,倒真是某种程度的众生平等。
笑得也看不出多少喜悦,几乎疑心是某种固定的表情了,脸上全是皱纹,堆叠起来的年月日。在他自己的时间河流里,一波波的人,像我们,都是短暂逗留;最亲近的,可能也真是周围的人。
靠着这位老和尚,寺院的捐赠收入很高,这些收入又不断地用于建庙,在佛教界,这就是巨大功德。
晚上和寺院方丈聊天。方丈也是奇人,他告诉我,本来他在湖北老家当公务员,不知怎么在一次当地活动中,就被老和尚看中,不间断地要他来出家,每天一个电话,不停歇,换了电话号码,还是被老和尚挖掘出来,最后终于被度了出家。这个故事,也是我们普通人爱听的一类,显然他极聪明,知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方丈四十多岁,处于盛年,表达好,身体也好,有时候见他要深更半夜,不是怠慢我们,是真忙,从早上六点开始就接待客人。深圳最红火的寺院,热闹程度非凡,能奔来方丈室里的已是经过筛选了,可还是川流不息。各路贵人,有穿着香奈尔当季的贵妇人,愁眉不展;有带着一车水果的水果老板,堆在佛前的供果都是我们所不常见的品种和尺寸;还有大公司的老总,把一群中层干部带来,让方丈一一观望,看谁有善根,堪重用。陪着我们的志愿者是研究生毕业,小姑娘慢声细语,说是在这里当志愿者两年,之后也会被安排在这家大企业,“好多员工是我们这里推荐过去的,我们是相通的。”听得我一惊。
这才知道,佛教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还真是盘根错节地深入。
这两年,这家大企业已经濒临倒闭,不过按照佛教道理,肯定有另外一番讲究。
方丈不见疲倦,他是大高个子,红面孔,寺院喇叭里终日播放着他的讲经语录,我是外行,但也听得进去。到了极深的夜里,见了十几拨人,终于休息下来的他泡茶请我喝,给我佛前供果,是青色的皇帝柑。就没有吃过那么清甜的皇帝柑,大约商人们在外面再怎么滑头,到了这儿也变得虔诚起来。
他对我,也是一等一的待客规矩,我还是不满,想听更多老和尚的故事。可是听来听去,都是普通的事迹,也怪我年纪轻,听不懂,多年以后才明白一句,“老和尚最大的修行,是断念头。”
“断念头?”
“对。外界不管怎样的浪潮汹涌,他不受影响。”
后来才想明白,这大概也是某种思想上的超人。老和尚还真是高人,“断念头”说易行难,最通俗的诠释,应该是在《盗梦空间》里:你越不要想一件事,你就越要想那件事。
要切断的念头,在我们俗人的心里,会重如泰山。
红头胀脑的方丈一天接客十五六个小时,天天如此,估计也有他的能力。这种接待,说不定对他也是一种修行,在深圳这个繁华世界里,这种修行是加了倍速的,凭空增加了。
简直有点像赛博世界里的宗教——我无法抑制自己这么想。
大约中国的僧侣,时间长河里摸爬滚打,都被修炼了出来。中断过几年,可是并没有大影响,行走的还是人情世故的江湖规矩,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都能被他们仅靠言语就笼罩住。
还是那句话,既然面对世间人,就要行世间法。一个繁华的寺院,也是分工严密,门口的接客僧不用说了,禅堂、厨房、后勤都各司其职,必须井井有条,越是大寺院,越是如此。行使实际事务的方丈基本等于世俗企業的CEO,庙宇的大小不得靠他们的能力?
想象中藏于深山的高僧,只恬淡地诵经说法,大概还是我们的天真。幻想出家能摆脱俗务,更是幻想。一百零四岁的本焕老和尚还要每天见客,完成某种佛教界的功德,也是“大成就”,在寂灭之前,添砖加瓦做贡献,倒是比世间人还要劳累。
前些年和朋友去见的另一位高僧,瘫倒在床上,也要替庙宇做贡献。
前年中伏的头一天,和朋友在北京西站坐上开往山东的火车,去山东看一位寺院里的老师傅。火车票难买,因是去往青岛的方向,无数的人,熙熙攘攘,裹挟着我们进站,裹挟着上车,前座的两家浙江人热烈地讨论着他们过去几天的经历,故宫不好玩,住宿不舒服,烤鸭不好吃,都是拒绝的态度,可还是兴高采烈地说着,近乎嚷,微妙地比较着两家人谁更会花钱——似乎都不是有钱人,还是努力高傲地表示自己花得起。高铁上的服务员显然看出他们的生命态度,热情推销列车模型,盒装的死亡的水果,还有油污的盒饭,一切需要不需要的东西。
有这些个鲜活的生命大肆发声,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模糊状态,想到那俳句: 露水的世啊,虽然是露水的世。
朋友是画家,说起她和老师傅的因缘。她十四五岁的时候,老和尚经常去她家。家就住在寺院旁边北京南城的胡同里,老和尚每天在她家写毛笔字,一写一堆,忙忙碌碌要送人。她家是书画世家,笔墨纸砚都齐全,外加自己的母亲经常和老和尚谈论书法,一待就是一整天。老和尚要不就是写字,要不就是忙着帮周围邻居皈依,后来连她家的狗都被老和尚皈依了——一点不记这条狗咬过他的前嫌。
十五岁生日,老和尚说要帮她皈依。大清早,家里人就开始准备净素斋饭。她说我去买酱油啊。逃跑了,一整天不回家。老和尚带着两个徒弟,阵仗不小地来了,结果硬是家里找不到她,只剩下母亲道歉,这孩子,太不懂事。
老和尚说没事没事,机缘没到。
老和尚在北京的道场是著名寺院,大约前二十年的样子,有个外地的工程师出家,拜老和尚为师傅。也是缘法,这徒弟出家后动员老和尚去山东中部一个县城的荒山野岭重新恢复历史名刹,虽然辛苦,也是大功德。老和尚真去了,也就是我们今天到访的寺院。后来到寺院里,我们看到十六年前老和尚刚到这荒山野岭的照片,才知道他当年面对的世界。此地实是荒凉,不仅片瓦也无,而且植物稀少。北方大山特有的苍莽感是靠山石生成的,这山只是土堆,反正什么也不是。
就是随随便便的土堆,山脚下数间破房,甚至连山都算不上,从没有在古画里看过这么寒酸的山丘。但此地又真的是山,北方的、平实的、残疾般的山。
照片里老和尚表情严肃,眉间有隐忧,显得心事重重。荒山背景里也没什么植物,越发显得童山秃岭。
梁朝的古老寺院选址在这里,想来当年的地貌要好许多。不过在这里重新建寺院倒是有故事:老和尚的徒弟用《大悲咒》给当地村民治病,村民病好了,强拉着和尚不愿他离去,徒弟于是发愿留下。后来老和尚查了古籍才知道,此地并非无来历。
徒弟也是能干,十多年下来,这里已经是当地著名的寺院,上网一查照片,金碧辉煌,巍然一座北方大丛林,当然老和尚的住持应该是能增加不少分量。现在这寺院已经成为当地一景,招待各方来客,难得的是,住宿、吃饭都是免费,一看就是那种发宏大愿渡众生的地方。不过说实在话,我还是害怕人来人往的庙宇。
去之前给寺院打电话,问还能见到老和尚吗。
能,最近身体还好,能见上。
朋友所以订了大伏天的票去,也是因为害怕老和尚身体慢慢不好。去之前,我俩一路玩笑。
要是这次让你皈依,你皈依吗?
皈。
他还能认出你吗?
应该行,我把手机里他写给我的字给他看。
他怎么就留在山东不回北京了?
我也不知道,去年听说他去世了,后来知道是谣传,这次才急着想看看他。
朋友的神态是有点焦虑的,一点没有平日洒脱的样貌。老和尚今年九十多了,谣传去世的消息不止一次听说,还是赶紧去的好。去寺院的头天,住在附近的城市,倒也没有焚香净身。我们愉快地吃了顿鲁菜,吃到有生以来最好的九转大肠,不太规整,一小截一小截地端上来,乌黑的团子,像是没完成的作业,偷工减料的。可入口就很狂喜,焦的,嫩的,膨胀似的在嘴里变成一体,不愧是本地佳肴。
内脏菜,不能细想,只能如狼似虎地去吃。
晨起大热,寺院距离城市也有一小时路程,沿途都是特定的乏味的北方城市,也懒得往窗外看。爬上山,汗透了,天气把人用金钟罩罩住了,一点不松快。
荷花倒是开得好,一盆盆种在龙盆里,摆在房前屋后,像农家院落,又是想象出来的超豪华的北方农村院落,一体的金色琉璃瓦屋顶,一路迤逦上山。要是有个大水池就更好看,规划时可能没想到,全部是骄阳下面的大广场,毫无遮阴,热得通透,估计是参照某些恢弘的传统建筑。我们急着见师父,跑到客堂,像个大公司的办公室,井井有条,也是新派寺院的一景。
排队办事的,在我们前面有个年轻人,黄脸,枯瘦身材,不知怎么显得不上品。一口当地话,显然是熟客,经常来寺院里住,点名要住山上的房子,不住在门前招待所般的大楼里,完全不符合我心目中清修的居士模样。
看来这里的免费住宿倒是真的,流传甚广。我小小地为自己的分别心检讨了下。
眉清目秀的知客僧倒是有礼貌,约时间,说是老和尚需要午休,可下午见面,我俩心里都徐徐出了口气。这时候也想去吃免费饭,说赶紧去,晚了就没有。去了还真晚了,只剩下粗糙的馒头,还有西紅柿豆腐杂菜汤,切成小块的西瓜,入口就知道难吃。有次去韩国寺院里吃饭,也是一堆素菜拌饭,也有辣酱,类似石锅拌饭,蔬菜也不可谓不新鲜,可不知道怎么就特别难入口。当然佛家要弃绝口腹之欲望,这样饭菜应该是对的?
也难说。有次去福建山里的寺院,完全是路过,饿了,进去吃斋饭,大白菜炒年糕,鲜美到吃了两大盘,厨房的师傅还一再抱歉,说东西太少。也许是南北不同?吃完饭,胡思乱想着,在太阳下面逛了一圈,越往山上走,越觉热得难当。
只能逃回客堂。知客僧说帮我们问问能不能提前,还真能。开了路条,我俩一路往半山爬去,老和尚住在最高处。以他的年纪,行动都难,看来已经不常下山。山上建筑也是金碧辉煌,我们气喘吁吁,爬到老和尚那幢楼前,空寥无人,只能自己推门进去,再上到二楼,出来一个广东僧人,不仅是口音,长相也像。
他就是照顾老和尚的侍者,双方客气鞠躬,把我们引到窗前,说,看吧。
大吃一惊。此时方知,老和尚已经卧床多年,所谓身体还行,是躺在床上隔窗探望他的还行。细看,老和尚已经不能说话,食管已经做了手术,吃东西都靠打成糊糊,做鼻饲,嘴巴一张一合。侍者说,这是在念佛,看起来,也就是平常的喘息。
生命的绝望,倒是不分僧俗。到了这个阶段,我不太能接受侍者的说辞。这广东籍贯的僧侣倒是能言善道,说老和尚受到的照顾无微不至,吃的什么,排的什么,都要记录在案,上交中国佛协,应该也是老和尚德高望重。
这种看望,大约在一般的寺院里,都属于探视者的福分,粤僧开始滔滔不绝说见了老和尚就属于有福气。想起本焕老和尚,反正见了,见的人履历上多了一些什么,至于那些老僧人究竟能给见的人增加什么福报,我是存疑的。
朋友已经眼中有泪,都没想到是这种场面。也不知道老和尚神智如何,不过即使清明,也不可能有什么交谈了。默默在窗外拜了拜,仓促逃出,一路无话。
过了半天,想了一句,老和尚现在这个状态还在人间驻留,想来是今生的业要彻底了结?也许是我太着相?佛教讲佛本尊的七十二相,临死的时候,不也有垂死之相?甚至有骷髅相示人。老和尚一息尚存,总有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