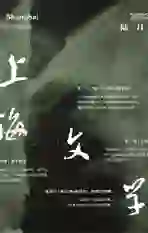父亲的地图
2022-06-28樊健军
樊健军
在父亲失踪多年以后,我依然清晰记得,那一夜我躺在阒寂的黑暗中整夜不曾合眼。第二天,我终于实施了蓄谋已久的计划,偷走父亲那张精心绘制的地图。
那是六月的第二周,父亲周五一大早就出门了。我被他弄出的响声惊醒。透过窗户,我看到父亲同往常一样戴着草帽,挎着暗红的泛着油光的用竹篾编织的工具箱,一瘸一拐朝村口走去。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劁匠,手艺是全能型的,劁猪骟牛,阉鸡阉鸭。在给动物绝育的行当里,没有他干不了的活。
每次父亲走后,我都会趁人不注意,悄悄溜进父亲存放工具箱的屋子。那间屋子一半空间是农具的领地,另一半空间被一只巨大的木桶占据,那是储藏杂粮的仓库。装猪油的瓦罐和腌酸菜的坛子,被母亲放置在角落里。这些不是我关心的,真正吸引我的是北墙下那只孤独的大木箱。自从发现那是父亲收藏私人物品的宝库后,我经常浮想联翩,幻想有一天能够打开它,一看究竟。
有段时间,我热衷于收集废钥匙,为的是能打开木箱上扣着的铁锁。现在,我不怕有人向父亲告密。我找到了那把钥匙,并且用它开启过那只大木箱。那里面毫无秘密可言,除了工具箱外,偶尔会发现一两包香烟,或者半瓶白酒。我尝试抽过他的香烟,也品尝过酒,这两样东西差点呛坏了我。还有几本账簿,记录的是别人的赊欠,对此我也不感兴趣。至于那只竹篾编的工具箱,我当然不会放过它,打开后只见里面放着无数的小布包。布包包裹着闪着寒光的刀具,形状怪异得很。总之,父亲从事的是个不怎么光彩的职业,始终无法令我骄傲。
在父亲的大木箱里,唯一牵动我的是那张用羊皮制作的地图。那张地图我只见过有限的几次。那个周五,在父亲走后,我蹑手蹑脚溜进了那间屋子。我用捏在手心的钥匙,小心翼翼地开了锁。正如我猜想的那样,父亲的工具箱不在大木箱里。叫人意外的是,那只灯芯绒袋子卧在一角,那是父亲央求母亲缝制的,用来保护地图。我解开袋子,拿出地图,摊在箱盖上粗略看了看。没错,地图还是原来的模样,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我将地图收进袋子,将袋子放回原处。
当天晚上,在确认父亲没有回来之后,我再次潜入库房,将那只灯芯绒袋子拿了出来。我已经想好了应对的策略,万一被父亲发现,我就躲得远远的,他不可能追得上我。第二天早上,我将书包倾倒一空,放进地图、两根黄瓜和平时积攒的零食。早饭后,我背起书包,在母亲的眼皮底下走出家门,往村口的方向走去。
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我肯定被许多人看见了。我按照惯常的步调,不急不慢地朝东走去。我沿着河堤往下游走,在枫杨树的庇护下,终于找到了一处安静之地。我迫不及待地拿出地图,铺展在干净的草皮上。之前我浏览得不够细致,因为那时心是悬着的,生怕被父亲抓着。我对地图的大概是了解的,至少从中读出了不少信息。那是一幅怎样的地图呢?柔软的羊皮上全是黑色的线条和红色的小圆圈。它们以用双重红色圆圈标注的水门村为中心,一圈一圈朝外发散、拓展。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村庄,像红色的果实一般被串了起来,东南西北,每个方向都有一串果实。南边的那串最短,只有三两枚,再往南,就是层峦叠嶂的深山区。往东的那串最长,经过三四个村庄后到达水门镇,再往东经过五六个村庄就到了洋湖港。洋湖港往东只多出一小截黑线,黑线的尽头是未知区域。这是最诱惑我的一条路线。我要到洋湖港去。我听父亲说过,洋湖港有马戏团,广场上每夜都放电影,幕布比一整面墙还宽大。父亲说过要带我去,可是一次也未能兑现。
我要到洋湖港去,我不相信没有父亲带路就找不到它。
从村子到水门镇的这段路,我已经驾轻就熟。我走过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到达水门河的北岸,然后顺着河堤往下游走。快接近镇上时,拐入北岸那边的村庄,抄近道继续前行。
第一次去镇上是父亲领我去的。那时我只有七岁。父亲兴致特别高,编了很多动听的理由,蛊惑我跟着去。父亲的举动很反常,往日出门时总是走几步朝身后扫一眼,担心我们会跟着,可一旦发现没人跟随,又很失望。久而久之,我对他的外出不再在意。我对水门村外的世界也因此一无所知,不怎么感兴趣。我的乐趣在于捕蝉、掏鸟蛋。但后来,我还是听从母亲的劝说,跟随父亲去水门镇赶集。那天镇上非常热闹,街道上熙熙攘攘全是人,到处都是叫卖声,到处都在讨价还价。父亲拉着我的手,在人堆里走来走去,最后给我买了肉包子和几颗糖果。我忘记出发之前父亲给我许下的承诺,但味蕾的记忆是最可靠的,以至于后来我只要到了镇上,必定会到包子铺前逗留。
到达镇上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许多。我并不慌张,如果当天不能从洋湖港赶回来,大不了在路上睡一晚。我选择这个季节出发,是因为白昼拉长了,天气也热。我跑到那间包子铺,用攒的零花钱买了两个肉包子,之后便朝镇子的东头走去。父亲在地图上没有注明水门镇到洋湖港的距离,我只是根据两地间隔的村庄来判断。
父亲为什么没有在地图上标注距离的远近呢?是他疏忽了,还是根本不在意路程的远近?父亲不是一个细心的人,他总是漫不经心的。这才像父亲画出来的地图。当我抵达镇东头时,发现地图上的缺陷远不止这些。摆在我面前的有兩条路,一条偏东北,一条偏东南,而地图上的黑线只有一条。起初,两条道路相距不是很远,但在往前伸展时彼此变得遥不可及。我仔细察看父亲画下的地图,希望能有所发现。可是沮丧得很,除了线条和圆圈,地图上再无其他参照物。我熟悉的水门河不在其中,况且我也不清楚它会不会流到洋湖港。
我踌躇了,不知该走哪条路。两条道路一条很宽,一条很窄。窄的那条连着许多村舍。父亲走的是哪条呢?想到父亲作为劁匠,需要走家串户,他八成走的是那条窄路。我不想重蹈他的辙,便踏上了那条往东北伸展的沙子路。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的选择纯粹是自作聪明,我走了大半个圆圈才到洋湖港。但那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些。道路进入丘陵地带后,我渐渐被周围的景色吸引。那些丘陵都是红砂岩,岩顶光秃秃的,呈红褐色。丘陵绵延起伏,一眼望不到边。低矮处是郁绿的马尾松,松针在阳光下泛着油润的光泽。我暗暗责备父亲,为什么不在地图上画上一些特殊记号,表明这是丘陵。我再次打开地图,试图寻找自己所在的位置,遗憾的是,我怎么也无法确定自己在哪儿。
父亲花费了好长时间来制作这幅地图,好像在我六岁那年,某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张羊皮。他找来几颗钉子,将羊皮固定在门板后,在空气中暴晒了一阵子。父亲用力握着钢笔,像雕刻一样在那张硬邦邦的羊皮上画下一个个红圆圈。那一次,他画上去的内容并不多。后来,每次外出回来,他必定会摊开羊皮,添加几笔。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父亲以罕见的耐心和细致来描绘和完善那幅地图。那时候,我压根不知道父亲画的是什么,更不知这有什么用。我曾冒失地问过父亲在画什么,父亲的反应很紧张,立刻将上身俯压在桌子上。他就那样侧着脑袋,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说,长大后你就会明白。直到我上小学三年级,我才弄清楚父亲是在绘制地图。
父亲到底为什么要画那样一幅地图呢?每次偷看时,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我暗自猜测,父亲绘制的有可能是作为劁匠的职业地图,是他在羊皮上宣示的势力范围。除此之外,地图还有别的作用吗?我不敢向父亲求证,也不能确定是不是这样。
路上极少能碰见行人,这样的日子,人们多半在田里劳作。我走在丘陵中间,脚步声在红砂岩之间回响,好像身后跟着无数个像我一样的少年。這条路到底能不能到达洋湖港?我萌生去洋湖港的念头,完全是被父亲的话给诱惑了。我想去看马戏团的演出。
我头一次看马戏团,是在水门镇。我从母亲那里讨要到门票钱后,心急火燎地跑到镇上。马戏团的节目异常丰富,那些老虎、狗和猴子特别乖巧,始终拽着人们的目光。掌劈巨石的和赤身滚铁钉的,看得我瞠目结舌。有个表演马术的小姑娘,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穿着一身红衣服,在一匹奔跑的白马上翻飞。
所以当父亲说洋湖港有个更大的马戏团,我对那里充满了向往。我相信父亲的话,因为他去过洋湖港。有一次,父亲从外面回来,比预期晚了两天。母亲问他上哪儿去了,父亲说走错路了,走到了洋湖港。父亲在一个村子里给人家骟牛,可能是活儿干得漂亮,主人家热情地挽留他喝了两杯。父亲喝醉了酒,结果走错了路。最终他走到了洋湖港。走到那里,父亲无处可去了,于是在洋湖港的码头上睡了一晚。
我怀疑父亲去过洋湖港不止一次,他很可能隐瞒了什么。从他的遭遇来看,他不可能有闲心去看马戏团的演出。他在羊皮上画下洋湖港的标记后,地图就停止在了那里。标识洋湖港的圆圈,加上后面的墨线,有点像个问号。那根墨线的下面还有一大块空间,一直是空白。
天气越来越热了。我的衣服汗湿了,贴在皮肤上,火辣辣的。我朝远处张望了两眼,阳光下到处都白晃晃的。我停下脚步,躲到了一棵松树下。我吃了包子,啃了一根黄瓜,才感觉好一些。
我休憩了小半天,重新上路。上路前,我找到一处小水沟,掬了两捧水,洗了把脸,把头发也给浇湿了。在树荫底下,我大约步行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走出了丘陵地带。眼前豁然开朗起来,道路往郁绿的稻田深处延伸,路边傍着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流动缓慢。我没那么燥热了,脚底下也有些松懈。如此走了三四里地,又到了岔路口,道路一分为二,一条往北,一条往南。
我走上了往南的沙子路,脚步不急不慢。走了一会儿,脚板有几个地方火辣辣的,估计是磨烂了。我在一棵乌桕树下坐下来,脱下球鞋察看,果真起了好几个血泡。我走路的姿势很可笑,一颠一跳的,脚掌一碰地就痛。幸好阳光没那么炽烈了,还有轻微的风吹来。就在我沮丧得快要绝望时,身后传来了马蹄声。我回过头去,真的有一匹马朝我走来,是一匹棕色马。赶马的老头戴着草帽,自在地坐在车架子上。我停住脚步,等候马车经过,盼着赶马人带上我。但马车不像我期望的那样停下来,而是保持原有的速度。赶马人舒服地靠在车帮上,闭着眼,好像睡着了一般。我勉强跟着马车走了一会儿,很快被拉开了距离。我放慢脚步准备放弃时,马车忽然停住了。赶马的老人朝我招手喊道,上来吧。
那架马车实在太简陋了,就一个凹字形车厢,前后连挡板都没有。车厢里空空荡荡的,除了一小堆干枯的稻草外,什么都没有。老人让我爬到车厢里,坐在稻草上。车厢大概拉过猪,稻草上散发着一股猪粪味,我忍受了下来。比起脚掌带来的痛苦,显然刺鼻的猪粪味要轻得多。待我坐定后,马车又开始运动了。老人穿着黑色上衣,脖颈上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盐白。
你要去哪里?走了半天后,老人才回头张望我一眼。
我要去洋湖港。
洋湖港啊……那可真是个鬼码头。老人的声音飘飘忽忽,像甩动的马尾巴一般捉摸不定。
我怔怔地,不明白他什么意思。
你是谁家的孩子?老人又回头觑了我一眼。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小声地说出了父亲的名字。他是个劁匠。我又补充说。
拐子啊……我认识,别介意,我们都叫他拐子。我还请他劁过猪阉过鸡呢。老人将草帽摘下来,递给我,示意我戴上。他又说,他是个很有趣的人,会讲笑话,会喝酒,喝醉了酒话就多。有次喝醉了,他向我借马,说是要骑马去北京,骑马去周游世界。他还没有爬上马背,就摔倒在地上,差点被马蹄踩伤。
父亲的行为叫我无地自容。我很是诧异,父亲是这样一个人,好像同在家时完全不一样。在家里,面对母亲的毒舌,父亲总是无言以对,不要说反抗,辩解的话都说不出几句。在愤怒的母亲跟前,他永远忍气吞声,甚至都不及一个孩子理直气壮。
我在距离洋湖港三四里地的位置下了车。赶马的老人邀请我到村里去,我谢绝了。他问我去洋湖港干什么,是不是去走亲戚,我含糊其辞地应答了。他扬起马鞭指向洋湖港的方向说,没多远了。我多么渴望同他一起到那个村庄去。在跳下马车的一瞬间,我几乎把他当成了亲人。我很感激赶马的老人,毕竟他捎了我这么远的一程,让我少受了许多苦楚。我瞅着马车慢慢变小,变成一个黑点,最终消失不见。
趁着残余的光亮,我加快步伐朝老人提示的方向走去。父亲第一次来到洋湖港也像我这样吗?大概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把灯火中的洋湖港误认为水门镇了。赶马的老人没有骗我,不出半小时,洋湖港现身在暮色中。那条沙子路径直深入洋湖港的中心,路两旁的建筑同水门镇没什么区别。低矮的瓦房,黑黢黢的,房屋里的情形一点儿也看不真切。孩子们在空旷之处跑来跑去。有些高大的身影在走动,昏黄的灯火充当了放大镜,把它们幻化得像巨人般魁梧。没有人在意我的到来,有个孩子跑到我面前,可能发现我不是他要找的人,随即又离开了。饭菜的香气随着晚风飘过来,加深了我的饥饿和疲惫。我的鼻孔酸酸的,眼睛也酸酸的。我差点哭出声来。
夜色把我合围了,我茫然无助,不知该往何处去。那些如豆的灯火好像被风吹动的浮萍,散落得四处都是。沒有哪一盏灯火是我的。我机械地走在路上,很快来到十字路口。我置身的这条道路笔直往前伸展,借助灯火的光亮,有一段能够看个大致的轮廓,再往前,就全是黑暗了。我很想找个人问问,广场在哪里。我猜想,不管是放电影,还是马戏团的演出,只有广场才能容纳那么多人。我环顾四周,希望有个人走近我。但真有人走过来时,我又羞于问询。最终,我往左拐入了一条横亘的街道。因为在它的远处,密集的灯火把天空染上一道光晕。
一股按捺不住的激动在内心翻滚着,我向那道光晕飞奔而去。那一定是广场,说不定马戏早已开演。我心急如焚,感觉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可受伤的脚阻碍了我,我没法跑得更快一些。那条街道超过了我预见的长度,光晕之处总是遥不可及,有几次觉得快到终点了,可仍旧差一截距离。有一个好的迹象出现了。街道两旁的灯火越来越亮,晃动的人影也多了起来。我气喘吁吁,脚步不自觉慢下来。我嗅到空气中有股不同寻常的气味。是鱼腥气,越往前越浓烈。对鱼腥气我并不陌生,水门河里就经常弥漫。我的鼻子告诉我,前方一定是河流。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是水门河的下游,河流在这里拐了个弯,像网兜一样把洋湖港给兜住了。
可能是夜色渐渐深沉的原因,那道光晕亮堂了起来。往前走没多远,一个光明的世界出现在我眼前。这个世界一半是地上的,一半是水上的。地上有一排低矮的棚屋,此刻躲在阴影中。它们的门前立着高高的灯柱,灯柱上的灯光全都呈扇形射向河面,也照亮了棚屋前宽阔的场地。在这里走动的大多是光着膀子的男人,有的三两一桌围坐在棚屋前喝酒,更多的是扛着木头往河堤下走。这段河流几乎被漂浮的树木覆盖,有些男人正用抓钉和绳索将树木捆扎成木排。河水在木排的空隙间荡漾,波光闪闪。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大声说话。间或夹杂着女人的尖叫,之后便是半真半假的咒骂和让人脸颊发烫的欢笑声。
粗略看去,这个世界如此混乱不堪,但是什么都没有耽搁,事情井然有序地进行。我站在这个世界之外,不敢贸然走到灯光下去。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好像只要被灯光照亮,我就赤身裸体了。我又不愿意走开,好像被诱惑、被牵扯了。父亲看见这一幕时,不知是怎样的感受。他为什么跑到洋湖港来?大概是对在乡村转圆圈的生活感到厌倦了。否则,真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我躲藏在一座无人的棚屋下,看着这一切。
这种熔炉般的场面持续到下半夜,才慢慢沉寂下来。场地上原先堆放树木的地方有好几块空了出来,树木都被放逐到河里,成了漂浮物。那些光膀子的男人一个个扎进河里,做一天最后的清洗。从河水中爬上来后,有的男人钻进了棚屋,有的躺在水边的石头上,还有的干脆躺在那些木排上。灯柱上的灯光几乎同一时间熄灭了,仅仅留下一盏马灯,半晦半明地照着码头。很快鼾声四起,整个码头像是口滞留了无数青蛙的池塘,蛙鸣泛滥。
场地上燃着几堆驱蚊的烟火,安静的河面上间或传来一两声水花的响动,那是鱼在跳水。我在距离烟火不远处找到了一块空着的石头。石头很宽,容纳我瘦小的身体绰绰有余。父亲那次肯定也是睡在这些男人中间,我猜测,他可能想成为其中一个。在他们中间,父亲会不会像个多余的人?他会不会同他们讲笑话,同他们一块儿喝酒?我得不到答案。在黑暗中,我默默嚼着干粮。
那个叫小乐的男孩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看清楚。当我发觉石头边立着一个黑影时,我委实吓坏了。我把他当成了从河里爬上岸的水鬼,一动也不敢动,更不敢叫出声来。我记起了赶马老人说过的话,现在已经应验了。我越发确信他是个湿淋淋的水鬼。我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别怕,是我。那个黑影可能察觉到了我的紧张,说话了。
谁?周围的鼾声此起彼伏,我稍微镇定了些,壮着胆子问。
我是小乐呀。那个黑影说。
听他的口气,好像我该认识他似的,八成他将我当成了放排工当中的一员。有谁想到一个陌生的少年会混迹于他们当中呢。后来,我才明白,是我霸占了小乐的石头床。我往旁边挪了挪,让出一块位置。我们并肩躺在石头上,仰望着夜空。夜空里有些散落的星星,有的明亮,有的暗淡。小乐的个子同我差不多高,叫人很难相信他是个放排工。可能是夜晚气温下降,加上河风吹拂,我接触到小乐的身体时感觉有些冰凉,像是触摸到冷血动物一般。
那个晚上我几乎没有入睡。小乐是个挺热情的人,不停地同我说话。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水门镇的,他说他的姨娘就嫁到了水门镇。他又问我,为什么到洋湖港来。我说来看马戏团的演出。小乐挺惋惜地说,你来得不是时候,上个月他们就走了。小乐的话至少证实了父亲不曾欺骗我,马戏团确实来过这里。我反问小乐,怎就来放木排了?小乐静默了一下说,我都十六岁了,怎就不能来?又说,我是来顶替我爹的。小乐的父亲有次扛木头时不小心滑倒了,被木头砸伤了腰。往后都是小乐在说,说他放木排的经历,说他到过石歧湾。我问他石歧湾在哪里,他说从洋湖港顺流而下,第一站就是石歧湾。我又问到石歧湾有多远,他说放木排一天就到了。我只是“嗯”了一声。后来,他说起了放木排时的趣事,但丝毫没能吸引我,我的脑子里分明有一艘木排在漂流着。
黎明时分,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可能是太困了,我睡得很死,也没做梦。我好像听到一声巨响,才猛然惊醒过来。我揉揉眼睛,怔住了。码头上空空荡荡,除了几个清扫垃圾的女人外,见不到其他人影。小乐不在。那些光膀子的男人都不见了,河面上漂浮的木排也不见了。我莫名地空虚起来,眼睛都不知朝哪儿看。如此发呆了一小会儿,我做好打算,先去河边洗把脸,再到其他地方转一转。就在我往河边走去时,一艘木排缓缓驶入了我的视野,一个光膀子的男人握着篙立在排头。小乐站在木排中间朝我招手。那一瞬间,我什么也没有想,脑子是空白的。我奔下了河堤,一个箭步跳到木排上。
就这样,我在小乐的怂恿下,踏上了去石歧湾的旅途。沿岸随处可见枫杨树和翠竹,同我在水门河里看到的没两样,只不过河床变宽了,水更深了。河水绿幽幽的,只有在下险滩时才会卷起白浪花。立在排头的是小乐的叔叔。木排经过急水滩头时,他最紧张。他将竹篙顶在岸边的岩石上,用身体死死压住竹篙。小乐守在排尾,学着他叔叔的样子,努力撑着竹篙,让木排距离岩石尽可能远一些。每逢这种时候,木排动荡不安,我的内心也跟着动荡起伏。木排冲上浪尖时,我的心也跟着飞上了浪尖。出了险地,河段平缓起来,有他叔叔照看就行。小乐得空了,挨着我坐在木排上,小声说着话。天空上的云朵在河水里留下洁白的倒影。从河面上吹过来的风很凉爽,带走了我们身上多余的热量。
午餐在木排上进行,吃的是小乐他娘烙的荞麦饼。这中间,好像奇迹发生了一样,有只翠鸟落在木排上,沒待几秒钟又飞走了。我问小乐,石歧湾的下游是哪里?小乐摇了摇头,稍后才嗫嚅说,这个要问我叔叔。
傍晚时分,果然到了石歧湾。老远就见到一处河湾,像是大河伸出一条手臂,臂弯里密密麻麻泊满了木排,一艘挨着一艘。因为到得比别人晚,我们的木排只能停泊在外围。待小乐和他叔叔固定好木排后,我们踩着别人的木排上了岸。石歧湾不大,形状像把锤子,同河岸相通的是一条笔直的街道,仿佛是锤子的柄。街道也不宽敞,两旁都是门面,杂货铺、饭铺、渔具店,什么店铺都有。小乐的叔叔走得很快,眨眼不见了踪影。小乐陪着我,慢慢沿街行走。一路上,小乐絮絮叨叨,说哪家店的饭分量足,哪家店的女主人热情。主街走完了,那锤子的部分是居民区,我们就止步了。返回时,小乐请我在一家馄饨店吃了一碗馄饨。我们就着馄饨汤吃了两张荞麦饼。
回到河岸边,小乐找到了一块石头,我们像前一晚一样并肩睡在石头上。这一晚我睡得十分香甜,第二天早上,太阳升得老高了才自然醒来。小乐不在身边,估摸是回木排上了。可是,当我朝河湾里张望时,才发现木排全不见了,一艘也没有。我呆住了。我在河湾里守候了一上午,小乐和他叔叔始终没再出现,十有八九是抛下我走了。
从石歧湾返回时,我怕走错路,用了一个最笨的法子。我沿着河往上游走。河流从哪里来,我就往哪里走。我蹚过溪流,爬过山崖,也走过了沼泽地。饿了,就摘一些河岸边的瓜果为食;困了,就在草丛中睡上一觉。我的裤管被荆棘撕裂了,成了一根根布条子。有一次,我以手当脚爬过悬崖时,险些掉进下面的深潭里。又有一次,我被一条野狗追得慌不择路。在路上,我邂逅了放木排的队伍,他们像一条巨龙,浩浩荡荡,逐河而下。这让我更加笃定,确信自己没有走错路。
我足足走了三天三夜,终于回到了洋湖港,回到了洋湖港的码头上。
在我知道父亲画的是地图后,曾问过他画地图干什么。父亲怔了一下,过后脸上浮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羞涩。他说,有了地图,你就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记得当时父亲是这么回答我的。我也理所当然地想,父亲是害怕自己会迷路。
回到洋湖港,我在同小乐一块睡过的石头上歇息了一阵。我没有记恨小乐,他没有理由带着我这个累赘。恢复体力后,我离开码头,走上那条回水门镇的沙子路。
进入水门镇,我的内心忽然不安起来,先前不曾想过的一个问题,这时死死地缠住了我。离家这么多天,同谁也没打过招呼,不知父母会如何惩罚我。我磨磨蹭蹭往回走,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才能逃脱即将降临的厄运。到达村口时正是半下午,我躲进河堤上的柳树丛中,直到太阳落山,才慢慢腾腾走回家。家里冷火寂烟,感受不到丁点儿温暖的气息。父亲和母亲相对而坐,守着一盏摇曳不定的灯火,妹妹被母亲抱在怀里,弟弟挺懂事地靠在父亲身边。我故意弄出一点响动,让他们注意到我。那一瞬间,泪水在母亲脸上汹涌泛滥,她放下妹妹,像老鹰一样扑了过来。
第二天,父母没有教训我。
第三天,依然风平浪静。
后来,我从别人嘴里了解到,我离家出走的那天晚上,家里炸开了锅。到半夜里,我仍旧没有回家。整个村子都被惊动了。人们四处找寻,不放过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甚至打着手电筒,沿河而下搜寻。他们做了最坏的推测,我一定是溺水而亡了。最终,他们在水门河里也没能找到我。几天过去后,我的家人都已经绝望了,认定我不在人世了,甚至尸体都没能留下。当我死而复生出现在父母跟前时,他们除了喜极而泣,哪里还记得惩罚我呢。
我特别留意父亲的一举一动,他只是用锥子般的目光盯着我,既没有冲我吼叫,也没有采取更恶劣的行动。他甚至没有立即追讨他的地图。我猜想他一定打开过大木箱,早已发觉地图不在里面了。他可能不想引火烧身,如果要追究责任,他的地图才是引发我出走的罪魁祸首。母亲若是知道了真相,她情愿父亲带回来的是牛睾丸,也不愿意是一张该死的羊皮。在这点上,父亲是我的同谋犯,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在母亲跟前保守了这个秘密。
几天后的晚上,父亲同我有过一场谈话。他把我拽出门,带到了村后的稻草堆后。他在地上铺了一层温软的稻草,将那张地图摊开在稻草上。然后,他开始审问我。那些天到底去了哪里?拿走地图干什么?我知道隐瞒不过,便将事情的经过删繁就简告诉了他。父亲用手电筒的光锁定洋湖港下的那根黑线,另一只手捏着下巴,沉思起来。片刻过后,他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哪里知道的石歧湾,如何去的石歧湾,又是如何返回的。他问得很细致,语气也很谦逊。我原本不想扯出小乐这个人,后来还是不得不把他搬出来。如果没有小乐,我到不了石歧湾,在父亲跟前也难以自圆其说。但最后我还是有所保留,没有说小乐丢下我,而是我主动下了木排,上了岸。
父亲听完我的讲述后,从口袋里摸出钢笔,在那根黑线末端画上了一个红色圆圈,在圆圈旁边写上了三个小字:石歧湾。补充完地图后,他继续问我,石歧湾往下游去是哪儿?相同的问题我问过小乐,小乐没能告诉我答案,自然我也无法回答父亲。
你不该在石歧湾下船的。收起地图时,父亲看了看我,似乎在暗示我要继续往前走。
我纠正说,是木排,不是木船。
都一样。父亲的语气可惜又可叹。
后来,我提醒父亲,地图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还可以画得更完美,把水门河添加上去,把每一条道路以及沿途的山脉都添上去。父亲只是斜睨了我一眼,没有接受我的建议。
父亲是那年秋天失踪的。
那会儿,稻子早已金黄,人们都在抢着收割。父亲也像别家的男人一样,起早摸黑忙于收获。事后,我仔细回想,整个收获季节,父亲都有些心不在焉。在操作打谷机时,他不小心轧到了腿,这让他的瘸腿更瘸了。父亲不是个称职的农民,干农活时总是会干砸很多事情。这在他是一种常态,见怪不怪。他也因此经常受到村里人的嘲笑。待到五谷杂粮都归了仓,田野上空旷起来,人们也迎来了一年中难得的片刻空闲。父亲没有听从母亲的劝阻,休息没两天,又背着他的工具箱出门了。往年的秋天,父亲是很少出门的,作为劁匠最忙碌的时段是春夏之季,秋冬季节劁猪骟羊的活计特别少。父亲出门的那天早上,天空飘着淡淡的云絮,是个晴朗的好天气。他走后,我搜查了那只大木箱,地图不见了,几包香烟也带走了,甚至那点可怜的私房钱也不见了。从这些细节中我嗅到了一丝可疑的气息,但当时又无法说出可疑在哪里。
父亲出门后三天没回来,过一周还是没回来,母亲这才慌了。按父亲以往外出的时间估算,早转完一圈回来了。这么多年,父亲在周围的村子里转来转去,像磨房的驴一样缓慢,但是很有规律,从未发生过意外。母亲将父亲没回家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的堂哥堂弟,但是没能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认为母亲大惊小怪,作为劁匠的父亲走家串户,几天不回家是常有的事,那么大个人,难道会丢了不成?半个月后,在母亲的一再恳求下,人们才分派出几支队伍,往不同的方向寻找。也许那些被派出去的人在敷衍了事,认为不值得为一个瘸腿的劁匠浪费时间。几天过去,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到最后,唯一确定的是,有人看见父亲经过了水门镇,后来往哪里去了,就没人知道了。
母亲挣扎一番后,不得不放弃。父亲不在家,三个孩子嗷嗷待哺,她已经不堪负重。寻找父亲成了我们兄妹三人的头等大事。我仔细回忆父亲的那张地图,借此推断,父亲可能是往东走了。
我一次次顺着水门河,去往洋湖港,去往石歧湾。我请求那些放排工捎我一程,有人拒绝,也有人乐意助我一臂之力。我过了石歧湾,继续往下游走,经过无数个码头,最后到了一个叫吴城的地方。所有的木排在这里汇聚,水门河也在这里汇入了鄱阳湖。这不是木排的終点站,它们还要北上进入长江,而长江通向大海。
弟弟稍大一些后,我带上他继续寻找父亲,后来妹妹也大了一些,抹着眼泪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在父亲走过的那些村庄,我们收获最多的是对他手艺的赞叹。我们同样收获了来自父亲身上的笑话,要么是父亲喝醉酒后的丑态,要么是父亲口出狂言,要带他们去看世界,要带他们到上海去耍。当然,谁也没有把他的话当真。那会儿,人们对上海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一双下狠心买来而又舍不得穿的解放鞋上。
父亲最终没有像他说的那样,依照他画的地图返回来。
在找寻父亲的过程中,我们不知不觉承祧了父亲身上的某些品质,一个个离开了水门镇。弟弟跑得最远,漂洋过海,去了地球的另一边;妹妹则选择了上海,那个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城市。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省城一家报社当记者。我借助职业的便利,走遍了水门河的上上下下,做过许多采访。我采访时,河流上筑起好几处大坝。河流断航了。我乘坐汽车奔走于各个旧码头,采访码头上的居民以及当年的放排工。我几乎断定父亲的失踪同这条河流有关。可惜的是,一点有用的线索也没搜集到。有一次,我采访了一位老放排工。老放排工告诉我,放排是个极为危险的营生,排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言下之意,父亲有可能遭遇不测了。
我把搜集到的讯息转告弟弟和妹妹,他们听了也像我一样保持沉默。我知道,此刻他们同我一样,内心充满了悲伤,但也有宽慰。父亲毕竟遵循了他内心的向往,遵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往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我们兄妹三人相聚时,谈论得最多的还是父亲,父亲油腻的工具箱、父亲带回来的纸风车,或者几只桃子、一捧红枣。我们的眼里噙满了热泪。我们是父亲的追随者。毋庸置疑,失踪的父亲成了我们的灯塔,我们不知他的确切位置,可是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他的光明。有一次,我们不约而同谈到了父亲最后的背影。于是,那个秋天的早上得以重现,父亲像往常一样挎着那只暗红的泛着油光的用竹篾编织的工具箱,在我们的目送下,一瘸一拐出了门,一瘸一拐向村口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