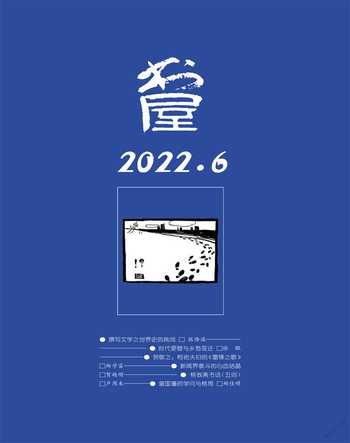曾国藩的学问与格局
2022-06-21郑佳明
郑佳明
我们现在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不仅要讲事功,而且要讲人的品质和能力——讲品质我们也不能仅仅讲道德,还要讲格局。所以我的看法是,学问改变格局,格局成就事功。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是格局?格局就相当于古人说的规模与气象、气质与境界。曾国藩给他九弟曾国荃写信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规模远大、圣贤气象。我读他的日记和他的书信,里边不停地在讲做大事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讲的是格局要远大。
所谓大格局就是说他超出了当时众人的眼界、心胸和判断。曾国藩在长达十年的战争中,在洋务运动中,哪些方面有这个体现?我总结了六条:
第一条,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是大格局。他1854年从衡阳起兵,带了水陆两支军队共一万七千多人。他那个时候发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叫《讨粤匪檄》。这篇檄文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忠义血性的旗帜,阐明了救时、卫道的起兵宗旨。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有远见也很聪明的做法。这个宗旨一明确以后,一方面,他得到了朝廷的首肯,朝廷就知道他“忠义”;另一方面,他又得到了士绅的拥护,中国的士绅基本上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培养出来的,所以士绅是拥护他说的那些的。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里讲了一句话,他说,太平天国搞的拜上帝教,这个教是异教,太平天国反对孔孟之道,烧书,烧毁孔庙,这个是人神共愤,数千年的文明被毁坏,他为此痛哭。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文化上很被动的一面揭示出来。他的忠义、血性、救时、卫道思想一出来之后,实际上使他自己获得了政治正确这么一个标签,所以他也形成了格局的高屋建瓴之势。这是他的大格局第一条。
第二条,另起炉灶、编练湘军,战略明确,艰难东征,攻克南京,是大格局。一方面,曾国藩有政治正确这么一个立场;另一方面,他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在满朝文武众目睽睽之下大胆地改革创新。朝廷本来是让他练民兵,结果他把它做成了军队;本来不要他出省,结果他跑去打武汉,还打赢了——当时咸丰皇帝特别高兴,准备叫他做巡抚。实际上他是没有军饷,他借助“厘金”制度“劝捐”筹饷。这个厘金后来就成为我们中国最早的地方税,是一种流通税,过境一百块钱的货物要收一块钱的税收。所以,曾国藩的湘军是带着税务局走的。他的以礼治军的方法中,包括军队里的组织形式,比如说一个人他可以召集五百个人建立一个营,这个营打赢了就由他领导,这个营打输了就解散了。这样,由“将”来决定“兵”、“兵”拥护“将”,就改变了过去朝廷的军队见死不救、一哄而散那种状况。这个建军的思想当然比不上现代的军事思想,但是有很多和中国的传统契合的东西,比如说宗法关系;比如说以礼治军;比如说“扎硬寨,打死仗”;比如说坚持从长江上游逐步推进的自主战略——咸丰皇帝对战局发展不满意,很着急,很生气,多次直接指挥,但是他坚持既定战略,先到江西,后到安徽,控制长江上游,截断对方的退路,巩固自己的后援,又把李鸿章推荐到杭州,把左宗棠也推荐出去,两个湘军大将作为奥援,最后他终于攻克南京。这种战略定力体现了难得的大格局。
第三条,曾国藩体现格局的地方就是他屡败屡战、坚忍不拔。“打脱牙”“和血吞之”,这些都是他的原话。他几次遇到非常危险的状况,三次在生死之间:一次是靖港之战,他蹈水,企图自尽;第二次是在鄱阳湖;第三次是在祁门。他这些时候都是处在危险之中。他是真正的书生领兵,迎战强敌,逆势而行。他跟家人讲,“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皇帝猜疑、官场嫉妒、朋友使绊,千难万险,他都把它们作为砥砺自己和修行自己的机会,这是大格局的表现。
第四条,以拙诚聚人,团结众人一起奋斗。这是个大格局。他说“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他非常重视“诚”的作用,并把它看作和部属处理关系的准则。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把“诚”看得跟性命一样重要。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他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诚者之效欤”,这个话实际上就是说:我湖南人能够鼓舞群伦,戡大乱,就是靠的拙和诚。
曾国藩团结人还有一条,就是他以身作则。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他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所以他做官是“不要钱、不怕死”,是真正比较廉洁的一个官员。这是我讲的在战争和洋务运动中曾国藩的第四个大格局的表现。
第五条,自剪羽翼、急流勇退,是大格局。南京打下来之后,满朝文武和朝廷上这些核心领导人,包括慈禧太后、恭亲王他们,都在看着湘军怎么办。那么,曾国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辞让自己过重的权力,使自己急流勇退。第二件,裁撤湘军,解除朝廷的疑虑。第三件,撤销厘金局,安抚地方的民众,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最后,他在金陵修贡院,开江南乡试,收两江士子之心。同时,他还办了传忠书局,开始出版被太平军毁掉的传统书籍。他这些措施的实行,消弭了朝野众人的猜疑情绪,使他声名鹊起,也就改变了自己过去那种被大家嫉妒和警惕的一种局面。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有一句话,叫“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数百名高级文人和军事将领构成的庞大的湘军集团占据省、部各路要津,后来又衍生出淮军集团,互相呼应,影响朝局,贯穿晚清历史。这些事情为政权重心后来转移到主张改革的汉臣手里打下了基础;后来曾国藩发动洋务运动,湘军在中法战争中、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在建立水师方面,为国家和民族作出巨大贡献。湘军后来能够善始善终,还为国家作这么大的贡献,和其战后急流勇退而积蓄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所以,曾国藩急流勇退,这是一个大格局。
第六条,从购“制器之器”到“师夷智”,是个大格局。他开展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始就是买兵船、买大炮,后来曾国藩说,买的靠不住。当时有一个阿思本舰队的事:从英国买来了军舰以后,清廷委任的英国人就插手。曾国藩说我们要自己造,自己造就要买制造大炮、军舰的机器,所以叫购买“制器之器”,这是他的一个进步,比“师夷长技”进一步。第二点,他提出“师夷智”,那么“师夷智”就不仅仅是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而且在科学知识上,甚至于一些人文知识上对西方开了方便之门,这是洋务运动中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比如,谭嗣同在维新时期能够有那样重要的思想,就是和他到曾国藩他们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图书馆看了很多西洋的书有关系。
我跟唐先生经常一起到美国、欧洲去讲课——唐先生就是写《曾国藩》这本书的唐浩明先生。我就说,曾国藩这个人一辈子好辛苦的。他自己有牛皮癣,晚上睡不好觉,血压还高。他在1861年打掉安庆之后就开始校对《王船山全书》。《王船山全书》是两百多卷,将近三百卷,他自己点校一百一十七卷,这要花费多少时间!外边还在打仗,晚上别人睡觉了,他还在那儿干活。他总体上的著作,最后《曾国藩全集》有多少文字?一千五百万字,我是查了的。其中有几本是他编辑的,也放在里边了,比如一本是《十八家诗钞》,一本是《经史百家杂钞》,这两本书是别人所著的,但是这两本书不厚、规模不大,加起来也就五六十万字。那么,其实《曾国藩全集》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写的。他的这一生里头做了那么多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问唐浩明先生:“你认为他吃大苦、耐大劳,动力是什么?”他说是信仰。这是我们看曾国藩格局的第一条,就是说他要做圣贤,他信仰“修齐治平”这么一个理学的基本信念。
曾国藩以读书为立身修身之本。在古代的文化人看来,要做圣贤就得从读书入手。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改变气质。他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古代那些会看相的大师说,读了书连骨相都可以变化)。所以,咱们现在女孩子不用去做缩骨,可以多读几本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具体来说,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从两点变化人的气质,那就是敬德和修业。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读书是做人的基本功。曾国藩不仅重视读书,还喜欢读书。他通过读书把儒家文化和程朱理学的各项基本要求铭记在心。
曾国藩把读书和修身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他说,“知德性未尊,则问学适以助长”。他认为真正要把知识学问转化为自己的德行、涵养,就必须把书本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意念情操,转化为每天的日常实践。他说:“《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他的意思是说,《大学》里的三纲——明德、新民、止至善——这些事情应该由我们身体力行,否则你读了有什么用?
勤奋刻苦,持之以恒。他说,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在京中虽然已经做了大官,但是每天仍发奋用功:“早起温经,早饭后读廿三史,下半日阅读诗、古文,每日共可看书八十页,皆过笔圈点。”看八十页都要用笔来圈点,这是他读书的一个方法,强迫自己读。第二个办法,他说,“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意思是说,老师和朋友之间夹持,就好像绑架一样,虽然是懦夫,但是也有立志——你跟这些老师和朋友在一起,如果你不读书,也说不过去,不好见面。他非常注重交友,而且特别注重交那些有学问的朋友,他通过师友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成圣贤的目标。
知行结合,就是他把读书和做事情结合起来。读书不仅仅是道德修炼,也要获得智慧和能力。圣人讲人的能力,包括智、仁、勇三项,曾国藩就讲,“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他这里讲了两个词,一个是高明,一个是精明,都是对孔孟里的三达德“智仁勇”的“智”做的一种解释。他说这个智是什么?就是观察俗物、理解事物的认知能力。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曾国藩对“智”的解释是指对俗物的了解,就是对世间这些最俗的事物和人间生活、油盐柴米这样一些具体事物的了解。它可以看作什么?认知外在事物表现出来的聪明和智慧。智识这个“智”,它是书本知识和做具体的事情形成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我们讲的格局的一部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格局,他这个智慧、聪明,不仅仅涵养了德行,而且有独立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利的价值。也就是说,有了知识和智慧以后,他的人格可以有独立性,它有独立的精神的意义。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曾国藩的话,一定要了解他的这种独立性,他的独立性是他的智慧。所以,他一方面是拙诚,见其大见其远,另一方面是智慧。我们已经多次看到,他跟朝廷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会想办法绕过朝廷的这些规矩,然后把事情做成。
诚而不欺,立身之本。他对儒家心术的规范最重要的理解,就是把“诚”看作内圣的内涵和达到内圣的途径,同时也把“诚”作为外王的一个阶梯。所以,他把“诚”看作内圣外王的连接点。内圣就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圣人,外王就是我们要实行王道、不搞霸道;那么又怎么样在内圣和外王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他说,“诚”就能做到这一点。他把关于“诚”的思想贯穿到他的事业之中。他说:“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他讲的意思是,人要有基业。这个基业是什么?这个基业就是诚。所以,人不要以欺詐为诚,要以诚为诚。他说,“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他认为,“诚”这个基础巩固了才能够建功立业。
英雄与圣贤兼备。正如他推崇的人格理想主要是强调要做圣贤,这一类的理想人格在实践中往往表现出恭敬、内敛、温柔、慎重、谦逊这样的一些人格特点。但是明清以来,由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这个士大夫的人格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有一些有开拓精神的士大夫,特别是湖南人,就提出了血性的思想,提出了要有豪迈的英雄气概——他们呼唤天生豪杰必有所用、“天生豪杰必有所任”这样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对曾国藩有很大影响。曾国藩向往什么?他就向往圣贤与豪杰融为一体的人格理想。而且我们湖南这个地方盛行一种强悍刚勇的文化性格,所以湖南人被称作“南蛮子”。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崇山峻岭,舟车不便,养成了湖南人尚武,而且刚烈、不怕死的气质——有人称为特别独立之根性,有人把湖南人叫“骡子脾气”,王夫之把它叫“秉刚之性”。曾国藩说什么?“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曾国藩强调自立刚强的精神,他给圣贤的人格注入了一种新的内涵和特质。所以,圣贤人格应该是什么?有“民胞物与”的这样一个人格,同时还要有什么?还要有一种内圣外王以成大事的这么一种气概。
内圣外王的统一,形成一种新的人格。我们讲,程朱理学有几个基本概念:一个概念就是内圣外王;一个概念就是对人的话,要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还有,人的生命要求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思想实际上有两个方面表现。一个就是,内圣要求立功立德、成己成物。立德就是成己,通过心性修养,增进道德,达到圣贤的境界。立功就是成物,就是身任天下,以立众生,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这个叫立功立德、成己成物。这是一种想法。关于内圣外王还有一种要求,叫修己治人、尽伦尽制。伦是伦理,制是制度,其实就是要求统治者端正自己的品行,有人格的力量,并且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稳定社会秩序。从孔夫子到曾国藩,儒家对圣王合一的追求一直是做人的最高追求。在这个过程之中,曾国藩努力做到这两个方面。
曾国藩的学问对他的人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学问实际上是有跟程朱理学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有创新的地方。对于这些创新的地方,我们讲这么几个方面:
曾国藩学问的第一个特点:一宗宋儒,兼容汉学,同时博览经史百家。这是曾国藩的一大特点。这里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他“一宗宋儒”——“宋儒”就是程朱理学、伊洛之学等。关于“兼容汉学”,汉学实际上是汉朝时候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它强调实事求是,强调咬文嚼字,要把经典搞清楚。到了清朝的时候,程朱理学和汉学之间产生了派别之分。特别是文字狱发生多了,大家都不愿意谈义理,都愿意去训诂,都愿意做考据工作。这时候,就分出两派。曾国藩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说:我是学理学的,我一宗宋儒这个不变,但是我兼容汉学。这里边还有故事。他认为汉学搞得好,可以使自己的理学也学得好——他没有把它们对立起来。除此之外,他博览经史百家——经、史这些东西他都在学。
所以,他用程朱的理学统治所有的学问,他把学问格局做大了。这是他的人生格局和事业格局做大的一个基本原因。他的学问无所不窥,他的治学态度包容,学用结合。他打仗很忙的时候,曾经画了三十多个历史上著名的贤人君子士大夫的画像,其中很多人不是程朱系列的,甚至于有人是程朱批评的对象,都被他列入其中,都是他的榜样。他这种兼容并包的治学效果,实际上是对宋明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整合,这个功劳非常大。他对宋明以来的各种学术思想及流派,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的经世实学、乾嘉汉学,乃至道家佛学诸子,采取了一种兼容的态度。这就使他推崇的人格理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人格比那些一般的理学家内涵又有了新的特征,有了时代的特征。
因为对学问的广博和扎实,在传统文化的资源库里,他找到了很多实用的工具,我们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戚继光的练兵之法。他在编练湘军的时候,想用礼治来治军,但是他发现礼治里就没有军“禮”——关于军队的“礼”就没有。这个时候他就把戚继光的这些东西找来,把军“礼”编制出来,让军队照着做。这样的话,他不仅投入了使用,而且填补了礼治学问的一个空白。
他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还体现在什么方面?他转向经济之学、义理之学之后,并没有把原来的词章给抛弃掉。他亲自编辑了《十八家诗钞》,而且他喜欢韩愈的古文,一生反复地阅读。他有的时候读诗词散文,把它当作休息。他说这些文字可以洗涤他的功利之心。所以,他博大的学问格局,里面有一种广阔的精神世界和跟古代圣贤比肩的神圣气象,还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和伟大的目标。
这是他读书,博览群书。有一位博士生做了一篇论文,把曾国藩日记里读的书的名单开出来,列了几十页。
他的学问的第二个特点是倡导经济之学。经济之学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管理,不是现在经济的概念。他在北京请见唐鉴的时候,唐鉴跟他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核就是格致,也就是说对文字进行考古、考据;文章就是诗词歌赋,各种各样的文章、古文。曾国藩马上就问他,那么经济在哪里呢?唐鉴马上回答,经济在义理里边。曾国藩听了这句话回去以后,并没有把这个事忘掉。隔了一二十年,差不多快二十年,他写了一个东西,叫《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他说学问分四门,把经济从义理中独立出来。大家注意,这个独立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个经济按他的说法就是“政事”、政治的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政治。经济之学实为经世济民之学。他认为,天下大事,考究有十四个方面: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对这十四个方面,他当时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就自己在那儿钻研,这为他后来做官、带兵打仗,打下了很好的学问基础。所以他从在北京就开始注意经济之学。这是他的学问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理论上的一个贡献,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同时,经济之学也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一个体现,经世致用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方面。
曾国藩学问的第三个特点是“以礼为规”——这个词是左宗棠评价曾国藩的,讲得很中肯。“礼”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礼节规范,第二个就是治国平天下之术。曾国藩说,过去“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他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可见,他是考虑以礼来消除社会的这些问题。他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全是靠礼),“舍礼无所谓政事”。所以他立下了什么?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并作为他治军的核心思想。他说,带兵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曾国藩是以礼为规。礼和法都是在约束行为,有的时候是礼使用得多一些,有的时候法使用得多一些。曾国藩在礼和法的过程之中用礼来治军、用礼来治国,形成了他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就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是曾国藩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王船山对理学有一个批判和纠正,对程朱、对陆王都有批评和纠正。那么,曾国藩继承了这个纠正,继承了王船山的思想,所以王船山对湘军、对曾国藩有重大的作用。曾国藩不但培养了一个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湘军集团,而且大量刊刻和传播了船山之学。他一边指挥打仗,一边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船山遗书》他校对了一百多卷——当然每“卷”的体量很小。实际上,从周敦颐到张载,到胡宏,到王船山,湖南人逐步形成了一种经世致用的特色;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湖湘理学的精髓。曾国藩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检验和实现他所有思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