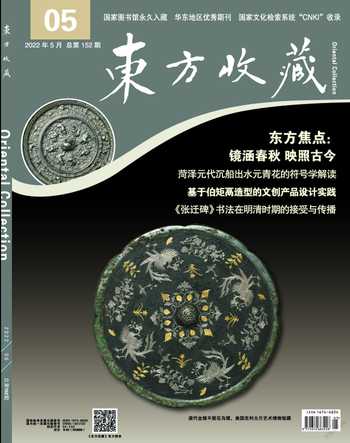略论金文月份合文与西周置闰问题
2022-06-17蔡立铮
摘要:通过考证寓鼎以及盠驹尊的铭文可以判定, 的准确释义应为“三月”,因此西周铜器“十又 ” 应释为“十又三月”。 所以,西周时期存在“年终置闰法”。由于周历仍是观象历,月建摆动较大,缺少实行“年中置闰法”的条件,可以确定,西周时期不存在年中置闰的现象。
关键词:置闰法;合文;金文
将数字与“月”字合写用以表示月份,是西周铜器铭文的常见现象。前人对月份合文“ ”的释读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二月”,另一种是“三月”。但是由于含此铭文的铜器缺少确切纪年,又因铭文内容缺少传世文献印证,以及现有西周历谱主观性较大,因此合文的释义问题仍有进一步论证的空间。笔者总结前人对夏商周三代历法以及铭文的研究,以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并且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研究,讨论西周时期的置闰法。
一、 应释读为“三月”
“ ”的释读问题源于对寓鼎(《集成》02718,西周早期)的考释,现将寓鼎铭文释文如下:
隹(唯)十又 丁丑,寓献佩于王姤(后),易(赐)寓曼 (丝),对扬王姤(后)休,用乍(作)父壬宝 (尊)鼎。
此铜器铭文记载了作器者寓将玉佩献给王后,王后赏赐他素丝的事情。释文的争议在于“ ”的释读。陈梦家与谢乃和将此合文释为“二月”;唐兰则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一书中,将此合文释为“三月”,并将此器断于康王世。
笔者认为,唐兰的“三月说”是正确的,原因如下:
其一,除“ ”外,金文中有另一月份合文,写作“ ”,见于铸叔皮父簋(《集成》04127,春秋早期)与另一寓鼎(《集成》02756,西周早期)。若该合文被释为“二月”而非“一月”,则“ ”的释义应为“三月”。研究证明,将“ ”释为“二月”是准确的。
从西周到战国晚期,中原诸侯国与楚国都称一月为“正月”,铭文中的“一月”皆表示“一个月”,尚未发现例外。所以,“一月”的释义并不准确。
《逸周书·世俘》记载了武王“有国”之年的干支日,起于一月丙午,终于四月乙未。一月到四月最少间隔60日,但是丙午到乙未仅间隔50日,可见,一月丙午当更正为“二月丙午”。若将此篇中的“二月”释为“三月”,则可以与《周书·武成》中“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的记载相合。所以,“二月”之合文应为 。
其二,凡有“ ”与“ ”出现的铜器,表示“月”的部分上部都较为平直,与表示数字的横大致平行。由此可以判断,“三”字当借用了“月”字一笔,“借笔”现象在古文字中并不鲜见,兹不赘述。[1]
其三,西周时期刻有“十又三月”(无合文)的铜器共有8件,其中西周早期3件、西周中期3件、西周晚期2件。可見,整个西周时期存在有年终加上一个月的置闰法,即年终置闰法,闰月写作“十又三月”。
所以,若某一铜器的作器时间为“十又三月”,其中的“三月”也有可能写作合文的形式,代表铜器为盠驹尊(《集成》06011,西周中期),其铭文记载:
隹(唯)王十又三月,辰才(在)甲申,王初执驹于 ,王乎(呼)师豦召(诏)盠,王亲旨(诣)盠,驹易(赐)两,拜 首曰:王弗望(忘)氒(厥)旧宗小子, 皇盠身。盠曰:王倗(不)下(叚)不其则迈(万)年保我迈(万)宗。盠曰:余其敢对扬天子之休,余用乍(作)朕文考大中(仲)宝(尊)彝。盠曰:其迈(万)年世子孙孙永宝之。
盠驹尊的干支日为甲申,在日期上与其有关联的是中方鼎(《集成》02785,西周早期),铭文记载:
隹(唯)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在)寒 (次),王令大史兄(贶) 土。王曰:“中, (茲) 人入史(事),易(赐)于珷王乍(作)臣,今兄(贶) 女(汝) 土,乍(作)乃采。”中对王休令, 父乙 (尊),隹(唯)臣尚中臣。
唐兰认为,十三月并非每年都有,甲申与庚寅只相差一天,所以两器所载之事,很可能就发生在同一年的十三月。[2] 李学勤认为,中方鼎之“中”,就是静方鼎(《集成》NA1795,西周早期)铭文中的“师中”。[3] 静方鼎记载之事与昭王伐楚有关,中方鼎亦然,所以盠驹尊也应与昭王伐楚有关。
在所载地点上,与盠驹尊有关的是遣卣(《集成》05402,西周早期),同样是与昭王伐楚有关的铜器,其铭文记载:
隹(唯)十又三月辛卯,王才(在) ,易(赐) 采,曰: ,易(赐)贝五朋。 对王休,用乍(作)姞宝彝。
盠驹尊与遣卣都提到了“ ”,此为地名。唐兰指出:此地与宗周相近,是昭王伐楚时的常住地点。[4] 所以,盠驹尊与遣卣之做器时间相距不远,很可能在同一年之内。如此,此两器与中方鼎应是同年所做。甲申、庚寅、辛卯日跨度只有8天,可以排在一个月之内。[5]
昭王第一次伐楚是其在位十六年之事,根据《夏商周年表》,该年为公元前980年,次年即有十三月。[6] 甲申至辛卯日为该月的第十六至二十四日。由此可知,盠驹尊之“十又 ”应释为“十又三月”。[7]
综上所述,“ ”应释为“三月”,但仍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从而无法将“ ”的释义完全确定。如下:
其一,除寓鼎与盠驹尊外,笔者搜集到带有此合文的铜器共9个。这些铜器四要素不全,缺少具体王年,甚至有一部分缺少干支日,只能根据其纹饰和字体大致断代。其铭文所载之事,尚未发现与其对应的传世文献,也缺乏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其他铜器的佐证。所以,无法确定这些铜器铭文的具体王年。
其二,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开始于共和元年,在此之前的年历主观推测成分较多,以致学界对西周时期的排谱尚无定论。所以,现有西周历谱的准确性尚存争议。
总之,“ ”的释读依然有待商榷,但是根据目前确定的研究成果来看,将“ ”释为“三月”是较为合理的。
二、夏商周三代皆实行“年终置闰法”
根据前文所述可以断定,西周时期存在“年终置闰法”,但“年中置闰”的存在尚有争议。
周历结合了夏历与殷历,研究周历的相关问题,需以夏历与殷历为先决条件。
夏历记载于《夏小正》与《尚书·尧典》之中,张闻玉认为,《夏小正》成书早于《尚书·尧典》,可以作为研究夏历的史料。 [8] 潘鼐考证《夏小正》所记的星象,认为《夏小正》记载的星象是夏时期的。[9] 所以,夏历的研究需要将上述两个史料结合。
陈久金指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月长较大,且随着月份增加,月间隔也越来越大。[10] 《夏小正》中对节气的判断有两种途径:一是观物象,即观察不同时间的生物活动;二则是观星象。《夏小正》记载了鸟、房等星宿在不同季节与月份的变化,也记载正月“初昏斗柄县在上”、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这表明在殷商之前,人们就已经观测到了北斗七星斗柄指向与其他星象的变化规律。
《尚书·尧典》的记载指出了夏历的两个特征:夏时人们已经观察到了春分到冬至日的白昼时长变化;夏历排谱有四个关键节点,鸟、火、虚、昴四星在天空正南方,分别对应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如果到了季节仲月,对应的星宿没有出现在天空正南,就表示月份出现了偏差,应在此时设置闰月进行调整,即“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由于四星的偏移时间并不固定,所以,夏历的置闰也不固定,有可能在年中某月,也可能在年终。但是夏历还处于历法的奠基阶段,实行“年中置闰法”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夏历应以“年终置闰”为主。
与夏历不同,《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载:“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11] 此记载被认为是对殷历的直接记录。但是,《左传》成书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距离殷商年代久远,其记载的殷历实为宋人的历法,与殷历虽有联系,但仍有差别。
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证,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殷商时期出现了年中置闰的现象,但此种现象是否成定制,是学者讨论的焦点。对此,学界产生了两种观点:殷历在一定时期内同时采用“年中置闰法”与“年终置闰法”;殷历置闰于年终,年中置闰是偶然现象或未发生过。
第一种观点得到了董作宾、冯时等学者的支持。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指出,祖甲继位之年,一月改称正月,置闰在当闰之月,不再用“十三月”之名。[12] 董氏之观点不被认可,因为在武丁之后的卜辞中仍有“十三月”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董氏关于年中置闰的观点是错误的。
陈梦家认同董氏关于年中置闰的观点,他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指出:《珠》199条卜辞(《合集》11 545)是商代出现年中置闰的证据,在这些卜辞之中,癸亥、癸酉等日期不满足无闰月情况下3至5月干支日的排列。由此可知,在当年的3至5月之间必然出现了一个闰月。[13]
冯时与张闻玉都认为,武丁时期出现了最原始的“无中气置闰法”,殷历用平朔平气,一年12个月均可置闰。[14] 冯时进一步认为,《甲骨文合集》10976证明了武丁时期可能出现了闰八月,而这一时期出现的闰十二月,有可能只是改变了位置的年中闰月,目的就是固定二分二至的所在月份。[15]
常玉芝进一步证明,在殷历之中,出现过闰四月、闰六月与闰十月。[16] 至此,商代出现了年中置闰成为学界共识。陈遵妫在《中国天文学史》一书中进一步指出,祖甲至乙辛时期实行年中置闰,但祖甲时期的卜辞还有“十三月”存在,说明“年终置闰法”并未废除,两者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共存。[17] 所以,殷历应同时采用过“年中置闰法”与“年终置闰法”。
但是,以郑慧生、朱凤瀚为代表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
郑慧生认为,传统的“殷正建丑”的观点是错误的,殷正应建未,以麦子成熟月为岁首。如果过了十二月麦子未熟,就补上一个月,卜辞写作“十三月”,此即“年终置闰法”。与此同时,有了麦子成熟度这一物象,采用年中置闰法就容易了。九月,麦子应起身拔节,如果麦子未出现此情况,就应在九月置闰。所以,殷历也应出现了年中置闰。
郑氏不否认年中置闰,但他也认为,由于麦子的成熟度不易观察,年中置闰并不常用,殷历仍以年终置闰为主。[18]
朱凤瀚认为,殷正建午,以大火星(心宿二)在黃昏时处于天空正南的月份为岁首。殷商时期的置闰就是为了让该现象固定在出现于夏历五月,因此置闰于夏历四月,即年终是最好的方案。[19] 所以,殷历应实行“年终置闰”。
更有学者认为,年中置闰可能未出现。张培瑜认为,殷历部分大月月长可能大于30日,可见殷历并不是严谨的阴阳历;殷历并不是推步历法,不可能精准计算出朔望月日期,更不可能产生二十四节气,即使殷商时人产生了年中置闰的想法,也不可实现。[20]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殷历出现过年中置闰。但是,由于实行年中置闰的条件尚不成熟,所以年终置闰才是殷历最常用的置闰法。
周历的月份排列遵从夏历,但以子月(冬至月)为岁首(建子)。《诗·豳风·七月》记载:“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一之日为周历正月一日。根据《七月》的叙述,夏历七月,大火星(心宿二)开始向西偏移,天气入秋;九月开始制作冬装。周正建子,夏正建寅。[21] 所以,周的正月应为夏的十一月。
但是,对于《七月》中日期的解释却有争议之处,争议在于,《诗经注析》等的注释中,“一之日”等日期使用周历,“七月流火”等月份又使用夏历,一首诗中为何会使用两种历法?只有两种可能:周正建子是讹误,或者周历的月建经历过变动。
张培瑜在《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一文中指出,若以“周正建子”作为依据,四十二年逨鼎(乙)(《集成》NA0745,西周晚期)等铜器与吴虎鼎的四要素无法排在同一历谱中,若将其著作《中国先秦史历表》中的月份整体后移一个月,上述问题即可解决。[22]所以周正应建丑。
若周正建丑,在“共和行政”不单独纪年,且并入宣王纪年的情况之下,吴虎鼎的历日与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西周晚期)等器的铭文历日,又无法排在同一历谱当中。[23] 由于“共和行政”是否单独纪年存在争议以及其他原因,周历月建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常玉芝认为,殷商到西周时期,皆以朏日为月首。[24] 王胜利进一步认为,周人应以观察到新月的后一日作为月首,体现在金文中就是“既望”“既生霸”等纪日法的使用。可见,周历也是观象历,而非推步历。张培瑜也提出过类似观点。那么在月建上,也应在观察到“日短至”之后的月份作为月首。所以,周正应建丑。[25]
陈美东认为,研究西周历法可从春秋时期的鲁历回溯。王韬认为,鲁历以僖公五年(前655)为界,前建丑后建子。但是陈氏的研究表明,僖公五年前也出现过建丑,之后也出现过建子,甚至有些年份建寅。《左传》记载,鲁历出现过失闰或多闰的情况,因此导致月建不规律。由此可以推断,周历也可能出现过此种现象。在置闰方面,作为与周人习俗最相近的诸侯国,鲁历置闰就是置于年终。[26]
所以,周历建子应为主要月建,但是也存在类似于鲁历的月建摆动,置闰也应置于年终。
综上所述,笔者的结论如下:
1.“ ”的释义为“三月”,“十又 ”为“十又三月”。
2.周历虽有推步色彩,但仍为观象历。由于此阶段天文观测不够精确,出现过数次“失闰”或“多闰”,导致月建摆动较大,不具备实行“年中置闰法”的条件,所以周历应实行“年终置闰法”。
参考文献:
[1]祝振雷.从铸叔皮父簋铭校正古书中对“一月”的误识[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01):79-82.
[2]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J].考古学报,1962(01):15-48.
[3]李学勤.静方鼎考释[C]. //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7.
[4]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J].考古学报,1962(01):15-48.
[5]何景成.盠驹尊与昭王南征——兼论相关铜器的年代[J].东南文化,2008(04):51-55.
[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版[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 :88.
[7]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M].山东:齐鲁书社,1987 :45.
[8]张闻玉.《夏小正》之天文观[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04):62-68.
[9]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7-9.
[10]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04):305-319.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1544.
[12]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5:闰谱[M].中国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3.
[1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217-223.
[14]张闻玉.古代历法的置闰[J].学术研究,1985(06):117-122.
[15]冯时.殷历武丁期闰法初考[J].中国历史文物,2004(02):25-31+63.
[16]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307-318.
[17]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6-137.
[18]郑慧生.年中置闰:先秦历法史上的重要改革[J].史学月刊,2009(11):25-30.
[19]朱凤瀚.试论殷虚卜辞中的“春”与“秋”[C]. //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纪念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70-187.。
[20]张培瑜,卢央,徐振韬.试论殷代历法的月与月相的关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84(01):65-72.
[2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437-438.
[22]张培瑜.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J].中国历史文物,2003(03):6-15+97.。
[23]张培瑜,周晓陆.吴虎鼎铭纪时讨论[J].考古与文物,1998(03):72.
[24]常玉芝.殷歷月首研究[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05):26-38.
[25]王胜利.西周历法的观象历属性[J].殷都学刊,2004(04):33-35.
[26]陈美东.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02):124-142.
作者简介:
蔡立铮,1996年生,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