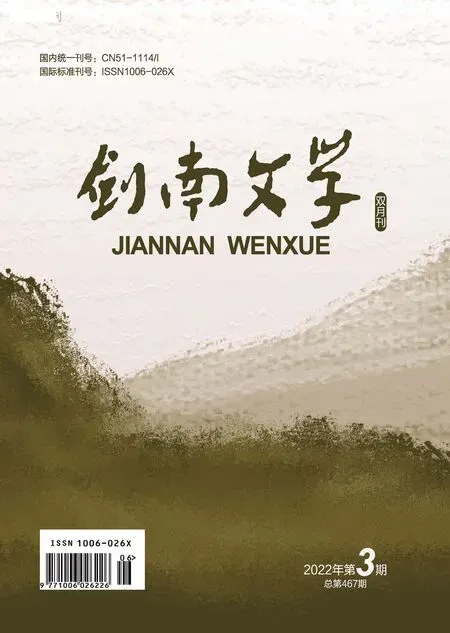薛叔
2022-06-16□李春
□李 春
我上小学的时候,苏保学校有两排房屋,一排砖瓦房和一排旧木屋,砖瓦房在苏保公社的对面,和采购站连成一片,形成长长的“一”字形。我家住在学校旧木屋,和采购站面对面,中间隔着一个大操场。采购站每天开门和关门发出的“咯吱咯吱”响声,我坐在家里都能听到。
当年的采购站是最具人气的地方,主要收购野生药材、农副产品和废品物资。采购站是老式的木瓦房,几根结实的圆形木柱立在房檐下的石礅上,形成很宽的廊道,廊道与木楼一样长。廊道边上有张简易木桌椅,还有几根笨重的矮长板凳。房屋右边有两道单开门,分别是工作人员的住房和办公室,左边靠堡坎的地方,搭了一间砖瓦炕房,专门用来加工新鲜药材。
从廊道正中的两扇大门,跨进高木门槛,便是呈“凹”字形的房屋,房屋进深很宽,靠里的左角边堆放着装满药材的麻袋,麻袋堆到了木楼板的顶上,麻袋上工整地写着黄连、当归、荷香、木香、川柏等毛笔字药名。靠里的右边是废旧物品,两床晒席安静地立在墙角边,中间是案板桌,上面摆着带钩和带盘的、刻度不等的各种杆秤,地上有两台不同型号的机械台秤。大大小小的漏筛、簸箕、箩兜、钉耙、扫帚等工具,整齐地横卧在案板桌下。靠大门的两边各自有两间独立房,一间是配送化肥的库房,一间是蚕茧作坊。中间有张桌椅,桌上的纸盒里装有圆珠笔、复写纸、红印泥和电筒,抽屉中锁着收据和印章。库房边有个木梯,上面有层木楼,楼上没有隔断,格外宽敞,存放着比较贵重的物品,如天麻、人参、蜂蜜、核桃等。
采购站的大门总是敞开着,工作人员是一位挺文静的中年人。他的额头上有一道浅浅的皱纹,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说话时声音很轻,有些腼腆,习惯用手扶一扶他的黑边眼镜,看上去像是个蛮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每天开始工作时,仍旧同往常一样,外面穿着蓝色的中长帆布工作服,上衣口袋并排插着一支红色和一支蓝色的圆珠笔,左边胸前佩戴着领袖像章。下方的两个口袋,一个包里鼓鼓囊囊,塞着工作笔记本,一个包里揣着方格子手帕。每次收购结束后,他都要扯下手臂上的袖套,把身上的灰尘在露天坝里掸一掸。手洗干净后,擤一阵鼻涕,掏出手帕擦鼻涕。他的腿看起来有些残疾,走起路来微微有点跛。那时,同行叫他薛光顶,乡民称他薛老师,我们小孩都喊他薛叔。
听大人在背后说,薛叔是川北行署从广元派到北川的干部,当年在擂鼓的区公所工作,后来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苏保当了采购员。那时,在我们小孩的眼里,薛叔极爱干净,对人亲切温和,做事小心、认真。不管是大人或小人、熟人或陌生人、城里人或乡下人,他都一样热情对待。很多时候,乡里人从沟里背着一大背药材走出来,往往不在上班的时间点上,有时薛叔已经下班休息或者刚端上饭碗,只要有人在外面喊一声,他都满口回应:“马上就来。”薛叔每天起得很早,遇上大晴天,薛叔更忙,先是拿起大扫帚把采购站的房前屋后、廊道院坝、排水阴沟从头到尾地打扫一遍,把屋内屋外的桌椅板凳擦干净,再从采购站的房屋里搬出筛子、撮箕、杆秤等收购工具,一边等待卖药材的乡民,一边把降了等级、手感有些润的药材搬出室外来晾晒。
那些年,采购站关系着农民的“钱袋子”,是非去不可的地方。乡里人喜欢看闹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他们的本意是来探听价格是否合理。薛叔似乎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不但提前把采购物品的价格公布出来,而且每天总是把采购点设在院坝和廊道上,吸引更多的人围观。在大家的评头论足中,薛叔很快掌握了各种药材的性能,练就了一套对药材鉴别的本领。遇上收购片状类的药材,即便薛叔一眼能认出来,他还是要认真做检查,拿出一小片药材凑在鼻子下反复闻,再咬上一口尝尝,过后轻轻一撇,药材发出脆邦邦地响声并断裂,便断定为上等药材。薛叔遇上草草类的药材,就扯下小段草药在手中揉几下,如果一揉就碎,说明药材干透了,倘若叶片保存完好,没有夹带泥沙杂草,自然会划为一等品,一等品的价格相对要高点。但凡草药捏在手中有点润,叶片脱落得多,便定为二等品或三等品,虽然降了一两个等级,乡里人也乐意接受,毕竟可以不白跑一趟路了。
薛叔确定好物品的等级,得到对方的认可后才过秤。称重量时,他明知道卖东西的人早就在家里过秤了,还是坚持提醒对方跟他一起看秤,因为药材背这么远的路,再筛出一些杂物,难免不出现称斤不相符的现象。在报出物品的重量后,他把物品倒进箩兜里,放下秤,就在廊道的桌边坐了下来,从工作服里掏出笔记本和蓝色圆珠笔,埋着头,很快写出采购的时间、物品名称、重量乘以单价的算式,然后拨弄算盘珠子,嘴里小声地念着口诀:“二去二、八上八、一去一、七上七。”把应支付的钱写在算式的等号后面,重新拨打算盘再复核一次,如果数据得不到一致,又拨打一次算盘,直到所有数据正确,再用红圆珠笔把错了的数据改过来。最后,从抽屉中拿出收据,仔细开好发票,盖上鲜红的公章和个人印章,撕下红色票据交到卖东西人的手中,叮嘱对方拿好票据向右拐,到办公室出纳那儿去领钱。如果收购的是大量新鲜药材或农产品,需要及时炕晒,他就招呼乡民直接背到左边炕房过秤,由工人来炕晒加工。薛叔采购物品的过程,像是玻璃杯里的冰块一样透明,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乡里人心服口服,都愿意把采集的药材或收获的农产品或家里的废旧品,放心地卖给采购站。
山区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有时下过几场雨,屋内潮湿,堆放的药材摸在手中湿润润的。只要天放晴,薛叔都要跛着一条腿,搬出笨重的晒席,把药材铺在上面晾晒。每次晾晒药材时,薛叔端出一根小板凳,坐在旁边的核桃树下,手里拿着一张《参考消息》,仔细地阅读。
住在附近的张大伯路过这里,关切地对薛叔说:“薛老师,药材回潮属于正常现象,反正过几天就拉走了。今天不逢场,你正好休息呢,这样大的太阳你守着干吗?”
薛叔说:“药材回潮容易霉变,晒干后便于储存。今天正好出太阳,我也想见见阳光。”
张大伯心疼地说:“薛老师,看你细皮嫩肉,也不是干这种苦差事的人,别把自己搞得太累。”
薛叔说:“没什么,我已经习惯了。”薛叔说完,抬头看了看天,只见云层厚了起来,看样子要起风了,薛叔回屋放下手中的报纸,拿出麻布口袋,忙出忙进地把药材打包,搬进屋里。
苏保沟主产洋芋、竹子、魔芋、乌药、黄连和茶叶等,到了九十月份,采购站忙得不可交开,每年还要承办一两次物资交流会,集中对物品进行采购,一般是三天时间。我和伙伴们听说要办交流会了,心早就飞出了教室,天天缠着大人问,什么时候开?还有几天时间?边算着日子,边在心里盘算家里有什么可以变卖的东西。我整天像个小喇叭,经常把从别人口中听到的,变为自己的东西,在同伴中说个不停:交流会要来了,还有好多外地供销社的要来摆摊摊。这次交流会,学校不上课,要放几天农忙假。去年的交流会闹热得很,来的人像蚂蚁搬家样,密密麻麻的,差点把我挤扁了,即便我站着不动,别人也会推着我走的。
秋交会这天,收购站把几周前贴出的宣传海报撕下来,重新换上了新海报。学校和采购站的墙上、柱头上都张贴满了我父亲和薛叔写的红、绿、黄、蓝、白、紫的彩色标语,诸如“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抓革命,促生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高音喇叭顶着大嗓门,不停地唱着《社会主义好》等歌曲,声音震动很大,隔着一公里远的倒石岩也能听到回音,热闹的气氛把交流会的场面渲染得沸沸扬扬的。外面收购洋芋的货车和拖拉机,一辆接一辆,满载着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停在沟口的大路上。买卖东西的,调换大米的,看热闹的,人多得像一锅煮烂的稀饭,挤挤挨挨,打头碰脸,挤满了粮仓的晒场、公社的庭院、学校的操场和采购站的院落。
高山的农民土地多,物产丰富,当年生产队分的黄豆、豌豆、胡豆、洋芋等农产品吃不完,放在家里只有养老鼠。他们干脆辛苦一点,走几十里山路,把东西背到采购站换成米和钱。天刚亮,家家户户带着一家老老少少,背的背,挑的挑,扛的扛,把全家人的希望背进了秋交会。洋芋换成大米,其他的东西卖成钱。
我就像猴子一样,在屋子里爬上爬下地倒腾,有时站在板凳上爬高,有时横躺在地上,有时跑到厨房后面,把书架上的旧报纸、床底下的烂凉鞋、竹兜里的肉骨头、茶盅里的牙膏皮等全部找出来装在背篼里,把夏天积攒的杏仁、桃仁放在布袋中。把晾晒得干脆的车前草、金钱草、通花秆、猪皮拱等,收拾起来捆成捆,装在背篼上,背到采购站去卖。
这一趟,我发了一点小财,卖了三元八角钱。七股八杂的东西变成了现当当的票子,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生怕把钱弄掉了,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我把空背篼丢在采购站,就像泥鳅一样,从人缝中艰难地挤到卖百货的摊位上。女孩一向爱臭美,我左看右看,拿出捏出水的钱,买了一盒香喷喷的白雀羚、一个带拉链的小钱包、一把彩色的橡筋圈和一个铁笔盒,剩下一元六分钱,就舍不得用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妈妈说过,有了钱,用一半得留一半,这样的日子才过得长长久久。我小心地把剩下的钱装进钱包里,把钱包放在贴身衣服的口袋中,用手在外衣上按住钱包,转身往回走。
秋交会上,采购站突然来了一大群背着乌药的乡民。院子里很快排起了长队,薛叔和外地来的年轻人忙着摆开了收购摊子。鲜乌药要拿到外地做种子,不按斤头算,只是数个数。薛叔戴着线手套蹲在地上,把乌药的大小分拣出来,五个五个地刨着数,边数边汇拢总数。那位年轻人坐在旁边,按个数等级开出发票。秋交会上,尽管卖乌药的人很多,但收购程序一点不乱,乡民遵照顺序依次进行。
采购站的工作人员忙得一塌糊涂,他们白天黑夜连轴转,白天搞收购,晚上也不歇息。天已黑定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工作人员打起电筒,牵出电灯,直到月亮挂在了半空中,才结束了一天的收购任务。我坐在家里的门槛上,看见薛叔站了起来,捶打着麻木的腰,指挥着工人把收购的药材连夜打包装进麻袋,麻袋堆满了整个采购站的廊道和学校的半个操场,公社派了民兵守夜。第二天晚上,开来几辆解放牌车,工人连夜装车,天快亮就开走了,所有的麻袋拉完,这才腾出了收购的场地。
第三天以收购竹子为主,造纸厂要用的毛竹,全部按照斤数来收购,虽然价格有些低廉,但收购的毛竹没有等级之分,卖竹子的男男女女连成了串,两个台秤都不够用。有的等不到过秤,打上记号,又去拉下一趟竹子来。堡坎下的菜园地,顺着一个方向堆放的毛竹,越堆越高,乡民踩上去甩竹子,脚下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放鞭炮一样响。
收购的百家竹和油竹,价格诱人,一根竹竿四至六分钱,但规格有些苛刻,食指大小,笔直匀称,竹节疤上的倒刺不能削得太深,百家竹三点二米长,油竹一点二米长,还要整百根成捆。幸好厂家和收购站提前做了标准样竹的动员宣传,才保证了收购量。那个时候,乡村不通公路,近处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用架架车拉运,绝大多数还是用肩膀扛。竹竿沉重而坚硬,扛着磨肩,好些人做了个荞壳的连肩垫在肩上,根本不顶事,肩上很快磨得青乌了一大块。但看在来钱的份上,都咬牙忍着。有的扛出了经验,找来一根坚硬结实的木叉叉,从另一个肩头往后斜插过去,木叉叉从后面托起肩上的竹竿。为了更省力,好些人喜欢扛着竹竿小跑,小跑一阵,有些累了,把木叉叉架在地上,撑起竹竿,歇歇肩头或者换上一个肩,继续向前跑。力气小的,两个人抬着走,虽然轻松一些,但挣的钱始终没有别人多。有时使了一身力气,流了一路汗水,如果竹竿被淘汰几根当毛竹贱卖,心里憋着那个气呀,真不知往哪里撒。惹急了,朴实的乡民只好再跑一趟,花点气力多带上几根竹竿,把第一趟的损失补回来。
竹竿的捆扎有规定,两头一样齐,各自用篾条捆两圈,踩紧竹竿,捆成一个模样。码竹竿也有讲究,横着一层,竖着一层,每层二十捆,横竖叠加挨在一起,这样码来的竹竿扎实,不易倒塌,也好记数。摞得有一人多高时,就斜搭着一块长木板作为支点,把成捆的竹竿往上加,形成三四米高的长方体竹楼。竹楼一座挨一座,占据了学校和收购站的整个场地,看上去非常壮观,宛如绿色的竹楼城堡。每个竹楼与竹楼之间,留下狭窄的通道,通道弯弯拐拐,如同迷宫一般。有些淘气的男孩爬上竹楼,站在最高层往下看,一个劲地说大人变小了,小人就像蚂蚁蛋蛋样。吓得薛叔跟着爬高男孩的屁股转,站在下面不断喊:“小孩,快下来。”并伸手接住朝下爬、衣服挂在竹竿上、身体悬在竹楼边的顽皮男孩子。我们女孩没有爬竹楼的胆量,就站在竹楼下玩捉迷藏,我们选出一个人来当猫抓人,其他的藏在竹楼后面,如果发现抓人的来了,马上转移到另一座竹楼下,我们不停地在竹楼里兜兜转转,跑来跑去地躲藏,有时不小心,与躲藏的同伴撞个满怀,或相互碰了个战头,哎哟哎哟地小声叫两声,摸一摸鼓起的大包块,跟着变成了同伙,把头蓬在一起躲起来,眼睛不时瞄着当猫的动向,嘴里小声说:“来了,来了,赶快跑到那边去。”说完,手牵着手,动作迅速地跑到另一座竹楼下。害得当猫的跑断了气,也找不到躲藏的人,喘着粗气累得灰头土脸,装着气愤的样子冲着大家喊了起来:“你们出不出来?我不当猫抓人,回家了。”同伴憋不住就走了出去,结果双手就擒。
秋交会结束了,竹楼在院子里堆不了两天,就有货车或拖拉机,一趟又一趟地开进来,把这些竹子全拉走了。空荡荡的操场上留下了我们奔跑的笑声,采购站又恢复了平静。没过几天,薛叔接到上面的通知,开始计划收购魔芋。通知上说,收购鲜魔芋每斤六分钱,花魔芋和黑魔芋按斤数称,分品种过秤。薛叔躬着背,写下通知贴了出来,过了几天,薛叔又要开始忙起来了。
那年三十的晚上,吃过团年饭,我跟着大人去院子里放鞭炮。绚丽的火花过后,眼前一片漆黑。当我正准备返回屋里时,却看到黑黢黢的对面有一小团暗黄的光。我眨眨眼睛,终于看清楚那光是从采购站的一间房屋的窗户上发出来的。我眼睛盯着那亮光,提着胆子走到窗户外将眼睛贴到窗玻璃上,看到薛叔正一个人端着一大碗面条慢慢吃,面条上盖着一个煎蛋。灯光让他的脸一半蜡黄一半隐在黑暗之中,如一尊黄泥雕像。我想敲开窗户问问薜叔怎么不回家过年,却听见大人在家门前焦急地叫我的名字,只好悄悄转身往回走。风把我的鼻子吹成了冰棍。坐在家里的火盆边,我眼前却始终是薛叔低着头吃面的样子。
一九七八年,我们搬到了河滩上的新学校,那儿清静,适合读书。听说薛叔也平了反,回到了擂鼓供销社。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薛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