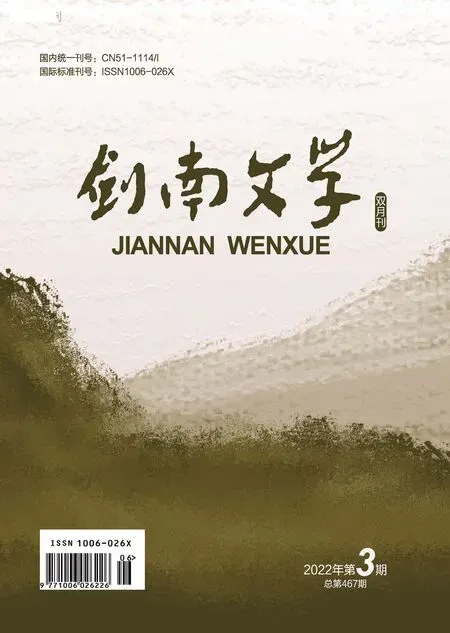方言写作的对抗与妥协
——评周恺长篇小说《苔》
2022-06-16庞惊涛
□庞惊涛
《苔》是四川青年作家周恺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晚清年间四川嘉定(乐山)富商李普福两兄弟的不同命运为线索,再现了蜀中百年前的地方风情和民间野趣。茶馆、染坊、饭铺、酒肆、青楼……市井之气,喷涌而出;袍哥、山匪、买办、纤夫……江湖之上,人来人往。《苔》于2019 年5 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21 年获得第十届四川文学奖。
青年作家周恺完成他的长篇处女作《苔》的时间线,如果确定是在2014年前后,那么,他实在是显得太年轻了:24 岁,这是一个大多数青年还在做梦的年纪;而当我们进入到《苔》用方言织就的古嘉州市井生活中时,又不得不感叹,这个作者真是太世故老练了。
作者真实的年轻和方言世界里虚幻的世故老练,就这样成为一对我们认知作者和作品的矛盾。
这样的反差,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是很少有的。我奇怪周恺何以能在这样的年纪,构建起如此全面、丰富、系统而复杂的社会生活经验,又何以能够将一百多年前的古嘉州市井生活日常复原得如此真实而细腻?在与生俱来的讲故事——文学概念上的虚构能力之上,他一定有一段相对长的蓄势周期,而他选择用方言来完成《苔》需要构建的社会变革(我并不太想屈从于他所津津看重的“革命”主题,相对于“革命”的宏大叙事,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才更具有文学力量)主题,更多是妥协于方言世界对公共话语的对抗力量——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像极了他真实的年轻和方言世界里虚幻的世故老练这组矛盾。
由此,话题再一次进入到《苔》的方言之魅。出版人欧宁在题为《方言之魅,职人之作》 的序里,似乎早就为《苔》的批评指定了方向。鉴于文学批评需要百花齐放,我也试图在鉴赏《苔》时跳出“方言”去寻找新的方向,但寻来寻去,我最后还是无可救药地落到了“方言之魅”的窠臼里。
特色何其强大,而要解读《苔》所构建的方言世界中丝丝缕缕的市井生活及其深刻的隐喻,又何其困难。历史久远,社会巨变,我们只有重新进入古嘉州方言世界的丰富韵味中去,或许才能找到《苔》所隐喻的变革密码和作家自己寄予其中的复杂情感。
一种对抗:不屈从于公共话语
其实,当代文学的方言写作,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从王蒙、王朔的北京方言写作,到冯骥才的天津方言写作,再到陈忠实、路遥和贾平凹的陕西方言写作等,方言写作一度在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中精彩纷呈、蔚为大观。看起来,普通话写作或者标准现代汉语写作有着覆盖性的强大力量,但还是有不少作家不屈从于这种公共权威,自觉性地选择用方言写作。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就坦承:一旦进入公共的交流,就不得不服从权威的规范,比方服从一本大辞典。这是个人对社会的妥协,是生命感受对文化传统的妥协。但是谁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一闪而过的形象,不会在意识的暗层里累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呢?
在我看来,周恺决定用方言来完成首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就是不愿意屈从于公共权威或者话语的规范。从最近的文学案例来看,金宇澄的 《繁花》一定对他产生了某种写作召唤。至少,从《繁花》达到的上海话阐释公共世界效果来看,它非但没有削弱读者对小说的理解能力,反而增强了小说的理解层次。对非地道上海人来说,方言反而成为了小说阅读最大的兴趣和吸引力所在。事实上,今天的上海,究竟还有多少地道“上海人”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说《苔》是写给乐山人、给四川人看的小说,实在是太过局限,也太不自信了。
按照今天对乐山方言的划分,乐山话归属于西南官话的灌赤片中的岷江小片。其特点是入声保留较为完整且有着独特的入声韵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言归属地划分,是从事语言研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黄雪贞在1986 年才提出并被学界接受的。也因此,小说《苔》中的古嘉州方言,本身就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并不能代表今天的岷江小片的真实语境。周恺在《苔》中所做的语言功夫,应是建立在古嘉州方言基础之上,而非用今天的灌赤片岷江小片方言去倒推古嘉州方言。
“方言写作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改变‘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对底层世界的代言方式,试图在叙事者与被叙事者之间寻找新的关系存在。”(《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第185 页,梁鸿著,中信出版社,2016 年。)比较有意味的是,《苔》的故事线恰好是“五四运动”这个巨大的变革之前,但这并不影响《苔》用方言写作的动机,即为底层世界代言。除了李普福等少数社会智识阶层之外,《苔》中所涉及的大多数被叙事者,都是底层世界的代表。不难想象,无论是刘基业,还是张石匠,他们的日常语言如果换成了标准的普通话,这部小说会耗损多少魅力。
而即便是李普福,也习惯了在和当地土族交流时,抛开他居高临下的官话,而试图用方言与底层人打成一片。小说开篇,李普福办八十桌大席,请堂口大爷、达官显贵、平头百姓吃酒。上一分台面上用普通话讲“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秒就用方言和希望攀亲的王棒客示好:“正将缺炷香火。”“正将”两个字,正是李普福精明世故讨巧之处。他用方言与王棒客交流,岂止是一种示好,深层次的动机,是通过示好稳住王棒客,而暗地里却不动声色地在戏台布局,让王棒客的女死于一场意外,彻底断了攀亲李普福的希望。方言在小说开篇之后渐次展现出了它看起来似有若无、实则大有妙处的作用。
为刘基业代言则几乎贯穿小说始终。为续李家香火,李普福抱走了刘基业的双胞胎中的一个儿子。作为回报,李普福许了刘基业管事之职,但新官上任不久的刘基业总是觉得各种不自在,于是去找李普福说话:“一天到黑背起手,晃过去晃过来,咋个会吃不消,只是晃得我心焦,背后还要遭人挞噱,老爷,你要觉得亏欠,不及如给我些银子……”刘基业不安然的原因,在于他受不了别人的挞噱,这是他这个身份的底层人适合的语言系统。成都话也惯用,表示轻视、蔑视、看不起的意思,但常写作“踏谑”,音近而字异,这或许正与方言在现实世界与时间中的流变有大关系。
张石匠作为底层人的代表,小说中的方言除了嘉州市井的“常用”外,还有石匠工人们自成一体的号子和黄话系统,如小说对古嘉州“小五行”行话或者说切口的呈现,即是方言写作在本书中的又一个细分。这一点,在《苔》中颇值得注意,尤其是黄话系统,特别值得提出来一说。如果说上面的方言,还是一种代言关系,那么,这种黄话系统的原样呈现,则是一种从代言到下沉的转化。作家周恺显然不是自甘“沉沦”,而是更干脆、直接和更赤裸地和底层对接,从方法论来说,这更无异于一次对底层细分语言系统的“考古”式发掘。无论是刘基业和幺姨太在江边野合的对白,还是石匠群体对张石匠与刘谭氏在石科野合的调笑,还是刘基业为满足吸食鸦片需要而为老婆刘谭氏招揽嫖客过程中的话语,都充满了强烈的诠释意义,即作家试图用对抗正式和典雅的公共语言,来对底层真实的精神世界进行生动的表达。粗野但表达逻辑无可替代的黄话系统,为本书的方言写作增色不少。在主流意识形态一体肃黄的大背景下,《苔》固执而且赤裸裸的黄话铺陈,毋宁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抗”。
除了对话语言,小说的情节和场景叙事里,也多用方言。这当然不是代言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叙事的亲近感和信手拈来的自豪感,更是一种民间写作立场的生动表达。从比例上来看,情节和场景叙事中的方言,似乎远远大于对话中的方言。这使得小说的语言风格从内到外、从开始到结束都呈现出一种刻意的“对抗”气质。周恺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用方言为小说中的人物情感和生活代言,即希望通过方言的生命活力、日常性与抗腐蚀性,对公共世界形成一种反作用力,并以此改变公共世界的面目。这种反作用力,表现在小说中,就是无论是李普福还是刘基业,他们都试图“对抗”和阻止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变革,将古嘉州的世界维持在当下看起来平静的大环境中。税相臣作为公共世界的代表,必将以暴力的方式破坏古嘉州自成一体的方言世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或者说变革者和保守者,在本书中也是一种对抗关系,表层的对抗,就是语言的对抗,而深层的对抗,则是对未来社会秩序建构的对抗。

无形中,语言成为了这两种对抗融合的桥梁。
或许还有一种对抗意图存在,即古嘉州方言与晚清强势政治话语的对抗。对刘河坝乃至大多数古嘉州人而言,政治话语是外来输入语言,而古嘉州方言是他们日常的生活话语。从来没有哪一种输入型话语能在生活话语中站得起手,更何况,天高皇帝远的古嘉州人对强势政治话语一贯保持着一种排斥的心理。官方政令和文告,在这里是迟钝的,除了税相臣的主动对接,书中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书院山长袁东山,也对这种强势政治话语进行了方言化翻译。送别最欣赏但是政见不同的弟子税相臣,他没有用圣贤之言,而是亲切如邻家老翁招呼“上去坐下嘛。”这样的方言表达,在山长袁东山说来,更像是对强势生长的税相臣最后一次教诲,他用这种语言,试图去淡化政治话语的强势性,保留一点方言的本真。但他没有料到,后者根本没有给他任何机会,这似乎也预示着方言世界最后不得不面对的妥协。这种言语的对抗,从心理上也助长了小说中人物观念行为上的对抗,语言和行动在小说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君臣关系早就荡然无存,父亲卖掉儿子、丈夫招嫖卖妻、朋友为利益翻脸不认,传统的五伦关系在小说语境和场景里被肆意冲击。种种痛快淋漓、匪夷所思的情节铺陈,都在表明作者的对抗意图。
一次妥协:与文明的对接势在必然
《苔》的第三卷臃肿而啰嗦地表达作者的变革主题,使鲜活生动的方言世界,到此急转直下,进入到强势政治话语主导的崭新世界。这标志着前面两卷的对抗力量,在第三卷被完全消解,方言写作到这里转向一次看起来不得不然、实则勉为其难的妥协。小说似乎是要将方言世界主导下的古嘉州城和所有人,负责任地带入革命性的文明新世界。也因此,方言与代表着文明世界的强势政治话语的对接,变得顺理成章。
从东洋杀回来的税相臣成为强势政治话语的代表力量,并负责与代表方言世界的李世景兄弟对接。
身处晚清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政治变革、经济变革和文化变革势必会削弱方言的力量。更进一步说,这样的变革,也必然会对方言世界进行强力清洗,这就不难理解第三卷中几乎铺天盖地而来的强势政治话语了。这体现出了作者一定程度上在直面变革时对方言的难以把握,更甚至说是一次有意识的妥协。此时,他更像是作为变革者的税相臣的代言人,主动地在自己的叙事中让渡出了方言的位置。到此,底层世界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退出,小说的民间立场也退出,为底层世界代言的功能也退出,方言的活力及其内部畅通无阻的交流性,在强势政治话语的覆盖下几乎片甲不留。朝廷和省府与古嘉州的时空距离在缩短,洋人的外语这个时候也插进来,啸聚山林的刘太清答应李世景和税相臣加入暴力革命,可视为这种妥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尽管,他们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
另外一点,这次妥协或许还寄托着作者对方言世界中的底层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和教诲,所以,要安排一个文明世界来的税相臣重回嘉州,为他们现身说法。一定程度上,作者在这里成为了税相臣的附体。但是,在刘基业们看来,激进而暴力的革命手段,哪里能代表文明世界,它反而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颠覆和破坏,“大国寡民”心态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执念在第三卷呈现出一种拉锯的状态,但和前两卷相比,方言世界的力量很显然已经被消解得所剩无几了,相互的妥协态度给变革留下了苟延残喘的时机。不得不说,这样的妥协是不得不然的。
公共话语的逐渐强大,让方言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也是不得不妥协的客观因素,当然,这种妥协也代表着一种历史规律。嘉州终归要被乐山取代,刘河坝迟早要被外部世界同化,方言的使用范围,随着外部世界的洞开,也必定会越来越小。即便李世景和刘太清还在说着方言,但过于冷僻的方言不再高密度地出现,而且,对话中的方言也在减少,粗鄙的或者干脆是黄色的语言慢慢退出。这种写作上的自觉“净化”,正是方言写作的一次集中妥协。
一个困境:方言写作的可能
《苔》绝不会是最后一部用方言写作的小说。
可以想象,未来还要诞生很多类似的方言写作的作品。但《苔》无疑是乐山方言写作第一部最为成功的作品,它第一次帮助乐山方言用文学传播的方式输出到了更广阔的“普通话”空间。仅就方言写作的贡献而言,《苔》初步具有了方言写作的言说价值。
在多重文化语境交会中自觉的方言写作,作家周恺和他的《苔》注定会受到持续的关注,这必将伴随着方言考古化重热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全球化浪潮裹挟之下,方言世界也必然面临方言言说空间的流散这个客观事实。“各种西方现代文化思潮与文学流派如意识流、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等,或是由‘供内部批判参考’转为向广大读者公开发行,或是由全译取代过去的‘节译’,在中国公开露面,让过去只能按一种模式思维,只会用一套话语表述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感到目不暇接。”(《让文学语言重归生活大地:论方言写作——以陈忠实为中心》,王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进入这种文化语境变迁的“后新时期”,就不可避免要带出一个写作困境:方言写作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面貌?或者说,以方言主导的文学写作,在未来还有没有必要?
评论家梁鸿对此持悲观立场: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的方言大地正在丧失,方言正在丧失其原有的活力与内部的交流性,它与地域、环境、生命情感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默契正在消失。(《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第199 页,梁鸿著,中信出版社,2016 年。)类似《苔》的方言写作,其实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作家周恺本人的“文化考古”功夫上,“与生俱来”的那点母语基因,早已经无法架构这样的方言巨构,或者说,支撑不起如此强大而细腻的叙事流。
如果说一定可控量的方言,尚可激起方言世界之外的读者的探究学习欲望的话,那么,高密度与高浓度的方言写作,则只能让读者望而却步,如此看来,《苔》 的方言密度与浓度似乎处在一个让读者尚可接受的范围,这可视为对未来的方言写作的一种警示方向。另外,从方言自身的进化和发展来看,一个局地的方言也正在受到更广大范围的语言的同化和侵袭。公共话语、强势政治话语代表着权力、高傲和理性,必然会以压迫性的方式,进一步破坏方言世界。
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方言写作会越来越弱化,相反,非遗化倾向的方言或许会更激发出当代文学重返传统的勇气和锐气。作为90 后的周恺,接受了现代标准汉语教育的作家,尚且以这种方言写作的方式最大化地进入方言世界的核心,更何况那些怀着浓浓乡愁的中老年作家,方言写作或许正呼应着他们重返故乡的精神需要。从上个世纪90 年代兴起的方言写作,虽然已经走过30 余个年头,但依然处于“后新时期”,弱化的迹象尚未呈现,兴旺的半途上,或许正酝酿着某种变革的可能。
那可能是另一组对抗与妥协的矛盾。《苔》在这个时间点的中间,不可否认地,既因应着一种方言写作的宿命,也承载了一定的方言写作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苔》 的价值需要在未来的方言写作中,得到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