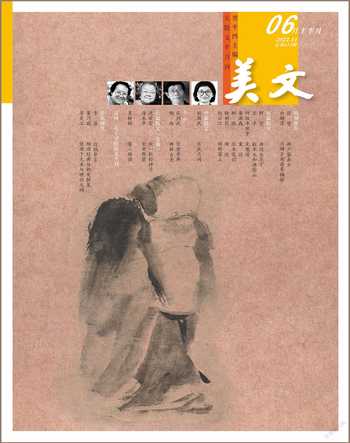两户服务台
2022-06-16匡燮

匡燮
“两户服务台”是我从商洛驻站回来后,农业部交我主办的一档专题节目。
这是档很新的节目。
此前无论什么名称的节目,除董其焕董老办的那档农村科技节目外,一般都由大家集体供稿,专人统筹编排的。现在由我一个人来办这样新的节目,除董老外,在其他同仁中尚属首次。另外,这是档专门回答听众来信的特别节目。过去,听众来信,只作为了解下情,看了就行了。若个别需要回答时,也只作为回信处理,少有在广播上公开回答的。像《两户服务台》这样专门回答听众来信的节目还从未有过。它与过往节目的最大不同处是对农村来信有问必答,是一档实实在在的服务型节目。而这档节目的出现完全是时势的产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三中全会后,农村形势大变,从农业学大寨到包产到户,异常地生动鲜活起来。长期被集体化束缚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犹如火山喷发一般被释放出来。江流拍岸,春色乍开,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时间,广大的农民群情激奋着在广阔的田野上,精耕细作,多种经营,向致富的道路上迅跑,便很快涌现出了一批万元户和养殖专业户来,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致富的榜样和先导。及时介绍他们的致富经验,解决他们的困难,回答他们的问题,从而向广大农民群众提供致富门路和有针对性的科学知识,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已经成了农业部对农村宣传的重中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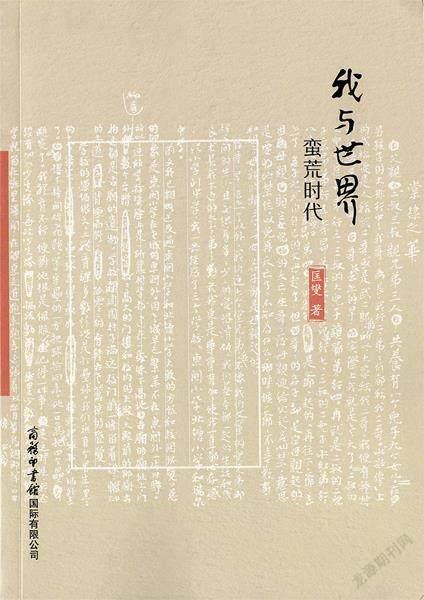
匡燮《我与世界》(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记得,这时候,农业部的情形也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起来,亮点是人才的被重新发现方面。比如,在曾经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了批判的、一直在农业部主任位子上多年的成方同志,一下由处级提拔到了厅级的职位上,先是副厅长,后来又正厅长。接着农业部的马希麟、李牧泉两同志,又被成方同志很快分别提拔到了省电视台副台长和省电台副台长的职位上。不久,董其焕董老被任命为厅总编辑办公室主任,简称总编办主任,统管电台、电视台两台的宣传业务。一时间,由农业部成长起来的领导成为全厅上下的一支重要的领导力量。农业部也被人们称作了培养厅台领导的党校。
董其焕董老虽然要总揽两台的宣传业务,但他心系农业部,依旧对电台的农业宣传关注有加。本来,从厅长郭成方到两台副台长马希麟、李牧泉,还有董老,原先也都是业务干部,是业务岗位上的佼佼者。尤其董老,可以说在业务上是电台编辑、记者群中的一面旗帜。他对广播语言的研究和造诣,以及对民间语言特别对农民语言的兴趣和热情,即使全国广播界也屈指可数。他曾参加了由广电部组织的全国广播志的编写工作,是重要的撰稿人之一。由于他在农业宣传上的长期历练和经验,使他在农村形势发生变化时,便很快敏感地认识到农村专业户和万元户是农民致富的新生事物,应该从宣传上及时地加以指导和帮助,便随即设计了这档专门服务型的《两户服务台》,并指定要由我来主办这档专题节目。
说来惭愧,自我来到了农业部,董老就对我期许甚殷,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扎根广播业务,钻研广播语言,为广播宣传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次把他亲自设计的《两户服务台》专题节目,交由我办,既是他心系农业宣传的一份托付,也是有厚望于我的又一次体现。但从我过往的整个经历来看,我是有负于董老的期望了,因为我并未把精力投入到董老所钟爱一生的广播宣传事业中来,而是一直从事着我业余的文学创作。不过,董老之所以能寄望于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自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广播战线,开始是小城广播站,接着便到了省电台,十余年间,我一直在自己的业务上努力奋斗着。尽管在小城广播站我已发现,广播新闻稿件写作的用字、用词重复的多,开拓的少,重音节,轻形义,如此以来,常此以往,只重了发音对否,至于错别字渐渐地便也被忽略过去了。记得,我到了电台后,有一次,我在母校中文系见到过一位老师,他曾是省电台很是著名的记者,毕业于北京的某所大学,但他分来省电台没过几年,便要求去大学教书了。我问他原因,他和我对广播稿件写作的感觉几乎一样,却说得更为形象和深刻。他知道我也在电台工作,便热情和随意起来。当说到在电台工作和在学校教书有何区别时,他笑了,显得激动的样子,便用手比划起来。他先是将一只手举到胸前,然后不断地往下压去,一边说:“你看,在电台当记者,你的水平就会这样,越来越低。可是,在大学教书呢?”他又把压到腿部的手,慢慢地往高抬,一直又抬到了胸前,“你的水平会这样越来越高。”当然,我没有像他那样离开广播,却从小城广播站开始,便业余兼顾了文学创作,以降低广播写作所造成的自己在遣词造句方面的退化和无力。然而,这一切只作为一种补充而已,重要的依旧是对广播新闻事业的追求和努力。我不是新闻科班出身,所以,不必说我在小城广播站十年,一开始如何独自摸索写稿,以及向经常下来采访的陕报记者学习,也不必说由对新闻稿写作的一无所知,到后来独立写稿在报上发表,其间的挫折和坎坷,失败和成功。这一些我已在另书中写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单就广播稿件的一种形式,录音通讯的学习和实践,就颇费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日。
当时的情形是,我初到小城广播站的前几年,下基层组稿和采访的多为报纸记者,并不见电台记者到基层组稿和采访。有一段时间,省电台似乎停播了大量的自采节目,以传播中央台和播报纸文章为主了。也许还有少量的自采节目,却因小城地僻县小,可采的典型不多,家有梧桐凤凰落,小城少有梧桐树,便也引不起省电台记者关注了吧。猜测而已,不足为凭。不过,我在小城广播的前四五年间,没见过下来的省台记者却也是事实。到地区来组稿,到县上来采访的是陕西日报记者,我便跟着他们学习,开始为陕报写稿。开始依旧不易,由屡屡投稿不中,到有投必中,成为报纸的重点通讯员,再到有一次,为了配合某运动,陕报记者电话约稿,我把赶写的稿子头天送去,第二天下午返回小城,下了火车,从站台读报栏前经过,当天的陕报张贴在读报栏内,回头一看,我昨天才送的那篇稿子,已上了某版头条。到此时为止,算来我已到小城广播站數年之久了,其中甘苦,不能尽述。AD37B3BC-544C-4618-B607-E0C4D0752DB9
还在我刚到了广播站不久,有一次,陕报到地区组稿,来的是一位著名记者,叫袁澍德,经常见到他在报上发表整版的长篇通讯。陕报下来组稿,联系的是各县的通讯组。县通讯组隶属于县委宣传部,曾一度隶属县革委会政工组,只有一个人的叫通讯干事。陕报下到地区来组稿的记者,先在地区召开各县通讯干事会议,汇报情况,布置选题,然后回各县分头采写,然后再分头送地区来,由报社记者面改定稿。能否上报发表,即在此一举。有一批老通讯干事,不光写稿经验丰富,还和报社记者人熟,面改定稿时,说笑中稿子也就通过了。但对有的新手来说,面改定稿不啻是一大难关,从开始便心中发怯。加之,这次下来组稿的不是别人,是心直口快,又恃才傲物,说话不留情面的名记者袁澍德,我们县的通讯干事左文武才刚从别的单位调来不久,是位新手,更是胆怯有加,我到广播站比他大约早了一年,所以,他一从地区开会回来就来找我,把领来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也不知道其中的水深水浅,更不知袁澍德何许人也。袁澍德住在地区招待所,我家就在附近的东风电影院的巷子里,送稿子还可顺便回家看看,就勇敢地应承了下来。
很快,我就带着写好的稿子到地区招待所见袁记者来了。那时的地区招待所比较简陋,四人间,相对着两张架子床。我进去时,袁澍德正在一边架子床的下铺上靠被子半躺着休息,一脸的络腮胡,是个很粗壮的人。见我进来,忽地折身起来,腰一直,头皮擦着了架子床上层床板,显得很热情,问我哪县的,我回答后,他说:“左文武为啥不来,叫你来?”态度严肃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当面审稿,本来就紧张,便一时没回答上来,他也不再往下问,说了声:“好吧,稿子拿来我看看。”我立即把稿子递给了他。他把稿子接过去,直着的身子又向后半躺了下去。不足千字的一篇稿字,他一会就看完了。开始我站着,见他向后躺下了,我也悄悄向他脚后的床沿坐下来。刚一坐下,就听他翻动稿纸的声音,感觉那翻动的响声有点烦,又赶紧站起来。他也折起身,半低了头,这次头皮没能擦住上边的床板。他看着我,抖了抖手中的两页纸,以略带挑衅的口吻说:“你说这稿子行吗?”我不知道行是不行,脸上发着烧,没有回答。他就继续说:“那天,左文武汇报的情况,我出的题目,你在这题目下装了些材料,没有一点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就这样拿上来了?”嘴角上有一丝似笑非笑,强调着他的质疑:“啊?”我脑子“轰”地一声,爆炸了。胸脯挺了挺,僵直得像個木头。“好吧,稿子留在这儿,你可以走了。”也许他看出了我惊慌失措的样子,是个新手,口气随即和缓了些说:“全用是不可能了,我回报社编个短讯发了吧。”从进门到出门,前后也就五分钟。走到大街上,我依然一脚深一脚浅的,原本打算要回近在咫尺的家里看看的,很长时间后,一抬头,却走到火车站来了。
此后,我便几乎每周都要向陕报投稿,有时候,还两篇两篇地投,泥牛入海,也坚持不断。终于有一天,我投去的稿子见报了。小城较远,当天报纸下午才能来到邮局,第二天一大早才由邮递员送到单位来。我为了看到当日的报纸上登没登我的投稿,便每天傍晚步行数里,由县城去址在岳庙镇的邮局先睹为快。那日傍晚,我再次来到了岳庙街上的邮局院子里,暮色已起,星星未出,天空很深邃地蓝着,院子深处办公室的电灯已经亮了,我知道邮递员正在那地方分发新到的当日报纸。我正要快步赶过去,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时候,不知一只什么鸟在高空里正从我头顶飞过,一点鸟粪,不偏不倚,“啪”一下,正好落在了我的鼻子尖上。用手一抹,水似的,白色。便在心里叫一声:“晦气。”就想往回走,却已来在了那个分报的办公室门前了。又转念想,既然来了,何妨进去看看也罢。分报的都是熟人,顺手便把一张报纸递给了我:“郭记者,快看看那上边登了你的文章没有?”“我不是来看那个的。”我掩饰说,“我是来看看这报上,有没有可供明天广播的文章哩。”可是,奇迹出现了。我一打开报纸,一眼就见了三版上登了我投的一篇稿子,立时激动起来。我是从四版往前翻的,又一翻二版,呀,二版上还登了我的一篇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张报纸能发我两稿子?不是做梦吧?刚还在院子里,天空那只飞过的鸟,空中落下的鸟粪,我再次摸了摸鼻尖儿,室内黄亮的灯光,分报纸的邮递员,又再次看了遍了报纸,当我确定这一切不是梦,而是真实后,便忽地拿起报纸,快步走出邮局大门,看四下没人,飞一般跑回广播站来了。
以此为契机,便终于踏上了向陕报投稿的坦途。之后,命中率越来越高,几乎每投必中。那年唐山大地震后,小城地面在救治伤员上出了个典型,由我执笔的长篇通讯《似海深情》也在陕报整版发表了,被选为了当时的中学辅导教材,恰是证明了我那时在新闻业务上的奋斗和进取,而且,要感谢袁澍德记者那次的面审和刺激。袁澍德先生性格爽直,在报社是位富有正义感,常爱打抱不平、很可爱的人。我调进省电台,相互熟了以后,我向他提起那次审稿的事,他哈哈大笑着:“有这种事?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可以说,在我与陕报记者交往的几年里,还从未见有省电台记者下来采访的。广播站和省电台的联系,也就是每晚必转的秦腔节目。省电台记者到基层采访,是后几年的事了。这一情况的改变,想来应该与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有关了吧。在这一时期,也许省台才又恢复了正常的自办节目。总之,这一时期,陕报记者到小城来的反而不多了,常常看到下来采访的几乎又全是省电台的记者了,便是两三年间,记得到小城采访的省电台记者就有政教部少儿组的马景华、邢继英,政教部学习组的王悦强;农业部的肖方、李效生、王先锋;渭南驻站记者田秉义,还有中央台驻陕记者站的老叶叶进前。而且,不同的是,陕报记者下来接头的多是县委通讯组,省台记者一下来,直接找的就是广播站。于是,我和周朝旺便很是忙碌和兴奋了好多年。
通常的情况是,凡有省电台记者来了,必先要在饭店请一次,为他们接风,以示礼貌和热情。然后的伙食便安排在了广播站的大灶上,伙食费和粮票也都由他们自己来交。而饭店的这一顿便是我和朝旺私人请的。但因我的月工资是四十七块五,比朝旺只有三十八块钱的工资高许多,所以,每一次便是我出钱。那时候,小城内只有两家饭店,一家公私合营的,一家国营的。公私合营的这家只卖两样吃的,一样是开花包子,一样是懒麻食。开花包子要比普通包子大了些,两头尖,菱角状,包子背上开口,露着粉条馅,吃的时候,就从开口处浇进去油泼辣子,吃起来味道很鲜美。懒麻食,就是油豆腐烩粉条。这两样吃的主要都是粉条。饭店一大间门面,里面一边是灶火,一边摆着两张不带漆的八仙桌,后边靠墙就堆着半墙高的粉条包。墙是土墙,墙角处有老鼠洞,粉条包里常有老鼠出没,所以,吃包子,有时侯一不小心,一口饺下去,那开花包子里会咬出一颗老鼠屎来。因有如此不便,这地方也算是小城著名小吃,招待起客人来,还是觉得不合适。AD37B3BC-544C-4618-B607-E0C4D0752DB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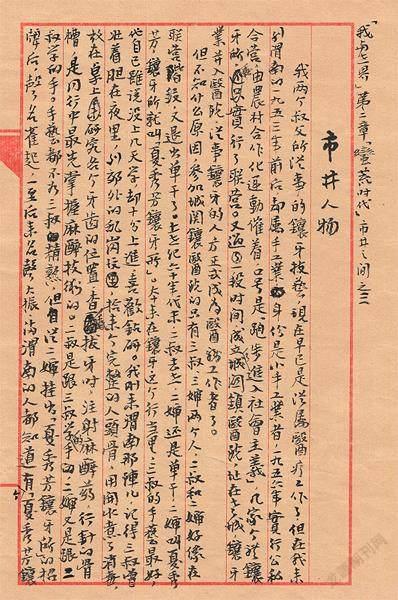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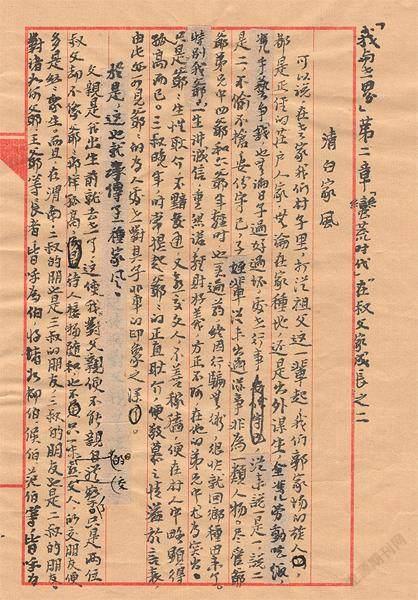
匡燮手稿
那家国营食堂里有炒菜,还有酒,相较之下,这地方是利于招待客人的,所以,每次给下来的省台记者接风,便都在那家国营食堂里。其实,也简单,虽说是炒菜,那年月困难,缺油,经常炒菜都是拿酱油炒的。就这样炒上一荤一素两个菜,每人一两散白酒,最后每人再来一碗荤面条,也就算是宴请了。感觉还是挺好的。虽然,每次都是我出钱,却从不觉得自己吃了亏,朝旺也不觉得沾了光,被招待的记者也不觉得受宠若惊般,一切都那样自在和自然,平淡和美好。宴罢,第二天,或在站上借辆自行车,或一时借不到,我或朝旺,主要是朝旺,他比我骑得好,就用自己的自行车带着,一路上说说笑笑,下农村采访去了。于是,凡到过小城采访过的省台记者,无一例外都成了我和朝旺的朋友。后来,比如肖方和王悦强两位,还向省电台推荐了我,使我调进了省电台。到电台后,朋友们依旧地对我照顾有加。这是后话了。
且说,省台这批记者朋友的先后到来,比之于先前陕报的那几位记者朋友,是又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冲动和喜悦,这便是广播稿件中的录音通讯,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奋和向往。报纸是文字的视觉传播,广播是声音的听觉传播。于是,广播不仅可以把文字变成声音,而且,还可以把讲话、自然音响、音乐等素材组合在一起,组成一篇听觉丰富的稿件,这便是广播传播的特有形式:录音通讯。这一稿件形式深深吸引了我和朝旺两个人。
那个阶段,省电台播放的这类稿件中,有一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郭成方、樊明生共同采写的录音通讯《“东方红”诞生的地方》,是介紹陕北民间歌手李有源如何创作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那首后来传遍神州大地、响彻云霄的革命歌曲《东方红》的。通讯音响丰富,激情澎湃,令人神往。
关于录音通讯的采写和制作,一开始是有争议的。争议的焦点主要在配乐上。一种认为录音通讯可以配乐,使其更为丰富动听。一种认为既是录音通讯,不可以配乐,配乐的应该叫配乐通讯,否则,便有悖于新闻真实。但实际的情况是,凡录音通讯都喜欢配乐播出,好听,对听众更具感染力。《“东方红”诞生的地方》,便是篇配乐通讯。
这原本不是个新鲜题材,“东方红“的乐曲是人们熟知的可以随兴填词的陕北民间小调,也曾用它歌颂过刘志丹。后来陕北民间歌手李有源,又把歌颂毛主席的歌词填进了“东方红”的小调里。这些都是很多人早已熟知了的。但是,这篇录音通讯将这段史实重新叙述,且有李有源站在黄土高塬上的引颈高歌,有他的讲话录音,再加以文字串联,背景交待,又有交响乐《东方红》的衬播,以及当时大树特树的形势,种种因素和机缘遂赋予了这一题材新的时代意义和无尽魅力。记得,我听到这篇录音通讯是在薇林就教的岳庙中学的校园里,大半早上,学生的早操已经下了,我正要从学校到广播站去,架在教师宿舍门楼上的大喇叭响了,是广播站转播的省电节目。但忽然异峰突起,一开始便是李有源站在陕北高塬上的引颈高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后才压低了,在歌声中播报了录音通讯的名字,然后歌声再次扬起。我立即站住了。接下来,记者采访李有源的录音,激情的串词,环环紧扣,高潮叠起。最后,交响乐《东方红》轰然响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仿佛真的看到了那轮金色的太阳,正从地平线上,从我眼前,从我心中冉冉升起,照亮了大地,照亮了天空,也照亮了我整个的灵魂……直到节目结束,我依然激动着,陶醉着,站着不动。下课铃响了,薇林从教室走出来,吃惊地问:“你还没走,站着干啥?”我这才猛醒过来,蹬上自行车,回广播站去了。
很快,我和朝旺就制作起录音通讯来了。我们录制的第一篇录音通讯是《华山脚下春耕忙》,说的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华山公社南洞大队发扬大寨精神,搞好春耕生产的事迹。按当时条件,县级广播站是没有能力制作录音通讯的。当然,文字稿是没问题的,现场录音也可勉强办到,难度在于合成制作。要把录音讲话、现场音响、文字稿、配乐等这几种不同的元素统合起来,组成一篇完整的、可供播出的录音通讯,不仅当年广播站的技术手段难以具备,即使省电台,我调进省电台后才知道,制作一篇录音通讯也相当复杂,要在技术部的录音组,经过数部录制设备并用,由编辑记者与技术人员通力合作方得完成。制作之麻烦,让人却步。像《“东方红”诞生的地方》这样气势恢宏、制作精良的录音通讯,便是在省台亦不可多得。为此,便一直对这篇录音通讯的两位作者郭成方和樊明生心存仰慕。有一次,我和朝旺到省台送稿,因审稿的是樊明生,让我们倍感荣幸。
由于省电台记者们的示范和激励,不仅我跃跃欲试想搞录音通讯,而且,朝旺的积极性比我还高。他对新的东西特别喜欢钻研,越难办到便越要钻研。比如省台下来采访的记者,都要在肩膀上挎台盒式的录音机,广播站没有,出于好奇,每次朝旺都要打开来试着录下音,研究一番。中央台驻陕记者站叶永前下来的那次,带了台比省台记者小了些的更轻便的录音机,朝旺看见,眼前一亮,没经同意,就打开摆弄起来。老叶一见,急忙上前阻拦,说:“不敢动,这家伙刚发下来,是最新型的,我还不熟悉哩。”但录音机已经打开,朝旺笑笑说:“就是比省台的小了点,没啥难摆弄的。”一边说,一边操作。老叶见他操作得宜,也笑了说:“行呵,看来你比我还熟悉哩。”过后,他对我说:“我们也能搞录音通讯。”我说,真的?他说,真的。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而且,告诉他,题目就叫“华山脚下春耕忙”。他听了十分激动。我说:“咱们只有一台开盘机,怕合成不了吧?”他说:“你放心,只要你把稿子写出来,剩下的你不管,我包了。”我们俩一拍即合,我写稿,他录音。录讲话,还录自然音响。末了,想尽了各种办法,不仅把到手的素材统一合成,还给文字配了乐。录音通讯《华山脚下春耕忙》一经在省台播出,立即轰动小城。同时,由于我们是全省第一家广播站在省电台播出录音通讯的,也引起了省电台的关注。之后,省电台召开全省广播经验交流会,经记者肖方推荐,录音通讯《华山脚下春耕忙》特许在会上播放,供与会者交流学习。再后来,省电台和中央台驻陕记者站能同时发函调我,也与这篇录音通讯的采录成功不无关系。AD37B3BC-544C-4618-B607-E0C4D0752DB9
但我并不满足。《华山脚下春耕忙》配有音乐,严格意义上说属配乐录音通讯。到省电台后,我很想再尝试不配乐的纯音响合成的录音通讯,甚至没有文字串联,是一种采访过程的记录和整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后来的主持人节目形式尚未出现,现在想来,我当时的那种构想,实际上是应广播在宣传形式上由自在向自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朦胧的自由意识,与主持人节目不无相通之处。
机会终于来了。
便在我刚刚从商洛驻站回来不久,广大乡镇和农村在三中全会的浩荡东风里,蓬勃兴起的农村多种经营已是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了。这时,关中道上的周至县有个亚柏古镇,那古镇上勃然兴起了一股刺绣热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带动了四邻八村,家家走线,户户飞针,一时间关中刺绣声名雀起,惊动邻省,大有与我国传统的鲁、苏、杭、蜀四大名绣争夺天下,平分秋色之势。
便听说这其中有位姑娘,心灵手巧,名动乡里,是这古镇上著名的刺绣专业户。恰逢这姑娘结婚那天,我即刻赶了过去。便在人流攘扰、热闹非常的新房里开始了我的采访。我手执话筒,一边解说,一边和新娘交谈。洞房内外的鞭炮声、吵杂声、欢笑声等等的现场音响也一并录了进来。回电台后,不再写稿,只到技术部的录音组进行了一番剪辑便播出了。我以为这是个很纯的录音通讯,会引起注意,却因广播节目的全面改革尚待时日,所以,如此面貌的录音通讯,也并未在当时引起关注。只作为一档普通节目,播完也就风流云散了。而当下,引起关注的倒是为农村多种经营专业户提供服务的《两户服务台》。

匡燮《野花凄迷》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不过,谁也没想到《两户服务台》的开办,会在农民听众中引起那样的强烈反响,节目开办不久,农村的听众来信真个如雪片似的飞来。开始每天百多封,接着数百封,到后来增加到每天一千多封。收发室的人开始还一封封地数,然后捆在一起送过来。随着听众来信越来越多,收发室数不过来也不数了,一大把一大把往面口袋里装,也不送了,装满了打电话通知去取。如此状况,为广播有史以来所未有。于是,在台内便传说起来,说是农业部办的《两户服务台》,每天听众来信拿大麻袋装哩。消息传到了台长冯百胜同志耳朵里,冯台长激动了,便向厅党组作了汇报,厅长正是成方同志,便要我向厅党组会议作专题汇报。我从未参加过这样的高级别会议,更没有在这样的会议上向厅上的领导汇报过工作。会前,冯台长还特地叮咛我汇报时不要紧张。但是,在汇报时我还是紧张得不行,只盯着备好的稿子念,始终没有敢抬头,一念完便匆匆离开了。我还是十分激动和兴奋。自到省电台以来数年间,还从未听说过有哪一档节目,被重视到在厅党组会议上汇报的。当然,这并不说明我的能力有多大,节目办得有多好,而是说明了《两户服务台》应运而生,乘势而发,办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心上了。这便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工作热忱,同时也坚定了自己为农村的专业户和万元户尽心尽力服务的决心和信心。
说到《两户服务台》中的两户,实际上说的就是多种经营中的专业户,万元户是专指年收入达到了万元的专业户。当时,一户农民年收入能达到万元的,己是十分可喜了,即是首先富起来的专业户了。当时,农村的多种经营项目很多,农、林、牧、副、渔方方面面,单是养殖业,除了通常的养羊,养鸡,养鸭,养鱼外,记得当时很是热门的,还有养蝎子和养土鼋。土鼋是一种带有软甲壳的昆虫,往往在房里屋外潮湿的角落里,能经常看到它,黑色,样子像鳖似的,跑得很快。这种虫可以入药,是种药材。有些人家就专门养土鼋,成为养土鼋的专业户。既然专业户如雨后春笋,五花八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就是门路、方法和技术,便纷纷致信《两户服务台》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来询问。为了能尽量满足广大听众的希望和要求,我联系了省市农林牧副渔等部门的六十来位专家,作为《两户服务台》的顾问,就听众来信所提问题,分门别类请这些专家回答了,再在节目中回答给听众。另外,组织专业户介绍经验,专业户之间互相交流。但这回答的信件和专业户交流的经险,都要经过编辑,形成稿件。主持人节目还未出现,这些编辑好的稿件,要送到技术部的播音组安排播出。每天一期,必须按时交稿。自《两户服务台》开办以来,我连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晚上也在加班写稿,礼拜天不上班了,在家里也还工作。直弄得精疲力竭。然而,这还不是最难的问题,最难的问题是看信,每天有那么多聽众来信,不要说编辑,一个人连信也看不完。我向部门反映,部门反映到台里。冯台长了解情况后,便随即从外部门调了一位女同志,来专门帮助处理信件。
她叫周玉清,还记得她爱人的名字,叫孙仲元,在厅办公室工作,是不是厅办主任,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好像是陕北人,干部子弟,不苟言笑,很有些男子气,人际圈子好像就是省电台的几个干部子弟,与别人不太交往。后来,周玉清到《两户服务台》节目来了,我们也都始终保持陌生,碰了面也不说话,只微微一笑就过去了。周玉清不同,平易,和顺,又很能干,是那种南方女人的利洒和干练。瘦瘦的中等个子,脸上有雀斑,不难看,反添了种淡淡的秀质,使人想起江南水乡的女子来。自她来到了《两户服务台》,每天早晨上班,她都比我来得早,进得门来,先用湿拖把,把水泥地面拖干净了,然后,就把信件一封封一排一排地摆地面上开始一天的工作,天天如此,有条不紊,有时侯,我来得早了点,她正拖地,只见她弯着腰,把单薄的身子俯在拖把上,那么用力的样子,就觉得在地面上滑动的那团碎布条显得又大又重。可我要换她,她总不让,笑笑说:“你快坐下看信吧,昨天的那一厚摞还堆着呢。”说罢,一甩头发,就到厕所的水池里洗拖把去了。这时侯,地面湿湿的,门窗打开着,能闻到一种水的清气来。
拖罢地,就该下楼到门房取信去了。取信回来,地也干了,便把信摆在地上一封封地拆开来,看着,分检着,归类后,再把有典型的信交我处理。于是,整个上午,她检信,我编稿,各自完成着各自的任务和工作,很少说话和交流。可以说,《两户服务台》能够取得听众的信任和赞誉,她的努力功不可没。我在台前,她在幕后,却从没见她争过什么,一如既往,默默无闻。后来,她丈夫前往深圳发展,她便举家南迁,从此,相忘于江湖,是连她的名字也记不得了。只是在近日写此文时,才忽然想了起来。而唯此,却让人不忘。AD37B3BC-544C-4618-B607-E0C4D0752DB9
然而,《两户服务台》在人们传统新闻的认知里,还并不认为它是一档真正意义上的专题节目,不能进入创优、评奖序列。当时,所谓创优、评奖的机制还未建全,全国广播系统虽已设立两个奖项:优秀节目、稿件奖和优秀节目、稿件提名奖。但省一级还未设奖。全国参评的节目和稿件,是每年由省台内部将评出的本台好稿若干件送全国广播系统参评的。属于创优评奖的初级阶段。随着时间推移,这方面的机制越来越建全,奖项细化,奖次也分出一、二、三等来,省一级广播系统也设立了专门的评奖机制,奖项、奖次也一一与上一级对应。省电台已不能直接向全国推荐,只能向省一级评奖机制推荐了。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获奖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有的省级电台还组织起一批人不干别的,专门创优。有的台虽没有专门创优的一班人马,但都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创优,而且,对于创优稿件或节目另行精心编采和制作,已成为各个电台的普遍现象,不再像初期这样,所有参评的稿件或节目都必须从已播稿件或节目中选拔出来才行。
我也从一年的《两户服务台》节目中,选出了一期自认为好的节目送台里参评。但在评选中,评委们认为,这档节目主要是回答听众来信,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传统意义上的好稿不同,送全国没有竞争力,于是,台评落选。但是,负责创优的程梦华却犹豫不决。评稿会上,她虽没有怎么表态,下来后,又思虑再三,终于拿定了主意,她向台领导建议把《两户服务台》推荐到全国参评。她说,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一种新的节目形式,她认为今年推荐到全国参评的节目,《两户服务台》最有希望。
程梦华,一位高个儿的女同志,五十岁上下,做事干练,有男子风。台里还有陈新华,与她同龄,也是高个儿。我调来省台那阵儿,一来就听说了这“二华”当年在编辑记者群里,是有名的两名才女,生花妙笔,不让须眉。当然,在我想来,何止如此,也应是美女。看那陈新华,虽是铅华不再,然那柔声盈步处,亦可见当年丰彩。而这程梦华确是高人一筹,她终于说服了台领导,同意将《两户服务台》推荐到全国参评,果然在当年的评奖中,《两户服务台》节目脱颖而出,获得了当时的最高奖优秀节目奖。台领导也就是冯百胜台长,他不仅采纳了程梦华的建议,而且,还让我代表陕西台参加了本届的全国评奖。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全国性会议。
第一次参加全国性会议,是数年前。农业部派我到四川成都参加一个关于农业宣传业务方面的会议,与会的都是各电台农业部的领导或编辑记者。会议的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会外的一些情景倒还清晰可忆。比如,开会的地方是个很大的会议室,中间没有桌子,靠墙一圈沙发,大家就坐在沙发上,对面的距离比较远,会开久了,人都半躺下来,伸直了腿,中间好像还空有很大的地方。那次开会是和薇林一起去的。会议那几天,她住在自己叔叔家里,末了,才一同随会议上峨眉山去玩。当晚,住在山下的一个旅馆里。接待的单位很热情,晚饭后,专门把大家集中起来,介绍峨眉山风光,我听得很入迷,其中吸引我的最是那群峨眉山猴了,说那猴们如何泼皮无赖,又可爱活泼。回来后,我写了四篇游记,其中一篇就是“峨眉听猴”。
于是,我一直兴奋着。但在第二天一大早,集体乘车上山时,自己却出了问题。也是该有事。我本就生性怯弱,长这么大又很少出过远门,偶尔像这样到了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便发虚,便紧张,便恐慌,便无端地担心着万一不注意什么的,迷失了路途怎么办?而这次便真的怕处有鬼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还特别警惕着不住地开门看走廊,看会上的人下楼没有?以便及时地跟上去,不要被拉下了后悔不及。正当我如此这般的小心着时,却一眼不到,转眼间,已是人去楼空,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了。便立时携薇林飞奔下楼,追赶人群去了。关于乘车地点,昨天晚上明明说是车就停在楼的转弯处,一路赶来,不仅没有见人,连车也不见了踪影。难道记错了地方么?还是……大恐。不知如何是好,是那种被弃于荒漠之中的感觉,一边在地上打转,一边不停地问薇林:“怎么办呢?”薇林想了想,说:“听昨晚会上宣布,中午要在万年寺集合吃午饭哩。我们现在乘公共车中午前赶到万年寺不就行了?”只好这么办了。赶到万年寺后,我依然心神不定,眼见中午时分将到,忽然看见山路上有会上的人向这边赶过来了,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下轻松得看着一群一伙的来人笑了。
这次开会的地点在上海。因有了成都之行的阅历和经验,这上海尽管是更大的复杂和繁华,处处充满着神奇和迷茫,我还是多了不少的淡定和从容。在那座十分宏伟的开会的大楼里,一时间没找到报到的地方也没有很慌,只定了定神,便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心想,一定还会有开会的人打从这儿经过的。果然,不一会,有一个女子进来了,很年轻,神色有点紧张,向着我走了过来,问道:“你是来开会的吧?”我说:“是。你也是来开会的?”她显然轻松了许多,一笑,笑得很甜,说:“我是广西臺的。你呢?”我说:“我是陕西台的,从西安来。”她眼里忽然闪着光:“西安,是那个有兵马俑的西安吗?”我点头。她个头不高,生得弱肩柳腰,凤目樱唇,说着话坐下来时,一直浅浅地笑着,自我们介绍说,她是广西壮族,姓覃。我以为是陕西的这个秦。她说不是,是西早覃。我暗自惭愧,原来还有这个覃呀。交谈间,从火车站接来开会的人一批一批地到了,楼厅内开始熙攘起来,办会的也赶来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现在我领大家报到去。”这样,她和我便成为整个会议期间最早熟悉的人。
于是,会议期间,她一有空,便来找我,当着同房间人的面喊我出去,一边闲聊一边散步,落落大方得一点也不知避嫌,倒使我有些不知所措起来。更有一次,从外边参观回来,路经著名繁华的南京路,她忽然要车停一下,车停后,忽然向我一笑,我还未来及想向我一笑是什么意思,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拉上我下了车,陪她逛街去了。
之后,河北广电局的编委办主任,姓名不记得了,告诉我,我俩下车后,车上人虽然没说什么,但从眼神里看得出来一车人的惊讶和好奇。但末了却安慰我说:“不管这些,他们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看得出,他对我很好,五十来岁,胖胖的中等个儿,红红的方脸宠,一只眼里有棠棣花,一身半旧的蓝卡几中山装,头上一顶蓝帽子,不苟言谈,觉得是个很老派的人。他与我投缘,饭后散步常是叫上我和她。那时候,凡来参加会的人就算是各台委派的评委了。评选中,评委有参评稿件的,该评委也不须回避。评稿初期的情形便是这样,制度、程序还很粗疏。我是带着自己的《两户服务台》节目来参评的,那天下午,就要评到《两户服务台》时,他悄悄叮咛我说:“到评你稿子时,不要上厕所,等评完了再上。”我十分感动,知道他这是在关照我。从上海回来后,他和我还有段书信往来,而后和他却相忘于江湖,再也没有联系过了。他那种老派人物的形象,对我的关照和指点,却始终在记忆之中,每一想起,依旧鲜明。AD37B3BC-544C-4618-B607-E0C4D0752DB9
总之,这次上海的全国评奖,算是给了《两户服务台》一个肯定,获得了当年的最高奖项:优秀节目奖。也算得给了我个人的一个肯定。似乎还促成了我后来的进入中层,成为一个部门的管理者,从此也便不再很具体地写稿办节目了。
然而,这时候,我却有了退意,有了要离开电台的念头。
我在小城时,就曾认为过广播宣传不是造就人才的职业,反而会稀释所学,矮化人才,不是我认为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我在前文已叙述过了。改革开放后,便觉得大学才是做学问,出人才的地方。且岳父郭校长复出后已在大学任职,也屡屡要我回大学教书,以学问为本。出于这番考虑的,还有个更现实的家庭问题。薇林已在大学工作有年,三个孩子渐渐长大,学习、生活都需要两个人共同投入更多精力。但我在电台上班,早出晚归,还要下乡采访,便经常弄得顾此失彼,首尾不能相照。就决意要离开电台,索性回学校教书便了。当然,最好是回母校,那是自己成长的地方,老师们了解自己,自己也熟悉老师,便决定我和薇林争取一起回到母校去。如此计议已定,即刻便与陕西师大中文系联系了。之前那段时间,大学停办多年,已是一片荒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却师资不足,甚至是稀缺。系上听说我们要回母校来,十分欢迎。决定薇林调动缓后,我调从速,正是学年中期,遂一边发函与省台联系着,同时,也便把我下学期据说教现代文学的课程都作了安排。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单等省电台放了人,我去上课了。

匡燮《记忆蛛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就在学校向电台发出商调函的同时,我的调动申请也及时送了上去。这样,便很快惊动了台长冯百胜。我不知道他听了台政治处关于我要调动的汇报后,是如何想的,却知道我递上调动申请的一两天后,冯台长便找我谈话来了。不是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而是就在电台的院子里,碰上了,便站住,显得很随便的样子,说:“哎,听说你要调走是不是?”我立即紧张起来,不知道冯台长会不会批评我,然后表示不放我,便吱唔着不好意思地说:“啊,我想回学校。”“为啥想回学校,电台不好吗?”他依旧用随意的口吻问。我只好把三个孩子小,薇林的学校在南郊,电台在城内,首尾不能相顾等情况说了一遍,总之是家庭困难无法克服。既然说了,索性又加重语气,脱口说了句:“我爱人的学校在南郊,我每天要来城内上班,两地分居,实在有困难。”后来才知道这是句太过无知得让人听来十分好笑的话,一个在城外教书,一个在城内上班,还算得两地分居?但冯台长听了没有笑,更没有批评,说了句:“过会你到我房子再来一下。我现在出去办个事,一会就回来。”说罢,匆匆去了。
不久,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电台像你这样的情况,两个人不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情况很多,都在一个城市里,这不算两地分居。”我脸上有点发烧,不再言语,结论似乎已经呼之欲出,既然不是两地分居,还有什么理由调动呢?家庭困难,像我这样的情况很多,谁家又没有困难呢?正在我捉摸不定,感到失望时,冯台长继续说,一开口,好像他早已经胸有成竹:“这样吧,你也别走了,既然你两个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家庭有困难,那就把你爱人调来好了,文艺部正缺少文学编辑呢。”
我立时吃了一惊。把薇林调到电台?这问题压根儿连想都没有想过,这怎么可能呢?改革开放以来,能进电台这样个党的“喉舌”单位的,一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二是安置来的复转军人,三是前几年像我这样极少数在基层新闻单位工作过的人。而在一个城市两个单位工作还要调进电台来的,据我后来所知,似乎是没有前例的。
有个情况,我还从未说到过,就是当时因孩子多,经济很是拮据。比如,有一次晚上下班,我从城里骑车到家,一进门,只见薇林和三个孩子,正围在小桌旁就着一盘咸菜吃米饭,一见之下十分恼火,那时候,所谓的自由市场才刚刚开放,薇林学校所在的古城南郊的小寨地方,已盖起了一个为卖菜者提供方便的大棚,于是,我二话没说,反身出门,骑车到大棚下买菜去了。已是黃昏,大棚下的小菜摊已经散尽,只有一个卖蒜苔的农民正在收摊,我买了把蒜苔,回家炒了,一家人才高兴起来。另外,那时候,想存点钱有些积蓄也非易事。记得当时时兴在银行储蓄,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也曾参加过一个定期存款,三年之后连本带息便可获得一千元的存整数。尽管这笔巨额存款让人兴奋和向往,然而,存了不到一年便不能坚持,只得取出来应急用了。还有一次,农业部分了一台台湾生产的价格五百元的十二寸黑白电视机的指标,经部门领导研究,决定把这一指标给我。当年电视机还极为稀缺,而领导的这一决定,不啻是对我的一次激励和奖偿,让部门的每一个人都艳羡不已。我在激动之余却犯起难来,不要吧,领导如此美意,却之不恭。要吧,钱从何来?思量再三,薇林忽然想起中学同班同学艾天宝在外贸部门工作,那是个有钱单位,他或许有些积蓄。果然,艾天宝同学尽其所有,慷慨解囊,帮我们买下了这台电视机。多年之后,借得的五百元钱才得以偿还。如此这般,不能说当时已穷到食不果腹的地步,但说家无余财却是当年的真实。
为了补贴家用,我从商洛驻站回台后,适逢西北大学向社会开门办学,中文系不知对外办了个什么班,正缺个代写作课的老师,中文系的郗政民老师,是我此前工作过的小城人,多有好吧往来,知道我孩子多,生活拮据,便举荐了我。告诉我一学期课时费为五百元,我眼前一亮,当即便应了下来。谁知为了要挣这点钱,既得瞒着单位,不能误本职工作,让单位人不能有丝毫觉察,又要尽量揽遍全国著名学府的写作教材,边搜集,边学习,边备课,边上课,夜夜挑灯,周日上课,甚至由家至校的路上,一边蹬车,一边还在酝酿情绪,思谋着如何在课堂上一开口便能引起注意,取悦学生。这样以来,听课的人把偌大个阶梯教室挤得了满满当当,窗子上也爬满了人,到后来,系上只得派人把教室门也把上了。心里自然得意得很,但是一学期下来,却累了个半死,竟然大病了一场,自此以后是再也不敢接这样的活了。
我既如此,薇林则更是如此。她除了代本校中文系的课程外,更在外兼职代课。那时候,教育被荒废许久,改革开放后,大有勃兴之势,各行各业的各种专业班如雨后春笋。于是,多在晚上和星期天,薇林便拼命在外代课,其中奔波之状,虽非我亲历,不可细数,但因用嗓过度,从此薇林的嗓子便落下了一个职业疾病,只要一开口讲课,便咳嗽不止,四处寻治,百医无效。她说,有一次,她在讲桌前直蹲了半堂课时间,还一直咳嗽不止,只好下课了事。以致后来到了几乎要离开讲堂的地步。至今每外出,薇林还必备一杯开水,时时饮啜,以防陈病复萌。正当薇林在讲堂上走投无路之际,柳暗花明,竟天上掉下了个进入电台的机会。我把冯台长的话向薇林说了一遍,她略一思索,便慨然应允了下来。我自是出于感激,随即也打消了回母校教书做学问的念头。两个人安家电台,一至今日。所以如此,是全仗冯百胜冯台长的鼎力相助了。
据传,厅长郭成方与台长冯百胜,都曾是电台的中层,还是很好的朋友。后来随着各自升迁的不同,却有了嫌隙,并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人事圈子,且各自抱有成见,只用自己圈子里的人云云。如此推论,郭成方原是农业部的老领导,显然,我该是郭成方圈子里的人了,也真的,成方同志不管在农业部时,还是当了厅长后,都对我十分关照。但实际并非仅仅如此。从我个人的实际感受中,特别在用人方面,我觉得不论郭厅长和冯台长两人的私交如何,他们所坚持的依然是以才、德论人,而非以“我”划线。
我怀念那个风清气正的年代。
(责任编辑:马倩)AD37B3BC-544C-4618-B607-E0C4D0752DB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