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理想没有照进现实
2022-06-14王潇
王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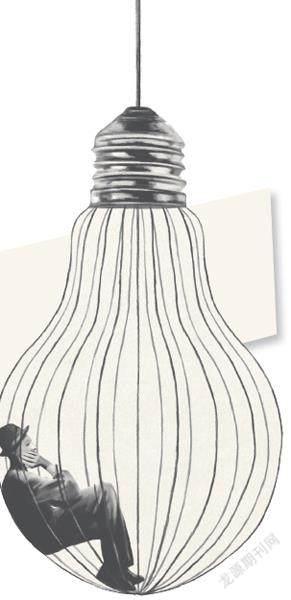
理想这个东西,通常在人生早期就会埋下种子。比如我的理想雏形始自七岁,是在我爸的引导下建立的。
我自從小学一年级,就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我那威严的爸勒令:放学后必须准时回家,回家后必须伏案学习至上床睡觉,雷打不动。晚饭后,楼下小朋友玩耍的欢笑声总会飘进小屋,扰攘得我抓心挠肝。一年级期末考试结束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向我爸提问:“爸,那谁家小谁小测验总得四分,还有谁谁,老得两分,为什么他们放了学都可以出去玩?我回回得五分,为什么我不可以出去玩呢?”
我那威严的爸一定暗暗惊讶于我竟然敢于质疑他的规则。他不动声色地沉吟了一会儿,做出了对我的整个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早期教育,他接下来这样说道:“好,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学得很差也可以玩,你学习好也不可以。那是因为,他们长大以后都是平凡人,你是要成气候的!”
我当时虽然还不大明白怎么样才叫成气候,但单就我爸那凛冽的神色和掷地有声的预言,已经把我深深震慑了!自那一刻,我就在幼小的心里定位和认同了自己的发展战略。
许多年以后,我明白了我爸的教育方法叫做心理暗示。从我这个案例看来,心理暗示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简直大得超乎想象。
在我爸的教导下,我自然而然就认同了如下逻辑:如果我力争上游、出类拔萃,那是应该的;如果我懒散懈怠、碌碌无为,就辜负了我成气候的天然使命。
我的荣辱观从七岁起就已经泾渭分明,所有事物都能够被一分为二地看待——那就是有助于成气候的,以及有悖于成气候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竟然动不动就学会审视当下,人生一有进展就沾沾自喜,一遇阻塞就愧疚悔恨,唯恐出现偏差,不能成长为命中注定的人才。花无百日红,学习再好,总有掉链子的时候,一掉链子我的情绪就灰暗沮丧,就暗暗不服。
回忆起来,我在整个少年时代,都是一个好战、喜胜的小姑娘,玩耍时候亦内心不得放松,时刻充满紧迫感。
这份紧迫感真是跟随我太久了,具体来说就是总觉得会的东西不够多,不努力小跑就跟不上大部队,这是往差里说。往好里说就是总想在人群中鹤立鸡群,熠熠闪光。求学时期就表现为考试好争个前几名,大合唱的时候老想当指挥,谁说哪个女同学漂亮我就暗中观察揣摩比对。
现在分析事物动辄提及童年阴影,在此也有必要提及我的中学阴影。因为一直到高中之前,我都对“假以时日,我终将成气候”这件事深信不疑。
我的中学叫北京八中,是一所著名的市重点中学。我家当时住在二环枢纽西直门,八中在复兴门,方圆一里内还有实验中学、三十五中,这些也都是西城区有头有脸的重点中学,是八中升学率的竞争对手。我每天会沿着西二环的辅路由北向南,骑15分钟自行车上学。
在高三那年的一个早上,我和平时一样捏闸刹车,单脚点地,停在复兴门立交桥北面的武定胡同十字路口等待绿灯。我前后左右布满了上学的男生女生,多如过江之鲫,他们和我一样风尘仆仆,面无表情。
人群之中,不知道那时我的心念怎样一转动,整个人瞬间被一种巨大的惶恐吞没,直让我后背发凉,心惊胆战。
我突然发现,从七岁起就孜孜不倦读书到今天,十年寒窗都过去了,我却还依然湮没在无数前途未卜的学生当中,在立交桥下等待红绿灯,像等着自己的命运。我曾经沾沾自喜的童年,自以为和大家有什么不同,还不是在众生(对,我当时就是想到“众生”这个词)中间继续挣扎。虽则身在重点中学,但在以后的种种人生测验里,只要稍有闪失,在任何一环上掉了链子,我就会更加惨烈地跌回到“众生”的深渊里。莘莘学子,熙熙攘攘,浩浩荡荡,什么时候才能出头?
我第一次怀疑,我能成气候这件事,只是我爸望女成凤的一厢情愿。
几年之后,第一次看《霸王别姬》,我在小癞子身上看到了我当年那种惶恐和绝望的重现。对,还有绝望,一个少年面对未知人生和难以企及的偶像的巨大无力感。
小癞子第一次溜入戏楼,终于看到京剧名角儿的时候,不可抑制地泪流满面,小癞子说:“他们怎么成的角儿啊?得挨多少打啊?得挨多少打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成角儿啊?”
不同的是,小癞子是看到了活生生的“角儿”而震撼和绝望,而那时的我并无真切偶像,只是恐惧湮没,只怕最后成了我爸所说的“平凡人”。
好在《霸王别姬》里,师傅还说了一句话:“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那天的惶恐过后,高考迎面袭来,我决定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几个月后,我考进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漫长的暑假结束后,我终于神清气爽、踌躇满志地步入大学校园。
开学不久,我很快就发现,我以为跳脱出了一个湮没的“众生”,又投入了另一级世界的“众生”里去,离成气候还早着呢,路漫漫,其修远兮。
由此可见,我要成气候的早期理想,受我爸的影响而种下,早已贯穿了我的前半生。多亏有了这个自我暗示般的理想,否则我天性中的自由散漫过早地开枝散叶,我今天的境遇就很难说了。
我工作几年重返校园读了研究生,年龄大得足够做本科生的小姨,几次遇到临毕业的青春男女们幽怨地向我发问:“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怎么办?”理想的美好总是与现实的残酷相提并论,听得多了,好似一对反义词。
我一般都如是回答:“理想和现实能没有差距吗?”
当然我还会加以解释:“我们国家都建设了六十年了,最高理想也依然没有实现啊!但是我们国家早就提出了现阶段的任务和N个五年计划,分段儿五年五年地实现。理想嘛,当然高高在上,先拟定一个现阶段的任务比较可行。”
他们听了,大多都似是而非地点点头,心事重重地走了。
我这厢望着他们年轻的背影,还在因心虚而暗暗流汗。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毕竟年龄一大把,好歹证明我没有虚度,总要故作姿态讲一讲道理。但我心里可是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也才刚刚摆脱前几年的纠结困惑,刚撇下书本一脚踏进红尘那两年,俯仰皆是理想与现实之争,日子当真不好过。
我是后来才明白,所谓理想职业与理想伴侣等只是个具体化的载体,人们终极追求的,是附着于这载体上的理想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通俗点儿说,活的就是个得到后的心情。
至于后来我的职业选择,确实真切地反映了我的理想:为了自由灵魂,我放弃了做新闻播音员;为了战斗的生活,我成为一名私企小老板。现在看来,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不是际遇和凑巧,而是我为了理想做出的选择。虽然今日,我依然距离理想状态相去甚远,但我已经走在路上了,一天即使前进一厘米,终归是越来越近。
追求理想有点像夸父追日,看得见却追不上,但不知不觉追出了百多里,回身一望早已有了可喜成就。理想当然要够远大,否则轻易就实现了未见得是好事,事成之后再无惦念之目标会有点沮丧,拔剑四顾心茫然;理想又不能够太过梦幻,夸张到走外太空和神话路线,根本就无从下手实践,令人完全没法有念想。因此好的理想,还是需要量身定做的。
“现阶段任务”,不是空穴来风,我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设定一个目标,抓紧忙活,直至把目标踩在脚下,然后再定一个。循环往复,以此为乐。
同样是抱怨理想没能实现的人,却可以选择两个截然不同的状态,一种是背道而驰,一种是走在路上。如果选了前者,就只好渐行渐远,切莫怨天尤人;如果选了后者,我十二万分地支持你,理想总要用现实一寸寸地走出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暂时没实现的理想,只有到临终前,才有资格说它破灭了。
(李昭瑾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趁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