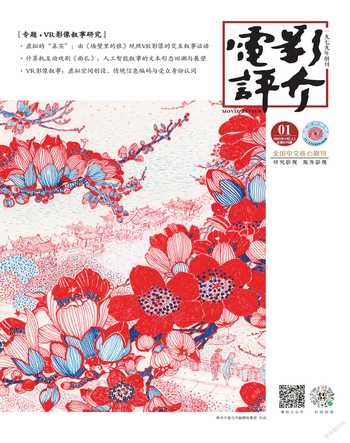《红楼梦》跨媒介叙事的符码重塑与美学再探
2022-06-11马言
马言
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而成的电影常因为语意的流失及与原著的差异而遭到批判,创作主体也表达了自我的无奈。要知道,电影改编是在基本遵循原著基础上的自我创新,小说中人物、服饰、饮食、屋舍、车驾、山水等具有史实性的内容,都在电影中获得充分的展现,而心理、情感则难以直接呈现。这是因为小说与電影叙事语言不同,进而造成不同表意符号之间的不可通约,但这并不否定电影独立的艺术地位和价值。《红楼梦》电影中所有视觉元素都在叙事,受众完全可以不依原著理解图像表达的内容,文本语言已被图像语言转化成独立的影像,达到“元图像”境界,具有独立的艺术审美价值。
《红楼梦》系列电影的拍摄始于1924年梅兰芳主演的《黛玉葬花》片段,后来大陆和香港地区共改编拍摄电影40余部,主要有《红楼梦》《新红楼梦》《红楼新梦》《金玉良缘红楼梦》《花落红楼》《红楼二尤》《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宝玉忆晴雯》《尤三姐》《大观园》《林黛玉魂归离恨天》《黛玉归天》《情僧偷到潇湘馆》等。有的是越剧电影纪录片,有的是昆曲电影纪录片,有的是黄梅调,有的是粤语歌唱片,有的是风月片,有的是时装片;有的压缩故事情节,有的节选一段故事;有的展现整个大观园的生活,有的聚焦个体人物。总的来看,电影有限的叙事时间和镜头语言的图像叙事,不同于小说语言长篇的情感描绘和意境营造,已经形成独立的艺术审美体,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一、创造主体的自我认知
《红楼梦》的电影创作其实是二度创作,是对原著的重新演绎和诠释,同时也是对小说的一次传播。受众及“红学”研究者始终对《红楼梦》视听媒体的诠释形式表达不满,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即使是1962年的越剧电影纪录片《红楼梦》及1987年的电视剧《红楼梦》这样较为成功的改编,也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原因就在于《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已经深入人心,部分受众先入为主,将小说文本作为经典奉读,但是电影艺术的人工剪裁会破坏原著的结构形式和诗意韵味。这不仅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也是影视批评经常探讨的问题。
其实改编者在改编过程中也左右为难,主要原因是古典小说以文本可读性和诗意韵味吸引读者,与近现代电影艺术有着不同的创作技巧和呈现方法,因而有的小说不存在电影要素,强行构建电影元素,自然会分割原著本身的艺术结构和表现方式。况且有些电影演员无法充分表现小说的精神内涵,那么二者产生的艺术表现力就自然不一样。例如,1930年,王乔南将鲁迅的《阿Q正传》改编为剧本《女人和面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电影剧本相较原著已经降低了格调和意蕴。鲁迅当时就说这本小说“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还说“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1]。从中可以看出,电影剧本已经与原著脱节,毋庸说搬上银幕的电影了,不仅当时的无声电影对于原著的转译造成语意的流失,而且即使是现代媒体技术制作的电影,也会对原著的本意形成挑战。夏衍的朋友曾经告诉他:“我从来没有看过一部从名著改编的电影而能够得到阅读原作那样的享受和感动。”[2]或许有人喜欢现代3D电影、IMAX电影等艺术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改编已经脱离了原著的韵味,形成另外一种艺术感觉。因为对《红楼梦》之类的长篇小说进行艺术的裁剪,呈现出来的只是编剧、导演和演员所理解的语意内容,与读者直接阅读原著所体会的内容并不完全具有一致性。不同的受众面对同样的电影感受自然不同,更何况这已经是改编之后的内容。因此,小说尤其是经典名著的影视化改编,是改编者为了适应电影行业需要,有意改变原著内容之举。即使本着“写实”原则的改编,也无法完全呈现原著的思想。因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都有与它们相适应的诗的思想,因而一种思想永远不可能在其他与它不相适应的形式中表现出来”[3]。
其实,改编《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往往事倍功半。电影理论家柯灵曾说:“改编文学名著,经常遇到的困难是读者先入为主,容易发生欣赏上的距离。未读过的,震于原作的盛名,也会有些不易膺足的要求。”[4]这从受众接受角度说明了改编的困难。其实,编剧在改编的过程中也是万分焦虑。曹雪芹文学功底深厚,小说中诗词曲赋众多,金陵十二钗判词、《红楼梦》十二支曲、《好了歌》及《葬花吟》等为典型。薛宝钗等人作诗就特别注重“十三元”,再加上小说语言文本的开放性,给编剧的改编带来巨大的困难。越剧电影纪录片《红楼梦》的编剧徐进在《重印后记》中说:“要把内容如此深刻、篇幅非常浩瀚的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改编成戏,确非易事。我一着手试编,便应了俗话所说的‘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主观上、客观上都存在着困难。”[5]《红楼梦》毕竟是四大名著中最具艺术色彩和思想性的作品,对于它的改编除了会出现一般小说改编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涉及“红学”的影响。每次电影改编之后,首先要面对影视批评和文学批评两种思潮的评点。前者主要从电影技巧分析,着力点在影视学、传播学层面;后者则基于《红楼梦》原著思想内容,将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比较,突出电影改造文本的种种弊端,尤其是曹雪芹的思想没有充分体现出来。除了“红学”专家的学理批评,普通受众也会因为个体的知识体系、自我认知及道德观念的不同,将电影呈现出来的效果与自我期待的形象进行对比,那么《红楼梦》电影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及结尾都会成为受众品头论足的重要内容,以致形成“人人都是红学家”的局面。
对于小说的改编尤其是经典名著的改编,往往会因为原著艺术水平的高超、受众对原著的熟悉,导致改编难度极大。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之外,《西游记》也常被改编成各种电影,无厘头的戏说甚至让人忘却了原著的样貌。尤其是现代电影的娱乐化、时尚化,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人事编排在一起,以穿越性和滑稽性博得一笑。票房数据的导向造成电影发展的畸形化,电影语言、演员装束及各种黑科技的滥用,无疑是对经典原著的亵渎。“不朽的经典作品总是在自身中蕴含着崇高的情感、哲学思考和对生活的生动观察。”[6]这些因素也许在电影中有所体现,但是电影表达的中心和表达形式已经偏离原著思想主线,只是为了迎合受众娱乐的心理,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内容。尤其是《红楼梦》这种较为深沉和感伤的题材,从爱情角度看,难与现代都市爱情类电影相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纠葛难以引起一些现代青年的共鸣;相反,霸道总裁和小职工的爱恨情仇,却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感情基调看,沉闷、压抑的故事情节,与追求娱乐化的时代心理又有隔阂。因此,《红楼梦》电影的改编无论是从与原著关系,还是受众的接受与批评,以及这种题材的市场反应来看,都成为编剧左右为难、百感交集的症结所在。编剧一方面改编原著,造成与原著的隔阂;另一方面又要遵循电影语言的规律,增强影视效果。因此,语言文本的本质与影视艺术现实需求间的矛盾,成为电影效果与原著思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语图转译的能与不能
在宋代郑樵看来,图文关系是对立的,“索象于图,索理于书”[7]。他认为图是表象的,书是表理的,一为形象,一为抽象。可是他忽略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图像符号功能,尤其是象形文字,与图像符号具有相似的叙事功能。中国早期谈论的图多是指《易》“象”,《周易·系辞》中记载“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8],故“象”为对外物的形容模仿,也就是谢赫说的六法之一“应物象形”,而意载于象之上。颜延之认为:“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9]因此,中国早期的形象思维特征,决定了语言文本与“图象”的先在联系。明代夏履先说:“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10]清代王韬又说:“两美合并,二妙兼全,固阙一而不可者也。”(《图像镜花缘·序》)他们都肯定了图文的互文与互补特征。
小说图文关系讨论的基本前提是语言文本“立象”本质特征的固有存在,与图画叙事功能的交叠,形成二者的互文互补,但又表现出转译之时的文体独立性。《红楼梦》电影的改编就遵循了这种规律,电影虽然源于小说,改变又造成原有语意的流失,但并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出现而地位低下,反而以独特的艺术优势,创造鲜活的艺术生命。
首先,圖像转译的基本遵循。语言符号切换成图像符号,使得自我封闭的语言符号所构造的语意图被转译成图像而直接呈现,实现由语象切换成图像的审美转化。这种直译是图像对语言文本内容最直接的转译,主要包含人物形象、器物形貌、场景位置及线性的人物出场顺序,这种转译是最接近语言文本的。电影《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场景布置及色彩渲染等,基本遵循原著文本,营造出非常逼真的历史场景,瞬间将受众带入环境,这也是电影艺术的优势。可见,图像符号寻求与语言符号的最大公约数,力求无限接近文字,并且发挥自身特性,将抽象的内容以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但是,无限接近并不等同于完全一致,事实上完全一致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电影图像摄录属于导演、摄像师的二度创作,他们自身的艺术修养与艺术认知对于创作效果具有直接作用。电影的艺术视角和主观选择,使得转译的复现总是与原著文本存在属性的隔阂。
电影改编会突出其与原著的差异,也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其作为独立艺术形式的地位。所以,电影拍摄角度的选择如同画家作画,需要精巧构思,凭借电影特殊的技法来实现,这也是电影改编脱离原著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红楼梦》系列电影的场景选择和布置基本遵循了原著的安排,导演的发挥空间并不大。《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借薛宝钗之口有这样一段关于绘画技法的宏论,也适用于电影的拍摄:
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阁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
位置、多少、主次、隐现等,也是导演拍摄的着力点,所以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的画面多是井然有序,具有鲜明层次感,以显性的暗示隐性的,以隐性的衬托显性的。正如朱光潜所说:“艺术家既然要借作品‘传达’他的情思给旁人,使旁人也能同赏共乐,便不能不研究‘传达’所必需的技巧。他第一要研究他所传达的媒介,第二要研究应用这种媒介如何可以造成美的形式出来。”[11]电影传达的媒介主要是镜头的切换和声音的调节,导演也正是从这些方面来架构一部电影。
其次,图像转译的语意流失。就《红楼梦》电影改编情况来看,小说中细腻的情感内容、丰富的心理描写和美妙意境的营造,难以在电影中呈现出来。涂光社在论述古人作品特征时说:“古人不喜欢阖盘托出一览无余的艺术表现,鄙薄一旦展示终结影响力也随之消失的作品。内容深厚耐人玩味;模糊的具有启示性的艺术传达,能够左右观照者的情感活动和心理趋向,激活和引导艺术的再创造……才受欢迎。”[12]因此,影像的转译只是对小说本体的模仿与佐证,只是借助“存在的”“有形的”“可见的”的形式使文意变得更容易理解,而复杂的内涵、深邃的语意则因影像符号的自身缺陷而被遮蔽。法国哲学家丹纳(Taine)认为:“艺术品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对象的基本特征,至少是重要的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越明显越好;艺术家为此特别删节那些遮盖特征的东西,挑出那些表明特征的东西。”[13]《红楼梦》电影的拍摄就是突出改编者认为的易于影像艺术呈现的特征,遮蔽了文学精华的内容。
一是小说以长篇形式容纳了众多的人物、丰富的场景和复杂的故事情节,并且善于对人物情感和心理进行细致的描摹。电影中虽然也运用了一些影视技巧,如镜头特写、镜头转换、意识流和蒙太奇等,但与小说文本语言相比,感染力要逊色一些。因为电影艺术呈现的往往是空间的、客观的物质内容,容易被视觉器官感知,表达人物内心也以人物外在的形神变化来暗示。但是“并非人类所有的心理活动、心理感受都具有外部的空间造型,都具有外在的表现形态,人类的某些情绪、感受、思想和精神状态是无形的,抽象的,无法诉诸视觉的,它们不具空间的存在”[14]。影像内容直观、形象,具有视觉冲击力;文本语言则更加复杂、委婉和灵活。所以《红楼梦》电影会借助旁白、唱曲等语言形式来表达人物的情感,这也是电影艺术取长补短的权宜之计。例如,《红楼梦》小说围绕贾宝玉、薛宝钗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进行多线索的并进,细腻的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和心理令人如痴如醉,但电影出于时间的限制,只能选择性地截取部分内容加以呈现;还有“黛玉葬花”的内容,小说以三回的篇幅详细描绘林黛玉的烦恼、嫉妒、悲叹和贾宝玉对生死的体验,内容丰富,情感复杂,心理纷乱,但是电影改编之后只是以二人的哭泣表达内心的愁绪,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红楼梦》电影以贾宝玉和林黛玉人物的对话和唱词的形式,宣泄情绪,忧愁、苦闷、焦虑等情感都在这一过程呈现出来。例如,1944年发行的电影《红楼梦》的“葬花”部分,林黛玉哭唱改编的《葬花吟》,将林黛玉内心的感伤情绪表达出来;1989年发行的电影《红楼梦》,也是以“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插曲,随着哽咽哭泣的声音,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复杂情感表达出来。
可见,电影虽然以独特的形式对小说中人物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情感进行表现,但只是借助外在形式来衬托、暗示。人物的内心活动要远比表现出来的表情、动作复杂、深刻,因此,电影演员的表演无法将语言描绘的抽象心理完全表现出来。因为小说文本语言具有“立言尽意”的功能,但又“言不可尽意”,所以电影对于那些深刻的思想、复杂的情绪,尤其是说不清理还乱的潜意识内容,无法呈现出与小说相似的审美效果。例如,小说中描绘林黛玉听到贾宝玉迎娶薛宝钗的消息后,“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停了一会儿,颤巍巍的说道:‘你别混说了。你再混说,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你去罢。’说着,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15]。这种情形虽然用语言可以形容,但是电影镜头却难以将林黛玉复杂的心情表现出来,只是徒有形式。因为这里面“意”的内容与电影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性,无法实现完全转化。“实际上,一切小说都侧重于表现内心的发展或存在状态。小说的世界主要是一种精神的连续。这种连续现在常常含有某些非电影所能掌握的元素,因为这些元素并不具有可资表现的客观形态”,并且“摄影机所攫取的生活主要还是一种物质的连续”,而“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常常会伸展到某些绝非电影所能再现的域”[16]。中国古典文学与电影艺术的关系,与西方文学与电影艺术间的关系具有相似性,都是文本语言与影像语言间的相离逻辑。
二是小说的开放性与电影艺术的封闭性。小说语言因为文字的排列组合,读者需要视觉感知信息,然后通过大脑中枢分析、判断,将人的形象感知和抽象思维全部调动起来,因而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丰富性。学者许波认为:“语言艺术充满了情境性和暗示性的间接造型,为读者的联想、想象和再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大地。读者的想象力越丰富,就越能在文学形象中获得愈加丰富的美感享受。”[17]但是电影却是通过镜头画面和声音表达内容,影像直接投射到人的视觉与听觉上,以画面和声效感染人,给予受众视觉的冲击和听觉的震撼,但限制了人的想象与联想能力。电影以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布置来呈现形象,具有单一性,受众的欣赏具有被动接受的意味。正是因为这样,才会造成电影改编效果与受众心理期待的差异。
例如,《红楼梦》第三回描写贾宝玉形象是从林黛玉的视角展开的,读者阅读小说会以自己的理解来塑造心理期待的宝玉形象。但是电影中的演员形象是固定的,虽然不同电影中贾宝玉的扮演者不同,但单一的人物表演只是呈现固定的形象,精湛的表演也无法回避演员与原著中宝玉形象的差异。因为文本语言的描绘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读者可以建构自己想象的宝玉形象,并且能够品味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对于文本的理解更加深刻。但是电影演员的选定限制了受众的想象,改编者塑造的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贾宝玉、林黛玉等就是这样的人物印象,阻碍了受众对于人物形象的自我建构,人物身上丰富的内涵难以表达出来。美国电影评论家乔治·布鲁斯东(George Bluestone)就说:“语言有它自己的法则,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构成这些人物形象的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些人物形象在外形上的具体化往往叫人感到不满足。通过语言之幕出现在我们脑际的人物形象和通过视觉形象展开在我们面前的人物形象是有区别的。”[18]因此,《红楼梦》电影的改编多是描绘写实的内容,比如庄园、府邸、器物、服饰及人的表情动作等,对于写意的,如小说语言背后的思想内容等,由于不可通约性,就无法表现出来。范烟桥在《宽中寻仄法》中直接说:“《红楼梦》改编成戏剧已是‘大难大难’,而电影不能表出言语上之精神,较舞台剧更感困难。”[19]
虽然说电影的改编会造成原著意蕴的流失,但电影仍然以其特有的艺术技巧营造画面和声效的美感。小说与电影都可以创造意境,但电影主要通过画面的剪辑和渲染体现出来,语言的声音只是作为画面的补充。这是因为电影受众主要欣赏流动的画面,而不是观看文字的内容。
三、文本语言与镜头语言的差异
《红楼梦》的电影改编之所以多被世人讥评,改编者也感到缺憾与无奈,主要原因在于改编后的电影无法完全呈现原著的韵味、思想和感染力,影视中人物形象、情节安排和逻辑结构与原著也不完全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关键因素是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造成小说“语象”转译成电影“影像”的符号变化,将“想象的”变成“观看的”,自我封闭的语言符号借助影像符号,使虚泛的意境在切实的影像中展开,想象的意境挣脱了文本语言的束缚,转换成受众可以进行身体感官的“影像”。从修辞学角度来看,文本的影像化也是一种修辞手法,只不过这种修辞使得艺术形式变得可见、可感。
如果进一步追问影像转译导致小说文本意义更易理解的原因,就要从文本语言符号与影像符号的差异方面探讨。语言符号编织的文学文本是虚构想象,符号与符号之间是以感性的形式临文组合,符号间不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这是由文学语言句式所限制的。影像符号则是对语言符号的选择性放大,以便取得预期的影视效果。文学语言与影视语言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它们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不同,造成二者审美效果的差异。
“不可通约”的概念由美国学者库恩(Kuhn)提出,主要运用于科学领域。他认为,“科学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常规科学传统,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20]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就是指不同的体式之间没有相似的逻辑联系,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相交与相切等关系,两者之间属于相离的关系,比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神话传说与现代科学间的关系就是這样。换句话说,不可通约就是不可公度,不同要素之间没有连接的桥梁,也就是缺乏媒介客体的沟通。英国学者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通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21]没有中性的转述工具,也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无法进行完全的沟通,强行的翻译势必导致原语言的损失。例如,中国古典诗歌与英语间的翻译,就是因为两种不同语言不可通约,才会造成英文内容丧失掉汉语诗歌的意境内涵。同样,《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文本与电影艺术间的转换,也是一种转译,小说文本的独特意蕴就是电影改编失去的内容,因为这部分内容具有不可通约性,无法通过影视艺术呈现出来。例如,小说《红楼梦》中“只有宁国府门前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这句话,电影就无法呈现这句话的深刻意蕴,无法表达曹雪芹对于宁国府人和事的批判。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详列。
尽管古典小说与现代影视艺术的转换不能完全等同于库恩所说的范式改变和语言翻译,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并且难以调和。小说与电影艺术确实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缺乏通约性。《红楼梦》电影的改编会造成小说精髓的流失和变异。彭亚非总结说:“文学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因此与其他任何审美方式都毫无共同之处。”[22]这句话虽然过于绝对,但也表明文学虽对读者具有开放性,但对于其他艺术形式则具有自我封闭性。
结语
《红楼梦》由于丰富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成为四大名著中最具艺术价值的古典小说。对于它的改编既有与《西游记》等古典小说改编的相似性,也表现出由于独特的艺术技巧和思想内容而不同的电影技巧。改编者由于原著内容和电影呈现效果的矛盾而表现出遗憾和无奈的心理。《红楼梦》的长篇形式为人物刻画、故事展开和场景布置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但正是由于长篇巨制,包罗万象的小说形式,才会造成电影表达的缺憾。短短几个小时的电影艺术,是无法充分展现纷繁复杂的《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况且小说诗意的内容和言外之意、韵外之旨,都是电影难以表现的。原因就在于电影与小说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和效果存在差异,造成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缺乏中立的媒介连接、过渡,因而也就不具有公度性。但也要看到,尽管电影艺术会悖离小说原著的语意,但它仍然以图像和声音的调适来吸引受众,取得了不同于原著的审美效果。所以,评判不同艺术体的借鉴是否成功,不在于看多大程度忠实于原著,而是看在新的艺术形式中,是否凭借新的艺术形式的优势,创作出完整独立的艺术作品,是否具有自我独特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夏衍.杂谈改编[ J ].电影艺术,1958(01):11-14.
[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M].增义,徐振亚,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23.
[4]解玺璋.围城内外——从小说到电视剧[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68-69.
[5]徐进.越剧红楼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157.
[6][俄]波高热娃.论改编的艺术(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改编[ J ].俞虹,译.世界电影,1983(01):100-126.
[7]郑樵.通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8]李镜池.周易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中国书店,2018.
[10]方汝浩.禅真逸史[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8.
[11]朱光潜.谈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3.
[12]涂光社.刘勰的简繁隐显之论——兼及文学传达中一种传统的审美取向[C]//中国文心雕龙学会.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326-340.
[13][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2-23.
[14]张卫.以电影的方式忠实原作[ J ].电影艺术,1983(09):35-42.
[1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6][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邵牧君,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319.
[17]许波.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 J ].电影艺术,2004(02):17-22.
[18][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M].高骏千,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25.
[19]范烟桥.宽中寻仄法[ J ].红楼梦学刊,2003(04):1.
[20][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結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5.
[21][英]伊姆雷·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M].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60.
[22]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 J ].文学评论,2003(05):30-39.
【作者简介】 马 言,男,河北巨鹿人,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影视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0年度贵州财经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项目(编号:2021YJ0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