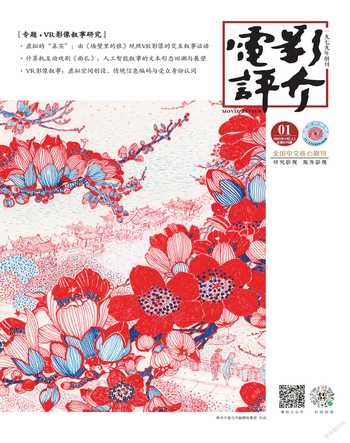从《紫陀螺》到《树上有个好地方》:儿童电影“童真美学”的西部范式
2022-06-11杨俊波韩文超
杨俊波 韩文超
作为一部表现西部乡村校园故事的现象级儿童电影,《树上有个好地方》无疑是依靠其真诚和淳朴来打动观众的暖心之作。“80后”新锐导演张忠华以儿童的视角切入,影片中看似零星琐碎的记忆片段,如珍珠项链般被缀连成一个孩子成长的同心圆,呈现了一段关于童年校园成长记忆的真切故事。2020年9月6日在“爱奇艺”线上公映,《树上有个好地方》收获了一系列极为亮眼的数据:豆瓣开分即获8.1的高评;网络上线4天时间,就收获抖音话题播放超6亿次;凭借6个月分账期内付费点击,所收超过600万元的网络票房,成为中国儿童电影网络公映的票房“天花板”。
《树上有个好地方》在业界也广受赞誉,先后荣获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提名奖、第24届德国施林格尔国际儿童电影节“杰出演员奖”、陕西电影奖“最佳导演处女作电影奖”、第八届中国影视“学院奖”最佳剧情片奖,并入围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推介展、2019年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第十五届韩国釜山亚洲青少年儿童电影节、瑞典马尔默国际电影节、第22届纽约布鲁克林国际电影节等,也获得国际上的一致认可。对于一部儿童电影而言,如此亮眼的成绩着实令人欣喜。然而,这样一部小成本的儿童题材影片,冠在其上的“儿童”“西部”“方言”等一系列关键词,却一度成为许多人眼中不被看好的潜台词,这也是儿童电影一直以来所面临的边缘化处境。
一、“儿童电影”与关于儿童的电影
回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从1922年由上海影戏公司但杜宇导演拍摄的中国第一部兒童电影短片《顽童》完成至今,中国儿童电影故事片已历经百年风雨。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对于诸如“儿童电影”“儿童题材电影”等相关概念的讨论,一直是儿童电影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理论界关于“儿童电影”的争论亦是由来已久,围绕“儿童”所展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儿童电影“为谁拍”“给谁看”“谁来演”等这样几个核心问题,而对于儿童电影的讨论也在此有着一定的分歧。
从“儿童电影”的概念展开,《电影艺术词典》定义儿童电影是:“为少年儿童拍摄的故事片。”1985年,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受广电总局、教育部、文化部、全国妇联、团中央委托创办的中国电影童牛奖,则给出了符合“为儿童所拍摄”“儿童生活为内容”“为儿童所接受”其中两项特征即可的界定标准。而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则给出了三重不一样的限定标准:“主角为儿童”“儿童参与或儿童视角的生活内容”“适合儿童观看”。作为中国儿童电影的最重要奖项之一,经原文化部改革,中国电影童牛奖于2005年并入中国电影华表奖,奖项先后命名为“优秀少儿影片奖”和“优秀少儿题材影片奖”。从对儿童电影概念标准的不同认识,到电影奖项名称的改变,可以看出电影界在“儿童电影”概念认识上的变迁。其中,“少儿题材”的提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儿童电影在题材和表现对象上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取向。
与电影奖项名称的变迁一样,近年来,“儿童电影”的发展状态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作为电影题材中相对特殊的一个类别,儿童电影受制于观众群体、作品品质、资金市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被主流电影圈所轻视,从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客观地看,虽然由于题材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儿童电影相对较小的市场体量,但是深入来看,实际上儿童电影的发展不仅是在内容、数量、市场等不同方面所表现出的不足,剧作质量、创作团队的缺乏更是掣肘儿童电影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回到儿童电影“为谁拍”“给谁看”“谁来演”的问题,首先可以确定,儿童电影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演绎对象,为“童心”“童真”而拍摄。其次,无论是“少儿影片”还是“少儿题材影片”,从其本体出发,儿童电影绝不是仅仅拍给少年儿童看的电影,而更多的是从儿童本位出发的“关于儿童的电影”,不仅是儿童观众,保有一颗“童心”的成年人同样是儿童电影重要的观影群体。无论是在生理年龄还是心理年龄上,“儿童电影”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儿童的界限。
二、从《紫陀螺》到《树上有个好地方》:童真与成长中的三重营构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下沉,电影的受众面不断扩大,越发广泛的受众群体与多元化的观影需求,为电影市场营造了全新的市场方向。相对于儿童电影所呈现的相对弱势状态,张忠华的《树上有个好地方》在网络上所引发的广泛讨论是有目共睹的,这样的成功案例也可谓是为当前的儿童电影艺术探索了一条创作的新路径。而纵观《树上有个好地方》之前张忠华导演的这一系列作品,足可见其对于儿童题材电影的偏爱和坚守。就影片的构成因素来看,《树上有个好地方》与其早期作品《紫陀螺》相比,两部电影在故事情节、人物设定、画面风格、方言运用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以一个通俗意义上被看作是“坏学生”的视角切入,讲述了一段儿童成长与师生情谊的纯真故事。而且两部作品虽均属于儿童电影范畴,却又明显地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儿童电影的概念桎梏,在鲜活的人物形象下对于童真与成长的多重营构,使作品显示出特殊的生命力。
(一)童真与成长
《紫陀螺》作为张忠华早期儿童电影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不仅使其在电影界崭露头角,也正式开启他的儿童导演生涯。这部片子不仅获奖众多,更在网络平台上持续广泛转播,也让张忠华逐渐在儿童电影领域积累起声誉。相对于《树上有个好地方》而言,《紫陀螺》这部完成于十多年前的影片更带有一种回忆和记录的性质,在如今看来简净真实中又显出青涩的味道。无论是《紫陀螺》中的席布鲁,还是《树上有个好地方》中的巴王超过,影片的视角都落在小主人公的身上,以小主人公的成长转变展开故事情节。《紫陀螺》以相对单一的席布鲁“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陀螺”为线索,讲述女老师米兰送“紫陀螺”,并引导席布鲁走上学习正轨的故事。而作为《紫陀螺》延伸出来的姊妹篇,《树上有个好地方》通过儿童视角的直观表现,真实地再现了“坏小孩”巴王超过的日常行为和心理活动。以“娃娃书”为引子串联起小主人公与女老师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关系。此外,还有面对不同老师背课文时的忐忑心态,模仿大人往自己头上抹发胶等情节,这些一代人成长过程中曾经历的画面内容,展现了导演对少年成长经历的真实细致的体味。尤其是巴王超过一步三回头转身指着镜头说出的那两句:“真拿你们这些大人没办法,难说话的呀。”让观众在那一刻直面一个儿童的诘问,第一人称的代入感将童真与成长的作品主题凝于画面的一瞬。
尤其是《树上有个好地方》围绕“娃娃书”这一线索,从窗口偷书被抓受老师批评,父亲撕书烧书再次批评;到管理书而获得认可,逐渐喜欢上学习;最后埋下娃娃书离开的背影……与《紫陀螺》中米兰老师在读书声中渐渐远去的身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一过程中,作为童年美好象征的娃娃书和少年的懵懂时光,在一种无形而有序的节奏中逐渐远去,而伴随着这种有序的节奏迎面走来的,则是一个少年成长的足迹。这种此消彼长的故事叙述中,对一段成长记忆的追寻,虽不是回忆却更胜回忆。正如谭旭东在《新中国70年儿童电影发展史》中所提到的:“优秀的艺术一般通过反映‘成长’、引领儿童成长的。”[1]
(二)乡土与自然
《树上有个好地方》以陕西关中方言入画,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北乡村儿童生活的真实情状,在故事背景上与《紫陀螺》保持一致。影片给观众的第一印象是真实与自然的契合,浓郁的乡土气息在旧校舍和方言声中悄然逸散。首先,片中的陕西方言很自然地成为大家首先关注到的一点,与一般的普通话相比,方言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观众在语音上的识别度,但却丝毫完全没有妨碍观众对于电影情节的理解。相应地,由于方言的表达适应了演员的日常习惯,与影片环境更好地融为一体,反而使作品显得自然生动。在近年来很多乡土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都多有方言的运用。其次,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校舍、破旧的老式手摇上课铃等,为整部影片营造了一方属于童年记忆中的真实天地。當然,演员们的表演也是这部电影令人动容的一重因素,尤其是《树上有个好地方》中主角巴王超过真实而不矫揉的表演很好地提升了作品的观赏性。同样的,《紫陀螺》中米兰老师口袋里总能拿出的棒棒糖,课余时间一起玩陀螺的欢乐时光……细节中透着自然而亲切的气息,也一样令人感怀。
在有着地域气息的自然表达之外,满满的乡土情怀也是电影中的重要内容。对比两部影片可以发现很多共通之处,导演通过“木陀螺”“洋画片”“娃娃书”“链条枪”,以及“掏鸟蛋”“打小抄”“下河”“上树”等一系列看似琐碎的物象与情节,构建起一个生动而触手可及的童年时空。在这样的时空中,不需要绚烂的特效制作,不需要精致华美的道具布景,甚至连精湛娴熟的表演技巧在这里也绝非必须……我们仅需跟随小演员的足迹,透过他们的眼睛在童年的记忆和成长中,追寻一段天真烂漫与朴实无华的故事。
(三)共时与共情
《紫陀螺》和《树上有个好地方》的故事内核有着很强的一致性,都是以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为情感依托,通过对拥有一个“陀螺梦”与“好地方”的意象化表现,构建了一个生动真切的童年时空,以达成与观众记忆与情感的共时共生。对于观众而言,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关于自己记忆与理想中的“好地方”,在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期望中,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珍惜之地。在看似零散的情节之外,《树上有个好地方》有着一系列细节表现。粉提老师踮起脚尖与巴王超过为老师垫木块的情节刻画,逆光的场景切换中,巴王超过手中的那块垫脚木,仿佛可以被每一位观众所触摸到。无疑,在影片中这一刻是少年巴王超过成长过程中心理转换的开始。而与片尾的大树被放倒相映照的,正是巴王渐行渐远的童年时代,在影片所营造的时空轨迹中,观众在心理上的共通情感在这样一步步的成长历程中被激发出来。
当然,两部作品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并均引发了以“爷青回”等网络热词为话题的一系列讨论,是影片在观众中产生共鸣的最有力证明,这也是作为儿童电影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方言俚语配合不同场景下演员们富于变化本色演绎,也是作品的亮点之一。诸如《树上有个好地方》全片在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中拉开序幕,伴随着一群孩子整齐划一的腔调,与摇头晃脑貌似统一却又姿态各异的手势,强烈的代入感为影片赢得了内心在第一瞬间被打动的效果,观众在这一刻被带入电影中的儿童世界。而影片中的“紫陀螺”“大树”与“娃娃书”等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象,呈现了一片属于少年时光的意象化心灵“景观”,从而引发每一个“少年”的成长记忆与情感共鸣。
三、“童真美学”:中国儿童电影的西部样式
作为一名长期坚持拍摄儿童电影的导演,张忠华从进入西北大学求学开始便以此为阵地,在这个曾培养了包括《黑炮事件》《站直啰,别趴下》导演黄建新,电视剧《玉观音》《大秦帝国》导演丁黑,以及《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编剧张子良等一批影视艺术家的综合性高校,依靠其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并以西安关中之地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根基进行儿童电影创作。2005年,张忠华的首部儿童长片电影《霸王年代》获第1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年影像单元“最佳长片”奖,自此开启儿童题材电影的探索之路。2006年,由其编导的儿童长片《紫陀螺》一举获得了包括共青团中央“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奖、首届中国成都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三个奖项。此后,包括电影《火箭鹌鹑》(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创意奖”·2007)、《可爱的孩子》(小猪快跑)(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08)、《骡子的10000米》(CCTV6-电影频道数字百合奖最佳儿童片奖·2012)、《偷心的番茄》(第28届波兰华沙电影节·2012)、《幸福蜜药》(第12届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2014),基于儿童题材探索的电影创作收获了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
从《霸王年代》《紫陀螺》到《树上有个好地方》的创作轨迹,尤其是随着《树上有个好地方Ⅱ——美术老师的放羊班》的杀青能够看到,张忠华用近20年的儿童电影实践,记录和呈现了一代人的成长。基于《树上有个好地方》这一系列儿童电影的成功实践,构建起张忠华具有西部地域特色的儿童风格样式。在观照“儿童—成人”的代际关系、“童年—回忆”的故事印象、“教育—成长”等现实问题的探索中,可见这些作品有着很强的内在共性,儿童电影的“童真美学”概念也由此提出。结合当前实践来梳理“童真美学”的概念内核,可集中由以下三个方面概括。
(一)童年童趣与真实真诚
对“童真美学”的解读,首先是语义上的理解——“童”即“童年、童趣”,“真”即“真实、真诚”。从这里进一步延伸,即是童年时代的生活趣味,以及真实的表达、真诚的情感共同构成“童真美学”的第一要义。正如张忠华所自述的:“如《紫陀螺》《树上有个好地方》这一系列电影,所拍摄的更多的是我自己所熟悉的。对于‘70’‘80’一代人来说,大家很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都有着共同的时代经历。”可见,只有自己所熟悉的,才有可能达到真实真诚的表达,也只有切身经历过,才更能在创作中显露出情感最真挚的一面。
从童真童趣到真实真诚,这些儿童电影多遵循这样的创作思路。“儿童影片大都以儿童为主要表现对象,因此必然反映编导的儿童观。”[2]如此,在对童年成长经历的回味中,可以说导演很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影子。一方面,结合张忠华自己的童年经历和日常观察,其电影中的主角往往是“坏孩子”的形象,角色在镜头下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被放大的人物性格与成人世界的惯性价值观从而形成鲜明的戏剧冲突。另一方面,他在作品中长期坚持以真挚的情感观照童真时代,以情节和物象引发观众的记忆回归。这种以细节打动人心,继而完成对儿童形象塑造的方式,有着直击内心深层的视觉品质,带有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烙印。而作品中源于西北乡村生活的画面与关中方言,则使得作品更显质朴而原生,展现了一种诗性的现实主义基调。
(二)儿童参与和关注成长
毫无疑问,孩子的内心世界微妙而纯真,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毫无杂质的儿童视角之下,是真实、澄澈、明净的童真世界……童真可贵,而成长教育亦然。从电影的教育功能层面而言,作为儿童电影首先就是要做到对儿童负责,这种负责不仅要体现在对儿童观众的负责,更需要有正确儿童观的输出。《树上有个好地方》等一系列作品在“立足儿童、为了儿童”这一方面做得较为深入人心。无论是《紫陀螺》在后半段以陀螺的“失”与“得”为契机,将米兰老师的悄然离开与席布鲁逐渐进入学习正轨的转变作对照;还是《树上有个好地方》以西部乡村校园为表现对象,展现粉提老师温情感召下巴王超过的成长转变。在影片丰富的故事与多彩的世界中,不仅是儿童视角下的儿童参与,每个孩子渐渐成长的过程背后,都有着一个“教惟以爱”的温暖身影。
另外,与传统意义上的“儿童电影”所不同的是,张忠华的儿童片不仅是“关于儿童”的影视作品,更多的是一种成长的复归。相对于一般儿童片面向儿童目标群体拍摄的导向而言,《树上有个好地方》达成了关于儿童题材电影面向全年龄段群体的转换,即张忠华所一贯坚持的“儿童片绝非只是拍给儿童看”。在其眼中,儿童电影有着打通年龄、民族、地域界限的内质,儿童电影不仅要为少年儿童立言、立行、立说,更是为每一个抱有少年之心的“我们”立德、立心,营造一片可以回味的童真净土。电影中对于儿童世界的再现,映照的是荧幕前“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在成长的回溯与童真的回归中,给予观众以心灵上慰藉。这种从“儿童本位”到“成长本位”的跃迁,很自然地将关注点落在孩子的成长问题上,而不仅是记忆的故事和对童年时光的追索。
(三)尊重儿童与理解生命
在当下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更要回到孩子的立场去看待问题,只有思考和明晰“坏孩子”何以“坏”,才能进一步探讨關于儿童成长和教育的问题。无论是《紫陀螺》中米兰老师循循善诱的温柔话语,还是《树上有个好地方》中粉提老师与孩子打成一片的赤诚之心……这里塑造了一种理想化了的教师形象。在“引导而非说教”的教育观念下,因势利导与因材施教,在科学的环境下启迪成长,给予孩子以试错的机会,才是一种对孩子成长负责的态度,这些都体现了导演张忠华对儿童成长、教育问题的思考。“透过一部电影的儿童观,可以看到该民族对儿童的尊重程度,它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3]在他眼中,儿童的世界里保存着全球化的共性“密码”,儿童片有着贯穿社会、心理、教育等各层面的多维文化价值,正是解开这套密码的一串“钥匙”。这把“钥匙”也可以说是导演“儿童观”的一种体现,也即对于“成长”的理解以及尊重。
那么从学理层面来看,童年童趣与真实真诚对应了儿童电影“儿童本位”的自然表达;儿童参与关注成长则反映了共时共情的现实主题;尊重儿童与理解生命则是立足于人性角度对成长的深层理解,指向对真善美的本质追寻,如此三个层面达成“童真美学”的内在构建。一如居伊·德波《景观社会》中所设想的:“梦想的活动会在景观中实现,它将借助符号和信号的中介——最终将抽象的理想物质化。”[4]在尊重儿童的前提下,“大树”“紫陀螺”等符号化了的现实物象,喻含一种理想化的成长状态,而“米兰”和“粉提”两位老师既代表了理想老师的形象,又化身为沟通孩子内心成长的桥梁,这种“童真美学”之下所构筑的理想状态,与经典的事件和人物形象则共同构成了张忠华西部儿童电影风格的基本样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忠华的一系列儿童题材电影作品在互联网端的线上传播状态,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2016—2017年,张忠华将电影《紫陀螺》剪辑成短视频投放到互联网平台,视频片段“仿佛看到小时候的自己”被网络转发超过1亿多次。到2021年底,抖音平台“紫陀螺”话题播放量达3.6亿次。对于一部儿童电影来说,如此广受肯定和关注可谓不易。其实,《紫陀螺》在网上所受到的广泛关注是有预期的。早在2015年,《紫陀螺》通过短视频形式进行传播而在网络端引发热烈关注之前,张忠华编剧执导的系列短剧《兔哈的苹果》拍摄完成,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形式进行了个人儿童电影风格的先期探索。作为与《紫陀螺》《树上有个好地方》风格相近的同题材作品,《兔哈的苹果》以一季五集的系列儿童短片形式投放,在被数百个微信公众号推送转载的同时,收获各网络平台数累计达千万人次的浏览点击量,仅抖音平台话题播放量就超600万次,在网络上收获了良好反响,并荣获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单元“最佳编剧奖”。而《树上有个好地方》在上线一年后,快手播放量达到3.4亿次,抖音平台的话题播放量更是超过12亿次。在融媒体多元化发展的当下,借由移动互联网平台的传播推广模式是这些作品得以为更多人发现的重要因素,对于儿童电影这一经验可资借鉴。
结语
综上所述,从《紫陀螺》到《树上有个好地方》,无论是立足于陕西关中的地域性选择,素人出境方言俚语的本色演绎,又或者是根植于童年记忆和童真成长的诚朴内容。在持续近20年的儿童电影创作过程中,张忠华通过一系列的探索实践,逐渐形成了一条个人的儿童电影创作独特路径。业已杀青的《树上有个好地方II·美术老师的放羊班》,则延续了张忠华“西部儿童电影”风格的类型化阶段,是其“童真美学”的一次新实践。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其个人儿童电影风格逐渐形成的轨迹。当然,《树上有个好地方》只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儿童电影个案,虽然近年来已有一些儿童电影的优秀作品产出,但整体的弱势和不足依然无可回避,如何走出当下中国儿童电影整体上所面临的围局之困,如何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儿童电影精品之作,还需要切实立足于新时期中国文艺“高原”攀登“高峰”的发展方向,有向上的审美趣味,有积极的价值担当,秉持一颗真诚真挚的初心,在儿童电影领域主动作为地坚持创作实践。新时代也期待一部部更为成熟、扎实、有价值的儿童电影的诞生。
参考文献:
[1]谭旭东.新中国70年儿童电影发展史[M].石家庄: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224.
[2][3]马力.中国儿童电影三重奏:文化·艺术·商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
[4][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137.
【作者简介】 杨俊波,男,贵州人,贵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影像及媒介传播相关研究;
韩文超,男,安徽人,遵义市美术馆策展人,西安美术学院西北当代影像艺术中心外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影像与数字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