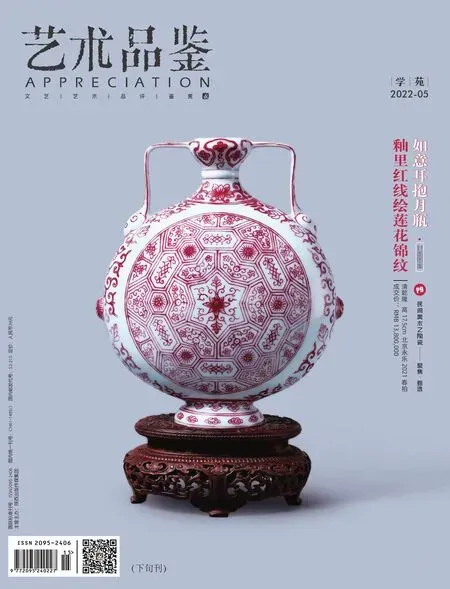对“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再思考
——《礼记·乐记》读书札记
2022-06-10曾雨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曾雨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
一、关于“德”与“艺”
对于“德”的论述,《周礼》中有“三德”“六德”之说,后孟子始以“四德”论,汉代经学家则发扬“五德”或“五常之道”之说,另有“九德”“十德”等,德目众多,较为混乱且互生歧义,缺乏明确的界定,因观察、界定的角度不同,这些归纳分类中的德目及其内涵,往往并不相同。“德成而上”之“德”,郑注解释为“三德”,孙希旦解释为“六德”。结合此句话所在的文本环境——《乐记》,为汉儒根据先秦诸子论乐言论辑录而成的音乐理论著作,“德”应专指“乐德”,即《周礼》中所述:“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故“六德”相对合理。
西周官学、乐教体系承续前代旧制,成为宗周社会礼乐制度的基本构成,且已有乐德、乐语与乐舞之分科,说明“德”之观念前代已有,周时提出“乐德”,将德之阐发与乐教相结合,后世诸子、儒生更申其中义理。先秦时期的乐德观念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体现了原始信仰观念的依附,而第二、第三阶段则代表着独立意识的觉醒,从制度阐发过渡到精神层面。《乐记》所论“六德”“乐德”为第三阶段的精神品行之德,如“圣人作乐,皆本于己之德以教人”,“乐所以使民象君之德”等。“象君之德”即周代政治品格的最高境界,是由一家、一宗族的伦理观念放大至一国的政治理念而形成的乐教目标。第二阶段的制度层面在《乐记》中虽没有直接论述,但对乐的诸多规定性则体现了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的“制度之德”,如“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其中“以成文”隐含了对乐的形而下层面的要求,即若要最终达到“象君德”,完善德性的目的,须五声八音彼此和谐且相互应和。而达到“和谐”的目标,在演奏的乐器、所用调式、律制等多方面又有符合“德”制的具体规则。第一阶段的“自然之德”亦有体现,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乐与天地相感通。”此时的理想化之乐即是德的本身。因此,仅仅从乐章歌词上表现不足以呈现德的全部内涵,应考虑到承载“德”之乐在功能性、演奏风格、乐队组合、乐悬的摆放、器物的物质内涵等多方面的规定性制度。认为“德”即内容的观点主要是从文本来认知德,诗篇乐章的文本呈示能够直接表现统治者的功德,用以教化,这是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德的全部。因此,应明确先秦文化体系下,理想化之乐与“德”相通,以及乐德由自然性规律和制度性规定上升到精神性约束的整体意义。
反观“艺”者有两种解释,分别是“六艺”和“技艺”。笔者认为后者较为恰当,其原因在于“重道轻器”的表述贯穿《乐记》诸多篇章。如“礼乐负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知本者尊,知末者卑”“精者”“本者”为形而上之道,“细者”“末者”为形而下之器。且前述对于乐德观念的解释中,已明确“有德之音为乐”,“乐”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相结合的综合体,形而上之概念为圣人之德,可知《乐记》的话语体系下,“乐”涵盖德本身。既然德是至高无上的最终目标,乐、德相通,那么说德为尊、乐为卑就会产生逻辑上的不通顺。再者《乐记》为论乐的环境,“六艺”中其他五艺,即礼、射、御、书、数在《乐记》中并未见论述,故“艺”应专指乐之“技艺”而不是“六艺”之技艺,更非“六艺”本身。
那么,既然技艺为“下”“卑”“末”者,这“技艺”究竟何指?是否“技艺”与“形式”有着相同的范畴?叶纯之先生将音乐形式分为“外部形式”和“内部形式”两部分,认为“外部形式”通常用音乐语言加以表示,包括带有语义性的节奏、节拍、旋律、调式、音色、和声等。音乐的“内部形式”指音乐语言局部之间的关系,即西方音乐术语中的曲式结构。和声、音色、曲式、调式的表现与乐队编制、配器、表演方式、演奏技巧都是分不开的,形式的表现需通过乐队的配器、演奏者的演奏技巧承载,不同的编配方式、演奏方式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音色和演奏风格,因此,“形式”实际上是除歌词和表演者、听众外,所有音乐元素的集合体,兼顾创作、表演层面。
“技艺”一词则是汉语原有词汇,《说文解字注》:“齊風毛傳曰:蓺猶樹也。樹、種義同。”“技,巧也,从手,支聲。”“艺”的本义是“种植”,是一种实践操作行为,此种行为的实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与效果,所以,它需要行为者具有一定的技巧能力,“技”就是由艺而来的,是于某一领域有所专长为世所用的技艺,后二者合并为“技艺”,偏重于“技”的含义,而“艺”则演化出“六艺”等多种词汇,其政治、文化含义愈加凸显。“技艺”既然源于实践操作,其本身含有较强的个体色彩。高超的技艺水准暗含着乐人对于音乐内部组织的结构规则掌握得较为娴熟,对于节奏、节拍等音乐语言把握得较为准确,此外,在演奏风格上还应展现个人独创性,偏重表演层面而兼有创作层面的内涵。因技艺更多涉及个体表演层面,而形式则暗含个体表演在内的音乐本体整体意义,所以,形式的范围比技艺更广。对应《乐记》,技艺偏重“声”“音”的含义,而形式则还涉及了乐悬摆放、乐队的组合方式等制度、文化范畴。孔颖达作注解:“乐师辨晓声诗,故北面而弦。”《周礼·春官·乐师》中有“诏来瞽皋舞”,郑玄作注云:“呼击鼓者,又告当舞者持鼓与舞俱来也。”,此种表演形式是击鼓与舞蹈相互应和的,乐工为瞽者,其职责主要是在乐队中负责击钟鼓。可见《周礼》与《礼记·乐记》相互印证,可以更好地把握《乐记》中“本末论”的含义。若过度重视技艺表现而忽视礼制规范和“象君德”的要求则不足以用“乐”来称呼,故《乐记》中大多时候称为“声”或“音”,如《魏文侯篇》:“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辞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郑、宋、卫、齐四国的“音”皆在追求听觉享受方面失去节制,乐工在演奏上极尽其所能制造悦人耳目的效果以满足皇亲贵族的视听之娱,而听众也不再在意歌词内容、所用乐器、所演奏的乐曲是否符合“德”的要求,而是沉溺于乐工高超的技艺中,故这种音乐表现仅仅呈现了乐之末节,显然未达乐德之本。
明确了德、艺的内涵,而延伸至本末论之后,可对“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这句话做出总结。总体而论,将此句话归为“乐”的内容与形式之辨,有过于简单化的嫌疑。若不联系《乐情篇》甚至《乐记》整体,单看这句话似乎能说得通,但仅以“内容”概括“德”的内涵,以“形式”概括“艺”的内涵不足以解释二者本质所在。“德成而上”强调的是“乐”从内容到形式两方面应符合制度规范、表达“六德”精神。符合德制的乐是为上、为尊者,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符合制度规范,且侧重审美娱乐而过于注重技艺表现的“音”“声”为下、为卑,这些音声样态是为了满足视听之娱而非弘扬先王君主之功德,以及由此功德内化出的精神品质,因此,为“过声”“慢声”,为“淫乐”,是为“艺成而下”的含义。乐由人心生,若将乐音都调和至纯善,即符合礼制规范,能够宣扬德性之乐,那么五声相协,天地阴阳之气平衡稳固,万物得其所得。
因此,《乐情篇》多处强调应对这种音乐加以节制。放在此种论乐环境之下,“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内涵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而非用内容和形式就可一概而论的。
二、“乐”的内涵及其内在规定性
礼、乐之间,及它们与“德”之间的关系为何?乐是否依附于礼?《乐论篇》中“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体现了礼、乐之间“辨异”与“统同”的关系。将“礼乐之同”的论乐思想置于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加以认知,我们可看到自周公制礼作乐,礼与乐就是相辅相成的存在,若非如此,何以后世以礼、乐并称,将“礼乐文化”“礼乐文明”视为中华文明基因构成的重要部分?郑樵所言:“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正是对这一理念的继承,解释了礼乐关系的本质所在。因此,乐非礼之附庸,先秦之乐也并非只是重内容的、刻板而僵化的,若如此认为,则忽视了礼乐之同,忽视礼乐整体功用意义。正因为礼、乐相同或相异的特性以及它们之间共生共构的彼此依附的关系,所以,更要对礼、乐进行形式上的规定,以更能让其发挥辨别等级次序、和悦情感的作用,达到“德”的要求。项阳先生在《由钟律而雅乐,国乐之“基因”意义》中提出国家用乐标准为“以钟为定,首重雅乐”,大体可归为几个方面:一是以乐钟为标准器定黄钟律高;二是立均出度定十二律核心为用;三是以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作为生律法;四是将六乐用于吉礼大祀;五是规定乐队组合为金石乐悬,且按照不同等级规定方位。以上六种制度规定性除第四是对乐之内容的要求,其余皆是对乐之形式的要求。可见,先秦乐文化在内容方面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各种礼制仪式所用乐曲的要求,以及歌词乐章需体现“君德”内涵的要求;在形式方面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对于乐队组合、表演形式、定律标准、律制、乐悬方位等多方面的要求。
从“礼乐相须”而论,既然礼制仪式具有多层次性和丰富性,那么,与礼制相辅相成的用乐必然也具有多层次、多类型的特性,其乐曲风格应具有多样性。将礼、乐所涉内容相对应,应首先对两周礼乐、俗乐二者之内涵进行辨析。礼乐指与礼制仪式固化为用之乐是无疑问的,而俗乐在先秦礼乐环境中,其定位应有“双重视角”,即与礼乐对应,在日常场合用作自娱、他娱的世俗之乐,以及与雅乐并置,属于礼乐之下一层级,为五礼中嘉礼、宾礼所用之乐。
在此种划分之下,笔者通过阅读、查证《周礼正义》中“春官宗伯下”和《仪礼正义》中“乡饮酒礼”“燕礼”“乡射礼”“大射礼”,与《乐记》中体现的礼乐观念互证,进而明晰先秦用乐内在的逻辑层次:
吉礼之下多种用乐形式虽不及主要用于人际交往的嘉、宾、军礼丰富,但总体上确实有多种类别的区分,只不过吉礼大类之下的层级概念稍显模糊和混沌。先秦之嘉礼、宾礼在五礼中,无疑是用乐类型最为丰富的,如二《南》 《葛覃》 《卷耳》 《采蘩》 《采蘋》 《南山有台》 《崇丘》 《鱼丽》等乐用于嘉礼之乡饮酒礼和燕礼的同时,也用于宾礼之乡射礼和大射礼,这些用乐非为雅乐,却是礼乐中体现仪式情感最重要的部分。因而言“乐”,若只论当今语境下的音乐形式及音乐本体意义则是片面、狭隘的,而只是通过古代学子的论乐言论推断先秦乐文化整体样态,陷入内容和形式二分的窠臼同样是不可取的,如此两种做法皆算不上回归历史语境对于乐文化、乐本体之含义进行辨析。《乐记》全篇虽有佚文,但仍可结合《周礼》中对于周代乐官体系和部分乐制的论述、《仪礼》中对于个别礼制仪式的详述、《礼记》其他篇章中对于乐之义理的阐释,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由此观之,先秦之乐文化重内容、轻形式之说确有疏漏,“乐”应是包含“乐舞”之三位一体形式样态至乐制、乐与社会的关系等多视角的考量在内,涵盖了包括技艺、乐器等“乐之末节”和礼乐文化在内深层性、整体性内涵。
“内容”与“形式”的概念表述源于西方哲学体系的话语表达,进而引入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成为中国美学、文学理论体系的术语。为了使中西方表述对应互证,文学理论界以“文质观”对应内容与形式的分野,进而运用至多种艺术学科中。影响至音乐学界,通常一说礼乐即言礼乐思想,即将形而上之内容与形而下之形式分开来看,进而得出重内容轻形式的观点。文质观是否真正能够代表先秦文学思想主流、文与质是否仅仅指代内容和形式,文学界对此已有争论,而将这种美学观点运用到对《乐记》的解读中时是否合适,确实是需要思考的。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需首先明晰中国音乐的术语表达,进而深入其整体本质特征,中国音乐的话语构建,要在对历史文献和民间音乐术语进行整理、辨析之后才具有可行性,同时,在此基础之上借鉴西方音乐的话语表达,对中国音乐研究相关问题进行对比分析,这样既能做到继承传统,又可达到对传统加以当代阐释的目标。在这之中,明确“源”与“流”之关系是进行共时性和历史性研究的基础,如此,才能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把握,不至于在西方文艺理念的影响下,迷失了自身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