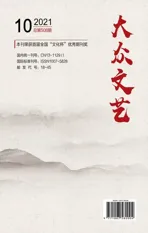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
——以《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英译本为例
2022-06-08齐亚坤
齐亚坤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 710128)
北美新侨民作家严歌苓早在出国之前就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收获一众忠实的读者,移民之后她又将目光重新聚集在中国土地上,并以全新的角度和视角塑造中国本土女性人物形象。严的作品无一不展现出她自身经历所带来的影响,即在东西文化矛盾融合碰撞下所形成的独特叙事方式。得益于此,严在创作中多将历史与人性结合起来,在女性视域下进行书写,这也使她的作品在诸多创作者中脱颖而出。她的作品同时也吸引了诸多汉学家、翻译学者,其中由英国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译著的《金陵十三钗》英译本与英国新生代译者狄星(Esther Tyldesley)翻译的《小姨多鹤》英译本也在海外大受欢迎。
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很多女作家创作时着重于身体叙事并过度强调女性意识,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叙事是和谐且自然的,她认为不能因为性别生理的位置、分工的位置有所区别就被称之为第二性。也就是说,生理层面的略低一筹并不能代表女性柔弱,在《金陵十三钗》与《小姨多鹤》中她也多次到女性伴随的生理疼痛与柔弱,但她笔下的女性在恶劣环境中仍顽强地展现出了韧性,因此这弱者的力量反而体现了女性特有的人性之美。由此可见,若为了颠覆传统女性形象而去过度强调女性意识和社会意识,反而只会适得其反,暴露其弱势处境。因此,如何忠实表达出严歌苓在作品中展现的东方女性主义观便成为翻译时的一大难题。所幸两位译者皆是多次翻译中国女性为主角的文学作品、深谙中华文化的汉学家,因此两部英译本都广受国内外读者、学者的好评。鉴于此,本文拟对女性主义意识是如何影响翻译创作进行说明,由此着重分析两位译者是如何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下传递出与原文相近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定义梳理
钱中文曾说:“语言一旦成为社会性的语言,它对人会产生制约性,甚至出现语言说人的现象。”这也正与话语理论中认为语言的内涵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思想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女性主义在此环境影响下,将话语研究置于政治语境便显得稀松平常。不得不说女性主义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学派种类愈发繁多,但其中也不乏观点激进的学说。时至今日,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中也仍有提倡“操纵”语言和“干预”译者甚至“干预”原文的声音出现,因此在一定程度,盲目推崇女性主义是偏离翻译活动本质的行为。所幸20世纪末诸多领域得益于女性主义思想,都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中自“文化转向”思潮中兴起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加深了学者们对于从性别角度去理解翻译的复杂性。著名文学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早在1992年便指出“对非西方世界新殖民主义的构建”,以殖民主义来类比西方女性主义译者过度干预非西方世界女性作品的翻译实质。因为译者为了达到适合西方读者的口味的目的所采取的“挪用”和“干预”策略都会改变了原文本与译者本身的写作风格,甚至还会抹杀了非西方世界女性的“不同”。若想达到忠实传达出东方女性主义思想的目的,译者既要顾及故事层面的转换又需考虑叙事形式的翻译重构,将意识形态批评与形式分析二者结合。此时仅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提及的方法策略已经无法满足译者需求,因此在进行翻译重构时,译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原文中女性话语进行新的建构,而这些建构又多体现于译本的叙述结构、叙述技巧、叙述人物等方面,这正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研究不谋而合。
总之,译者在考虑到外部社会语境、性别因素对于原文东方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之外,也应了解如何利用不同叙事策略达到发出女性声音,传递东方女性形象的重要性。
二、在历史中书写女性:《金陵十三钗》与《小姨多鹤》
《金陵十三钗》和《小姨多鹤》是严歌苓于2006年、2008年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两部作品皆反响热烈,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严歌苓重拾中国大陆女性题材的取得回归和移民后融合东西文化创作的转型。
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自“农村”到“大上海”再到“留学海外”全部囊括,由此可见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整体性的。她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读者喜爱,海外读者也逐渐发掘出这颗明珠。其中由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韩斌翻译的《金陵十三钗》英译本与英国新生代译者狄星翻译的《小姨多鹤》英译本也都受到海外读者的追捧,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的评分分别高达4.4和4.1。
《金陵十三钗》发生于侵华战争那场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之中,秦淮河边的风尘女子代替藏在教堂中的女学生为侵华日军献唱,舍生取义的故事。《金陵十三钗》以“书娟”的回忆带领着读者进入故事之中,通过刻画“书娟”“赵玉墨”等人心理活动、行为举止烘托了对于女性生存困境、悲惨宿命的深刻关注;《小姨多鹤》则是讲述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惨遭战争折磨的中国人民挣扎谋生的故事。与《金陵十三钗》中所建构的风尘女子与女学生二元对立不同,《小姨多鹤》则是在平淡的日常叙事中刻画中日两国女性形象的不同与相似。国内对于《小姨多鹤》的研究多从历史叙事、婚恋叙事、家庭伦理叙事的角度展开,但正如译者狄星在前言中所写:“本书献给饱受战争之苦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由此不难看出狄星更倾向于宣传反战思想,凸显战争灾难中女性的自我意识。
严歌苓这一时期的小说出版后引起文烈反响,相关研究层出不穷,这不仅得益于原作者叙事手法的巧妙,两位女性译者对书中女性的深刻理解、共情也是推动她们考虑到性别政治与叙事模式的结合对传递原文女性主义思想、女性形象的重要因素,这也正是韩斌和狄星的译作广受欢迎的原因。
三、译者对东方女性形象的传递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曾指出,译者应向原作“移情”,与原文形成“共生关系”,也就是说好的译作应当与原作融为一体,相互共生依存。原文本与译作,乃至原作者与译者在这种关系之下,不再被视为两个分离的个体,而是一个融合的整体。而此时译本也就成了翻译者和作者基于文本进行共同谋划与交流合作,翻译的过程也就成了他们共同参与的对话。而这场同时需要原作者与译者“发声”的对话则正是体现出“女性话语”对于翻译重构女性形象、女性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正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在提倡构建女性权威时所关注的研究层面,即基于性别化视角和经典叙事学的文本研究方式,研究结合社会历史语境的前提下女性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voice)。因此作为文学再创作的翻译活动在翻译重构女性形象、传达原作女性思想时也应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纳入指导范围。
韩斌,英国著名汉学学者。1972年在取得中文系学士学位之后便成了一名大学教师。在2011年时,韩斌不再教书,而是选择成为全职译者,投身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传播中。她认为严歌苓的作品有着超出旁人的细腻,书中人物与故事二者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并且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眼中中国现当代的情形。韩斌也同样强调主体性的影响,她认为不同译者翻译时的行文习惯存在差异。即使是最基本的层面,译者也需要根据自身经验作出判断。因此在她的创作过程中,除了在翻译重构的过程中增添了自身理解,更是对原文的叙事结构、叙事视角进行了调整。原译文叙述视角的变化可以通过 Search and Replace以及AntConc来对《金陵十三钗》的中英文语料分别进行检索。下表为《金陵十三钗》原作与英译本中人称代词和人名的频次统计对比(见表1)。

表1 《金陵十三钗》相关中英语料检索统计
从表1中英语料对比不难看出,原译文的检索结果对比在叙事视角上有很大不同,这一点也引起诸多争议,有学者指出,韩斌忽略了故事的叙述者“我”的重要地位,有些不妥。严歌苓在创作时多以全知视角、固定式内视角、变换式内视角进行叙述,即使是以文中不同人物、不同视角推动情节发展,也会不时穿插全知视角“我”的看法评论,这种做法可以将“我”叙述那段历史时的内心独白更贴近读者,让读者直观了解到“我”的感受,将人物想法以最直白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但韩斌的译文则删去了“我”这第一视角,虽然使译文情节更为流畅,对于书中女性形象更贴近于读者,但很大程度地削弱了“我”这一全能视角所传递出更为深层的女性情感,同样也限制了严歌苓作想表达的女性主义史观。
为将原文中人物的情感更强烈地突显出来,她还不时调整原文的叙事顺序,不过这样一来更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逻辑,如例(1):
(1)书娟看着那个姣好背影慢慢升高,原来是个高挑身材的女子……要不是她父母的自私、偏爱,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刻单单把她留在这里,让这些脏女人进入她干净的眼睛?
Shujuan watched in horror as a colourful assortment of women swept in,cluttering the neatly swept,stone-flagged courtyard with their belongings:baskets,bundles and satin bed quilts from which tumbled hair ribbons,silk stockings and other intimate articles.How could her parents have left her to witness such a vile scene? It could only be because they were selfish and loved her less than her sister.
在例(1)中译者在将原文对于场景描写的顺序做出调整,以书娟的视角描述了几位风尘女子进入教堂时的丑态,更加突出前期作者意图构建的“纯洁——淫荡”的二元对立,同时突出书娟对父母的埋怨质问,增添了一句书娟对质问的自我回答,即表明父母“偏爱”妹妹,而书娟被抛弃了。如此强烈的对比更能使读者在阅读时置身于这一场景,与书娟共情。
同样作为西方女性译者的狄星在翻译时不同于韩斌为突出女性形象而采取的“创造性叛逆”,而是摒弃了长期盘踞西方译界的本族中心主义,将原作作为其创作指向之尺,对原文的理解和诠释都达到了一丝不苟、高度忠实。通过对原作“移情”,将译文与原作化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故其译作不仅忠实表达了原作中女性的生命毅力与地母情怀,同时又带有西方译者视角下理解的“女性觉醒”元素,因此她的译文也大受欢迎,如例(2):
(2)“谁说要休呢?我们是那种缺德的人吗!”母亲说。
Who said we’re going to put her aside? Are we that sort of wicked people?
文中的女主人公之一小环由于日军侵略而流产,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因此在战后为了“留后”,张父张母在人贩子处买回多鹤来为张家延续子孙。《小姨多鹤》故事的发生本是以封建社会的落后理念致使,这一时期女性的自主权益被大大限制,无法生育成为女性原罪。即使张母也身为女性,但早已屈服于封建社会的男权思想,因此狄星将“休”这种带有传统糟粕中宣扬的物化女性的文化负载词译为“put aside”,从内容层面突出了张母这一人物性格的传统以及对小环的漠不关心,话语层面上扭转了新中国旧社会时期封存在的物化女性顽固思想,使译本读者能在不被偏低的语境下下尽善体验书中女性的话语权。
在翻译重构过程中,狄星不仅保留了《小姨多鹤》异国女性视角的抗战后叙事,对于原作采取叙事视角与其独具匠心的限制性叙事手法也得到了最大化地还原,这正体现出狄星对于严歌苓表达女性形象时采取的叙事手法的认可,同时也体现出,不仅是文学创作领域,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对于译者翻译重构女性话语的影响也同等值得研究。
结语
通过两部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故事层面上,韩斌与狄星两位译者对于原文本的情节的翻译重构都比较忠实完整;而在另一层面层面,《金陵十三钗》的译文省去了全知视角的叙述模式,加深了读者与文中角色的情感共鸣,但无法完整传递出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女性主义史观,而《小姨多鹤》的译文则是忠实再现了原文的叙事结构,译者仅增添了细微的叙事改动,使译文更加流畅的同时也忠实传递出文中女性形象和严歌苓的女性主义思想。由此可见,若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且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留心加以运用与考量,不单能使今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加考量策略的使用,更能以形式分析的方法,消除诸多译作常出现的故事层面虚假对等现象。事实上,故事层和话语表达层都是译者在翻译重构过程中需要考量的两大任务,谨以此才能将以往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应用的短处,也就是译作停留在叙事情节层面和过于印象化的缺点尽量补足完善,将译文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更好地传递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