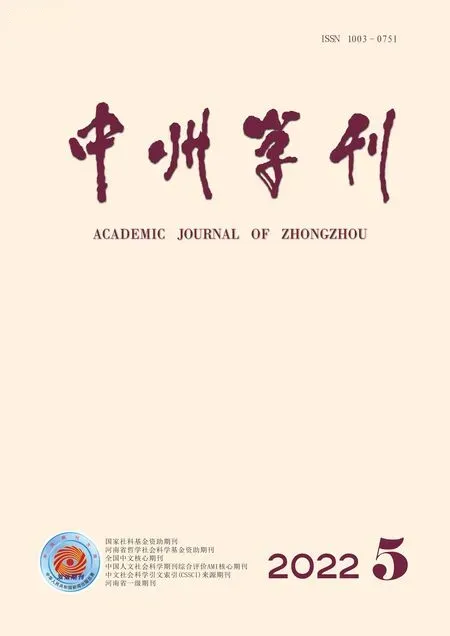现代“形式”意识的自觉
——以王国维“古雅”说为中心
2022-06-08贺昌盛陈玥颖
贺 昌 盛 陈 玥 颖
人存在于世界之中,但世界之于人却又无可捉摸。为了传达和呈现人的“心灵”(soul)所感知的“世界”的总体样态,文学艺术的创造就成为人类赋予“世界”以可把握的“形式”(form)的“赋形”(form-creation)活动。如同“诗(韵文)”与古典世界的对应一样,现代世界同样需要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心灵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中国文学的演化历程,实际上也正是寻找与现代中国的变革形态相对应的形式的过程。王国维对于形式问题的发掘,新文化运动对白话语体的逐次推进,新文学初期小品散文及现代小说的萌芽与成长等,都可以看作是汉语新文学对其自身的形式探索。如果说迄今为止现代中国还远没有完成其自身之现代形态的定型化建构的话,那么,汉语文学的“形式”确立也将同样一直处在持续的探索过程之中。
一、现代形式的转换:从诗到小说
太初之时,人类与自然和神祇和谐共处,这个圆融的统一体世界拥有其自身的完整的“总体性”(totality)。从“吟唱”的“歌”到书写留存的“诗”,即是早期人类的心灵感知和呈现这一世界总体性的最初形式。古希腊时代的“诗剧”或“史诗”借信使赫尔墨斯(Hermes)之名传达着来自统一体的诸般讯息与启示;中国的“古诗”以借仓颉造字为依托记录了天道人伦的序列与情感的本初形态。“口传”的“歌”被书写成为“诗”,富于结构、修辞、韵律和节奏的“诗”就被确定为真正能够与源初的统一体相沟通的可以把握的“形式”了。因此,“诗”一直被看作是对统一体本质最为切近的呈现,诗人则是被赋予了特殊秉性而有能力完美地传达天道、神谕、真理、德性和本心等隐秘信息的代言人。
在西方文学史上,处于最高“形式”位格的一直都是“诗”,这一点从西式理论思想的基本范畴如“诗艺”(poetic art)、“诗学”(poetics)、“诗性”(poetry)等之中即能得到证明。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有诗、骚、赋、词、曲等的主流文体之别,但源自《诗经》的“诗”也同样始终处于绝对的正宗地位。当然,这里的“诗”无论在东西方,都并不单纯是指作为常用文体的诗歌,而更多的是指以富有节律的“韵”来对应世界总体完整性与规律性的“诗”的形式。尽管如此,东西方的“诗”在形式的所指意味上仍是有所差别的。西式的“诗”强调对统一体世界的本质呈现,其所偏重的是求真,带有追溯其先验/本源的意味;而汉语的“诗”从一开始就重在言志,在抒情的向路上更重视向善的内在道德诉求,所以与抒情者自身在具体生存境遇中的“经验”关系更为密切,而少有西式“诗”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神圣的、超验的“真理性”意味。西式的“诗”主要以“史诗/诗剧”的方式呈现,与对神谕、圣迹、英雄伟业等的“叙事”相互关联;中国古代的这类“叙事”却是由“文/史”来承担的。由此,中国古典的“诗”与“文”就有了大体区别于西方的不同分工,“诗”的言志功能主要提供一种个人情感宣泄的出口(宋诗的“说理”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尝试)。但无论如何,在文学范畴内,“诗”都始终是作为最高的形式来看待的,这一点在东西方是基本一致的。
依照通常的共识,古典形态的世界总体性的根本转型,是源自“现代性”的发生,也即人类社会从“神本”向“人本”的转换,其标志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所谓“主体”(subject),是指“人”无须接受“神”的指引而可以“自行决断/自主其体”,其根基即是“人”自身所本有的“理性”;现代世界不再是“神造世界”的“摹本”,而是人依据其理性自行设计、规划、建构、修正和最终定型的人生世界。如此,世界的总体性的基本面貌也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借以呈现这一现代世界之总体性的形式也将必然地发生改变。就西式的形式而言,诗对于本源/真理的呈现不再是对神谕/启示的单向传达,而变成人对于源初统一体之总体性的追溯、探寻与回归,诗成为“人之思”的载体;而诗在“史/剧”层面上的叙事维度衍生出了小说(romance/novel)这种更具自由度和开放性的新形式。
卢卡奇曾指出:“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外延总体性不再直接地既存,生活的内在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但这个时代依旧拥有总体性信念。”“史诗为从自身出发的封闭的生活总体性赋形,小说则以赋形的方式揭示并构建了隐藏着的生活总体性。”“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今天世界的状况本质上是一致的。”伊恩·瓦特也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的趋势也在日益增长,这种转变似乎构成了小说兴起的总体文化背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说由此成为与现代性相呼应的能够更为准确地呈现现代世界样态的最为典范的形式。小说赋予了现代世界以可感知且可把握的形式,小说从诞生、成熟到变形、否定的过程可以折射出现代世界从规划、成型到变异、反思的清晰的轨迹。即此而言,写实性可以看作是小说几乎与生俱来的本性;小说呈现的是人类心灵所感知的现世/当下的实存世界的总体性经验事实,这是以倾听和传达来自超验世界的信息为目的的“诗”,以及剖面式展示有限时空的现代生活的“剧”等所无法实现的。
毋庸置疑,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浪潮一直都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蔓延,东方中国也同样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西式的“romance/novel”也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文学对应于现代中国之总体性的必然形式呢?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汉语语境中的所谓小说实际上并非与西式的“romance/novel”完全对应,作为形式的汉语小说在为现代中国赋形的过程中会做出自主的调整,甚至生成出有别于西式“romance/novel”的新的形式;另一方面,基于现代性在中国的外源性与后发性,以及自身传统历史延续的相对稳定性,中国的现代性尚处在逐渐推进的过程之中,而远未达至最终成熟、完善和定型的程度,与之相呼应的汉语小说也就同样处在持续寻找真正契合于自身形式的焦虑与演化之中。有鉴于此,重新返回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晚清民初之时,以王国维的“古雅”构想为切入点,来进一步追溯现代中国文学的形式诉求,或许能够寻找到更加切合于中国文学实际的未来发展向路。
作为文学评鉴的“古雅”概念并非王国维的首创,但将“古雅”纳入与“优美”“壮美”相并列的纯粹审美形式,却是王国维的独特发明。佛雏即曾指出,“古雅”范畴的提炼虽有其内在的矛盾之处,却仍需要被看作是一种抽象而不空洞的“有意味的形式”。刘成纪认为“古雅”传统对中国美学史的影响具有纵观性,它重新激活了华夏民族对自身人文传统的追忆与复现。日本学者须川照一则认为“古雅”的构想在康德和叔本华之外更可能与席勒的“典雅”形式之论有内在的关联。陈鸿祥也指出,“古雅”之所以有别于传统的“雅正”,正是为了将文艺创造的权力从“圣”的手中交还给俗世的普通“人”,或者说从康德所谓“天才”之“制”转向“凡人”之“作”,且因其更为普遍和常有,“古雅”甚至比“优美”和“宏壮”更加纯粹,因而属于“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
学界有关“古雅”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在整体上一直主要偏向于对“古雅”与西学的影响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的辨析上。就审美范畴而言,王国维对于“古雅”的构想也许确有其局限之处——王国维在后来的诸多论述中也不再使用这一概念。“古雅”虽然无法进入西式审美理论系统中得以存身,但依然可以在汉语诗学语境中光大其彩,“古雅”说可以看作王国维“境界”论的前兆。换言之,正是因为“古雅”的构想剔除了传统文学中向善的道德诉求因素,才使得“古雅”本身成为一种去除了功利色彩的纯粹的、无目的的形式。进一步说,我们不妨将“古雅”视为王国维心目中一座尝试连接古典和现代世界的形式之桥,借此以完成古典→现代的延续性转换(而非断裂或否弃),“古雅”或许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启发意义。如果说康德和叔本华的西式理念只是王国维建构“古雅”说的触媒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诗性传统有意识的形式提炼,则无疑是王国维在西学之外的全新发掘。
二、“古雅”的形式意味
王国维有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氏的这一论断与清代中叶经学家焦循所言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有着密切的关系。焦循的思想颇富创见,他认为,上古之所谓“易”绝非简单的“变”,而恰恰是指诸多个别“异”元素的叠加,并且这种叠加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遵循一种内在隐含的秩序,由此,宇宙才能够显示为一种生生不息的有序过程。所以,“易”的根本正是于表面呈现的“异”的变化之中隐含有内在恒定的法则。循此理路,他认为,就学术思想而言,众生各异的“性情”(“六经注我”式的自我诠释)与“经学”考据的“求真/求实”(宗经征圣之“道”)并不矛盾。据此,他对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给予了充分肯定。焦循甚至认为,经学的实证考据同样也需要“性灵”的融入,主张“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说之性灵”。由此可见,焦循之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实际上是在强调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体之间总是会呈现出差异性的“变/易”,但这种有所差异的“层叠/累加”又都是依据宇宙总体的有序来展开的;如果说“性灵”可以视为“人”的心灵感知“天道/伦常”序列的通道的话,那么,经学之“道”中也必然蕴含了前代先辈各个有“异”的性灵的“叠加/延续”。虽然呈现的形态有“变”,但其中蕴含的“道”却是恒定不变的;无论言说/书写的形态如何变化,实际上都是对宇宙“本源—秩序—形态”的呈现。焦循以此解《易》的目的,是为了协调清代学术关于“汉学”“宋学”孰为“正统”之争,但他对于《易》的创造性诠释,却直接启发了王国维对于“心灵”为世界赋形的“形式”问题的追问,《宋元戏曲史》即是这一追问的最初成果。
在以诗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视域中,“卑下”的戏曲从来都未曾荣登大雅之堂,更遑论将其纳入“史”的层面上来给予高度肯定了。王国维以“宋元戏曲”为研究对象,由“考”而入于“史”,正显示出他从边缘出发来重新观照中国文学之精神内核的独特眼光。在王国维看来,所谓诗、骚、赋、词等,都不过是表层文体形态的“变/易”,文学本身则是这种“变/易”的“叠加/延续”,其作为内核的文学特质实际上一直是保持恒定的。他将这种恒定的文学特质具体概括为“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据此而论,兴盛于宋元时代的戏曲也同样属于以恒定为内质的“变/易”。如果考虑到戏曲与上古巫舞形式之间的转型关系的话,戏曲也许是更能够综合性地呈现文学特质的最佳形式。既然诗、骚、赋、词都只是呈现文学内质的表层“变/易”形态,那么戏曲也应当享有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文学样式同等的地位,这才是王国维充分肯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真正用意。



虽然“古雅”借助了“西学”的外衣,以康德的“优美”和“壮美”作为参照,但王国维的思考重心却是源于东方中国的审美经验。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1907年是王国维从“(西式)哲学阶段”(可信)转向“(中国)文学阶段”(可爱)以开始自行建构其审美思想系统(“境界”说)的关键过渡时期。作为“诗之余”的词成为王国维考察其“境界”之论最为“独绝”的对象,自五代至于宋代的词是诗达至顶峰之后再创极致的一种形式,如同诗的没落之后有词一样,词的没落之后更有戏曲和小说的繁盛,所有曾经被视为“末技”的形式最终都可能取代前代之形式,成为呈现一个时代总体性的真正形式。进一步说,“一代”之文体是一个时代的总体性的“表征”(“变/易”),而在呈现出来的不同“(具体)文体”背后,真正起着支撑功能的正是被王国维称为“古雅”的(恒定)审美精神。王国维的用意实际是在暗示,“古雅”可以作为呈现古典时代总体性的形式,同样也完全可以被视为呈现现代中国总体性的最佳形式;“古雅”绝非古典时代的精神要素的单纯延续,而恰恰可能是现代中国人值得保存的“诗性”文化传统。唯有如此,才可能使中国文化既立足于现代世界,又不迷失自身的传统特性,“古雅”可以成为展示和确认华夏文化身份的真正的呈现形式。在由“俗”转“雅”的“雅化”过程中,“古”之凡俗,今人视之为“雅”;今之凡俗,未始不会被后人视为“雅”。循环此道,正是中国文化能够得以恒久延续的奥秘。
三、古典叙事的“古雅”特性



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立论出发,王国维将骚、赋、诗、词、戏曲、小说等具体文体形制定位在了“变/易”的“更迭/叠加”层面上,并借此发掘出了蕴含其中的带有普遍特质的深层恒定形式。王国维并没有完全套用康德或叔本华的理论思想来考察东方中国的审美现象,而是在西式理念之外独辟蹊径,提炼出了“古雅”这一形式范畴来对应于古典世界总体性。应当承认,东方中国以心灵来感知宇宙万物的方式确实有别于西方,“诗”虽然是东西方所“共名”的一种形式,但在内质上,以经验性抒情为指向的“诗”与以先验性真理为指向的“诗”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西式的“诗”可以从“神谕/圣言”转向“人之思”,作为形式的“诗”本身并没有改变;中国的“诗”虽有诗词曲赋等具体文体形制的变化,但作为内质的“人心/人情”(精神形态)却没有改变。所以,在王国维看来,能够呈现这种“恒定人心”的经验性形式只能称为“古雅”;“古”意味着超越时空的与初民“心声”的衔接,“雅”则是顺应于不同时代的艺术形态的“累加/层叠”。恒定不变的“古”正是在“雅”的“变/易”过程之中,完成自身的形式呈现,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特别称颂的屈子(赋)、渊明(诗)、子美(词)、《窦娥冤》(曲)、《红楼梦》(小说)等即为最有力的证明。




王国维认为,《桃花扇》将其悲剧的根由归于外在于自身的政治、国族与历史,而未能真正揭示出人生所“本有”的悲剧本质;歌德的《浮士德》以其超于“常人”的“天才”能力完成了对悲剧的生命本质的体味与呈现,但“天才”毕竟属于俗世所“不常有”的个别“特例”;相比之下,正是因为《红楼梦》所描摹的全然是常态俗世之中的常人常事,它才更为切实地呈现出了人生之悲剧本质的恒常性与普遍性。由此可见,在王国维这里,世界形貌、心灵感悟与“形式”呈现,三者只有形成高度的融合,甚至融合至于“无形无间”,才能达于“古雅”的最高境界。
王国维所标举的“古雅”的形式意味,其核心即是心灵如何为世界赋形。王国维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为古典世界的总体性寻找到了一种与可之相对应的心灵形式,并以此尝试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搭起一座诗性沟通的桥梁。但他对于行将到来的现代世界却充满了忧虑和怀疑。现代世界是一个以个体的自由欲望为出发点来寻求实现个人价值意义的世界,而个体欲望的自由释放将必然导致世界总体性的崩塌;以多元异质的观念形态出现的人为的真理已经彻底取代了源初统一性的“唯一真理”,现代世界因此变成一个分散的、碎片化的差异性世界,人也无可挽回地变成了各自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思想的危机或现代的堕落。当现代世界逐步由西方向东方推衍的时候,王国维所感受到的并不是梁启超等人那样的进化的乐观,而恰恰是对统一性世界行将崩塌的恐惧。正因为如此,他才尝试着希望寻回和重建曾经充满诗意的“总体性”古典世界;但他同时也坚信,即使生活在现代世界,由欲望所生成的人生之“苦”的本质是不可能有所变化的,高度形式化的诗为叙写常态的戏曲/小说所取代,也无非只是心灵赋形的活动随世界之“易”将有所“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