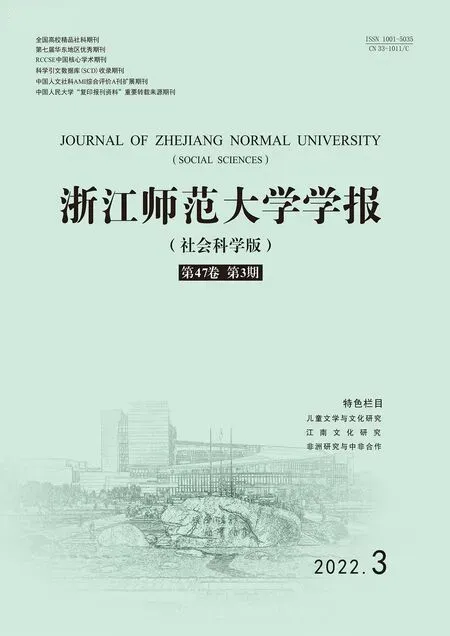《折槛图》寓意考
2022-06-07寿玲,杨勇
寿 玲, 杨 勇
(1.浙江师范大学 行知学院,浙江 兰溪 321100; 2.浙江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折槛图》(图1)的故事出自《汉书·朱云传》:“朱云,字游,鲁人也,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至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御史遂将云去。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争。’庆忌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1]1086

图1 《折槛图》 (宋)佚名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学界对《折槛图》的专门研究文献较少,有专家认为此画表现的是“以君主为对象的人物规鉴画”,[2]89其目的是“歌颂明君谏臣”。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一、“时间矛盾”:《折槛图》的“误读”与“误解”
在历史学家眼中,汉成帝刘骜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明君”。刘渊《晋书》记载“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3]汉成帝在位期间,内宠赵飞燕姐妹,外信外戚王氏,最终导致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作为后戚的班固也认为成帝“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1]108汉成帝确实不值得歌颂,至多在朱云折槛事件的处理中,有些许“容直”因素,与其原来的昏君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已。
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以平常心观《折槛图》,会发现此画描绘的重点似乎并不是成帝纳谏,甚至不是单纯的朱云直谏。依据《汉书》,作者若想表现成帝“能体谅臣下的忠直”,可选“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一幕;若想表现朱云的直言折槛,可选“攀殿槛,槛折”一幕。这些都是能更好表现成帝“容直”、朱云气节的场景,但《折槛图》作者却创造性地构想出朱云与成帝对峙,辛庆忌据理力争的情节。若不是作者的创作力有欠缺,就是另有深意。
宋代遵循的“祖宗之法”,言论环境宽松,虚心纳谏是君主的基本行为准则,大臣直谏实属平常。有宋一代,除特殊时期,高宗杀了岳飞之外,很少杀大臣,尤其是因言杀大臣。宋代士大夫何止敢直言,有时臣子的“直言”,在现代人看来都显得过分。如神宗想治罪陕西用兵失利的漕臣死罪,遭到章惇阻拦,神宗非常生气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面对愤怒的皇帝,章惇不仅没有丝毫退让,且语出惊人,“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①宋神宗并不是一个软弱之君,况处理战事失败的相关责任人也在情理之中,章惇还是直言犯上,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令神宗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事情在宋代几乎俯拾皆是,特意作画鼓励大臣直谏,似属多余。
学者石守谦认为《折槛图》表现的是“容直”主题。石氏注意到《折槛图》与史料之间存在的一个图文矛盾,即《汉书》中朱云折槛与辛庆忌求情不在同一时空:辛庆忌登场“免冠、解印绶,叩头”之时,朱云早已完成“攀殿槛,槛折”,被拖下去了。辛庆忌的求情,朱云当时是不知情的。但在《折槛图》中,朱云与辛庆忌却同台登场,朱云似乎在看着辛庆忌为自己求情。针对此矛盾,石守谦认为此图“不去呈现事件的高潮时刻,而另创造一个‘史实’所无的‘画面时间’”,[2]125进而得出“以较缓和的气氛去呈现君主能体谅臣下的忠直,而容忍不得宜的批评的理想状态”的结论。[2]126
石氏的解读似乎存在着“误读”与“误解”。一些研究早已表明,眼睛并不是单纯的物理器官,绘画记载的也并不是单纯的眼睛所见。对于绘画的解读本身,具有深深的文化烙印。②
《图画见闻志》中班婕妤劝诫成帝的那段对话,较能代表中国传统的观看之道:“孝成帝游于后庭,欲以班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幸。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4]
首先,班婕妤在绘画中关注的是主体对象——“圣贤”“名臣”“末主”与“嬖幸”,但是在论述这些对象时,她并未提及这些人物的具体行为,仅仅是人物象征寓意的辨识。其次,在辨识完具体的人物之后,班婕妤还按照一定的顺序对绘画进行了解读,如“圣贤之君”与“名臣在侧”到“三代末主”与“嬖幸”。
班婕妤对话中的绘画现在已不能得见,但从同时期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可得窥一斑。如汉山东武梁祠西壁画像石(图2),其画面注重的是辨识度,第二层至第四层描绘的是历代君主、烈女、刺客,都标注了各自的名字,第三层的烈女与第四层的刺客,选取的都是最具标识性的场景,第一层的西王母与最后一层的车马出行并无标识文字,其原因是前者的辨识性很强,后者则不需要。近现代的研究表明,这些图像在识别之后,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解读的:最上边一层是西王母,第二层是历代君主,第三层是烈女故事,第四层是刺客故事,最下面是车马出行图,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以分层的方式,全面展现了从天界到冥间的一切。随后每一层,都按照时间顺序,从右向左展开叙述,如第二层从伏羲、女娲一直到夏桀。③这种对图像的运用与文学十分类似,即首先辨识“词语”,随后按照读书习惯从上到下,从右向左对绘画进行解读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反思。

图2 山东武梁祠西壁 山东嘉祥
武梁祠展现出来的这种时空表达方式,完美实现了观者与图像的互动,有效传达了“指鉴贤愚”,达到了“发明治乱”的目的。④也恰缘于此,班婕妤才能通过绘画劝诫成帝。这种读图习惯,造就了人物画从上到下、从右向左的传统叙述方式。如《女史箴图》就是按照《女史箴》的原文从右向左一段段进行描绘的。
佛教的传入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形式,尤其是佛教中以佛陀为中心形成的“一佛、二菩萨、二弟子”格局,强化了绘画中段的价值,使得从右向左的顺序有时被从左向右代替,甚至是以中间为中心的模式替代,但是从上到下的顺序不变。如北魏-257窟西壁中段的《鹿王本生图》(图3):左段以描绘九色鹿救溺水者起,右段描绘王后夜梦九色鹿,国王开出分国而治、赏赐重金的条件来捉拿承接,最终的高潮在中段,描绘了国王与鹿王相见。
佛教绘画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人物画强调从上到下、从右向左的表达方式,但为体现佛教“十方世界”的时空观,“经变”往往把多个叙述单元组合到一个画面之中。如《鹿王本生图》中故事在一个画面之中展开,不再是武梁祠中的多段式样。这种把人物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画面的方式,对后世绘画影响深远。如著名的《洛神赋图》,采用卷轴画形式,显然受到了佛教叙述方式的影响。

图3 北魏-257窟西壁中段的《鹿王本生图》 甘肃敦煌莫高窟
作为后来者的《折槛图》显然是延续早期传统的产物。《折槛图》为立轴,按照传统的解读方式,观者首先看到的是坐于右侧穿着宽大黄色衣服的成帝,顺着成帝的眼神,读者可以关注到正被拖走的朱云,随后读者的眼神顺着朱云挣扎的姿势转而向下,指回画面前景的辛庆忌。成帝、朱云与辛庆忌三人形成了一个从右向左、从上到下的视觉回路。按照这种顺序观看《折槛图》,显然《折槛图》没有另创“画面时间”,只是按照传统的叙述习惯而已。石氏的“误读”,最终造成了认为此画主旨是“容直”的“误解”。
需要指出的是,石氏的“误读”是情有可原的。传统中同一人物可以在整幅画作中反复出现,却往往不出现在同一画面,如《韩熙载夜宴图》(图4)中的韩熙载在整幅画中反复出现,但是在同一画面之中却仅出现一次。《折槛图》作者刻意把朱云与辛庆忌二人处于同一画面,虽然不能说是一种对时间的“创造”,却可能与主旨的表达相关。因为这样的表达似乎还暗含了朱云与辛庆忌之间的惺惺相惜。在现实中,朱云并不是立刻知道辛庆忌为其求情,但是事后朱云一定是知道的,作者这样处理的目的似乎是想展现朱云与辛庆忌是同类人。

图4 《韩熙载夜宴图》 (南宋)佚名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二、“空间矛盾”:朱云与辛庆忌的交集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联系《折槛图》中的另一处矛盾,即故事发生地点的不同。《汉书》“云攀殿槛,槛折”一句,透露朱云折槛的地点是宫殿,但《折槛图》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却是庭院。庭院是传统绘画,尤其是宋代绘画的常见题材,以前多有学者关注此处,却又简单地以审美为由忽略了。在绘画中,物象选择、事物叙述以及组织方式与背后特定的文化密切有关。对这个细节的忽视,遮蔽了一个巨大的视角。
若对中国传统稍做回顾,就会发现除佛教艺术外,传统绘画对于背景的描绘时有时无。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有背景,但是唐代的《步辇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又无背景,这种现象似乎与中国独特的空间意识有关。
与西方绘画表达的物理空间概念不同,中国绘画中的空间可以认为是一种“认识性”空间,它不仅不受物理空间甚至是时间的限制,有时甚至为了达意,会把空间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如《早春图》,郭熙把多种自然元素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表达出国家一统的观念。再如《韩熙载夜宴图》,通过把韩熙载配置到画面中的不同段落,展现了韩熙载所有的夜生活。可以说,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摆脱了物理真实的束缚,走向了心理真实。巫鸿也意识到了空间所具有的表达特性。在近作《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中,他提出了“女性空间”一说,认为户外与男性关联,户内与女性关联,山水题材用于暗示男性,花鸟画则用于暗示女性。⑤
《折槛图》中作者把人物放置于庭院而不是宫殿,这不是简单的审美考量,而是与主题表达密切相关。换言之,庭院本身不仅具有含义,也是解开这张图的关键。
庭院很早就出现在绘画中,如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就出现了庄园样式。宋代伊始,庭院的描绘明显增多,如北宋的《西园雅集图》《听琴图》与《文会图》,南宋更是大量出现,如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佚名的《靓妆仕女图》《绣栊晓镜图》等。
学界对庭院的出现研究不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庭院的出现要么与绘画技术的发展有关,要么与宋代院体画的发展以及绘画观念,如“以小观大”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庭院的出现与当时理学思想盛行有关。石守谦从观者的角度,在近作《山鸣谷应》中提出,由于燕游活动的兴起,南宋时期的绘画中出现了大量记载宫廷游赏的画作,这些画中的人物、屋宇等形象偏大,占据较重要的位置。这种观点虽不能完全解释庭院出现的现象,但从观者出发,看待绘画形式演变的思路却可能更接近庭院出现的事实。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从政治、文化以及经济角度,提出唐代是“中世”结束,宋代是“近世”开始的假说。⑥内藤的观点遭到不少专家质疑,但至少在官吏选拔方面,宋代确与前代不同。
宋代采取了以儒学经典为考察内容的科举制。科举制虽然创制于隋唐,但无论是选拔范围还是人数,隋唐与宋代都无法比拟。科举制彻底打破了讲究身世门第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是中国吏治制度的一次飞跃。与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不同,儒家十分重视师生关系。所谓“天地君亲师”,在儒家看来,师生关系是仅次于血缘的重要关系。科举制选拔出完全不同于前朝的政治精英,营造了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它在打击旧式血缘纽带关系的同时,建立起了以座主门生、举主门生、师生同学为中心的新型纽带关系。
对于宋人而言,无论是为了科举、举荐,还是为了维系关系纽带,士人之间的交游都显得必要且重要。⑦现代学者一般把士人之间的交往分为拜谒、走访、宴饮、雅集与送别几类,其中最能体现文人之间交游的是走访、宴饮与雅集,尤其是雅集。雅集是士人之间更加正式、层次更高的交游形式。它往往与场所有关,如著名的兰亭雅集,发生于会稽山的兰亭,九老会则发生在白居易“敝居”。
宋代是私家园林的成熟期,彼时名园无数,如北宋时仅汴京就有19处名园,南宋时杭州的名园则多达40余处。大多数研究宋代的学者都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宋代文人之间的雅集不仅密集,地点也大多转到私家园林。宋代私家园林的兴盛为雅集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如著名的《西园雅集图》就发生在王诜私人园林,与王诜、苏轼过从甚密者。从现存的绘画来看,与雅集相关的绘画一直与园林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五代卫贤的《高士图》。同时期出现的有园林背景的绘画,大都有雅集的影子,如《文会图》,此图的人物活动安排、构图以及环境设置,都受到雅集形式的影响,故至今学者还在探究主座的人物是否是徽宗。⑧
《折槛图》把人物安排在庭院,显然是借鉴了雅集形式,有突出朱云与辛庆忌二人交集的意味。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折槛图》与史料之间存在着至少两处矛盾,而这两处矛盾都指向了朱云与辛庆忌的关系。
三、史实矛盾:从“义利之辨”到“真朋”
依据现存史料,折槛直谏典故在唐代受到关注,至宋则出现爆炸式增长。⑨最早以折槛为题进行绘画创作的记载来自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记载吴道子曾画过折槛题材。稍有美术史常识者,都会意识到郭氏的记载极可能有误。但这从侧面暗示,朱云折槛典故在唐代就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翻检史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即张禹在汉代人眼中竟然并非奸臣。关于张禹是奸臣的记载《汉书》有两处。其一是朱云所言:“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1]1087另一段来自杜邺:“安昌侯张禹奸人之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尤不可不慎。”⑩班固虽记载了朱云、杜邺等人的言论,但却并不认同:“初,成帝性宽,进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进等绳法举过,而刘向、杜邺、王章、朱云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师安昌侯,诸舅大将军兄弟及公卿大夫、后宫外属史、许之家有贵宠者,莫不被文伤诋。”[1]1575此处班固的用词是“被文伤诋”,并不认为张禹是奸臣。班固认为张禹的恶习是奢淫和不理政务,“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1]1249
在汉代,奢淫者比比皆是,奢淫并不是十恶不赦之大罪,张禹其实并不算突出者。《汉书》中记载:“禹与凤并领尚书,内不自安,数病,上书乞骸骨,欲退避凤。”[1]1249张禹由于与王凤并领尚书事,不敢与凤争锋,屡次称病请退却不得。在这种背景下,张禹不勤于政务,甚至喜爱奢淫,更像是一种自保之法。进而言之,汉成帝时期王凤一族势力强盛,几乎无人敢于与其争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情景下,若真有奸臣,那么非王氏一族莫属,张禹充其量只不过是王凤的党羽而已。张禹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在当时人看来,似乎并不是问题,故《汉书》对张禹的评价是“谨厚”。[1]1249
进入唐代,张禹的做法,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如唐代名相李德裕,从“义、利”角度,对范雎和张禹进行了比较,认为前者单枪匹马“入虎狼之秦,履不测之险”,成就了一番功业;后者身居高位却不仅不及时劝成帝铲除王氏,且为王氏辩护,“以年老子弱,与曲阳有隙”,使得成帝“由此不疑王氏”,铸成“致汉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的大错。最终李德裕得出“臣可以范雎为师表,张禹为鉴戒”的结论,认可重“义”的范雎,反对重“利”的张禹。
李德裕对张禹颠覆性的评价,与韩愈、李贽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面对唐中后期愈演愈烈的道德思想混乱,韩愈、李贽等借鉴孟子“重义轻利”与“修身成德”的思想,提出了所谓的“道统论”,希望强化君权,收拾人心,重建国家权威。这种思想以“性善与四端”为起点,重心不重迹,认为人内在的心性比行为更加重要。在此思想下,李德裕认为成帝“辟左右,亲问禹以天变”之时,张禹为王氏的庇护,是王莽篡权,汉室覆灭的根本原因,“致汉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发,可谓汉之贼也,国之妖也”。故,张禹虽无可诛杀之“迹”,却有可诛杀之“心”。
在这种“义利之辨”的思想下,朱云成为后世大臣追随的典范;有时甚至为了凸显朱云“鼎镬弗顾,宗祧是图”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全心为国家社稷考虑的思想境界,不惜罔顾历史事实。由此,张禹被认为是重“利”的“奸臣”,而朱云则成了“大义”的化身。
除朱云外,折槛典故中辛庆忌其实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免冠解印绶”,并且“叩头流血”,以死力争才使得“上意解,然后得已”。在早期折槛主题中,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辛庆忌都很少被提及,但《折槛图》却将辛庆忌作为重要人物,对其进行了刻画,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索。
为朱云进行辩解的辛庆忌,其实是大将军王凤提携的:“成帝初,征为光禄大夫,迁左曹中郎将,至执金吾。始武贤与赵充国有隙,后充国家杀辛氏,至庆忌为执金吾,坐子杀赵氏,左迁酒泉太守。岁余,大将军王凤荐庆忌:‘前在两郡著功迹,历位朝廷,莫不信乡。质行正直,仁勇得众心,通于兵事,明略威重行国柱石。父破羌将军武贤显名前世,有威西夷。臣凤不宜久处庆忌之右。’乃复征为光禄大夫、执金吾。数年,坐小法左迁云中太守,复征为光禄勋。”[1]1342
在了解了辛庆忌的背景之后,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冒着得罪王凤的风险为朱云求情。换言之,他身上体现的恰是孟子所提倡的“舍生取义”精神:“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5]
分析至此,可发现无论是对朱云、辛庆忌二人各自的评价,还是二者的关系,都与宋代“义利”思想密切相关,即与宋代重新定义了君子道德的评价标准有关。
需要知道的是,辛庆忌不顾身家性命为朱云求情,其实会触犯一个忌讳,即“朋党”。早在孔夫子时期就有“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6]的提法,认为君子之间不能过从甚密。在中国古代,朋党之祸时有发生,如唐朝著名的“牛李党争”。故而,在早期的折槛典故中出现的大多是朱云,却省去了辛庆忌为之求情。换言之,《折槛图》中出现对朱云与辛庆忌之间关系的正面描绘,就显得尤为突出。
无独有偶,对朋党的评价在宋代发生过一次重要讨论。据《宋史》记载,庆历新政之时,以吕夷简与范仲淹为首的两帮人相互指摘对方为朋党:“初,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之。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天下。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为支持庆历新政,作为参与者之一的欧阳修针对政敌,于庆历三年(1043)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
在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中,欧阳修对朋党进行了深入思考,对君子之间的交集提出了新的认识。《朋党论》开篇就承认“朋党之说,自古有之”,[7]但随后他不仅指出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交往大不相同,“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而且认为重用君子朋党,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进而希望君主“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从而达到“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的目的。这似乎才是《折槛图》真正的主旨所在。
《折槛图》作者刻意把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于庭院,着意刻画朱云与辛庆忌之间的互动,其实暗合了欧阳修的理论主张:张禹是“利”的化身,其与王凤是小人之间的“伪朋”;朱云不顾个人生死拼死直谏,辛庆忌不顾自身荣辱安危以及与王凤的个人恩怨,挺身而出,都体现出儒家所追求的“义”的精神,二人是君子之间的“真朋”。作者着重描绘二人的关系,无疑是劝谏君主辨明君子与小人,亲“真朋”而远“伪朋”,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注释:
①“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批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以刺面配远边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失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清)潘永因,刘卓英点校,《宋稗类钞》上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188页。
②这类研究颇多,无论是阿恩海姆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或是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还是近来的视觉文化研究都有所涉猎。
③对于武梁祠的详细论述请参考巫鸿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岑河、柳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④这种线性的顺序,与西方从中间向左右两边展开的方式截然不同,如马萨乔的《纳税钱》。
⑤参见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⑥参见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PoliticsandSinology:TheCaseofNaitoKonan, 1866—193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⑦李觏《上江职方书》中有一段论述颇能说明士人的游谒的秘密:“觏伏以新进俗儒,乐游富贵之门者,莫不有求也。或崇饰纸笔以希称誉,或邀结势援以干荐举,或丐禄粟之余以免困饿,或借威柄之末以欺愚弱。”参见李觏,《李觏集》卷二七《上江职方书》,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2页。
⑧其实《听琴图》同样具有雅集的因素。王正华曾对《听琴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徽宗通过听琴传达政令的信息(参见王正华《〈听琴图〉的政治意涵徽宗朝院画风格与意义网络》一文)。王氏曾把《听琴图》与《祥龙石图》《五色鹦鹉图》等绘画之中的物象进行过类比,却未涉环境叙述,尤其是雅集,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对此画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用琴声进行隐喻与儒学密切相关,如“琴瑟相和”来自《诗经》,本身就是儒家士子喜爱的主题。
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汉代记载朱云的书籍有3处,记载朱云折槛的有2处;晋代记载朱云的有4处,折槛记载2处;南北朝有4处都记载了折槛典故;唐代开始有19处记载朱云,都是记载折槛典故;宋代则出现了100多条记载,且基本都是记载朱云折槛事件。
⑩《汉书》“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权臣之党。曲阳侯根前为三公辅政,知赵昭仪杀皇子,不辄白奏,反与赵氏比周,恣意妄行,谮诉故许后,被加以非罪,诛破诸许族,败元帝外家。内嫉妒同产兄姊红阳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弃。新喋血京师,威权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安昌侯张禹奸人之雄,惑乱朝廷,使先帝负谤于海内,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谦让未皇,孤独特立,莫可据杖,权臣易世,意若探汤。宜早以义割恩,安百姓心。窃见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宜征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则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诸吕欲危刘氏,赖有高祖遗臣周勃、陈平尚存,不者,几为奸臣笑。”参见(汉)班固,《汉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10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