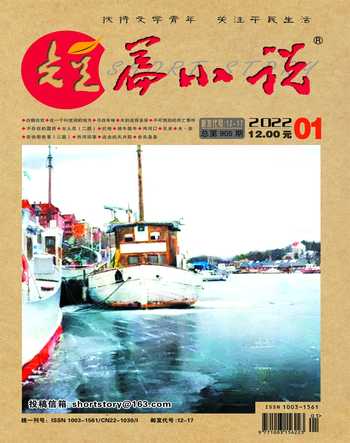远去的天井院
2022-05-30梅子红
梅子红
天井院是一座老宅,门前有个大土场,院里一棵古槐的树干上有个窟窿,小孩子们捉迷藏时常在里边钻来钻去的,树冠很大,半个院子都有荫凉。初夏时节,满树的槐米一串一串的,槐米崩了嘴儿开了花,金灿灿的一树招来成群的蜜蜂,嗡嗡嗡很是热闹。到了秋天,槐角挂满枝丫,乡下人叫它天豆,密不透风的树葉遮不住天豆,有人吆喝小孩上树用杆子打,天豆纷纷扬扬落下,女人们拾了蒸晒之后装在瓦罐里,是最好的良药,崔婆总爱把天豆施舍给东邻西舍,把它放在嘴里咀嚼,甜甜的药味穿肠过肚,能清热消毒。
崔婆不是小脚女人,脚大手大,说话办事爽利。她年幼时可能害过天花,鼻凹里有几颗白麻子,但不妨碍五官,白净的脸上有几分安详几分沧桑,眼睛虽然明澈,却掩不住些许忧伤,脑后光滑的发髻用网兜裹着,没有一丝乱发。人们记忆里的她干净利落,没有半点邋遢。崔婆嫁到崔家后先后生养了五个女儿,五个女儿费尽了他们夫妻一生的心血。多年来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崔婆怎么会嫁给懦弱无才的方全并且窝囊一生甘愿为他吃苦受累。方全上辈人是村上的殷实户,在乡下有田就有根基,后来方全父亲暴病而死,他成了崔家独苗,寡母把儿子视为掌上明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管娇惯。
俗话说寡妇的孩子没胆,方全迟钝、愚笨、厌学,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性格绵软温良。所以场面上的事全赖崔婆出头露脸,方全是个甩手掌柜,间或打着口哨溜到杂货店里讨二两白酒,抓一把花生往嘴里一撂咯嘣嚼了,手擎酒杯脸一仰滋地喝了,自斟自饮自在得很。
崔婆一连养了五个闺女,老辈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崔家的香火还怎么续?为此崔婆在人前低了一头,族人的冷言冷语、妯娌的冷眉冷眼都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咽。她带着五个女儿,白天地里侍弄庄稼,晚上织布纺花,直到把她们养得离了手,心头的结还是没有解开。
那时崔家门前的大场是赶集赶会、说书唱戏、打耍斗猴的好场地,那一代乡下人没有文化娱乐,方全坐在大门口尽兴地望着男女打情骂俏,那时的他没有别的兴致,心里只求一个欢乐,大概他的精神世界里有了欢乐就满足了。
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大场边上那棵弯腰的枣树,风吹雨打,树皮皴裂。男人在树下滋滋吸着旱烟,烟雾萦绕;女人拿上针线筐纳底子缠线,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呱。若是夏天,卖西瓜的会在树下摆个摊,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匆匆从胡同里走出……有的怀里抱一个手上拉一个,大场沸腾起来,脚步声、说笑声、咳嗽声,追逐打闹声响成一片,崔婆和她的女儿们也在里面。卖瓜的从篓子里搬出一个花皮西瓜用手嘭嘭地拍着,随后弯刀一切瓜开两半,黑籽红瓤的好瓜,崔婆在人前殷勤地把瓜一牙一牙地递给女儿们,五个姑娘五张嘴,滋溜滋溜吃得很香。崔婆爱听那种声音,音色热烈,音律亢奋,音韵绵长,像一组悦耳的小合唱,她忘神地聆听着,微微扬起明净的额头,眯着笑眯眯的眼睛,潜意识里那种自命不凡让人敬而生畏。方全呢,村人喊他“不愁”“油瓶倒不扶”,他都不介意,往往一笑了之。
有段时间家里的大小似乎都把他忘了,偶尔有人提及方全的名字才记起还有这么个人。他是大事不问、小事不管的甩手掌柜,喜欢配角。冬寒春月是最悠闲的时候,村人大都上山到煤窑里推煤驮煤,方全对此毫无兴致,懒洋洋地躺在麦秸垛上晒太阳,一待就是半天,太阳快下山了,方全才起身拍拍屁股,散散漫漫地走着回家,夕阳照在他身上,影子长长的虚虚的。方全喜欢赶集,崔婆对此并不表示好恶,几个女儿却踊跃了,他赶集回来刚到大门边,女儿们便一个个彩蝶似的朝他扑去,知道父亲总会捎回稀罕吃食。方全沉住气慢慢把手伸进口袋摸出几颗花生,女儿们嚷着哄抢,接着拿出几颗糖,女儿们又是一阵嬉闹。方全偷觑着崔婆的脸色,崔婆不冷不热一副漠然神态。
天井院是姑娘们的乐园,不时响起脆灵灵的欢笑,那些甜蜜的笑靥和喜盈的脸庞像一朵朵正在盛开的鲜花,少女的气息弥漫了岁月。白天姑娘们小鸟般飞出天井院,在蓝天白云下尽情欢悦;晚上回到家里聚在煤油灯下,或缠线或纳底子或打毛衣。纳底子是待嫁出闺姑娘的事,姑娘寻了女婿后都要给男方做几双新鞋,新鞋表达了姑娘的心愿,蕴含了脉脉深情,所以姑娘们做鞋十分投入,做鞋时大都用干净毛巾裹住半截底子,恐怕汗水或不干净的手弄脏了它。纳底子讲究飞针走线的匀称,线儿勒得不紧不松,做出的底子才会平平整整、结结实实。针脚在小小的鞋底上排列有序,横看是行,顺看是行,左看是行,右看是行。姑娘的绵绵情意都寄予既丰满又柔软的鞋底上。
有时几个姑娘坐在天井院的槐树下,一个姑娘拿着剪子谨小慎微地学剪鞋样,纤手握着剪刀一张一合,该弧的弧,该弯的弯,该圆的圆。阳光从叶间射下来照在脸上,那种认真虔诚的神态似乎在完成一件庄重的事。姑娘们的眼睛顺着移动的剪刀忽儿闪亮忽儿喜乐。一股小风吹来,淡黄的槐花轻轻落下,沾着鬓角扫着鼻尖掠着耳唇,她们却不为所动,静无声息地一片寂然。突然人群里不知谁忍不住笑了,便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掌,一院子的喧腾,惊得树上的喜鹊轰然飞去。
崔家院里闺女多,村上的姑娘都喜欢来天井院凑热闹、说悄悄话,慢慢地这里成了村上的信息集散地,谁相女婿了,谁换手巾了,谁的婆家过礼了,七嘴八舌褒贬不一。有福气的嫁入了殷实人家,命相好的嫁了军官,命苦的屎盘坡挪到了尿盘坡……姑娘没过门前,如果见了女的就喊男的名字,见了男的就喊女的名字,叽叽呱呱笑个不停。
天井院里只有小闺女青青读过初中,在这群姑娘中算是佼佼者。青青俊俏,为人随和,在村里招人喜欢。那时村里办了夜校,每次上课时总有青青的身影,夜校设在大队部的一间活动室里,上课时把桌子板凳挪成一排一排,姑娘们挤着坐在头排听青青讲课,青青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转身拿上教鞭点着抑扬顿挫地念着,樱桃小嘴一张一合,吐字清楚。青青领读几遍后点名叫一位中年男子站起来读一读,他竟读成“毫不利己,砖不离门”,教室内忽然一片笑声,青青有些失望地示意他坐下。
月光从窗外泻进来,与室内的灯光融在一起,黑压压的人头无数双眼睛,在那晕光里被一种黏黏的东西凝住,那是求知欲、是渴望。人们的眼光聚在黑板上,聚在青青的身上,直到下课。
村上时不时有说大鼓的,如小孩满月、老人过寿,或许愿还愿等。有时一个村上能说上十天半月,人们就撵着一家一家地去听,早早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去占地方了,有的画上个大圈写上名字,有的摆几块石头抢占地盘,有的干脆搬上板凳占位……青青和姑娘们几个挤到一条板凳上,她们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你搡我一下我打你一掌。鼓书艺人每到一处都要唱一段酸曲,姑娘们听了脸红心跳,小伙子们却上瘾了,不是鼓掌起哄就是吹口哨喝彩,闹得乌烟瘴气的,姑娘们小声轻骂不要脸,然后又是低声地嬉笑。
青青坐在板凳上,浑身燥热,眼睛发亮,心底滋生了一种隐秘的愿望,似有些许恍惚和蚀骨销魂的感觉,青青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问及伙伴她们也不懂,只是痴痴地笑。村上有个姑娘与青青要好,叫凤彩,她哥哥在县文化馆上班,常常带回一些画报,封面好看,插页精彩。其中《刘三姐》的电影剧照光彩迷人,就是这份画报在姑娘心里产生了磁性效应,她的气质神情让她们着迷更让她们向往,于是讨论的话题是刘三姐,赞叹的人物是刘三姐,她们叹服她的貌美更惊讶她的聪明。
时隔数日凤彩又拿出一本刚刚出版的电影画报,其中有一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彩照,那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之作,凤彩把新近看到的剧情介绍给姑娘们,青青听得最认真,凤彩讲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青春的光晕把姑娘的心魂都摄走了。
凤彩是侄女随姑,父母给她订了终身,她曾跟他们闹过,但还是没有拗过去,所以姑娘们拿她开玩笑时她总是泪眼涟涟的。青青知道她哭的什么,她心里早就装着罗密欧那般模样的男子,可是世俗把她的心上人毁了。有段时间凤彩成天黑丧着脸谁都不理,有人悄悄告诉青青说凤彩的姑家有钱,决定肥水不流外人田,而那女婿是个斜眼塌鼻罗圈腿,实在配不上凤彩。
崔婆家的四姑娘敏敏很少有人提及,因为天井院里的敏敏背了个辱没门风的坏名声。
在乡下,挑担剃头是一种营生,一头煤火一头盆架刀具,走村串巷很受欢迎。谁家办丧事总要叫师傅去为长辈剃头修面忙活一场,主家有酒饭有酬金。后来村上开了理发店,男的修脸理发,女的剪发洗发,在当时算是一门好生意。敏敏出入了几回理发店就闹着要学这门手艺。可崔婆不松口,她认为剃头理发是下九流,再说女孩子家摸摸这个的头摸摸那个的头成啥体统,本分人家是看不起这个行当的。敏敏怄气了,又哭又闹还绝食三天,崔婆只当没听见没看见。哪知崔婆不允,敏敏却跑了,崔婆央求人四处打听,几天后才在县城一家理发店找到她。崔婆叫她回家,敏敏说答应我理发就回去,崔婆长长吁了口气说了一句答应你。
那时理发不分淡季旺季,天天有人在理发店门前排队。师傅康小涛又是烧水又是剃头,据说小涛祖上几辈人都干这行当,到了他这辈学会了用推剪理发。小青年发型多,小涛会赶时髦,小分头、大分头、小平头、大背头,样样技艺超群,因此招来了不少顾客。
敏敏进了理发店后更是蓬荜生辉,大闺女小媳妇络绎不绝地拥来……敏敏的剪刀耍得轻快,敏敏理出的发型又流行又好看,后来男的也找她。敏敏稳重的举止震住了一些花心的男人,推剪在乌云似的发丝上游走,该长的长该短的短,长短适宜使人显得精神帅气。她用窄长的剃刀为男的刮脸,手轻刀快,肥皂沫裹着胡楂,很快一张白净的脸就映在镜子里,老诚的一脸满意,轻佻的一脸坏笑,年老的一脸惊讶,年少的一脸春风。
小涛从小就跟着父亲剃头游乡,十五六岁那年父母撒手人世,孤独的小涛拾起了父亲的手艺。村人小看他,伙伴取笑他,说他是烂泥巴难上墙,因此小涛三十多了还没有妻室。说句实在话小涛长相不错,浓眉大眼,帅气洒脱,但他心里知道自己的轻重,从来不在人前轻浮用事,更不招惹女人。村人感叹生在寒门,人品再好也被人看不起。有时敏敏在理发店忙到小半夜,往往由小涛送她回家,一次敏敏抱了小涛的脏衣裳回来洗,敏敏摸黑擦了火柴点灯,灯光照在墙上,她和他的影子叠在一起,敏敏抬眼看时眉目生情,把小涛惊呆了。也就是那一回开始小涛对敏敏产生了好感,渐渐他喜欢敏敏到了痴迷的程度。再后来崔婆发觉大门门脚臼里滴了油,开门关门都听不见门的声音了,她仔细观察发现敏敏出落得更漂亮了,接着发现小涛进出天井院也有些频繁,常常双双对对,敏敏的异常行动很是扎眼。
于是长舌妇的流言像股暗流悄悄地涌向村子的角角落落,说敏敏跟了小涛,这闲话传进天井院飞进崔婆的耳朵,崔婆倒是沉着,她细细地回想门臼里的油是敏敏怕弄出动静精心设计的,看来是敏敏把小涛偷偷引进家里的。人强嘴强心强的崔婆,忙家务忙庄稼,脸上不挂事的样子,但心里像开锅一样沸腾,敏敏是自己一尺八寸养大的,养了她的身,怎么会不知她的心呢,敏敏学理发后心就野了,但没想到敏敏变得这么快。
天井院只要关了大门一只苍蝇都不会飞进来,可五大三粗的小涛却进来了,深更半夜来,五更时辰去,崔婆自认为崔家家规严,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居然没想到。崔婆清楚一个女人如果在这方面有闲话那是天大的丑事,天井院养的一群闺女往后都要出嫁,村人会怎想?
那年腊月敏敏再没去理发店,崔家要打发闺女出嫁了。他们给敏敏寻的是个庄稼人,身高马大的,人是粗糙了些,和细皮嫩肉的敏敏相比一个是黑汉一个是白雪公主,崔婆说人黑点不算毛病,老老实实过日子比什么都强。那天正好雪停了,冷晴冷晴的,敏敏穿得大红大紫,却一脸不悦地坐在罗圈椅上,唢呐在天井院里呜呜啦啦地吹着,新女婿涂了一脸红印油抿不住嘴直笑。迎亲的女人拥着敏敏催她上轿,敏敏噙泪走出院门,在大门口坐上小轿。马上就要离开天井院了,人群里怎么沒有那双大眼睛?她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
送走迎亲队伍之后,天井院一下子静了下来,崔婆站在门口看着远去的花轿,心终于放进肚里了,敏敏能平平静静地走出天井院,没有惹出大麻烦就是崔家的幸事,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从敏敏出了事儿崔婆的脾气就古怪多了,她动不动就恶声恶气地扔碟子摔碗,方全蹲在一边,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天井院一摊子事全由崔婆撑着,要不是崔婆办事利索,就是用再大的被子也捂不住丑啊,是她自作主张不显山不露水地办了,她把这杯苦酒悄悄地咽了下去,希望往后小涛是小涛、敏敏是敏敏,车走车路,马走马路,谁也不碍谁的辙。
晓晓在天井院里是老大,崔婆觉得大闺女靠得住,就偏爱她,姐妹中她长得最漂亮不说,且有一手好针线,懂得替家里分忧,姐妹五个除了她,谁不是在她背上长大的?晓晓虽没读过几天书,但懂人情世故,村人都说她聪颖有悟性。早年崔婆跟方全说想把大妞留在天井院为崔家续香火,但在乡下倒插门是不光彩的事,谁又愿意把养大的孩子送到外姓人家去做儿子呢。
荣庆是本村的,兄弟六个的日子过得不宽绰,但他生性刚强,是个有头脸的人。晓晓跟荣庆结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崔婆暗里托了媒人把口信传给荣家,荣家看晓晓孝顺温和,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
晓晓进了门后才知道婆婆的厉害,占理不让人,总是刁难媳妇。晓晓嫁到荣家后小心谨慎、逆来顺受,荣庆跟晓晓相亲相爱,日子过得还算融洽。
荣家的那场硝烟是因为二儿子要结婚催着晓晓他们出去借房住而引起的。过门不到三年就撵他们走,崔婆气不过,于是找上亲家商量,哪知弄了个横里撑,坐不住也走不了。婆媳对峙好久了,荣庆夹在中间,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媳妇,着实难堪。晓晓站在窗前看着还没褪色的囍字叹气,婆婆没理还强占三分,最后荣庆和晓晓借了人家一间破瓦房住下了。
那时晓晓有了身孕,崔婆抽空替她收拾新家,没几个月晓晓生了个胖小子。崔婆比晓晓的婆婆还高兴,月子里帮忙洗屎布抱婴儿,没让娃娃哭一声。晓晓躺在床上看着母亲忙碌,却不见婆婆来问一声,只有流泪的份。晓晓月子里没过一天舒心日子,尽管崔婆关照,但那是母亲的心;荣家去哪了,自己的骨肉都不看一眼。荣庆倒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人,不断地出入天井院帮着拉粪割麦砍高粱。
一回晓晓和荣庆闹了矛盾,晓晓跑回娘家把吃奶的孩子丢到家里。小孩哇哇哭叫,小脚蹬开小被子晾在一边,荣庆只得去天井院找晓晓。荣家到天井院的一段路是土路,刚到天井院崔婆就接过嗷嗷哭的孩子哄着。荣庆叫晓晓回家,晓晓坐在床上垂泪,崔婆看看女婿又看看闺女叹口气说:“庆子你先回去吧,晓晓在这过一夜就回去了。”荣庆在天井院立了很久才悻悻离开。
小孩养了三年,总算离手了。从前的拮据困难也像梦一样都过去了,奔日子有了底气。晓晓常常引着小孩去天井院,荣庆也是天井院的常客,天井院渐渐有了笑声,方全这个闲人也对外孙有了感情。后来晓晓二胎又生了个小子,崔婆有意收养荣庆的大儿子,可荣家一百个不愿意,两家又起了一次风波,从此女婿不踩天井院的门边了,孩子也不准上崔家了,唯独晓晓还回天井院,僵局一直持续了十来年,这是后话。
崔、荣两家那场风波之后,崔婆笃定要招赘上门女婿了,二姑娘素素正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素素模样一般,没有大姐高挑,没有青青文气,但干活操持家务肯下力气。素素嘴拙,话头不碎,听话孝顺,崔婆让她留在天井院招个女婿,她顺从了。素素结婚的时候是阳春三月,老槐抽出嫩枝,桃花开得正盛,素素红绒上衣深绿裤子,鬓角别着一朵花,脖上系着水红碎花纱巾,垂眉低眼的,脸上泛着羞涩的红晕。上门女婿是山里人,在煤矿上班,手脚粗大,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眼神却有穿透力,是那种稳重而有心计的人。
对于这个上门女婿,崔婆充满了信任依赖,她收敛了往日的任性恣意。女婿也随和,叫改姓就改姓,在乡下这么好说话的人不多了,难得。他似乎看破了红尘,世上的事哪能那么较真。天井院人来客去,见面他都点头微笑,他处事通达,大事小事都弄得滴水不漏、有条不紊,真的同天井院打成一家连成一块了。素素跟着亲娘过日子,心里却不开心。男人吧,素素挑不出毛病,他成天乐呵,人也幽默,会讨女人欢心。素素烦恼的是母亲,素素头胎生个丫头,崔婆一见是女孩扬长而去了。素素二胎又是一个妞,崔婆犯了心病。素素知道母亲恼的是什么,只有无声哭泣,因为她是她的母亲。很快素素又临产了,崔婆无动于衷的,也不过问一声。
那天是个响晴天,日头刚冒红,素素家里传出男孩的哭声,把天井院都震撼了,崔婆推醒老伴披上衣裳跑进素素屋里,双手抱起襁褓里的男婴,眼里噙着泪花。可是母亲的在意刺伤了素素的心,崔婆问了几声她都没接一句。
多年后崔婆的两个孙女都上小学了,孙子也会跑了,一天方全赶集回来买了把甘蔗,孙女见了围着要吃,他大大咧咧地撅了根梢递给她们,把中间的留给了孙子。当时谁也不懂他的意思,后来才明白方全也是重男轻女的。
青青是崔家最小的闺女,文静柔情、漂亮率真,是天井院盛开的一朵鲜花。当时乡下由于受到《小二黑结婚》的影响,男情女爱已经比较自由,小河边的树林里可以说是伊甸园。初夏的月夜迷蒙幽美,月亮黄亮黄亮的,星星都隐没在天幕里。青青和一个年轻人并肩走着,小河里的水潺潺流着,偶尔几朵浪花晕黄晕黄的,两岸是葱茏的麦地和摇曳的树影。晚风从小河尽头飘来,含蕴着潮气,掺和着田野气息。草丛里的蛐蛐悠悠低吟,夜晚静谧朗润。
年轻人伸手去捉青青的手,她先是心慌而后平静,任他湿漉漉地握着。抬头看时,年轻人没有说话,只是一双灼亮的眼睛冒着火星,青青有预感,连忙离开了他,年轻人一阵微妙的惊愕后便沉默了。青青走在他的身边细细品味着男方沉默的意蕴,她觉得沉默不是故作冷静,而是情感的积蓄。多年以后事实证明了那次沉默的意义,那个年轻人成了青青的如意郎君。
在天井院里青青嫁出去最晚,因为崔婆庇护,青青有些任性且孩子气。天井院虽是巴掌大的地方,但近年也有变化,尤其是二姐夫袁潤,毕竟他是个外来男人,这使青青的任性有些收敛。那时天井院的厕所是共用的,不分男女,进去前先得干咳几声,没有声息了才能进去,方便的人若在厕所里,听见来人的脚步声就吭吭两声提示不便入内。自从袁润来到天井院后,青青如厕不仅放慢了脚步,还得支棱耳朵听动静,怕不小心出了差池。
一次青青闹肚子,想都没想就快步入厕,袁润惊叫一声连裤子都未来得及提好就站起来,门里门外的她和他都愣了,哪想到青青边走边解腰带边脱裤子,小腹露出白嫩白嫩的十分刺眼。青青忙掩了衣裤扭脸就走,又不小心一脚踩了小猫,小猫凄厉地嗷了一声,青青心里更加惶惶了。
打那以后袁润和青青生分了,两人不在一起吃饭不在一块干活,从前袁润常跟青青开玩笑:“你都快成天井院的老闺女了,拖啥呀?”青青就耍脾气冲他:“咋了嫌了?你撵青青了?青青就是不走,在天井院扎根哩,在崔家立老女坟哩。”崔婆一旁听着抿着嘴笑。可从那次之后哥妹之间的闲话少了,晚上袁润在月下编箩筐,青青则回到自己房里点灯看书或戴上耳机听收音机,且悄悄插上门闩。
有时村上的凤彩来了,两人坐在一起头顶头、耳蹭腮地咯咯呱呱连说带笑,把天井院闹得很不安静。那时素素身子不利落,挺着肚子坐在床沿用手抚着腰,冷冷看着青青和男人的微妙变化,争厕的事她责怪过袁润,可他有口说不清,素素知道他是无辜的,却不原谅他,青青也没有过失,只是一次冒失酿了错,但这事在两人心里系了疙瘩,像一堵墙把男的女的隔开了。其实隔开了也好,省得往后再惹难堪。素素一边想着一边用拳头一下一下地捣着腰窝,酸溜溜的,隆起的肚子一阵骚动,胎儿在举手投足练功夫呢。
院子里槐花正在盛开,芳香流动,一缕一缕飘进房里,素素在天井院里是主妇,却没有主妇的权力,她在崔婆的眼皮下沉默,崔婆是亲娘,是亲娘亲手把她欲飞的翅膀折断了,没有自由没有开心,有的只是压抑和委屈。偶尔三姑娘和四姑娘回到天井院,坐在一起聊着聊着就聊起了家事聊起了婆婆,素素听了心想老三老四多好,她们能在人前人后一吐为快,而自己不能,有话只能压在舌根下烂在肚子里,素素现在不能,将来不能,永远不能。素素的脚有些肿了,仄着身子长长地打了个呵欠,眼睛竟有一层泪光,突然觉得一阵恍惚。
那年青青出嫁了,青青的男人就是小河旁曾经恋爱过的小伙子。男人是青青的同学,对岸一个村子里的现役军人。青青的婆婆是个瘫子,卧床多年,恋爱时青青常常背着天井院的父母去伺候未婚夫的母亲,原来青青总往河西跑是在替未来的男人尽孝。青青未過门就先尽孝,恐怕崔婆都不知道,那时媒人快踢折了门槛,青青就是不开口,原来是有这么一个秘密。天井院里的老闺女要出嫁了,崔婆舍不得,素素心里也细细地疼,只有袁润僵硬的脸上绽出了笑意。青青出嫁头天晚上,凤彩和要好的姑娘来到家里陪着新娘过夜,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床腿压得吱吱响,蹭耳磨腮地说悄悄话。
天井院一片灯火,光影里的人们忙忙碌碌,脸上喜滋滋的。青青坐在床沿上两条腿吊着,一双锃亮的红皮鞋轻轻地悠着,一闪一闪挺晃眼,她整个身子罩在灯晕里,晕晕的灯影在她脸上游移。她眯起眼睛,脑子恍恍惚惚,一会儿是隐隐约约的村庄,一会儿是月夜迷蒙,一会儿是男人的眼睛……她无意地看了一下院里灯光下的崔婆,心里不由得疼了一下。
最近母亲对她格外近乎,二姐对她更是殷勤,像对待一个客人。天井院还是从前的天井院,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二十多年前青青出生在天井院,这里的一草一木伴她长大,在这个家里,父母惯她,姊妹宠她,她天真自由、开心任性,二姐突然对她亲热,过分地亲热,那亲热中暗藏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东西,有些疏远有些陌生。袁润一本正经的,轻易不肯说笑,走路都是机械式的不自然。母亲小心翼翼,恐怕哪句话不称意惹闺女不耐烦。
青青知道明天就要走出天井院了,与母亲、姊妹告别去另一个地方了,这个晚上对她是多么重要啊,既短暂又漫长。明天是她走向新生活的开始,也是她马拉松式恋爱的终结。可是明天以后会是什么样呢?她也不知道。
一大清早,热热闹闹的迎亲队伍走进村子,鞭炮炸响,唢呐高亢,为冬日的天井院增添了浓浓喜气。青青在前簇后拥的人群里显得格外鲜丽,她小步走着,恋恋不舍地走着……那悠远的未来明晰而又朦胧,她向它走去,而且是义无反顾地走去。
天井院静下来了,太阳从东边升起西山落下,把阳光悄悄灌进井一样的院子,老槐树的枝枝杈杈印在地上像一幅水墨画,黑是黑,白是白,浓是浓,淡是淡。崔婆坐在竹椅上,抬眼看看头上四四方方的蓝天,太阳的光线一下子触到了她的视线,只那么轻轻一刺,她的眼里就蹦出了两粒泪珠,她拿指头在眼边沾了沾,下眼睑便是一片湿湿的泪光。她心里好像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自己也不知道,似乎天井院昨天还是热热闹闹吵着嚷着说着笑着,一转眼全没了,如今天井院只剩空壳,寂静得让人失落。村里的姑娘们很久没来了,凤彩也已经嫁到了远处,几年不见了。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袁润跟素素从医院回来了。这个家,这个天井院里,还有素素和半个儿子。不,不止半个儿子,是名正言顺的一个儿子。崔婆看见素素挺着肚子走路,她估摸崔家小四快要降生了。
人们在忙碌中匆匆前行,天井院在诱惑中蠢蠢欲动,袁润似乎让一股春风吹醒了头脑,他在信用社贷款办起了一家皮带加工厂,很快成了村里的万元户,接着靠着自己的看家本领又在县里挂起了建筑公司的招牌。
崔婆的两个孙女在皮带厂里上班,两个孙子读中学,素素跟着在工地上给工人们做饭,天井院只留下了两个老人。崔婆常常站在院里仰脸看着老槐树,听着枝丫间的鸟叫,痴痴地好一阵呆想,他们都进城了,就丢下我这个不中用的了。那会儿她真的忘了老伴方全。唉,老了,儿孙一个个翅膀硬了,就由他们去吧。崔婆坐在院子里,阳光照在她的身上,鸡鸭咯咯呱呱地叫着,初夏的风摇动着偌大的树冠,槐花雨纷纷扬扬,一朵灿灿的槐花掠着她的发梢,只那么一弹便寂寂地掉下来,掉在一缕光晕里……
眨眼工夫,老伴方全过世了,天井院没了往日的热闹,格外僻静。平日里她总是拿笤帚掠着地面上的树叶,看着地上白花花的阳光,树叶在她的脚下哗哗刮过,荡起淡淡的烟尘。
天井院还是那个天井院,景况却与先前大不一样了,原本指望有了儿女后天井院里什么都有的,谁想到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一下子全都走了,只留下了她孤单一个人。她那个安闲懒惰的丈夫也驾鹤西去了,撇下她在这乱糟糟的人间煎熬,有时她也想他,不管他有没有能耐,总是崔家的一棵树,歪脖子树也好,弯腰树也罢,毕竟在村人眼里顶着门子。他把自己轰轰烈烈娶进了天井院,怎么一下子就去了呢?崔婆一屁股坐在石墩上,笤帚撂在脚下,她腾出手理理鬓发继续想:我这是咋了,心里这么伤感?她用袖子沾沾眼睛,一阵心慌。
姑娘们全回来是正月间,那时候天井院闹翻了天,她们拖家带口地全来了,男的喝酒划拳,闺女们坐在她身边说笑,孩子们在院子里点鞭放炮,满院子欢声笑语。那几天崔婆穿戴一新,头发一丝不乱,脑后坠着圆圆的发鬓,时不时伸手从口袋里摸出几粒花生和糖果分给孩子们,她看看这个长高了,看看那个长俊了,一脸的兴奋和满足。她在儿女中走来走去,她喜欢那种场面。
多年以后天井院不存在了,一条高速横穿村庄把天井院填平修成了公路,崔婆搬进了新宅,可她心里还牵挂着天井院,整天坐在大门口念念不忘过去的一切。
天井院蓄满了她和儿女们一生的辛酸、困苦、惆怅、兴奋和无尽的忧伤,所以当修路的大铲车开进天井院去挖大槐树的时候,她断然坐在树下哭闹着,最后是袁润劝她并把她搀出了天井院。古槐倒下的那一刻,崔婆看见了一树的槐花如锦如霞,还有蜜蜂嗡嗡的声音……一声“咔嚓”后她茫然四顾,一股黄尘迎面扑来,汹汹的气流吹落了她浑浊的老泪。
如今崔婆有事没事总是拄着拐棍在门口久久地站着,望着东来西去的汽车想着天井院。有时她让素素送她回家,素素说:“妈,天井院早就填平成了公路了。”崔婆不信,她颤巍巍地去找邻居,人家也是说村庄没了,哪还有您的天井院呢!
责任编辑/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