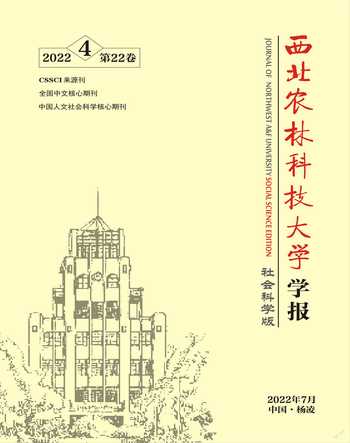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
2022-05-30罗博文吕悦余劲
罗博文 吕悦 余劲



摘要: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村干部;村干部角色;乡村治理有效性;村庄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F3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2)04-0017-10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摹画出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时代诉求。这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坚强保障,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保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看,村民自治制度是构成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作为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实践者”与“领路人”,村干部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建设发展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村干部角色作为影响和评估乡村治理有效性的一个关键视角,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中都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在我国乡村社会网络中,村干部往往会由于所扮演身份的多样性而时常处于一种“角色冲突”的状态当中,同时对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1],这会加剧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弱化、村庄资源集聚能力削弱、村干部“精致利己主义”倾向冒头等突出问题,制约了乡村治理有效性。因此,正确划分村干部角色,深入分析不同角色对乡村治理模式以及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就成为村干部管理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对于村干部角色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学者们在结论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总体而言,目前存在三种观点:徐勇从村干部政府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双重角色”出发,诠释了历史上“双轨政治”思想与现实中“乡政村治”实践,准确把握了集国家行政工作与村庄自治工作于一身的村干部行为角色[2]。一些研究者认为作为一种兼业状态[3],村干部一方面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具有村“官”身份,另一方面也行使村民自治权,具有作为村庄“代理人”身份[4],这是村干部“名”与“实”融合的最好状态[5]。付英、王惠林等学者在徐勇等“双重角色”论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角色”理论框架,指出村干部具有政府“代理人”、村民“当家人”以及“理性人”的三重角色,认为村干部作为一名“理性人”,更会利用职务便利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使得村干部原有的“双重角色”逐渐向“双弱”状态转变[6-7]。这种角色变化会导致村干部在进行村庄公共资源分配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私人关系化”的显著特征[8],使村干部出现角色认知不足、角色行为越轨和角色能力欠缺[9],从而导致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与角色外冲突等问题[10]。梁晨通过研究发现,在项目下乡的时代背景下,村干部会采取“钓鱼”的经营方式拿到社会资源和政府项目,并通过加深村民信任与政府支持,使“获得村民信任”和“获得政府资源”形成良好的有序循环,让不同的主体之间的社会资源产生良性循环,同时使政府、村庄和个人三方都受益,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11]。还有学者指出,虽然村干部能够通过“经营村庄”在短时间内实现村庄的迅速发展,但村庄经营风险的问题仍需要依赖政府资源的不断补给,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政府负担的持续加剧[12]。
以上观点丰富了学界对于村干部角色问题的认识,为后续关于村干部角色问题的进一步纵深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第一,尽管众多学者就村干部角色对乡村治理成效的影响路径作了探讨,但仍然存在不深入、不清晰的问题。村干部角色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机理仍缺乏系统、细致的划分路径,逻辑黑箱依然存在;第二,对于村干部角色的梳理和分析仍局限于将某一个或某两个角色进行单一的简单分析,忽视了村干部角色的多重性与外部性特征;第三,已有研究虽然对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实践的成因进行了描述性解释,但大多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少有学者能够对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逻辑分析。
本文在科學梳理归纳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角色理论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来构建村干部角色分析框架,同时引入类型学视角建立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之间系统、细致的影响路径与逻辑机理,以期补充和丰富基层乡村治理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案例资料来源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近8年间对我国西部地区云南、甘肃以及陕西等省份村庄的持续跟踪调研,通过对不同村庄的对比分析凝练出村干部角色结构以及乡村治理模式的理论范式,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代表性。
二、村干部角色的生成逻辑及其划分
(一)“社会角色”理论的含义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学者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首次将“角色”概念引入学术领域,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进行解释[13]。1936年,美国学者林顿(Ralph Linton)在其著作《人的研究》一书中正式使用了“角色”概念,认为角色是在任意一个特殊场合,作为文化构成为行动者提供的一组规范[14]。依照社会角色理论,社会网络体系中的某一特定角色在形成时往往会经历由外到内的一系列过程,并通过外界环境的影响进而采取行之有效的角色建设,包括角色形象、角色意识、角色规范、角色机制等等,如图1所示。如果个人的行为模式偏离了其角色期望,则会导致周围人的反对与异议。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能够依据别人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评判来认识自己的角色结构,并且根据别人对自身的角色期望来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最终实现自身角色的社会化。
对于村干部来说,明确角色定位、履行角色行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村民、政府或其他社会成员对自身的角色期望。村干部在扮演其角色的同时,“主我”与“客我”之间所产生的不同倾向都会影响其对于身份定义的自我认同,从而使其所扮演角色的职务行为发生改变。因此,村干部往往会在村庄的多元需求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并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15],而村干部角色又会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最终结果造成不同影响。
(二)村干部角色划分
根据相关学者的论断,当政府、村庄以及个人三者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可以根据村干部行为的实际选择来划分村干部角色[16]。因此,假设村干部个体意识到自身的角色行为是需要根据国家政府政策规定进行的,即通过政府授权来完成“行政任务”,村干部则扮演着“政府角色”;假设村干部认为自身的角色行为是需要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来执行,需要更多维护村庄的“社区利益”,村干部则扮演着“村庄角色”;假设其意识到自身的角色行为是将职位获取的资源和权力变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村干部则扮演着“个人角色”。但是,处于农村社会网络中的村干部群体并非只单单扮演着某一种角色,而是会根据个体偏好的不同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一并影响着错综复杂的乡村治理结构。村干部角色划分见表1。
1.“政府角色+村庄角色”:应然理想角色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村干部源自于政府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双重角色”的理论基础,是学界最早对于应然村干部身份的定义和划分。该理论认为,村干部一方面需要对接上级政府并完成政府下派的各项任务指标;另一方面,村干部还作为村庄治理的主要负责人需要对村庄建设发展的各项具体事宜进行决策部署,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并统筹规划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的具体举措。因此,“政府角色+村庄角色”的角色范式也成了社会公众对于村干部群体所理应扮演角色的普遍认知以及应然诉求。
笔者发现,调研区域的村干部普遍扮演着村庄“当家人”与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此类型村干部在其角色行为中既对上承接乡镇政府的任务指标,按照上级规定开展村庄的党务工作,又对下负责村集体事务的正常运转。此类型村干部在心理选择上对于“村庄角色”的归属感更为强烈,认为当行政任务与村庄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自己会选择去维护村民的利益,因为自己本来也是农民,不是机关干部”(宣威县西泽乡丁家湾村,村干部DJW)。另外,应然理想角色村干部对于经营各种高质量社会关系的意愿程度较低,不会刻意地寻求政府支持及政治庇护,并表示“干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行了,没有必要去巴结领导”(宣威县境外镇赤水河村,村干部SGQ)。此类型村干部在与上级政府官员的交往中存在利益输送、以权谋私等现象的情况较少。从2018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来看:要健全从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考录乡镇机关公务员、招聘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制度[17]。由此,村干部在理论上存在着向上晋升的可能,但在实际访谈中笔者却了解到了相反的情况。有村干部提出“村干部向上晋升的难度非常大,像我们这种文化层次低的连政审这关都过不了”(师宗县龙庆乡落红甸村,村干部HQC),这说明村干部在晋升渠道上仍会受到年龄、学历等条件的限制,这也是村干部职业化无法顺利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访谈了解,当地担任村干部的农户大多是村庄中的经济能人或有着丰富经商经历的村民,这些农户作为村庄中的经济能人,拥有丰富且成功的种植、养殖及经商经验,在村庄内被广泛认可,这在最终民主选举的结果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个人利益实现路径,除正常的财政补贴外,多数村干部会采用发展村集体经济使村集体成员利益共享的方式获取自身利益。但是,多数村干部也都认为村干部职务并不能够给自身带来任何便利,相反还会对自身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表示“权力小了,做的事情大了,压力也大了”(师宗县龙庆乡白石岩村,村干部ZQS)。在基层治理体制的不断健全、乡村农户素质的持续提升、村务工作透明化的持续推动的同时,大部分村庄小微权力贪腐的情况明显改善。
基于此,當村干部作为“政府角色”时,其行为逻辑倾向于通过政府授权的方式在村庄内部实现政府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角色行为属于政府导向,其角色的预期目标等同于政府规定;而当村干部作为“村庄角色”时,其行为逻辑倾向于代表村集体利益为村民争取最大收益。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村干部“政府角色+村庄角色”的角色范式得以构建。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村干部向上晋升难度大、社会公众应然期望高、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以及村干部利村、利他价值观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村干部更多地回归职务本位并扮演着应然理想角色村干部,成为村庄的职业精英。
2.“政府角色+个人角色”:资源汲取角色村干部。资源汲取角色村干部是根据学界提出的“政府代理人”与“理性人”角色所延伸出的一种新的村干部角色范式,它区别于以往对于村干部单一角色的划分,将不同的个体偏好结合起来进行诠释。在此类角色结构框架下,村干部属于“政府角色”,执行着“代理人”的工作内容。另外,村干部也是一名“理性人”,作为乡村社会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个人角色”,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来谋取最大的利润与效用。因此,此类型村干部会注重与上级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利于自己在资源的争取上获得一定的优势。另外,当此类型村干部争取到政府资源后,其作为“理性人”角色能够利用制度空隙并借助村干部身份牟求不当利益,抑或利用政府资源获得进一步的提拔发展。
调研区域中很多村干部都是在产业发展时通过经济竞争的形式脱颖而出,并且大部分都是村庄经济合作社的带头人,此类型村干部在正式当选后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进而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因此,在这种个人优势赋权下,自身的经济实力就成为村干部向上争取资源、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关系的筹码。同时,村干部通过向上争取资源、经营人际关系的方式也能够帮助自身的产业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抑或实现自己的体制梦想。据访谈了解,调研区域村干部善于维系与上级政府的关系,并表示“与民政、农业、财务等政府部门的来往较多,并且与部门工作人员建立良好关系对于资源的争取具有一定的优势”(通渭县碧玉乡石滩村,村干部RJB)。因此,调研区域村庄在低保、医疗救助、疫苗接种等项目的指标与红色革命遗址、广场器械、广场绿化等项目的维护金额上都会得到相应的“照顾”。在村干部公共身份的加持下,村庄的各项指标、项目与资源会优先经由村干部处理并落实,这也为“理性人”角色中“精致利己主义”的行为倾向提供了便利,村民的切身利益也就会任由此类型村干部攫取、侵占。这种做法将损害村庄的公平秩序,进而降低乡村的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危害乡村社会稳定。
在“政府角色+个人角色”的角色范式中,村干部一方面作为“政府角色”,在村庄内部执行上级规定的行政任务,并切实落实和分配好下派到村庄的各项资源与指标;另一方面,村干部又作为“个人角色”,其行为逻辑更接近追求利润与回报的“理性小农”,这就导致本应造福村庄的政府资源成了可供村干部利用的社会资本。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村干部在乡村社会网络中扮演着资源汲取角色,成为村庄的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
3.“村庄角色+个人角色”:宗族势力角色村干部。关于宗族势力角色村干部的界定源自于学界“村庄当家人”与“理性人”角色理论的结合。一方面,村干部作为农户群体中的精英代表或村内宗族大姓中的绝对领袖,具备较普通农户更为扎实的群众基础,社会关系网络也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村干部作为“理性人”,角色更善于挖掘和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甚至会借助职务便利通过资源互换的方式来实现利益攫取。因此,此类型村干部会更注重以维持高质量的社会关系来巩固自身在村庄内部的地位与声望,通过与宗族成员交换利益的方式建立村庄的“权力文化网络”,并以此牟取更多利益。于是,原本作为“村庄当家人”角色理应满足村集体诉求的村干部,在“理性人”角色的助推下往往会在有限的村庄资源中忽略多数村民的切实需要,其表面利用资源经营村庄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利己行为,致使村庄资源成了村干部为自己牟利的工具。
调研区域的农户长期受到当地血缘关系与地缘文明的影响,思想观念中对于农地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较强,加之其积累外部政治关系的意愿程度较低,认为“提拔晋升只是激励村干部的一种方式,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提拔,政策悬在空中无法真正落地,而转岗也一般是通过考公务员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没必要刻意去认识上级领导”(白河县茅坪镇枣树村,村干部HYK)。因此,传统乡村中村庄精英外流现象的比例较少,多数村干部更多偏向于“道义小农”的生存伦理,并表示“没考虑过晋升的事,更喜欢现在的生活情况,能与村里人保持更好的关系,地里的活也不荒废”(镇安县米粮镇光明村,村干部LKW)。由此可见,调研区域村干部处于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网络之中,人际互动的行为逻辑也主要是以人情、面子等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性规范为准。因此,此类型村干部会更加注重对于村庄内部地缘关系的维系以及自身经济产业的发展,其行为会受到家法族规、村规民约以及各种约定俗成的软规范以及宗族观念的制约,并深深嵌入于村落社会结构网络之中。调研区域受访村干部表示,“当自己有难处时,也会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也会比较愿意帮助自己”(汉滨区吉河镇高水村,村干部GXB)。在经济利益以及“理性人”角色的双重驱动下,村干部与宗族成员即可达成“利益共赢”的合谋策略,并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当村庄涉及利益问题需要抉择时,调研区域村干部面对政府和村民两方,会借村民不满补贴金额为由向政府建议提高补贴标准,也会以政府意志无法更改为底线积极去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据村民表示,“我们村村干部的家族在与政府的协商过程中拿到了不少好处,但事后却威逼利诱他姓村民向其宗族成员妥协,以此维护自己在宗族中的威望”(榆阳区上盐湾镇尹家庄村,村民LWJ)。也有村民表示,“我们村的村干部不给我们村民办事,找他们办事都一大堆借口,他们的亲戚和给他们好处的什么都给办,国家下来的优惠政策都没我们的事情”(榆阳区上盐湾镇马家梁村,村民HDJ)。
宗族势力角色村干部作为乡村社会网络体系的一部分,其个人所属的社会网络及其相关的社会互动首先表现为一种血缘、地缘关系。这种血缘、地缘关系是指以村干部为中心而向外扩散的宗族网络,这种宗族网络关系会使村干部在行使职务权力时包庇或偏向宗族成员,由此所滋生的“精致利己主义”动机会进一步引发合谋策略,使其“利己”行為倾向盛行的同时也实现了村干部从职业精英向社会精英转变的角色拓展,并最终造成了乡村治理发展滞后的现实结果。
三、基于村干部角色的乡村治理类型与乡村治理有效性评估
村干部作为国家治理单元中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面临着“如何正确理解国家政策并从中为村庄发展汲取有效资源”和“如何高质量执行国家政策并切实满足农民的生产生活诉求”这两大核心问题。上述关于村干部角色的划分是基于政府、村庄以及个人三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代表着村干部在不同的博弈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行为倾向与价值偏好。由此衍生出“理解准确-高质量执行”“理解准确-低质量执行”和“理解偏差-低质量执行”的结构组合并对应着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笔者将其归纳整理为村政双向联动模式、政府资源驱使模式和宗族权威依赖模式。相关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基层出现了普遍的村级治理行政化、利己化现象,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村干部角色弱化甚至异化的体现,这必然会导致村庄公共性的消失,造成乡村治理的低效甚至无效[18]。因此,本文借用学界观点,将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评价指标分为乡村高效治理、乡村低效治理和乡村无效治理三个维度,以“村庄受益程度”作为评估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案例分析划分不同村干部角色所产生的不同乡村治理模式,并结合村干部角色、乡村治理模式来评估该区域乡村治理的有效性。
本文所选取的三个案例分别来自云南省宣威县西泽乡新建村、甘肃省通渭县碧玉镇石滩村和陕西省丹凤县峦庄镇桃坪村,案例均由课题组实地调研过程中所收集到的资料整理所得。选择上述村庄的原因是:三个村庄的治理情况、村干部特征较其他案例样本来说更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能够完全阐释本文对村干部角色及乡村治理模式框架的构建路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一,对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实践定义在理论上还仍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例如,“对国家政策理解偏差”,但却“在乡村内部高质量执行”所导致的 “乡村治理失效”的乡村治理模式。但是,这个理论假设并没有在我们的实际调研过程中得到证实,因此本文不予讨论。第二,本文所凝练出的三种乡村治理模式在理论上会根据不同的影响路径各自分别对应三种乡村治理有效性的结果,而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区别在于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结果的倾向性。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倾向性显著(图2实线箭头)的乡村治理有效性结果影响路径展开具体分析,对于其他两种倾向性不显著(图2虚线箭头)的乡村治理有效性结果,本文只说明可能性不做具体分析。
1.村政双向联动模式:乡村高效治理。“理解准确-高质量执行”组合的行为逻辑中,村干部一方面能够准确理解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以及政府的资源禀赋为村庄发展提供物质动力,通过村集体成员利益共享的路径实现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在国家政策落地村庄的过程中,村干部也能够对政策内容进行高质量执行,确保政府的规范和要求落实到位。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不仅村庄的内生性发展动力得以有效激活,并且能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进一步实现村庄良性发展的社会秩序。因此,“村政双向联动模式”的形成机理也得以构建。在村政双向联动的乡村治理模式中,村干部受权力获取、利益实现和精英属性等因素的影响扮演着应然理想角色,在意识到自身的角色行为是根据国家政府政策规定而进行的同时,也认为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更多注重维护村庄的“社区利益”。基于此,在行为逻辑中村干部也逐渐成为平衡各项博弈力量的关键人物,村庄的治理形态也因此逐渐呈现出乡村高效治理的有序格局。
宣威市新建村村委会主任SWQ案例。新建村位于宣威市西泽乡东南部,全村下辖10个村民小组,农户699户,全村耕地面积1 931.10亩,其中人均耕地1.24亩。新建村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公路交汇点,交通四通八达,村庄的资源禀赋十分突出,当地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以外出务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村委会主任SWQ以前有过经商的经历,且自身发展较好,在成为村干部后为村庄的经济、民生发展都做了很多的实事,比如:劝说村民流转土地、村集体合作社入股、建立养殖场、输出劳动力、引进小企业以及村庄道路硬化、房屋维修加固等等,能够带领村子往好的方向发展。村庄也集聚了良好的社会资本,村干部与农户之间关系融洽、彼此信任。在成为村干部后,SWQ积极与上级乡镇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去乡镇政府进行沟通对接。除了办理村庄业务或者协调村庄事务(如项目工程)之外,SWQ更多则是通过上级政府来了解和学习国家的最新政策、文件以及任务,以此对本村情况进行评估分析,使得新建村与周边其他村庄进行资源竞争时处于优势地位。但SWQ并没有与上级政府领导刻意维持私交,仅保持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在日常交往中也只是沟通工作中的事情。另外,经上级政府考察并批准项目执行后,如何使政策平稳落地也是乡村治理有效性评估的重要路径。SWQ表示“对于政府布置的任务以及争取到的项目,首先会在村里进行广泛宣传,向村民告知目的和要求,取得村民的支持与信任,然后带领村民一起高质量完成”。对于难度较大或阻力较强的情况,SWQ表示“肯定不会降低工作质量,先带领大家一起做,实在困难的话会向上级政府如实反映”。在SWQ的积极努力下,新建村引进了龙头企业、农业企业,并建立农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经营范围包括种植和加工辣椒、种植猕猴桃、养殖牲畜等等。另外,SWQ还通过发布务工消息等方式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信息,大部分农户通过村委会的就业平台得到了务工机会,个人收入进一步提升。据悉,新建村辖区2020年总收入达到15 320万元,人均总收入达到43 771元,基本实现了全民小康的政治目标,形成了乡村高效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新建村的案例中,SWQ作为村庄的职业精英扮演着应然理想角色,能够有效对接上级政府的资源项目并在村庄内部顺利实施。当SWQ通过村集体成员利益共享的方式获得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村庄也在SWQ应然理想角色的影响下最终形成了乡村治理高效的良性循环。
2.政府资源驱使模式:乡村低效治理。“理解准确-低质量执行”组合的行为逻辑中,村干部能够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并借助政策扶持迅速提升村庄的资源集聚,以此来奠定村庄的建设发展基础。但是,在国家政策落地的具体执行中,村庄由于村集体参与机制、村干部考察监督机制的缺失使村干部“理性小农”的利己倾向滋生进而逐渐成为资源汲取角色。在资源汲取角色的影响下村干部经济精英的特征开始凸显并逐渐对下乡资源进行角逐和博弈,从政府下放资源和扶持项目中欺上瞒下、中饱私囊。这种现象会使村干部“干部得益、农民受损”的越轨行为频发,使得国家公共资源不能被合理、公平的使用,从而导致基层小微权力腐败现象严重,村庄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政策导向赋予的资源禀赋就不能完全成为助推村庄内生性发展的有效动力,反而随着村干部资源汲取角色的形成路径而逐渐成为阻碍乡村治理有效的“资源诅咒”。因此,乡村“政府资源驱使模式”的形成机理也得以构建。在政府资源驱使的乡村治理模式中,村干部在意识到自身的角色行为是需要通过政府授权来完成“行政任务”的同时,由于利己倾向的滋生而会在职权范围内利用职务权力将政府资源变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基于此,村干部在其行为逻辑中从本应促使政府项目、惠农政策得以公平分配的“当家人”转变为利用公共资源支配权实现个人自利性诉求的“利己者”。
通渭县石滩村村委会主任HWG案例。石滩村位于通渭县碧玉镇,全村农户共499户,总人口约2 171人,全村耕地面积10 110亩,其中人均耕地4.67亩,当地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以种植业和外出务工为主。HWG属于本村的经济能人,一直生活在本村,后因机缘巧合熟识了乡镇政府官员并萌生竞选村干部的想法。在成为村干部后,HWG成为了坚定的政府“代理人”,积极向上级政府靠拢并协助完成上级政府下发给石滩村的各项行政任务,因此也得到了一些政策资源方面的倾斜扶持。对于政府的资源下放,HWG不仅“照单全收”,并且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存在以个人意志为主导的分配。以此为基础,HWG的自身产业发展在石滩村中也占据了更有利的主导地位,国家政策、项目资源也成为部分村干部牟利的工具。HWG的这种做法进一步导致本应普惠村庄的国家资源被村干部“垄断”,在资源分配评议工作中不以村民实际情况、需求程度为依据,而是以能够满足自身利益“拉关系、看人情”的利己倾向为主要条件,优先分配给自己人和身边人。对于颇有微词的上访群众,HWG会通过以小组长头衔为交换的条件让上访者的親戚去做上访者的工作,说服这些村民不要上访。另外,HWG还会以“五保户”“低保户”的评选为条件拉拢上访者,进一步杜绝村庄的上访行为。至此,石滩村村干部与农户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同时也导致了石滩村治理低效的现实困境。
由于村干部角色异化与石滩村监察机制的缺失使得资源下乡过程中干部与村民之间缺乏横向互动,导致原本致力于石滩村发展的国家资源成为了村干部牟利谋权的来源和手段。在石滩村社会网络结构陷入寡头秩序的同时,村庄治理的有效性受到传统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所制约,形成了政府资源驱使的乡村治理模式。在该模式下,村干部能够保证公共项目在村庄内部的平稳落地,但是村干部“私人关系化”的分配方式导致了村庄内部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结构失序的结果,最终造成乡村低效治理的现实局面。
3.宗族权威依赖模式:乡村无效治理。“理解偏差-低质量执行”组合的行为逻辑中,村干部一方面被血缘辈分所划分出来的等级制度所约束,从而缺失链接外生性资源禀赋的能力,无法准确理解国家政策。这会造成外部项目资源下乡后难以落地的现象,使得村庄资源配置呈现碎片化、空心化特征,导致村庄治理的内生性动力不足并加剧对宗族力量的依赖性,造成村庄治权被乡土族权俘获的情况。另一方面,在农村基层体制改革中,部分农村地区管理与组织体制并不完善,导致其治理职能未被充分发挥。村民对于外部资源性质来源缺乏认知,只能通过宗族长老或氏族家长的意志来建构社会治理秩序。因此,村庄“宗族势力管制模式”也得以构建。在宗族权威依赖的乡村治理模式中,一方面,村干部需要维持已有的治理红利并对村庄内部的宗族权威持续赋权;另一方面,村干部为了进一步谋取利益必然会强化和延续当前的治理路径,并通过其身份的附属价值来获取更多回报。因此,当宗族权威的势力范畴超出治理权限并具备对村庄的强支配力时,便容易引起乡村的制度失灵从而逐渐呈现出乡村无效治理的结局。
丹凤县桃坪村村干部DM案例。桃坪村位于丹凤县城东北部,全村户籍人口共计716人。由于地理位置距乡镇较为偏远且村庄经济发展的情况不容乐观,桃坪村与当地乡镇政府的接触相比周边其他村庄较少,在与周边村庄进行项目资源的竞争时往往处于劣势,导致村庄资源禀赋较差。因此,桃坪村的基层组织体制趋于软化,村中大姓为了增加在村庄社会中的话事权、彰显宗族力量并且牟取不正当的利益,通过修族谱的方式形成了当地的非正式治理组织,并以族谱名单为依据从中推选村干部的候选人。据当地村民LQS反映:“我们村的村干部不给我们小姓村民办事,找他们办事都一大堆借口,但大姓家族的人找他们就什么都给办,如果不给他们好处的话,国家下来的优惠政策都没我们的事情”。在具体的职务行为中,DM对上消极应付、积极性不高,面对乡镇政府的行政任务往往持被动执行的态度。另外,对下维护宗族权益,对本族农户和给予自己好处的村民偏袒庇护,优先向村中大姓农户和近亲友邻分配公有资源,并且在公有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侵占村庄小姓农户的既得利益,导致村庄发展陷入停滞阶段。农户DJM表示“村干部在划分村庄地基的时候不顾个别村民反对,强行在其他村民的地基上盖上自己的房子,就因为他们是大姓,人太多我们惹不起”。在此现实背景下,桃坪村的良性治理格局被打破,村庄的科层体制秩序被非正式的宗族势力所割裂,最终形成了“宗族权威依赖”的村庄治理模式,导致乡村秩序混乱,造成乡村无效治理。
桃坪村外部资源禀赋的缺位使得村庄进一步发展的机会逐渐丧失,而上级监察机制的盲点又为村庄非正式组织的治理权威提供了“生存”的沃土。在村庄治理空间被宗族势力不断吞噬的情况下,农户参与乡村治理就不再是一种自治层面的社会公众参与,而是衍化成为派系利益之间的拉锯与争夺。
四、政策启示与建议
纵观我国西部地区的村庄治理现实,目前所面临最大的实践困境源自于村干部角色的弱化甚至异化。这使得基层治理组织的主体性缺失,造成村庄治理能力的断崖式下跌,在破坏了“政府村庄个人”良性互动关系的同时,也导致村庄的治理有效性趋于低效甚至无效。鉴于此,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路径应在于如何正确引导村干部角色归正,通过激活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进而挖掘村庄的资源禀赋,并促使资源汲取、宗族势力角色村干部向应然理想角色村干部转型,以此来构建乡村善治新格局。
1.培养正确角色意识,构建应然理想角色村干部队伍。培养村干部对不同角色定位的正确认知并使其能够准确领悟角色定位可以帮助村干部养成符合角色期待的观念,在促使自身应然角色与实然角色达到平衡的同时,实现组织期待与个人期待的同构。第一,要积极组织村干部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政策文件精神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村干部理论水平;第二,要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强化培训的深度广度,可依托高校成人教育、地方党校等教育机构,也可以发展现代新媒体平台、远程教育等途径提升村干部的综合素质;第三,应善于利用各种正反面典型对村干部进行思想教育,以此来进一步构建乡村应然理想角色的村干部队伍抑或促使资源汲取角色、宗族势力角色村干部向应然理想角色村干部回归。
2.促进角色规范建设,完善村干部小微权力监察机制。促进村干部角色规范建设、构建农村基层公权力监督机制是推进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环节,能够充分发挥出制度对村干部角色弱化、异化的制约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村干部权力出轨、个人寻租等行为。第一,要规范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结合本村实际制定“村民会议议事制度”,避免个人独断现象的发生,进一步约束村干部的权力范围;第二,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及村务公开有关规定,建立小微权力农民协同监察机制,形成上下联动的监督模式;第三,要结合实际创新民主监督的具体形式,使民主监督制度落到实处,并针对《村组法》缺乏责任追究规定的不足,建立村干部违规决策、管理损害赔偿制度。
3.厘清治权与族权的治理格局,稳定农村发展环境。随着宗族权威正面功能的逐渐衰退,其在处理村庄事务和宗族事务上往往会呈现出偏私性的特征。因此,使村干部职能在应然理想角色层面发挥出最大效用能够提升宗族势力在政治介入时的自我约束,对厘清乡村治权与族权的治理格局、发挥党领导的乡村治理优越性具有助力作用。为此,第一,坚持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打击村庄一切非法宗族势力和活动,清除阻碍村庄有序治理的“頑疾”,推行农村基层法制建设;第二,强化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使村干部能够拒绝为不合理的请求、要求提供便利,引导其发挥正向积极作用;第三,利用好宗族权威资源,使其良性嵌入村庄治理,引导农村宗族势力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
参考文献:
[1]唐晓腾.村干部的“角色冲突”——乡村社会的需求倾向与利益矛盾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2(04):61-67.
[2]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J].21世纪(香港),1997(08):151-158.
[3]王向阳.改革开放后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之路——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6):26-33.
[4]褚红丽,魏建.村干部双重身份的腐败惩罚差异[J].中国农村观察,2019(05):110-126.
[5]胡业方.村干部“名”与“实”的历时性嬗变——基于浙江赵村的实地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99-105.
[6]付英.村干部的三重角色及政策思考——基于征地补偿的考察[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9(03):154-163.
[7]王惠林,洪明.“双重角色”的弱化:日常工作中的村干部研究——以湖北省L镇的调查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16(01):69-73.
[8]王艳,沈毅.资源下乡、私人关系与村庄秩序——以T村绿化工程承包权竞争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4):54-62.
[9]欧健.乡村振兴视域中村支书的角色期望及培养机制建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8(02):23-31.
[10]王海军,简小鹰.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村干部角色冲突与调适[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06):32-38.
[11]梁晨.村庄经营者与“钓鱼”经营:项目进村背景下的村干部——以华北P县西水村为例[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3):28-37.
[12]李祖佩,钟涨宝.“经营村庄”:项目进村背景下的乡镇政府行为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0(03):39-50.
[13]BLUMER H.George Herbert Mead and Human Conduct[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 Pub.Inc.,2004:535-544.
[14]LINTON R.The Study of Man:An Introduction[M].New York:E.P.Dutton,1936:1-10.
[15]梁振华,李倩,齐顾波.农村发展项目中的村干部能动行为分析——基于宁夏张村的个案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01):66-73.
[16]杜姣.村干部的角色类型与村民自治实践困境——基于上海、珠三角、浙江三地农村的考察[J].求实,2021(03):83-97.
[17]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EB/OL].(2019-01-10)[2021-10-21].http://www.gov.cn/zhengce/2019-01/10/content_5356764.htm.
[18]陈宝玲,黄英,国万忠.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20(02):277-285.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Village Cadr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Shaanxi,Gansu and YunnanLUO Bowen LYU Yue YU Jin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A&F 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2.School of Economic Law,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Xian710122,China)Abstract:As the “practitioners” and “leader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village cadr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The role of village cadr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This article uses social role theory and takes actual cases of three typical villages in Shaanxi,Gansu and Yunnan as objects,condenses the roles of village cadres into ideal roles,resource extraction roles and clan power roles,and analyzes the society of village cadres.The roles influence the two-way linkage of village and government,government resource drive,and clan authority dependence on the three rural governance models.The study found that:when the village cadres play an ideal role,the village governance presents a two-way linkage structure model of the village and government,and significantly promotes its governance efficiency;when the village cadres play the role of resource extraction,the village governance presents a structural model driven by government resources,and it significantly prompts its governance to be inefficient;when the village cadres play the role of clan power,the village governance presents a structural model that relies on clan authority,and significantly causes its governance to be ineffectiv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 ideal role of village cadres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the endogenous social resources of the village should be used to resh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dres and the masses,and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the small and micro powers of village cadr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On the basis of the two-way linkage of village administration,the ultimate goal of effective village governance is further realized.
Key words:village cadre;role of village cadre;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village governance
(責任编辑:董应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