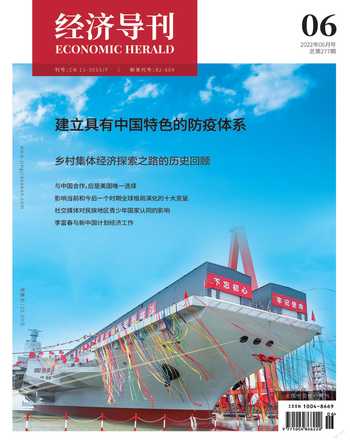乡村集体经济探索之路的历史回顾
2022-05-30杨团
杨团



1987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要构建“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2016年12月29日,中央再次发文“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展示了接续30年前改革的重大信号:一是重视集体经济;二要将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到户。2017年年底,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未来30年全党全国全社会统一意志、全面实施的国家战略,再次将壮大乡村集体经济提上重要日程。
中国历经40年、跨越两代人的农村改革,迄今人们熟知的是包产到户的改革解放了农户、让农民家庭经济破土而出的成长史,而不太熟悉的是,曾经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变身为乡、村、组后的集体经济到底怎么样了?夹带在经济改革大潮中的集体经济是不是消亡了?其实,历经坎坷的集体经济并没有全部消亡,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顽强表现着自己。本文试图通过对30年来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改革的实践梳理,提出多年来未解决的问题——乡村发展为什么离不开集体经济?何为持久发展集体经济的制度载体?面对广大乡村地域,如何实现既能维护社区集体公共资产又能实现农民收益分配权利;既要满足个人利益又要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合作;既要经济增收也要社会服务;既要搞活机制又要合乎法理的组织框架,让乡村再次充满生机和活力。
历史的回顾:集体经济的钟摆式探索之路①
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的变革与演进
20世纪70年代末期启动的农村改革,是伟大的历史变革。在政治上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改为“政社分设”,在经济上取消了剥夺农户个体生产经营权利“归大堆”式的集体经济,开始设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崭新制度。这一新制度的设想不是在农村改革前就提出的,而是在农村改革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自1982年后,中央开创了5年内连发5个“一号文件”推动农村改革的局面。在分户经营成为主体经营形式之后,政策界和理论界就一直在争论,是实行土地私有、还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做联产承包、双层经营?后者的主张占了上风,才有了5个“一号文件”。可见,这5个“一号文件”就是心中有集体但要对原有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的文件。
为纠正农村改革就是进行“土地还家,分田单干”的误解,中央先是在1982年提出“联产承包制的运营,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宜统则统,宜分则分,通过承包把统和分协调起来”;又在1983年将统分结合明确为一种经营方式,“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而作为合作经济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之所以必须存在,是要承擔“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到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决议更加明确地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直至1999年写入宪法。②
在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开”后,原来的“社”——即承担集体经济功能的乡、村组织还要不要,如何改革?针对这个问题,中央在1983年就提出“人民公社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即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在实行联产承包以后,……它们仍然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而且为了“管理集体的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公共财产,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必要的。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1984年再次提出:“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进一步提出,这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乡、村合作组织”,它“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组织的基本职能是“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产积累和资源开发”。③可见,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将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的“社”改造成一个新型的乡村合作组织。它是地区性或社区性的,是综合性的,既能承担集体土地所有和承包发包的土地经营,各类公共资产和资源的管理开发,又能为农户提供生产、生活中“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服务。它的性质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合作经济,由此区别于将全村、全乡的农民视为同一个经济主体的公社集体经济。这样的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农村实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基本制度的组织载体,其制度框架不是一刀切地要求纯集体或纯个体的经营制度,而是允许各地在一定的经营制度空间中采用符合实际的做法。现在看,这就是人民公社消失后,从中央到地方几十年来对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主体持续探索的源头。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建设表述在十三届八中全会时达到最高峰,但及至今日,这个制度也未建立起来,被称为“完成了一半的改革”。尽管文件“有了概括性的规定”,但是“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使得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基本内外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状态”。①
上世纪90年代集体经济的兴起和衰落
到1984年年末,各地设立乡人民政府的工作全部完成,“政”分出来了,而原公社控制的集体经济在“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以“政企合办”的新方式继续“政社合一”,乡镇企业成了乡政府的钱袋子,自然不会再设立“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村组也通过大办乡镇企业让集体经济获得空前的大发展,并支持了村组的公共事务。乡、村两级的“社”都难以分设了。
当时的乡镇企业不是政府刻意扶持的,而是顺应农村和农民需要自然发展的产物,邓小平都说“没想到”。源自社(乡)队(村)企业的乡镇企业,抓住城市企业还未醒过来、改革尚未启动的机会,先行一步,大办乡村工业,为农民也为集体找到了农业之外的增收出路。
乡镇企业的突出作用,一是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年,在我国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已经达到12819万人,比1980年增加了近1亿人。②二是实现了农民、村集体、乡财政整体增收,改善了乡村福利。三是支持了中国改革早中期的高速经济增长。③
可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这固然有历史原因,城市经济改革加快,乡镇企业的各种粗陋和不足统统显现出来。不过,当时政府要求的改制才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①当时所说的“改制”就是从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个体企业。改制的重点是被农业部称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股份合作企业。②而文件规定,两三个人就可组成股份合作企业,结果,集体企业大部分半送半卖给了私人、个体。③可见,当时的这种改制中确有意识形态分歧。即认为资产由集体拥有就是不清楚的,产权只有归属个人,按股拥有才能清晰。从“要创造出一个新型的乡村集体组织”这一改革初衷的角度看,这次改制的负面影响深远。尤其大面积推行改制后,乡村集体企业基本私有化了,乡村公共开支来自本土集体经济的链条被切断,侥幸留存下来的乡村企业也脱离了过去替政府承担的“以工补农”和解决农村就业的职能。
在乡镇集体企业改制之后,乡村集体经济又遭受两次打击,一是延长承包期,这削弱了村集体对于土地的调剂和管理权力,加之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部分地方取消了集体留存的机动地,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上没有了收入。二是在农业税取消后,连同农业税一起收缴的村集体提留也被取消了。④
国家取消农业税本是重大惠民政策,但在取消乡统筹的同时将村集体提留也一并取消,这不但消除了农民对村社集体应尽的义务,还导致因乡镇企业改制失去经济功能的村集体更加彻底地退出村庄公共事务。农户不得不“户自为战”、孤立面对生产生活中所有“办不好和不好办的事”。正因为如此,农户称分田到户后为“第一次单干以来”,称取消农业税改革后为“第二次单干以来”。⑤第一次单干以来,村社集体在共同生产事务上还有一定的统筹能力,第二次单干以来,这个统筹能力就彻底丧失了。
曾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最先喊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专家李昌平针对税费改革提出:“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否则,“村集体所有者的权益如何体现”?如何“通过补偿摆平占地不平衡导致的不合理”?如何“给予村委会”这个村民自治组织“必要的财政基础”?村集体经济组织“何来为村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资源”?①。
在传统集体经济衰落的同时,股份合作制兴起,甚至几乎成了农村新集体经济的代名词。股份合作制早期是乡镇企业转制后一种类似个人合伙的经济形式。村集体最先试验股份合作制的是先期卷入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沿海地区。②为顺应民意,改革一开始就以第二次分配即解决村级集体福利分配的需要为目标,以折股量化为手段,以成立股份合作社为改制最终结果。广东省动作最快,1990年5月、8月连续出台规定,③接着浙江、上海和江苏等地在少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以建立股份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对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进行探索,再后,股份合作制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路径依赖。
回顾这一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集体经济既展示了因管理机制不健全而积累的致命的内在矛盾,如“产权不清”,又展示了能够自发创造令世人震惊的乡镇企业奇迹的一种优势与生命力,而“政社分开”的“社”一直找不准实现形式,先是乡镇企业与村集体合一搞生产经营,后是集体性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撇开生产转而从分配入手清晰化产权。情况纵横交错,改革路向不明。不过,应当承认:一旦集体经济被削弱或被分解、隔离在乡村事物之外,失去经济来源,乡村就会陷入处处掣肘的困境。
21世纪以来,艰难的合作经济发展之路
由于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更多进入城市打工。2016年末农民工总量2.8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进入21世纪,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郊和市镇周边的大量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资本下乡,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快速拉大,与此同时,农村基层财政也越来越窘迫。农村的状况越来越差。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①正式颁布实施,提出解决“分”有余“统”不足、“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的问题,就是要加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强化“统”的功能,以各种新型主体实现“集体统一服务”的功能。但是,1987年提出的“统”是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统”,是具有社区范围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具有整体性意义的“统”,是类似“一串葡萄”的“统”;而专业合作社时期提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统”,只是局限于某种产业活动范围在对接市场时类似“一袋土豆”式的数量规模化方式的“统”,内涵大不一样。②
一开始,专业社的设立不太顺利,经政府行政手段推动,将成立合作社的数量纳入年度工作考核,才有了迅速增长。据农业部统计,2009年成立了20多万家,2013年年中就达到82.8万家,占农户总数的25.2%,到2019年10月底,已高达220万家,占农户总数过半。③不过,大部分合作社人数很少,规模很小,更严重的是,相当部分的合作社是“空壳社”,即合作社只挂名、不运作。据一些地方的调查,空壳社占到合作社总量的30%-40%。④
在运作的合作社中,不少由外来资本的農业公司操纵,农民社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更有资本和部门与大农联合,强势主体“利益共谋”形成合作社。这种大农主导的合作社,等于在部门、资本与小农中间增加了一个类似于合伙制企业的中间商。购农资低买高卖,卖产品低收高出,对内“大农吃小农”,对外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止于汇集社员的购销需求,而真正得到垄断收益的是资本和大农。这类合作社与市场股份制企业无甚区别,内部治理是大股东控制。这种变异现象甚至成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初级阶段的突出特征”⑤。
2008年以后,中央加大了倡导土地流转的政策力度,意在解决耕地撂荒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之前的流转主要在农户之间,之后政策给企业创造了整片租用土地建立规模化现代农业的机会。但受益者是企业,农民得益仍然有限。且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企业绝大部分是靠政府行政干预实现的,农民并非完全自愿。现在看来,原想以土地流转政策破解农业效率问题,却陷入更为复杂的部门、资本、大农、小农、村集体相互博弈的陷阱。更出乎意料的是,很短时期公司制企业就快速崛起,成为中国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主体,这在全球农业大国中是“独有的现象”。①
这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一段时期内占据了乡村发展的主导地位。尤其沿海一带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量快速增长,②让少数城市化的城中村村民对快速升值的集体资产分红产生强烈诉求,而且,“如果不尽早确权到户,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这些资产再过若干年就更难说清楚归属,就有流失或被侵占的危险”③。这就是中央在2016年年底决定在全国范围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背景。其直接目的,是查清家底,防止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集体资产流失。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6.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1万亿元;资源性资产总面积65.5亿亩,其中宅基地面积1.7亿亩。④同时,对查清家底的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以统一颁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证书的方式,确立其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地位。这项改革要求于2021年年底基本完成。⑤但是,尽管民法典已经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系“特别法人”⑥,却因尚未出台适用法律,被颁证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并非法人,未能成为独立运作的法律主体。
30年集体经济改革之启示
今天看来,农村改革走到现在,道路曲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记载了很多有名和无名的参与者集体性的创新努力,也记载了很多无奈、很多惋惜。
尤其改革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发展却明显滞后。农民的经济收入是有提高,但是太多的村庄成了空心村,土地抛荒,集体无能为力,农民形容“外头捡到梁上草,家里丢了老母鸡”。
为什么中央努力推动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在实践中不但没能贯彻,反而被一些人认为是掩盖单干?为什么专业合作社大比例是空壳社,较好的社也是企业翻牌社?为什么一谈合作就只是经济合作?为什么一提集体组织就是股份合作社?为什么“政社分设”一到村庄就贯彻不下去?
30多年的农村改革就像钟摆,在传统和现实之间,集体和个体之间,行政和市场两端之间不停地摇摆,没有稳定在一个核心位置。
与某些人看法不同,笔者认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体制当年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功亏一篑这个“篑”不是别的,就是没能在当时将已经认定的双层体制的组织载体——社区性、综合性的乡村合作组织,采取上下结合、政府推动的方式真正建立起来。若没有框架只有提法,再好的思路也没有根基,后来就被一风吹了。今天看,当时的确错过了建立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最好时机,需要构建真正适应农村农民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从合作主体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三种方式
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社或股份公司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折晓叶,曾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依靠村集体力量,以村社合一为组织形态,自主发展的这一类村庄,并且将其命名为“超级村庄”①。老牌超级村庄只有1000多个,占当时68万个村庄的万分之三。这些村都属于没有分田到户、坚持生产大队式的一个传统集体经营的方式。最有名的是江阴华西村。该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办起了社队企业,在农村改革中没有包产到户而是继续集体统一经营,主要依靠乡镇工业致富,村集体转身为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广东沿海地区为主,又出现了一批新的超级村庄,他们紧邻市、镇,在城镇化进程中被划入城市街道,成为城中村。农村土地因此而实现成百倍上千倍的增值。村集体依靠社企合一的股份公司,为脱农入城的农户分配这些“天赋资产”带来的天赋红利。
村党支部领办村社企会合一的农村集体经济
改革大潮中,一些地处边远、土地零碎、农户分散、集体负债的穷村几乎无一例外,都走上了在村党支部带领下“村、社、企、会”②合一的路。历经数年奋斗,全部依靠自身的力量摘掉了贫困帽子,村集体资产和收益与户均增收均数倍增长,实现了村、民共富。
这些村庄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返乡创业担任村党支书的好带头人。陕西礼泉县袁家村的郭裕禄(郭占武),贵州安顺市塘约村的左文学,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的何允辉,山东莱西市后庄扶村的王希科,河南兰考县南马庄村的张砚斌,四川郫都区战旗村的高德敏等,这些带头人都将自己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经营经验带回家乡,带领村民走集体经济带动个体经济共同发展、义利并举的路,为家乡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类经验怎样才能推广到更广泛的农村地区呢?
2017年,烟台市委组织部学习塘约村经验,开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试点。从11個村起步,2018年发展为100个示范村,2019年年底覆盖了1470个村。2020年8月,在村党支部领办的2779个村中,年新增集体收入4.15亿元,群众增收5.23亿元。到2020年年底,在烟台覆盖了3045个村,①山东全省已达11407个村。②他们的经验是,地方党委组织部支持基层村支部突破政策限制,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以个人入社带入集体资产股,与村民个人股共建股份合作社。党支部牵头主导,担职担责,组织大家一心一意谋发展。结果一招破题、全盘皆活。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是心气大增、面貌大变。烟台经验证明,乡村振兴的“术”要服从和跟着“道”走。方向对了头,才能一步一层楼。
县乡农民合作组织联合会(社)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将农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农业公司、协会乃至村两委等多类主体整合起来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它们名称不一,但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类似,大都建在县、乡,也有在跨村跨乡的区域。如内蒙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四川仪陇县养牛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暨养牛产业协会、石棉县坪阳地区黄果柑专业合作社、山东青岛莱西市院上镇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等等。而且,这些新型组织无一例外都设立专职的总干事经营团队,都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对下集中组织农户、对上整合各部门资源,在党的领导下为乡村振兴搭建平台,成为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
其中,于2018年设立的内蒙赤峰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最为突出。该镇组建了全镇13个村党支部与镇、旗、市的34个涉农部门党支部共建共融的跨部门跨体制的联合党组,由镇党委书记兼任党组负责人。党组办公室设在镇联合会。镇联合党组针对各村党支部提出的问题清单,发动政府部门党支部提供供给清单,通过党组织渠道打通了基层与政府功能部门的联系。镇党组支持镇联合会在各村设立生产、信用、供销综合服务网点,形成镇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共建共享的服务体系。到2020年年底,13个村的集体经济积累达2400万元以上,年内经营性集体经济资产达360万元,全镇农户纯收入达3万元以上。该镇联合会因此被农业农村部评选为2020年全国第二批农业社会化服务24个典型案例之一。
(编辑 杨利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