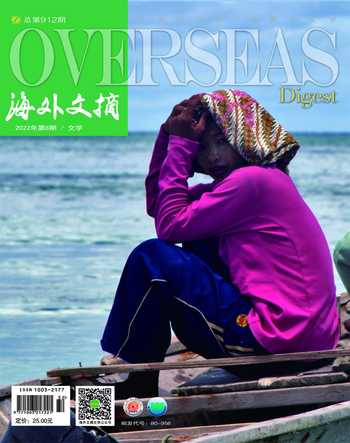布谷飞过圭塘河
2022-05-30赵燕飞
赵燕飞

到了小区地下车库的入口闸门前,她踩住刹车,放下车窗玻璃。还是那个矮矮胖胖的保安,他戴着口罩,看不出是微笑着还是绷了脸。她能肯定的是,他的眼睛有些浑浊,眼神却很专注。他的手里握了一把额温枪。他将那把枪伸进车窗,几乎抵到了她的前额。她咬住下嘴唇。每当这个时候,她的心里就没来由地紧张。他好像按了好几次测温开关,才将额温枪收回,大声读出测试结果:三十六度三。她赌气似的踩了一脚油门,车子往前轰地冲进地库的下坡通道,通道路窄,又是弯道,有车从地库出来,差点碰到一起,她赶紧松了油门去踩刹车,同时将方向盘往右打了一小把。车子在惯性中滑进地下车库。慌乱中,她发现车子前面有一团黑色的影子,影子长了两粒小小的破洞,里面迸出绿莹莹的光来。她吓得一脚刹车踩到底,车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猛地停下来。
她的心跳到了喉咙眼,定睛一看,车子前面什么都没有。
见鬼。她嘀咕了一句。
电梯里空空的。她用右手提着鼓鼓的购物袋,左手按了按横跨鼻梁的口罩金属条,屈起食指,在蒙了透明薄膜的电梯按键上敲了敲“12”。薄膜有点湿,可能有谁刚喷过酒精。电梯在一楼停下,门开了,一个戴着白色KN95 口罩的小女孩要往电梯里冲,被身后那个戴着绿色一次性口罩的女人一把拽住。门关了,她仍听得到小女孩委屈的声音,“为什么不进去啊?”
电梯重新上行,到达十二楼时,她仍是一个人。
进了家门,她取掉口罩,挂在阳台窗户的把手上,将购物袋里的泡打粉、柠檬汁拿出来,放进紫外线消毒柜,按下选时开关。又从玄关柜上面拿了一瓶酒精,对着手机的保护壳和保护膜仔细喷了一遍,去卫生间用肥皂反复洗了手,打开冰箱,拿出一盒鸡蛋。
她从微信收藏夹里找到“怎样做古早蛋糕”,将手机竖放在厨房窗台上,亮着的屏幕上,显示的是古早蛋糕的配方及制作程序。灰色的大理石台面上堆满了东西。她将摆放在台面角落里的厨师机机头抬起来,抽了一张干净纸巾,抹了抹打蛋棒,又抹了抹打蛋盆。“蛋白打发的关键之一,容器不能有半滴油或半点水”。她弯腰从灶台右下方的消毒柜里取了一个大菜碗,三个小饭碗。玉米油、牛奶、细砂糖、低筋面粉、食用盐,都用迷你电子秤分别称好。蛋白分离器架在饭碗上,她拿出鸡蛋先在台面边沿磕一下,再往分离器里一倒,碗里的蛋白放入打蛋盆,留在分离器里的蛋黄放入另一个饭碗里。
她将装了玉米油的大菜碗送入微波炉,选择高火加热30 秒,拿出来,碗沿上架一只面粉筛,把称好的低筋面粉倒进筛子里,左手轻轻晃动筛子,右手用手动蛋抽做“之”字形搅拌。油温可能高了点,面糊有些小疙瘩。她放下蛋抽拿起手机,百度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她干脆拿起量杯,接了50 毫升过滤水倒进面糊。
她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热油来烫面。牛奶和搅散的蛋黄都加进面糊了,小疙瘩终于少了很多。手机忽然响起来,是萨克斯乐《暮光》。她怔了怔。这首曲子是她那张电信卡的来电铃声,那个手机卡是某人给的,只有他知道。她还没来得及扔掉那张卡。犹豫了一下,她拿起手机。铃声断了,一看号码,很陌生。可恶的骚扰电话。她站在那里,一时忘了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门铃好像响了一下。她飞快地跑到防盗门旁边,眼睛凑在猫眼上,门外,什么都没有。她打开门禁监控,镜头之下依然空无一人。
打发蛋白时,她还在想门铃刚才到底响没响。厨师机激烈地抖动着,蛋白很快变成了膏状,她突然记起打蛋盆里只放了白糖,泡打粉和柠檬汁还在紫外线消毒柜里,赶紧停了厨师机,按照攻略,用克勺挖了小半勺泡打粉放进打蛋盆里,又滴了五六滴柠檬汁,重新将厨师机开到十二挡,顺手拿了那只绿色的苹果状定时器,把闹钟定为两分钟之后。蛋糕模具早已准备好,铺不铺油纸?算了,模具原本有不沾涂层,油纸放不放都不打紧吧。她在心里为自己的偷懒找借口。
闹钟响了,她关掉厨师机,将打发的蛋白和蛋黄液拌在一起,倒入模具,送进烤箱。
她站在烤箱旁,盯着蛋糕慢慢长高,表面慢慢有了裂痕,裂痕越来越长,越来越宽。她叹口气,走到客厅落地窗前。好安静啊!偏偏传来一只布谷鳥的叫声,“哥哥——苦——”她凝神听了听,好像来自圭塘河方向。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去圭塘河边散步了。不过是隔了一条马路,她却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往那个方向去。圭塘河是这个城市唯一的内河,曾经变成了臭水沟,如今又干干净净的了。两边的风光带绿的绿,红的红,黄的黄,绿化树越长越高,麻雀也越来越多。但她很少听到布谷鸟的叫声。
想到布谷鸟,她没法不想到母亲。母亲快过生日了。她得为母亲做一个古早蛋糕。以前都是他做。
他知道母亲喜欢吃他做的古早蛋糕,也知道母亲曾经并不喜欢他。她戴了口罩开着车转了小半个长沙城,所有的蛋糕店大门紧闭。没法预订,也无法预料这种像是按了暂停键的日子还得持续多久。
“哥哥苦。”她自言自语了一句,回到厨房。烤箱里的蛋糕不知什么时候塌了下去,表面的裂痕倒是小得可以忽略了。她戴上硅胶手套,打开烤箱,一股浓烈的蛋香扑面而来。她吸吸鼻子,忍住喷嚏取出模具,轻放在晾架上,又屈起拇指和食指,掐了一小块塞进嘴里,烫,甜,香。只是味道太结实了,不应该是蛋糕该有的样子。
她拿起手机百度蛋糕塌陷的原因。是玉米油温度太高还是蛋白打发不够?她对自己说:“没关系,从头来过。”
她洗了模具,擦干,用硅胶刷刷了薄薄一层橄榄油,她还是决定不铺油纸。原料都用电子秤称好,蛋白和蛋黄也都分开了。她改用平底锅加热玉米油,液化灶的火苗开到最小,玉米油有了纹路时,她关了火,将油倒进大菜碗里,筛入低筋面粉,快速“之”字形搅拌,几个小疙瘩划拉几下也散掉了。打发蛋白时,她一直守在厨师机旁。蛋白出现鱼眼一样的泡泡时,加入三分之一的白糖。继续打发,鱼眼泡变成细密的小泡泡时,再加入三分之一的白糖。接着打发,蛋白变成了细腻的膏体,她把碗里剩下的白糖都倒进打蛋盆。厨师机一直开在第九挡。感觉蛋白越来越硬了,她关掉厨师机,提起打蛋棒,棒尖上果然有一个小小的白色三角形。她取下打蛋盆,双手提起,倒过来,歪了头一看,里面的蛋白还是原样待在盆里,打蛋棒离开之后留下的小三角也还是原样立着。这就是硬性发泡状态吗?她的眉头不由自主地拧了起来。
将拌匀的蛋糕液倒入模具后,她双手握住模具的两端,提起来,往下一顿;再提起来,再往下一顿。每一步都严格按照攻略来,她就不信做不出古早蛋糕。
她任由新的蛋糕在烤箱里慢慢长高,自己拿了一只干净的大保鲜袋,将晾架上几乎完整无缺的蛋饼装进去,外面再套一个棕色垃圾袋,打开防盗门,放在门口。这个楼栋的保洁阿姨很负责,如果有人没按规定将生活垃圾扔进一楼的大垃圾桶,而是摆在自家门口,保洁阿姨会顺手提进电梯带下楼。
那天,她准备开门扔蛋饼,发现门口放了一个黑色的垃圾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青菜和两只口罩,中间夹了张字条,“谢谢您的蛋糕,又香又甜,完美解决了我的中餐问题。可惜地库那只流浪狗只能吃我从家里带的饭菜。我还是有点好奇,这么好的蛋糕,您一口没吃就扔掉,是不是太可惜了?这些青菜是我妈种的,口罩是我昨天去药店排队买的,每人限购三只,送两只给您。您放心,我不是坏人。”
这是谁啊?她看了看对面的大门,朱红色的防盗门上仍然贴着印有装修公司名称的塑料膜。这个单元是两梯两户,唯一的邻居家处于装修停工状态。以字条的口吻,不像那个保洁阿姨所留。难道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也不太可能。这段时间除了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大家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她将蛋饼先套个保鲜袋,其实就是希望有人拿去吃掉。而现在,不知是谁拿走了蛋饼。没关系,谁吃了都不浪费,哪怕是喂流浪狗呢。至于青菜和口罩,的确都是她需要的,管它呢,用紫外线消消毒,就不用担心病毒和细菌了。
这天,她又在做蛋糕,厨师机嗡嗡地打发蛋白,门铃响了。她飞快地跑到防盗门前,打开门,没看到人,她之前放在门口的蛋糕也不见了。难道门铃坏了,没人按也会响?她试着按了按防盗门上的按钮,客厅内传来欢快的音乐声,她站在那里,直到音樂声停下来,她又按了一下门铃,音乐再次响起来。是幻听?好像布谷鸟在叫。她关上防盗门,奔到客厅的落地窗前,望着不远处的圭塘河。的确有叫声,的确来自圭塘河方向。她退了几步,颓然倒在黑色的真皮沙发上,闭上双眼。怎么可能出现同样的幻觉?除非自己的脑子有病。她拍了拍涨疼的脑袋,站起来,往厨房去。
这一回的蛋糕,虽然还是塌的,但没有裂缝了。
她的嘴角划过不经意的一抹笑。“会成功的,”她对自己说,“总有一天会成功。”她将装了蛋糕的棕色垃圾袋放在门口,关上门,她站在猫眼前,观察外面的动静。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外面没有任何人出现。她的小腿有点酸麻,便一瘸一拐地进了卧室。
她躺在床上,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男人站在她面前,“起来吧,我带你去看看圭塘河。”
“我认识你吗?”她心中疑惑,这个男人好眼熟,却一时想不起他是谁。
“我叫布谷。”
“布谷?布谷鸟?”她惊讶地问,“你怎么变成人了?”
“我本来就是人,”他似笑非笑地说,“我可以带你飞过圭塘河。”
她应了声好,不知怎么就到了他的背上。他的背像一床羽绒被,柔软、暖和,很轻,却很踏实。抱紧点,他说。她便紧紧搂住他的腰,他背着她,忽地一下钻出了窗户,从他腋下伸出两根长长的桨,明明在空中飞,那两根光溜溜的桨却像在水里划呀划。他带着她越飞越高,一幢又一幢高楼好像珊瑚礁。她记起那次和某人去张家界,坐在高空滑行的缆车里,她一直紧闭双眼。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而某人,始终搂着她的双肩,要她别紧张别害怕。她怎么突然不恐高了?难道是她变了吗?她下意识地想将他的腰再搂紧一点,却摸到一颗凹凸不平的肉痦子,位置、大小、手感都无比熟悉,她忽然喊出了某人的名字,刹那间,她的身子一空,布谷不见了,她却侧躺在电影院的座椅上,好像还是最后一排,与她面对面躺着的,是一堵散发热气的矮墙。不知放的什么电影,巨大的银幕里雪花飞舞,雪花飘到她的身上,一股寒意袭来,她缩了缩身子,想离矮墙更近一点,才发现自己被一只长长的手臂搂得紧紧的,那只手臂越过她的肩头,扣在她的胸前,她有点喘不过气来,用力去推那只手,怎么也推不开。正着急,那堵矮墙突然变成了一个高高胖胖的女人。女人坐起来,朝着那只手飞快地咬了一口,传来一声男人的尖叫,女人瞬间变回矮墙,扣在她胸口的手也凭空消失了。她转过身子,一个模糊却又似曾相识的背影向银幕飞去。不知怎么回事,银幕一黑,整个影院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哦,电影放完了。她站起来,跟着人群往出口走。才走几步,想起还有东西落在座位上,又高一脚低一脚往回跑——她的左脚穿了一只低帮儿皮靴,右脚却是光着的,连袜子都没穿。有个男人站在她的座位旁,看不清他的脸庞,他瓮声瓮气地问:“你看到我的桶了吗?里面装了很多鱼。”她莫名其妙。他又问了一句:“你看到我的桶了吗?里面装了很多鱼。”她没有理他,眨眼之间,矮墙不见了,她的座位也不见了,她站在一片芦苇前,黑色的芦苇长满了红色的手臂,哗啦啦地随风舞动。她不敢去芦苇丛里找她的蓝色外套和她的洗漱包。外套是新买的,洗漱包里装了她最喜欢的珍珠耳环。“谁拿走了我的外套?谁拿走了我的洗漱包?”她绝望地跟随人流的方向,大声呼喊着。影院忽地变空。观众都走了,那个面目模糊的男人也不见了,只有出口处坐着两个戴了帽子的工作人员,他们面前乱七八糟地堆着东西,有各种各样的鞋,有缺了齿的牙套,有转着圈爬来爬去的小宠物。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冲着她怪里怪气地问:“喂,你的鞋子还要不要?”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穿了鞋的左脚带着光溜溜的右脚往前走,径直走到一只低帮儿靴前,她的右脚往里一套,好合脚啊。正要走,一阵狂风吹来,似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她推倒在地,她刚刚穿上的那只鞋一眨眼就不见了。两个工作人员张着没有牙齿的嘴嘎嘎地笑。她吃力地爬起来,在剩下的鞋子里找啊找,没有靴子了,她只好将右脚塞进一只男式皮鞋里。鞋子有点大,她啪嗒啪嗒出了影院,到了一处荒郊,她茫然四顾,发现一块悬空的大石头下面开了一朵蓝色的大牡丹,颜色和她丢失的那件外套一模一样。她不由自主地走过去,原来不是牡丹,是一件外套,她心中狂喜,拎起来一看,没有领子,不是她的外套。她正要扔掉,外套却唰的一声将她吸了进去……
“啊!”她大叫一声,终于从噩梦中逃了出来。
按计划,这天她还要做一个古早蛋糕。打开冰箱冷藏室,她发了好一阵呆。冰箱发出嘀嘀的警示音。
她的脑海里突然窜出一只黑色的影子。她好像忽然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了。她啪的一声关上冷藏室,打开冰箱冷冻室的门,抽出一袋筒子骨,又翻出橱柜里闲置了个把月的高压锅。把筒子骨倒进高压锅,加了两勺冷水,没有放盐,也没有放生姜和大蒜。排气扇呼呼地响着。半小时之后,每一间屋子都弥漫着骨头汤的香味。她握了一把不锈钢漏勺,将骨头和肉都捞进一只打开的背带式保鲜袋里。
她戴了一只深灰色的KN90 口罩,双手也戴了一次性手套,左手拎着那袋热乎乎的筒子骨,右手攥着车钥匙,一个人坐着电梯来到负一楼。车库里只有沉默的车子。她把袋子放在一个立柱下面,袋口完全敞开,香气伴着热气扑向她的脸,她走向自己的车位,就几十米的距离,她走了好几分钟。上了车,她并没有启动车子。她将头靠在椅背上,眼睛注视着前方不远处的那袋筒子骨。
不到十分钟,一只黑色的土狗出现了。它的左后腿是曲着的,虽是一瘸一拐,速度并不慢。它的两只眼睛发出绿莹莹的光,她立刻想到了那天进地库时遇到的黑色影子。
黑狗在那袋筒子骨前面停下来,低下脑袋嗅了嗅,又抬头望了望四周。隐约传来布谷的叫声。她一惊,怎么又出现幻觉了?黑狗好像没听到任何声音,它埋头叼了一根筒子骨,坐在地上,一边咀嚼一边左看右看。它很警惕。地下车库很安静。安静并不代表安全。一只车轮,一根电棒,甚至只是半截木棍就能要了它的狗命。它从哪里来?為什么流浪?为什么要躲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库?为什么能活到现在?是主人抛弃了它还是它抛弃了主人……她苦笑起来,它和她有什么关系?她不是它,它也不是她,为什么要问这么多为什么?真是吃饱了撑的。
那人是谁?他(她)怎么知道她家门口有蛋糕?罢罢罢,黑狗已经离开,她也该回家了。一个人的家,那也是家。这样一想,她比这只黑狗幸福多了。让母亲知道一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天天研究该死的古早蛋糕,天天为怎样圆谎而发愁,这样的日子,她一天都不想过了。承认自己错了,承认母亲当年的预言无比准确,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电梯在一楼停下,一对小情侣手牵手走进来,突然从男孩的裤口袋里传出蟋蟀的叫声,女孩提醒他,“有人给你发信息了。”男孩掏出手机看,女孩盯着电梯显示屏。他们都没戴口罩。专家说了,即便是低风险地区,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狭窄空间,还是建议戴口罩。她下意识地屏住呼吸。他们只到五楼。进了家门,她摘下口罩连着做了好几个深呼吸。家里弥漫着一股腻人的香味,像半生不熟的鸡蛋,又像开败的蔷薇。“再来一次。”她艰难地下着决心,“最后一次。”不管成不成功,这都是她最后一次做古早蛋糕。
往蛋白盆里加泡打粉时,她犹豫了一下。按之前的用量,瓶里的泡打粉大概还能用三四回。反正是最后一次做,干脆都放了。
门铃响了,她跑到玄关处,监控画面显示有人在地下车库按了她的房号。那人戴着口罩,看穿着和身形,像个大学生。“你是谁?”她按下听筒键。“对不起,”那人说,“我是做保洁的,忘了带门禁卡了,麻烦您帮我开一下地库的门。”
“保洁的?什么时候换了人?”她嘀咕着按下开门键。屏幕里响起“嗒”的一声,还有语音提示,“门开了。”
她又走到猫眼前,凑近看了看,外面空无一人。
她回到厨房,将装了蛋糕液的模具送进烤箱,设置好闹钟。腰有点疼,她要去床上睡一会儿。
没想到沾床即睡。闹钟响时,她梦里的古早蛋糕刚好出炉,那种蓬松度,与蛋糕店的毫无区别。她跳下床,奔到烤箱旁。她吓了一跳,右手在左手手背掐了一下,疼。难道梦有延时功能?原本应该是蛋饼的,被梦里那个古早蛋糕的灵魂附了体,所以,她成功了?她翻了翻手机日历,离母亲生日还有好几天。这个蛋糕显然等不到那一天。老天在考验她还是在暗示她?她用力揪了一小块蛋糕,好烫,她还是将它塞进了嘴里。她一边吃一边咝咝地吸着冷气。
“布谷——布谷——”
该死的幻觉又来了。她吐掉嘴里的蛋糕,奔到落地窗前,不远处的圭塘河仍是绿的绿,红的红,黄的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她坐在书桌旁,扯了一张空白便签纸,握着圆珠笔想了半天,终于动了笔,“您好,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古早蛋糕。明天的中餐您不要省给流浪狗,我会给它准备吃的。您以后也不要再给我买东西了。虽然我不知道您是谁,但我相信您不是坏人。我一直把您当成布谷。谢谢您!”
她拿出面包刀,在蛋糕上比画了一下,将揪坏的那一处去掉,又将边沿切整齐。她用手机给蛋糕拍了几张照片。是纪念,也是提醒。她得说到做到。
第二天,她开门扔垃圾,发现蛋糕不见了。
第三天,她没听到布谷声。
她好像再没听到布谷声……
母亲生日那天,她推着行李箱准备回老家。打开防盗门,发现门口有一个大大的纸袋子,袋子并未封口,里面是一个古早蛋糕。有点像梦里那个,又有点像某人做的。她几乎没有犹豫,将纸盒拎到门框旁,将行李箱拖到电梯口,想了想,又回去将那个纸袋子往门口移了移。那个位置,是她平时放蛋糕的地方。
她启动车子,快到地下车库出口时,她又发现了那团黑色的影子。这一次,影子没动。她松了油门,踩了踩刹车。
是那只黑狗,它好像冲着她的车子摇了摇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