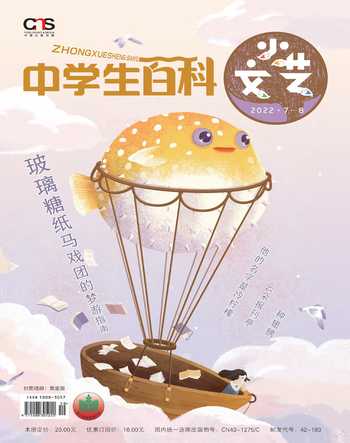太阳宫
2022-05-30顾一灯
顾一灯

这是我头一回没和父母一起过年。
拉锯战般的疫情打乱了惯常的生活节奏。难得有稍长些的假期,也逃不了被困在北京的命运。
起初也没觉得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放假前一周赶上冬奥会,居家办公,头几天甚至乐在其中,觉得免去了来回两小时的通勤时间,多了空闲用来读书和锻炼,也挺好。可后来内心却被一种焦虑、烦躁的东西裹挟,明明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明明还有许多待写的稿子,却什么都看不进去,什么都写不出来。想出去转转的念头在脑子里盘旋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落回原地——我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也无处可去。
这时很好的朋友W问我,要不要和她一起住。我马上答应,收拾了一个书包、两只手提袋的物品,从租住的小房间跑出来,雀跃地跳上地铁10号线,往太阳宫去。
W是我的本科同学,祖籍河北,爸妈念书好,从县城考进北京名校,之后便留了下来,因此她的身份证号顺理成章变成了110开头。她爸妈都已退休,家里老人年纪大,身体一般,每年大半时间都得回老家照顾。对W来说,独自过年不是新鲜事,这几年都是如此——单位倒没不让她回老家,但她怕回去后又撞见一波疫情,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也没了。
在这个除夕夜,我们便因此生发出了相依为命的味道。
我们凭借记忆中的仪式感,复刻以前被父母包办的环节:贴福字,粘对联,搞卫生,买鲜花,做一桌丰盛的年夜饭,以及包三鲜馅的饺子。当然,还多了年轻人的部分:打开音响播放新潮的音乐,在白墙上投屏NBA记者的篮球资讯直播,模仿老年人打听工资和男友的喋喋不休。起初气氛是欢乐的,我们闹腾到要把天花板掀翻。直到吃完饭刷完碗瘫在沙发上,打开手机给父母发消息,收到回复后,我们竟不约而同地掉了眼泪。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哽咽着说这一年实在太辛苦了,末了没忍住,哭得一塌糊涂。
这一刻才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渴望陪伴,渴望爱,渴望最简单的温暖。
中学时最常有的感受,无非世界之大,时间之多,恨不得赶紧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荡,手上有大把年华可以挥霍。当时对于过年的态度很漠然,颇为特立独行地觉得所有节日都没什么好过的。远离了物资匮乏的年代,对年夜饭、新衣服没有任何兴趣,甚至讨厌不得不熬夜,听见吵闹的鞭炮声会堵住耳朵。我还养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在本应休息的节日学习和工作,效率格外高,远胜平日。
可工作之后,却滋生出越来越强烈的急迫感,就像那个很俗套的比喻,时间像一把流沙一样从指缝间溜走了,越用力抓,越是一粒沙都抓不住。与W不同,我家不在北京,父母尚未退休,我的薪水距离买房接他们来住仍遥遥无期。工作很忙,忙到没空休年假,算来一年能回去的时间甚至不会超过十天。怎么算怎么觉得日子短,又如何能克制焦躁的情绪呢。
于是在远离家乡的许多个年头后开始思乡。与风景无关,与记忆无关,只是思念在故乡的人。再快捷的互联网,也没法抹平地理的距离。就像此刻,我们打着字,说着祝福的话,仿佛彼此近在咫尺,心里却更加难过,悲伤弥漫,以至于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

痛快地哭过一场后,心里渐渐归于平静。先是听着那名NBA记者提及篮网惜败勇士的赛后采访,欧文说虽然我们面临着严重的伤病潮,每个人的负担都很重,但我们没有时间脆弱。我和W以此自勉,这样好的年纪,不应该将生命耗费在自我怜惜上,还是要学会坚强,还是要一步步往前走。
沉默了一会儿,我们岔开话题,提起上一次看到对方哭的时候,大概是她被校内精神有问题的同学吓到,而我被双学位折磨得疲惫不堪。再后来我们吐槽春晚,又趴在落地窗前,数对面的楼有几家亮着灯,猜测那些灯火或黑暗背后,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体育是有意义的,不仅在于某一刻的热血澎湃,更在于目睹他们更戏剧化的经历,见证与我的性格有相似弱点的人摸爬滚打,最后战胜了它,便有了爬起来继续往前冲的信心;想象是有意义的,不仅因为八卦是人类的天性,还因为它使我们得以在残酷的现实之外,与某种格外奢侈的浪漫主义亲密地相拥。
那晚十一点多,W的表弟打电话来拜年。他出身于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在北京一所很好的中学读高三。我曾见过他一面,个头很高,笑容自信,是小太阳般能照亮别人的存在。
W开了免提,我们与他聊到未来。他说希望考上大学后爸妈都去住新买的大房子,让他自己在现在的家里自由自在地独个儿生活,那该多爽。音色略显稚嫩,语调有独属于少年人的、对八字还没一撇的事都能欢天喜地的特质。
我和W听了以后面面相觑,又不好用“少年不識愁滋味”这样的话扫他的兴。W将一本手头的杂志卷了卷,做话筒状递给我,说你来评价评价。“年轻真好。”我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我想他一定觉得这个姐姐磨磨叨叨,更像住在隔壁的阿嫂。
编辑/胡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