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头里的江河
2022-05-30GULU
GULU

第一部关于中国工人诗歌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
看过《我的诗篇》——第一部关于中国工人诗歌的纪录电影——打工诗人创作的诗与他们创作诗的那双手,令人难忘,“我觉得是女人就应该爱上这只手”(韩东《工人的手》),的确会爱上,不是因为它们“结实”,而是因为这双结实的手写出了充满生命力的炽热诗篇。
有煤沫子深染的纹理,有洗不净的黑,矿工张克良用粗糙的手握住一只粗糙的笔,写出一位工友粗糙的命运:“黑暗的巨手忽地一翻,顶棚上就落下/一大堆煤,将他紧紧拥抱”(《煤火》);羽绒服厂充绒工吉克阿优的手,填着鸭毛的同时,也掂量出生命的分量:“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制衣厂女工邬霞握住“集聚我所有的手温”的电熨斗,熨开裙子的吊带、腰身、皱褶,当风吹起某个姑娘的裙摆,就是风在诵读邬霞的《吊带裙》;巷道爆破工陈年喜常年在引爆炸药,开山打眼,他的手轰开山体的同时也轰出坚硬、炫黑的诗行:“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炸裂志》)……


彝族打工诗人吉克阿优
如果为打工诗人看手相,会看出他们共同的命运——“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陈年喜的诗句让我想起一位打工诗人,他叫王立生。立生,本该是站立着写作的一介书生,像海明威一样,可站着的他不是在码字,而是在码砖,他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
多年前,王立生以“水娃儿”为笔名,向《生活报》星期天版的《青春号列车》投稿。那时我正在策划一部反映都市自由撰稿人生活的纪录片,编辑李涛于是推荐了他,说他是一名热爱写作的农民工。

关于平凡世界与非凡诗意的故事
踏上想象中的列车,努力靠近都市文明,了解了這位乡村少年的经历后,我很想见一见他,于是便按照信封上留下的地址去找。找了很久,终于找到原无线电十六厂旧址,可那里已夷为平地。站在残砖断瓦上,犹如身处都市和乡村的交界地,王立生在给编辑的信中写下的激越心语,随风曳曳而来:
“……我很穷,全部财富只有5元6角2分,还有一沓稿纸和一支英雄牌钢笔,但我有一双手,一双农民儿子的手,苦活、累活、脏活我都不在乎,忙里偷闲,我就握紧‘英雄笔写呀写,期待着汗水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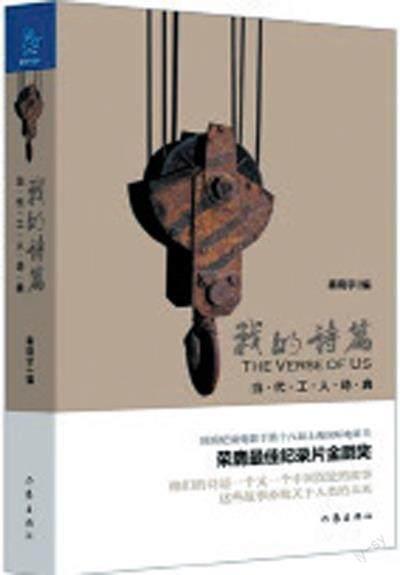
《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

诗歌来自于地下800 米深处
为了能找到水娃儿,我在报纸上登出“寻找王立生”的短消息。一直在等也许返乡了的水娃儿,再次出现在都市的视野里,可是直到采访结束,也没能等来。每当我经过一处忙乱的工地,每当我读到一首不起眼的小诗,都仿佛看到年轻的水娃儿正在挥汗劳作,他像一块砖那么普通,但所有的高楼广厦,所有的华采文章,不是都起始于这样一块砖、一双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