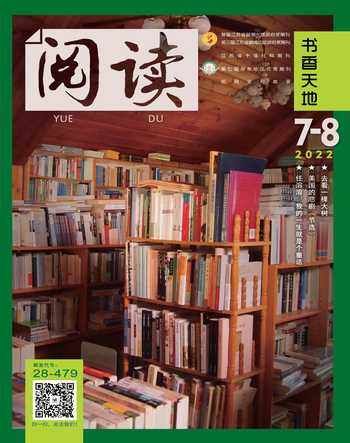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2022-05-30许燕吉
许燕吉
作者在八十岁高龄写下了《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但她和父亲许地山在一起的时光只有八年。她说:“1941年8月4日,我的父亲许地山去世。如果上帝允许,我希望时间永远留在前一天。”父亲的慈祥永远留在一个八岁小女孩的心底。
香港的家
爸爸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
一块儿去的有七人,爸爸、妈妈、哥哥、我,袁妈和刘妈,还有外祖父的那位姨太太。她被送到周家时,我母亲才一岁多,我们称她婆婆。袁妈和刘妈两人在我家是舒畅的,她们照顾我们兄妹也好几年了,互相都舍不得,所以她们毅然离开了京郊的亲人,随我们南下了。
到香港时,哥哥四岁,我两岁了。袁妈那时48岁,管做饭;刘妈36岁,管卫生。婆婆那时56岁了,她没有任务,有时绣花。我家客厅的大靠垫上,绣的都是我爸爸读书或教书学校的校徽,全部出自婆婆之手,好些还绣出立体的花纹,真不愧为湘绣的传人。
妈妈到香港后,没有到社会上去任职,除了协助并参加爸爸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外,就是育儿和理财治家。她是数学系毕业的,理财治家自然是她的强项,也是爸爸的弱项。
妈妈育儿有一套科学方法:我们放学回家,喝一杯水就得坐在书桌前。我和哥哥的书桌是对着的,妈妈坐在中间就像排球裁判那样,监督着我们二人做作业。学校留的作业不是很多,做完了就开始上妈妈教的中文课。因为我们上的都是英制学校,中文课相对较少。读书、背诵和作文是主要内容。作文写好后妈妈修改,改好了再抄一遍,我们还得把改过的作文背下来。背错一字得挨一下手心板子。哥哥聪明,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认错,所以他挨打很少。而我则死犟不服,气得妈妈连打带拧。打痛了,我就张嘴大哭大号。我知道妈妈怕邻居嫌吵,最恨我号叫,我偏偏就号。我有两颗乳齿就是妈妈拿毛巾堵我嘴给塞掉的。
爸爸不赞成妈妈的教育方式,有一天早上他们二人在客厅为此吵了一架,妈妈还打了爸爸一下。爸爸生气地上班走了,我吓得噤若寒蝉。妈妈哭着说都是为了我。直到中午在饭桌上,我看他们又和好了,我压抑了一上午的心才放松下来。
妈妈很少有吻我、抱我的亲昵举动,也几乎没和我们玩过。说实在的,我挺怕她的,我们家里是严母、慈父。
天崩:爸爸死了
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那是1941年8月4日下午2点15分。
暑假期间,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安心写他的《道教史》。这次,他回来已几天了。回来的那晚,他冲了个冷水澡,睡觉又受了风,感冒发烧,躺了一天,已经退烧了,还在家里休养着。这天,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袁妈、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袁妈说:“您别看报,还是睡午觉吧。”爸爸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他总是爱说笑话。之后他就回卧室去了。我们饭还没吃完,妈妈就回来了,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忽听到她大喊一声,叫着:“快来人!怎么啦!”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只見爸爸面色发紫,躺在床上没有反应。也不知谁说了句“快请大夫”,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我在后面紧跟着。
到了胡惠德医院,哥哥就大喊:“我爸爸快死了,你们快去呀!”护士长原来都很熟悉的,慌慌张张拿了药械跟我们跑到家里。那天中午院里没有医生,护士没有权力给人治病。她一手托着爸爸的上臂,一手拿着注射器,头颈转过来,对身旁的我妈妈连声说:“你负责啊!你负责啊!”妈妈攥手在胸前点着头,也连说:“我负责,我负责。”针打下去,爸爸长哼了一声,就像睡熟一样了。
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爸爸死了呀!爸爸死了呀!”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呢!”事后,妈妈回忆说,爸爸晴天霹雳似的一死,她脑中一片空白,听见哥哥哭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顿时清醒镇定。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晰,终生不忘。
第二天上午,灵堂已布置好了。宋庆龄前一天就送来的大花圈放在中间,两旁都是花圈。第三天中午盛殓,是西式棺木,板子很薄。灵堂里站满了人,我扶着棺材沿,我知道以后就再看不见爸爸了,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们盖上棺材板,拧上螺丝。随后,棺材就被抬去了香港大学的大礼堂。
大礼堂里面、外面挂了许多挽联,一副挨着一副。我转着脖子四面一看,只看懂也只记住了两副,一副是“赤子之心”,一副是“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问先生”。
爸爸下葬后,开过追悼会,丧事就算办完了。妈妈出去工作了,顶起了天。朋友们叹为观止,说:“哎呀,许太太真了不起!”四个月后,香港沦陷了。
记忆中的爸爸
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清算我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马上“结业”,我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劣迹”,就是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因为他喜欢孩子,而且见孩子都喜欢。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的确,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
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伴,跑呀,蹦呀,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 “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他在释放“小俘虏”前,必须尽情亲吻一番。他留着三撇胡须,挺扎的,凡被亲的,都两手捂着腮,以做抵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大人们自然有正经事要谈,但爸爸一定会提前抽身出来,和孩子们“疯”上一阵。
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的。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罢“哐哐”,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去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恍然大悟,是爸爸的拇指戏演过。
爸爸还真有艺术的天赋,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博得全场叫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会吹笙,还会唱闽南戏。爸爸也写过许多歌词,有时候也自己谱曲。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我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纪律》,歌词是:“在上学以前,床铺要叠起,在讲堂内里,文具要整齐,所做不苟且,件件合条理,那就叫做有纪律。如果事事都能如此,将来服务才有效率,可爱同学们大家齐努力,一切行为守纪律。”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孩子们写的。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我记得他教我认北斗星。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他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子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家里也常有人来找爸爸,我们管这些人叫“求帮的”。爸爸妈妈总是尽力满足他们。记得只有一位,爸爸没帮助他。那个人来了就对爸爸说英语。爸爸很生氣,说中国人和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英语,请他走。那人在院子里还冲我们楼上大声又说又喊,还是用的英语。爸爸从窗子里训了他几句,就走开了。爸爸说,他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的人,也就是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有位台湾青年要到香港邮局工作,而邮局要求有人担保,其实爸爸过去并不认识他,也爽快地给他作了保。这人就是后来台湾政界的“大佬”谢东闵,20世纪80年代,他还托人带了张照片送给我妈妈,向我们问好。
爸爸和他学生也很亲近,常有学生到家里来,每年还会在我家举办一两次“游乐会”。头几天全家就忙起来,制作游戏道具,准备奖品,布置会场,还要做些点心之类,学生们来都玩得很开心。每学年,他们要公演文艺节目,也到我家来排练,爸爸还给他们当导演。
一般说,爸爸总是面带笑容的,但他也会发脾气,挺凶,打过哥哥一次,因为哥哥弄坏了他的宝贝台湾兰花,打完还问哥哥痛不痛。打过我四次。有一次是迈克上楼来玩,我无意中用棒子打了迈克的脑袋,迈克大哭。爸爸闻声过来打了我几下,我觉得挺冤的,就记住了。另三次挨打大概是罪有应得,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但有一次打得重,用鸡毛掸子在我胳膊上打出了一道紫棱。妈妈拉着我去,撸起袖子向爸爸“问罪”。爸爸冲我做了个怪相以表歉意,把我逗笑了。
爸爸死时,我只有八岁多,又愚昧不开,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爸爸的乐观豁达,仅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润色了我的生活,受用未尽。
(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