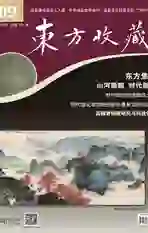在石窟壁画中实证的中国传统绘画面貌
2022-05-30杨艳宏
摘要:石窟壁画是我国古代珍贵的艺术瑰宝,一方面记录着历代政治经济大环境下民众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绘画艺术方面的面貌。其中,榆林窟第 3 窟壁画面貌就代表着发展至西夏时期壁画的较高水平,尤其是文殊变壁画中大面积的背景山水图,不仅印证了西夏美术多元化的风格特征,同时从线条的表现形式到亭台楼阁、树石、水流等画面具体元素的刻画,均反映了宋代绘画对西夏绘画所产生的较大影响,实证了两宋时期的中国传统绘画面貌。
关键词:榆林窟;文殊变;绘画面貌;宋代壁画
我国古代绘画历史的面貌和特征大部分被直接或者间接遗存的理论作品所记载,遗存到今天的早期绘画寥若晨星。然而,石窟造像和壁画以其媒介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构成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三大门类,是古代美术的主流。虽然最早以人物画形式出现,花鸟画的出现则更加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内容面貌和观赏体验,但山水画后来居上,从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到构成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内容,更好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境界,在山水画中出现的山水树石的面貌,零星的人物、草亭、楼阁等点缀也都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客观记录和主观感情的再创造。
壁画与中国传统绘画分别于不同的媒介之上进行描绘,佛教壁画是佛教思想以不同于传统绘画的媒介但以传统绘画的形式出现的一种绘画面貌,主题内容为反映佛教经变故事等,在绘画手法、绘画工具上均规于中国传统绘画的主流。佛教自魏晋传入中国,随着各朝代的更迭,历经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演变,佛教石窟和壁画也随之不断发展、修整和演变,不仅体现了历代佛教思想内容的新发展、新样式,也平行体现了各时代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和面貌。
榆林窟位于安西县城西南边缘的山谷里,经历河水的冲刷和历史的掩埋,窟内壁画依然色彩明艳鲜亮、庄严肃穆。榆林窟第 3 窟位于榆林河东岸下层,考证为西夏瓜州晚期壁画,总面积达到 4000 多平方米,壁画精妙绝伦,体现了西夏瓜州晚期多民族融合后的丰富文化面貌。壁画中的山水画作为经变故事绘画的背景尤其精美,是壁画中鲜杨艳宏 / 文(宁夏大学,宁夏 银川 750021)摘要:石窟壁画是我国古代珍贵的艺术瑰宝,一方面记录着历代政治经济大环境下民众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绘画艺术方面的面貌。其中,榆林窟第 3 窟壁画面貌就代表着发展至西夏时期壁画的较高水平,尤其是文殊变壁画中大面积的背景山水图,不仅印证了西夏美术多元化的风格特征,同时从线条的表现形式到亭台楼阁、树石、水流等画面具体元素的刻画,均反映了宋代绘画对西夏绘画所产生的较大影响,实证了两宋时期的中国传统绘画面貌。关键词:榆林窟;文殊变;绘画面貌;宋代壁画见的大面积的山水画面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西夏与宋有着共同的时空交集,政治交往密集,文化上也相互交流,并以宋对西夏的文化输出为主。且在宋时期,河西走廊途经西夏境地,西夏就成了宋人远走印度的必经之路,河西走廊上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碰撞对各民族的文化宗教等方面无形中进行了滋养和丰富,加上西夏为了振兴和繁荣自身,主动对宋经济发展和繁荣文化的学习,使得西夏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呈现出宋的发展痕迹。绘画方面的风格和手法:一是发扬自身的独特创造,同时也呈现出对宋人绘画学习的痕迹。两宋的山水面貌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而又略有差别,南宋山水在继承北宋山水大的面貌上发扬了画面空灵之感,其中尤其以构图取胜。二是一贯沿袭的理性思维,“宋人善画,要以一‘理字为主。是殆受理学影响之暗示。惟其讲理,故尚真;惟其尚真,故重活;而气韵生动,机趣活泼之说,遂视为图画之玉律,卒以形成宋代讲神趣而仍不失物理之画风。”[1] 最后,南宋山水画在承袭北宋自魏晋以来山水画写实风格、完全崇尚自然再现造化的理念之外,衍生出诗意化主题的升华,以本心造万物,这也是其时代化的提炼。榆林窟文殊变背景山水图体现了南北宋山水过渡的痕迹。崇山峻岭高耸,中景一片飘渺虚无之境,掩映之下近景的楼台建筑分外渺小,更不用说蜿蜒曲折的小路和两旁隐约的矮树。在精妙繁丽的各色楼阁传递梵音袅袅的宗教声音之外,不乏茅屋乡舍映带于茂林修竹之中,山雾弥漫,乡野之景与理想国之空灵境界融合于一体,让观者在现实与理想的虚幻境界里穿梭游移。
一、以线造型的整體面貌
线条是中国画造型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历代画学画论强调和品评的重要一环。榆林窟第 3 窟背景山水图整体大面积以线造型的特征十分突出,只有部分树丛以石绿色染成,其余画面内容线条刻画的面貌显露无疑。宋代文人气息浓厚,文人画面在传达的境界上力求“简古”“淡泊”,这种审美境界可以通过朴素的色彩构成在画面中使用传达出来,这也是宋代文人绘画的审美态度。《宣和画谱》记载:“绘事之求形似,舍丹青朱黄铅粉则失之,是岂知画之贵乎有笔,不在夫丹青朱黄铅粉之工也。故有以淡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者,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制作”[2],尤其在北宋后期,多将对朴素色彩的应用归结为词人墨卿之所作,在结论上与文人画进行了紧密的联系。再反观榆林窟第 3 窟文殊变背景山水图中的用色,除去精丽严整的楼阁线条有借助工具绘制而成的痕迹外,线条造型的手法体现了画工成熟的技巧和手法,使得整个画面饱含文人画的气息。
二、画面具体元素的刻画
(一)山石的皴法
系无旁出,榆林窟第 3 窟文殊变山石的皴法显示出了对以披麻皴为基础皴法的发挥,兼带有斧劈皴的手法痕迹,线条以长线条为主,有以南宋李唐摒弃北宋以来反复皴擦描摹的手法,而以果断的阔笔一挥而就,简率干练、敏捷无滞、豪放洒脱之感毕现的风格,显示出作者晚年经历、生活的现实情境决定的内在性情,将描绘现实山水的笔墨程式加以个性化处理,独具风格趣味。这与南宋特定时期皴法的面貌有相通之处,至南宋,地理的迁移使得画家也经历了皴法上的沟通和交汇,例如李唐、刘松年等画家的绘画中出现了披麻皴、斧劈皴和卷云皴并用的痕迹。
(二)倒垂的枯树
北宋李成创立了树木“蟹爪”造型,枝干斜出并向下展开,如同螃蟹的爪子,用墨也较为浓重。后郭熙沿用了这种手法,我们可在他的《早春图》中看到这种画法的应用,至南宋,“拖枝马远”形成这一手法的创新发展。南宋马远出生于绘画世家,为“南宋四家”之一,以其独特的画面构图影响世人深远,以山水独步南宋画坛,不仅在构图上独树一帜,在皴法和具体事物的表现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思考,“拖枝”画法即是其独特的创造,他在李成向下展开的“蟹爪”基礎上撇去高度严谨写实的面貌,长短线加上点的笔法,使树木更加鲜活灵动,用墨也较前者更为轻快,巧夺天工,如他的《梅石溪凫》,图中,陡峭的山峰侧立于画面一角,生长于山峰上的树枝倒垂,为畅游于水中的野凫营造出一片静谧安闲的天地,野凫游动打闹的动感和低垂不动的树枝山峰形成动静的强烈对比。另有《眉间俊语图》,老梅树盘桓曲折,枝头倒垂,似乎有意将画面的中心指向相对而坐的老人,老梅因为两位老者的对话充满了温情的关照之感,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了文人情怀,而落款“马远”则暗示了马远率性的在我创造性表达,我们在榆林窟第 3 窟文殊变中看到了“拖枝”的面貌,这种样貌出现得很少,似乎与宋代马远独特稀有的审美情趣相呼应,相比勃勃生机、环绕亭台楼阁向上而生的绿植,那些倒垂的几株枯树则似乎象征着现实世界的残酷寒凉,营造出一番现实与理想盘桓交错之境。
(三)精密的界画元素
界画主要再现中国传统建筑,界画“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是一种对古代建筑形象具体的书写记录和审美表现,在中国传统绘画历史中源远流长。《史记》中早有记录,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分别模仿建造六国建筑样式作于咸阳北版之上,可见当时已有对于建筑样式的绘制,功能侧重于对建筑外形和内部结构样式的观察与记录。到魏晋时期,对于界画的描绘在画论中初见端倪,但将其归类于绘画内容的边缘,因其时空的固定性,仅仅将绘制界画与人物鞍马等类作绘画难易的比较;界画的痕迹在作品中相对很少,但也达到了与山水画同样的可居可游的绘画要求和境界。隋唐时期界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山水画方面,创造性发展了以大小李将军为代表的青绿山水和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官方画家在宫观山水方面也做出了较大的突破,这与宫廷上层丰富的物质生活决定的精神要求有着紧密的关系。同时,画面中出现的界画元素一般呼应了中国传统儒道精神,以从侧面隐晦传达出仙境,逃遁的画面氛围和作者主观意趣,最直接地迎合了贵族对于奢华生活的歌颂炫耀趣味。擅长绘画界画的画家也涌现出来,如董伯仁、展子虔等。董伯仁是一位多才多艺全面的画家,唐代《画拾遗录》中记载他“楼台人物,旷绝古今”,著有《周明帝畋游图》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唐代《九成避暑图》,绘有亭台楼阁,设色厚重端庄,雕梁画栋于群山环抱之间,仙气逼人。唐懿德太子墓壁画绘有的建筑样式反映和代表了当时界画的水平,在之前水平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精密的刻画。宋代是我国古代绘画发展的高峰,政治经济繁荣,文化风尚空前融合,艺术方面体现了个人主观情感的创造性表达,界画也取得了新的发展和成就,从宋徽宗的《瑞鹤图》就可窥见一斑,宣德门的灰瓦飞檐刻画得精妙非常,雕镂的装饰也尽现眼前,斗拱雕栏等描绘精微、庄严神圣。再如郭忠恕的《明皇避暑宫图》,用笔精细、繁丽工整、层次分明,疏密对比强烈,体现了宋代界画的较高成就。同时界画的表现范围扩展到了市井巷陌,表现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惟妙惟肖,这是宋代界画新的延伸内容。榆林窟壁画中的仙山楼阁与宋代界画的面貌是一致的,一般不进行设色,个别之处也是以墨色来填充,线条遒劲精丽、细节顿显无疑,一如自北宋以来山水图中建筑的精细写实。这里显示了南北宋交融过渡的山水中建筑物的描绘风格:一是发展至南宋李唐的笔下,建筑物作为画中的构成元素,不再如北宋时期那样精准刻画,不借助工具,只徒手绘成,形制也不像北宋那般复杂,南宋夏圭也是如此,同时也有对北宋精致院体一路的继承,如刘松年、马远等。另外,蝴蝶门是南宋独特的新创造,在榆林窟第 3 窟普贤变中多处有蝴蝶式对称敞开或关闭的门,更显示了这一壁画对时代传统绘画的直接映照。再者,格子窗也是南宋绘画中常出现的建筑元素,这是政治朝代更迭原因造成的向南迁徙、气候不同导致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变化,格子窗更便于通风,解暑也防寒,是南宋广为流行的建筑样式。刘松年画风精雅细腻、独具风格,其《四景山水图册》中就多次表现了格子窗的形象,作为世俗生活的映照,这样的形象在榆林窟第 3 窟文殊变壁画山水中也是可见的形象。
(四)独具装饰趣味的水纹
苏轼在谈及画水时曾记述:“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洼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3] 早期的水的绘画面貌大抵如苏轼所言,以中锋规整行笔,水的面貌趋于静止的状态。唐代孙位冲出传统藩篱,刻画出具有动势的水纹,北宋也贯穿以上的手法,到南宋李唐,水的表现手法又启用了新的丰富手法,“水不用鱼鳞纹,有盘涡动荡之势,观者神惊目眩,此其妙也” [4],李唐跳脱出前人仅用细线勾勒鱼鳞式水纹的模式,灵活应用多种形似生动描绘水流的动态,分别在如《万壑松风图》和《虎溪三笑图》中展露出不同的笔法面貌,线条粗细、长短、疏密排布均呈现丰富的变化,服务于画家想要呈现的水流急缓动态的表达。马远对水的刻画有专门的一幅作品《水图》,也显示了作者对水的不同动态的描绘手法的把握。榆林窟第 3 窟文殊变壁画山水图中水的布局采用魏晋时期曲水流觞形式的布局与北宋时流行起来的营造一方池水的形式相结合的形制,水纹的排布在近处采用易圆以方的平行排布形式,投射出一定的装饰趣味。联系南宋传统绘画,这种呈现装饰性趣味的线条的应用也较为常见,如南宋佚名所作《搜山图》长卷,各色人物的线条、场景元素的刻画等均采用了方折的线条形式,榆林窟水纹的刻画将这一传统绘画中的线条形式应用得自然流畅,形成水势涌动的动感。
三、结语
佛教的传入,不仅在思想上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还对中国传统绘画内容以及形式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绘画的媒介由宗庙发展到佛教石窟,从张僧繇到吴道子均有在宗庙祠堂等创作的历史记述。而由于佛教信众的需要促成了历代佛教壁画的兴盛,并紧跟各时代传统绘画的新风不断更新进步,壁画形式将绘画与观众的距离空前拉近,壁画的内容与形式也得到同时代观众的审视和检验,获得长足的进步,佛教壁画就此成为除了实物遗存之外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另一重要实证。学术上也不乏通过研究某一时期壁画的内容形式来推敲这一时期绘画面貌的大致轮廓的先例,佛教经变故事绘画使得佛教绘画中出现了世俗的山水树石等元素,使得壁画内容与传统绘画有了共同的描绘交集,塑造的可视可感的形象更加感人,榆林窟第 3 窟文殊变壁画背景山水图就是深受宋代影响的西夏山水画发展变化的实证性图像。
参考文献:
[1][ 南宋 ] 洪迈 . 容斋随笔 [M]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
[2] 卢辅圣 . 中国书画全书(二)[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400.
[3][ 宋 ] 苏轼著,王其和校注 . 东坡画论 [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19.
[4]余安澜 .南宋院画录 [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杨艳宏(1990—),女,汉族,山西朔州人。宁夏大学美术学院 2020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画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