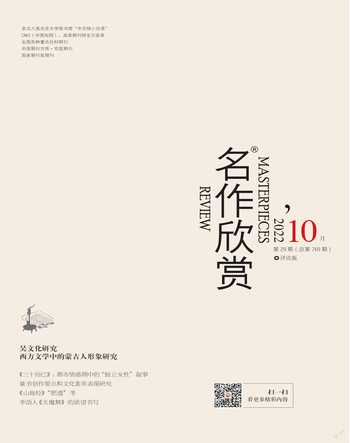“哥特—罗曼史”与“哥特—反罗曼史”
2022-05-30周爱华
关键词:哥特 罗曼史 《 简·爱》 《 异香》
哥特小说诞生于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故事情节中带有暴力或悬疑因素,场景多设置在古堡、废墟等僻静、阴森的场所,追求惊悚的美学效果。哥特类型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而创造着新的表现形式。“只要文明与欲望的对立仍然存在,只要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在命名着它的‘异者,只要社会冲突的危机没有得到化解,哥特小说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一、哥特式情感故事
《异香》不同于一般的都市或乡村爱情小说,有意把故事场景设置在深山老林,与男女主人公情感发展历程相伴随,诡谲的香气、神秘老妪、动物干尸、木乃伊等哥特式元素制造出悬疑、惊险、恐惧的美学效果。《简·爱》罗曼蒂克情调中交织着鬼影、怪笑、夜半失火、超自然现象等哥特情节,使浪漫的爱情故事变得复杂与意蕴丰厚,具有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性别意识,也成功地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女性哥特小说作家更多受到了性别身份的束缚,小说内容以女性的经历为主,聚焦于女性的恐惧与焦虑,并不追求感官刺激,而是靠悬念取胜。”b情感故事中融入哥特式风格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初遇场景设置。《简·爱》孤身的简与黑披风的阴鸷男人相遇于昏暗、僻静的树林。受惊的马匹、大狗,以及简想象出的鬼怪情节等,带给读者奇幻体验。《异香》单身男女相遇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虚惊一场后,为驱除孤独与恐惧,结伴而行。阴森、空旷的自然与孤独的个体,是情感滋生的温床,给读者创设了“罗曼史”阅读期待。
第二,与情感发展相伴随的诡异事件。《简·爱》发生在古宅桑菲尔德庄园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疯女人半夜火烧罗彻斯特,疯女人咬伤探视者,疯女人半夜潜入简房间,撕毁婚纱。疯女人的存在和举动制造出悬念,营造恐怖氛围。疯女人也成为主角婚姻的阻碍。吉尔伯特和格巴认为,疯女人伯莎是简的自我的另一面,她代替簡实现了潜在的欲望,发泄了对罗彻斯特中心位置的愤怒与反抗。《异香》深山中漂浮的异香,孤身老妪,满屋子动物干尸,卫瑜意外发现躺床上的老人是具木乃伊,她惊吓过度,痛哭失声,把恐怖气氛推向高潮。两个闯入者面对种种诡异现象,战战兢兢,相互取暖。“罗曼史”小说往往借助这种不寻常时刻,让相依为命的男女打破防线,敞开心扉,接纳对方。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离婚女人白流苏千方百计抓住花花公子范柳原结婚,战争的残酷、荒凉让这对精刮的男女生出一丝真情,成全了白流苏。而《异香》两人关系没有出现转机,仅仅是人性的软弱、孤独不足以摧毁强大的理性城堡。两人无力摆脱消费主义时代精神的钳制,孤独至死,找不到救赎的可能。
第三,富有神秘色彩的男主人公。两部小说都采用女性视角,通过女主眼光审视与揣测男主,男主的身世经历隐讳,性情深沉复杂,行为乖张,颇具神秘色彩。《简·爱》中罗彻斯特的婚姻史、在欧洲游荡的经历,以及反复无常的性格,给简也给读者留下悬念。《异香》中张楚河的身份通篇未交代,女主卫瑜通过其穿着打扮揣测其有钱人身份。“在消费社会中,身体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物质形态,而变成了社会要素和交换符号。”这里,男主的身体符号,象征着身份、社会地位与世俗认可的成功。他的言行呈现诸多让人费解的矛盾,他对非人类动物满怀爱意;与之对比,他对同类冷漠、无情,吝啬与相依相伴的女主分享食物,舍不得付给卖苦力的老妪几块钱。他为何独自往深山探险?为何不敢走进婚姻?有过什么创伤经历?叙述者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留下谜团。
二、“罗曼史”与反“罗曼史”
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严格遵行身份等级制,身份地位、财富的悬殊是阻碍家庭女教师与乡绅贵族不同阶层通婚的现实障碍。《简·爱》男女双方超越世俗陈规,追求情趣、心灵的契合,罗彻斯特把简看成是自己的“共鸣体”与“更好的自我”。简把罗彻斯特视为自我的另一半。简的信仰与自我道德律令使她无法接受在罗彻斯特已婚的情况下与他结合。简追求人格平等与经济独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单身女性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跨越几乎不可能,这段感情似乎走入绝境。小说采用违背现实主义的策略,安排简意外继承叔叔的遗产,又让疯女人跳楼身亡,罗彻斯特残疾,婚姻的障碍扫除了。简在罗彻斯特面前不再自卑,反过来她成了男性的救赎者。小说中女性意识大获全胜。超自然现象在两人的结合中起了推动作用。简在难以抗拒表哥以上帝赋予的责任的名义求婚时,荒野中传来罗彻斯特的呼声,给予她勇气拒绝表哥。小说表明,真爱至上,超越时空限制,显示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异香》采用故事中套故事的套层结构,外在叙述层采用全知视角,洞悉女主卫瑜的心理,女主盘算着捕获眼前这个貌似有钱的男人。全知视角不知转换成女主视角,卫瑜的“凝视”目光,看透男方张楚河的精刮算计。可以看出,追逐婚姻的较量中,两人棋逢对手,彼此揣测对方的身份与身家,类似当下盛行的按双方条件匹配的相亲。看重金钱财富,不考虑精神层面的志趣、爱好等,恰恰是反“罗曼史”。小说没有用浪漫主义手法重写灰姑娘的故事,呈现了现实冰冷、残酷的一面,正如女主反省自己“恨嫁”的原因,“她又暗想自己,遇见一个萍水相逢的男人都敢给自己这么多幻想……就因为平素里,现实严丝合缝得连只苍蝇落脚的地都没有?”现代都市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两极分化严重,阶层固化。高房价阻断了外来务工女性落户扎根的梦想,嫁个有钱人便成为她们逆袭的有效途径。小说直面当下女性生存困境,没有粉饰现实,打破了鲁迅指出的“瞒和骗”的文学。
戴锦华认为,《简·爱》是关于“情欲与禁恋的张力”,“因禁恋故事而张扬饱满的情欲想象或书写”。罗彻斯特成为公认的“拜伦式的英雄”,“具有深沉而强烈的情感潜能”。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而“道德观念相对保守”,倡导性节制,克制情欲,“将灵魂置于身体之上的女性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理想形象”。简长相平凡、身材矮小,她瘦弱的身型恰恰符合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女人的身型与性纯洁度相关联,苗条身体需要靠节制饮食,体现了高度自律与自我道德感,也彰显了女性的高度精神性与纯洁度。作为与简对比的女人,英格拉姆小姐身材高大,头脑简单;疯女人伯莎健硕如野兽,对其体型的描写暗含鄙夷,与其淫荡作风相关联。罗彻斯特历经风月场之后,简的身型与思想带给他清新、寡欲的印象,是他渴望的脱离肉欲的纯洁的生活,简激发起他的爱欲。
《异香》也书写“情欲与禁恋”,男女同床共枕数天,心中有想法,谁也不肯主动。两人丧失内在的激情。张楚河在女主的幽微洞察下自私、狭隘又可怜的形象无处遁形,他戒备、提防身边的人;他不愿结婚,不停更换女友,不相信婚姻能改变孤独状态。卫瑜想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阶层处境,婚姻类似交易,与感情无关。21世纪女性解放已取得重大成就,女性在教育、就业、选举等方面获得平等权。卫瑜女性意识倒退,生出依附性人格,与《简·爱》中简形成对比,简把人格独立、自尊、平等看得高于一切,不惜放弃唾手可得的爱情与财富。《异香》反映的是消费社会的交易型爱情,即“在市侩型意识流行的文化中,在物质上的成功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中,人的爱情关系和调节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交换,都遵循同一模式”。男女双方在利益考量之后,压抑了追逐快乐的“本我”,罗曼蒂克的“自我”被迫遵循现实原则,回归狭隘的理性状态,体现的是消费社会两性关系受压抑而致“爱无能”的典型性症候,过度理性化以及选择套路的普及化摧毁了爱欲。从这个意义上说,貌似罗曼蒂克故事,实则与“罗曼史”背道而驰。
三、“罗曼史”杂糅哥特式风格的原因
两部小说中两性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上都不对等,《简·爱》中简家庭教师的身份,介于贵族阶层与仆人之间,靠劳动赚取不多的年薪养活自己。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要有丰厚的陪嫁才能谋取好的婚姻,孤儿简一无所有。现实的卑微处境与精神上追求平等,使简内心充满愤懑与反抗精神。《异香》中卫瑜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阶层,收入介于农民工与高薪白领之间,都市高房价下不奢望买房,租不起公寓,只能租低廉的民房。残酷的生存竞争壓抑她的浪漫天性,培养她的精明、势利。她捕获有钱男人的计划一次次落空,内心充满着焦虑、压抑。“ 文明的基础是压抑,但压抑会造成精神的焦虑和不满。哥特小说中的鬼魂、噩梦、幽灵,其实都是这种焦虑和不满的外化。”“罗曼史”故事采用哥特式风格是以男性为主导的两性关系结构中女性压抑与愤懑的外化。
两部小说都试图从大自然中寻找通往两性平等的路径,小说中性别意识与生态思想交织,水乳交融,成为作品主题的一体两面。女性与自然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的等级制度、二元论和压迫性的思维模式已经对妇女和自然造成了损害。”女性常常被“自然化”,《简·爱》热恋中的罗彻斯特称简为“小鸽子”“小鸟”“红雀”“花朵”“像根芦苇”等,不自觉地把女性“自然化”。而自然也常被“女性化”,当“她”被作为“处女地”开掘、开采、征服时;或当“她”被作为大地母亲来尊崇时,自然被“女性化”。
《简·爱》中简拒绝成为罗彻斯特的情人,逃离桑菲尔德庄园,饥寒交迫的简采取“亲近自然”的策略。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凯伦·沃伦指出:“女性在精神上亲近自然可以为女性和自然治愈由父权社会带来的伤害提供一个场所。”简从“自然母亲”得到慰藉,“我除了万物之母大自然外没有亲人,我要寻找她的怀抱并请求安息”。象征着生命力的石楠丛庇护她入眠,野果减轻饥饿。“从人那儿只能预期得到怀疑、拒绝和侮辱的我,带着孩子一般孝顺的深情依恋着大自然”。大自然给予简坚持自我、反抗男性权威的勇气和力量。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小镇惠特克劳斯,落魄的简没有得到救助。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是以开垦、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简视村子“肮脏”,宁愿死在荒原,被鸟啄食,也不愿回到有人的村庄。简自我放逐于荒野,意外地在离群索居的沼泽居得到食物与友情,生命得以延续。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沼泽居是风雨飘摇中的诺亚方舟。沼泽居三姐妹眷恋住宅周围的荒原,诗意栖居的场景,与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现实处境类似。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哈沃斯僻静的牧师住宅里,勃朗特三姐妹与荒原为伴,从事阅读与写作。妹妹艾米莉《呼啸山庄》中旷野的风暴与石楠丛是常见自然意象。《简·爱》中在远离人群,密林深处的芬庄,简得到了渴求的幸福生活,自然怀抱中的芬庄就如伊甸园。小说表明,只有回归自然,两性才能保持自我的完整,构建两性和谐的生态社会。
《异香》内层故事叙述者山上老妪讲述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至死不渝的情感。与世隔绝的山上小屋收容着被山下世界排斥的“他者”,这些现代社会里的边缘人回归自然,过着原始、简朴的物质生活,他们情感世界充盈,爱森林、爱动物,一家人彼此相爱。老妪、聋哑儿子、林中动物这些人类世界中的弱者与“他者”,处境类似,承受着人类中心主义的男权制的压迫。老妪与动物“同病”而“相怜”,她批判现代人的傲慢与偏见,“万物都是有灵的,你不知道那些野兽们有多通人性,人千万不能杀它们啊,它们其实什么都知道,也会哭会笑,只是说不出来”。聋哑儿子具有懂动物语言的灵力,他救助伤残动物,把动物尸体制作成干尸珍藏。因为爱,他们把死去的丈夫、父亲做成木乃伊,陪伴着他们。山上世界是以“爱、同情、分享和养育”属于女性气质的价值为主导的。与之对比,山下人们虐待、屠杀动物;工业社会是金钱欲望交织的名利场,致使人身心疲惫,乃至人格分裂。男女主人公去大自然探险,是对现代性压抑的反抗与释放压力的方式。张楚河时刻提防着同类,只有在与大自然和非人类动物相处时才能放松戒备,释放乐于施舍、有爱心的本性。山上“有情”与山下“无情”的对比,说明高度现代化对人的挤压与异化,只有回归自然,才能摆脱阶层、金钱的枷锁,人性保持健全,两性之爱达到逾越生死的境界。
作者:周爱华,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