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视野“观春秋”
2022-05-30陈燮君
陈燮君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历史悬案,若虚若实。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著名辞赋家、学者。《西道孔子—扬雄》一书认为,扬雄故里位于郫县走马河畔白鹤里。白鹤里有大片湿地,林木蓊郁,沟渠两旁遍布桤木、杨树,树上栖息着一群群白鹤。长安,依旧繁华如梦。但是,这里不再是唐玄宗的长安,也不再是李白的长安了。豪放不羁的诗仙终于厌倦了,仗剑出游,远走他乡。多年以后,李白一反其诗词的豪迈飘逸,用汉乐府歌辞的寄寓手法,写了缱绻悱恻的《长相思》:
长相思,在长安。
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
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
长相思,摧心肝!
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这个被大学者李贽赞誉为“到中国十万余里”“凡我国书籍无不读”的虔诚教徒,着手绘制了一份影响整个世界的中文世界地图,“明昼夜长短之故,可以契历算之纲;察夷折因之殊,因以识山河之孕”,利玛窦将其命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幅气势磅礴的地图上,杭州准确地被标注在北纬三十度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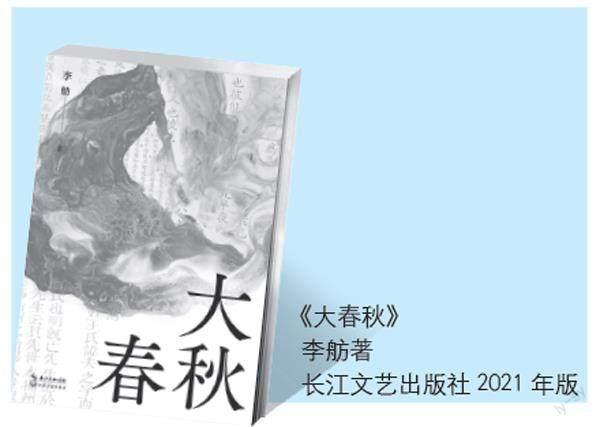
在李舫的《大春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这本历史文化散文集中,有历史的追问、细节的探究、风骨的讴歌、思想的放飞。《大春秋》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各代,从千古名士到悠悠古城,从人文胜迹到山川天地,在这些恢宏浩荡而又沉郁厚重的历史文化场域中,作者漂泊、寻觅、思索、叩问、眷念、批判、热爱、忧契,酣畅淋漓地书写了一幅幅磅礴丰沛、蕴思深刻、充满传奇与智慧的大历史、大文化景观。《大春秋》探寻“士”“脉”“道”,崇尚“真”“善”“美”,记录扑朔迷离的历史命运,讲述文化现场的深沉传奇,注目文人士子的生命风骨,留驻中国历史的风采独具。《大春秋》用学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视野“观春秋”,叙述文明舒展与荣耀铸造,描写南北交融与东西碰撞,发现秉独探幽与文化年轮,领略纵横捭阖与风起云涌,直面琴文剑胆与信仰大爱,唤醒千古斯文与文化敬畏,寻觅心灵相通与情感共鸣,缅怀大道不改与脊梁铮铮,览读跌宕起伏的大春秋,展示波澜壮阔的大历史。
一、关注历史的深处和岁月的留白处
给历史留份文学底稿,让文学进行历史定格,这是《大春秋》的逻辑起点。
李舫是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著有《重返普罗旺斯》《不安的缪斯》《在响雷中炸响》《魔鬼的契约》《纸上乾坤》《自在独行,丰盛的灵魂终将相遇》等。同时,她还担任了中国文学“丝绸之路”大型名家散文文库、大型名家诗歌文库的主编,也是《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四十人》一书的主编。她善于仰望历史星空,努力发现人文睿智,积极展现文明成长,坦诚演绎古今之道。
在读《大春秋》时,笔者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学者和文学家“观春秋”的视野和方法,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同?在李舫来看,学者和文学家的“观春秋”,同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理想和信念;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才能够葆有理想和信念”;异在“文学的书写在历史的深处,更在岁月的留白处”。
“文学的书写在历史的深处,更在岁月的留白处”,这一写作手法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慧眼所识。两千年以后,李舫对“岁月的留白处”留下了自己的文字和思考:文学家书写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说到底,就是人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和勇气。于是,我们才能够看到,司马迁笔下,春秋时代的种种顽强坚韧、不屈不挠。几千年来,人类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变故,一次又一次迁徙,大航海时代、大动荡时代、大颠覆时代、大变革时代……正是有了这些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对于这些历史的不断探究,才有了人类思考的无限丰富,人类进步的无限可能。春秋者,时也,史也。古代先人对春、秋两季的祭祀,让这个词具有了农耕文明的鲜明气质,春种秋收、春华秋实、春韭秋菘、春露秋霜、春花秋月……典籍里的美好词汇,负载着先人的美好期待,也收获了先人的美好祈福。春去秋来,四季复始,成就了中华五千年的浩浩荡荡。历史囊括了一切过往,以及关于过往的记录和思考、研究与诠释。历史具有三个特性:一是时间的意识性,二是思想的在场性,三是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时间是流动的,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未来的历史又是过去的未来。历史的意义在于不断发现真实的过去,不断用新的发现修正以往的谬见与误读,这恰是历史研究的价值,而在历史学家不能及、无所及之处,让历史的细节变得更加丰盈、丰富、丰美,恰是文学家存在的意义。我在阅读之外开始思考很多从未曾深入思考过的大问题,比如理念与信念、人类与世界、文明与传承、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文学、经纬与未来……书的内容还没有眉目,可是书的名字却那么固执地横亘在我眼前—大春秋,像一座巍峨的山峰,吸引着我去攀登。在那个风起云涌、命如草芥的时代,那些“仰望星空的人”孜孜矻矻,奔突以求,终于用冷峻包藏了宽柔,从渺小拓展着宏阔,由卑微抵达至伟岸,正是因为有他们的秉烛探幽,才有了中国文化的纵横捭阖、博大精深。在古文明的起源地,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从而成就了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实现突破的古代文明,如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虽然规模宏大,最终却难以摆脱消亡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大春秋》拂去岁月的尘埃,打捞记忆的残片,找到先人留给我们的琳琅珠玉,传之后世。《大春秋》在“岁月的留白处”留下了已有的思考,也留下了对新的思考的期盼。
关注历史的深处和岁月的留白处,是文学书写的“纵深空间”。然而,要真正把握、驾驭“大春秋”,还是要用学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视野、综合能力。让我们来看看《大春秋》的“驾驭之道”:如何既关注历史的深处和岁月的留白处,又兼具“双重视野”和综合能力。
(一)寻春秋时代的春与秋,探历史悬案的真与道
关于历史悬案“春秋之道”的探寻,在《大春秋》中的视野是宏大的,立意是深远的。正如作者在《春秋时代的春与秋》一篇的“题记”所书:这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两个巨人的对话,中国思想史上两位智者的相遇,更是两个流派、两种思想的碰撞和激发。在战乱频仍、诸侯割据的春秋年代,老子和孔子的会面别有深意;直至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亦颇具启示。春秋,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老子与孔子所处的时代,西周衰微久矣,东周亦如强弩之末。有周一朝,由文、武奠基,成康繁盛,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余年,是周朝的黄金时期。昭、穆以后,周势渐衰。后来,厉王被逐,幽王被杀,平王东迁,进入春秋时代。是时,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夷狄交侵,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老子作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作为鲁国大司寇,两者自有辅教天子行政的职责。救亡图存的使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进入“问礼”的同一时空。老子和孔子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们把哲学问题升华到人类思考和生存的宏大范畴,甚至由人生扩展至整个宇宙。他们开创了一种辩证思维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一种身处喧嚣而凝神静听的能力,一种身处繁杂而自在悠远的智慧。这是个体与自我相处的一种能力,更是人类与社会相处的能力。在公元前五百余年,孔子问礼于老子—时间,不详;地点,不详;听者,不详。其中的一位,温而厉,恭而安,儒雅敦厚,威而不猛。另一位,年略长,耳垂肩,深藏若虚,含而不露。这场对话对于世界历史、对于人类文明意义重大。
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说了些什么?司马迁记录:“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问:“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老子認为,孔子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腐烂了,只有其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他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品德,他的形色谦虚得好似愚钝。他建议孔子,抛弃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去的志向,这些对于孔子、对于世人,都是没有好处的。
孔子的思想在数次向老子讨教中逐步形成和成熟。思想的碰撞有助于演进,学问的辨析有益于成长。老子的哀民之恸,孔子的仁者爱人,都是哲人之思。老子的回答点醒了孔子,孔子的提问也敦促老子反思。两千多年来,儒道两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司马迁评价老子之学和孔子之学的异同,历数后世道学与儒学对于他们眼界、胸怀的退缩,怅然若失:“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二)赞千秋一扬雄,吟南岳一声雷
有时候,“不胜唏嘘”是在千秋以后,感慨万端发自岁月深处。
刘禹锡的《陋室铭》名垂青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文中的“西蜀子云”,就是指扬雄。
扬雄,西汉蜀郡成都人。四十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其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其官职一直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当政时,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扬雄在学术研究及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太玄》和《法言》奠定了扬雄在中国哲学史和儒学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蜀都赋》《逐贫赋》等使其与司马相如齐名而并称“扬马”,被称为“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辞赋家”;《方言》和《训纂》使其被后世称为“世界上研究方言第一人”。扬雄还在天文学、数学、历史、音乐等方面有重大建树,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他文采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具有“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巍然“大儒”。然而,“参圣之才”最终被时间吞噬,被厚重的尘埃淹埋。千年流光,弹指而逝。王安石回眸历史深处,感慨万分:“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有此扬雄,方使得烟波浩瀚的中华文化长卷,成为我们今天回溯历史的遥远的远方。”

扬雄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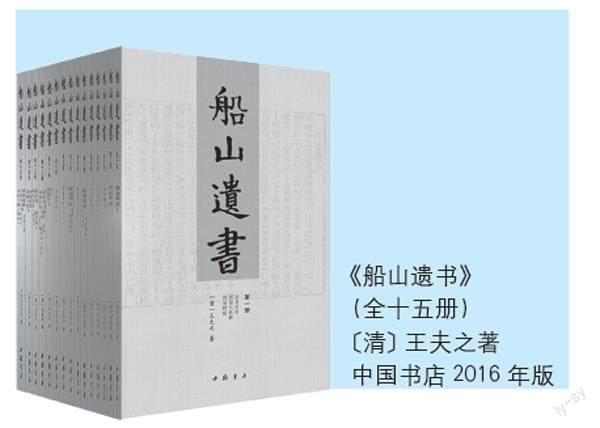
有时候,学术和思想的星星之火在后来的岁月中会成燎原之势。
王夫之故去两个世纪后,晚清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谭嗣同的“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王夫之的敬佩。这位戊戌变法的斗士,在王夫之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走向革命之路,坦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他怀抱船山精神,大义凛然地走向断头台,以死唤醒中国,成为民族复兴的英烈之士。
“秋水蜻蜓无着处,全现败荷衰柳。”一六九○年的一天,斜阳如血,王夫之伫立在湘西草堂前,面对石船山,四野衰草连天,乱石穿空,荆棘丛生。他缓缓转身,走进湘西草堂,挥毫写下“船山者即吾山”,心迹淋漓。王夫之自忖来日无多,自作墓志铭:“拘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王夫之用了数十年时间,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看到了那蛰伏于平静水面下的湍急细流,那隐藏在繁华背后的人性丑恶、制度弊端。他在历史中溯游,也眺望未来。数百万字的巨著集千古之智,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包括了中国历史的教训和反思,更包含着中国政治文明未来走向的预言。其中有石破天惊的呐喊,在王夫之辞世的二百五十年后,震惊了在内忧外患、丧权辱国中苦苦思考的中国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王夫之的心中,生长着两个中国。一个中国是王朝中国,一个中国是文化中国。他追溯中国文化的本真本源,寻找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梳理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家亦是国,国亦是家,从家国情怀升华到爱国主义,王夫之断言“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王夫之主张“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反对治经的烦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三百年后,章太炎评价王夫之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他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再赞曰:“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王夫之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英雄、中国思想史上重量级巨匠。
(三)念天地之悠悠,读人间之文豪
“念天地之悠悠”,是理想破灭的悲歌。峥嵘风骨赢得了薪火相传。
初唐陈子昂怀才不遇,报国无门,面对寒风凛冽,眼前一片黯淡。万岁通天元年(696),从营州回洛阳的路上,陈子昂写下了《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把弥漫于胸的对历史、对人生、对世界的旷绝尘嚣的悲哀与绝望,瞬间倾吐,遂成千古绝唱。
在与《登幽州台歌》几乎同时创作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陈子昂凭吊碣石馆、轩辕台,缅怀燕昭王、乐毅、燕太子丹、田光、邹衍、郭隗,表达对盛世的向往、对明君古贤的追慕,以及自己生不逢时、壮志未酬的无限感慨。他在序中写道:“丁酉岁(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异,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山河依旧,古今迥然。陈子昂孤单寂寞,悲来泪下。

陈子昂像
陈子昂的诗文高昂清峻,直斥时弊,绵绵传承,代不乏人。唐代初期,诗歌创作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反对柔靡之风,力挽齐梁颓波。他存诗共一百多首,其中五言古詩居多,有六十余首,五律约三十首。他留下重要诗论《修竹篇序》:“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他的古诗穿越时空,“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风泉夜声杂,月露宵光冷”的秋夜禅坐,“岩泉万丈流,树石千年古”,“林卧对轩窗,山阴满庭户”的夏日唱和,直接启迪了王维、孟浩然。《送别出塞》中“平生闻高义,书剑百夫雄。言登青云去,非此白头翁”之句的雄健荡气直接影响了盛唐的高适、岑参,慷慨悲壮的边塞诗歌从此开启。陈子昂于文,坚持朴实畅达,标举汉魏风骨,反对浮艳,重视散体。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十分感慨:“在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鲜明,以至在世界文明史上立即引发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提问,中国如何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而赢得了这个伟大的领先。”
《大春秋》写了大文豪苏轼的豪放,认为苏东坡超越了他的时代,在千年之后,仍可感觉他的超越、超迈、超拔。
读人间之文豪,一读其广博。诗词文书画,苏东坡无所不能,以词论,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以文论,他与欧阳修并称“苏欧”;以书法论,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二读其文风。多有评论谓其“豪放风流,不可及也”,“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遂开豪放一派”。三读其奔放不羁、纵情放笔、适性作词的创作境界。四读其吐纳百川、冲决一切、淋漓直泻的气势,如陆游所论:“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这种豪放,实是一种有操守,有坚持,有定力、能力和魄力的放达。
二、让人文进行历史定格
写历史文化散文贵有文学性,也定然要让人文进行历史定格。
流动的睿智的大春秋大文化毕竟是大历史的产物,从大历史而来,又随大历史而去。
(一)听江南文化的云和水,辨稷下学宫的流和变
听江南文化的云和水,自然会吟咏唐代白居易《忆江南·其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也会飘来宋代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大春秋》的“题记”是这样演绎的:数千年来,杭州—这座叫作天城的古城,傲岸地俯视着接踵而至的拓荒者、朝拜者、淘金者、筑梦者、远征者,他们兴师动众而来,兴师动众而去。在朝圣的故事里,杭州是—有无数个前世,却是唯一可以今夜枕梦的城市。在游子的梦呓中,杭州是—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在乡朋的宴席上,杭州是—为我踟蹰停酒盏,与君约略说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写绿油。在远方的客人不辞万里的驱驰中,杭州是—一叶扁舟泛海涯,三年水路到中华。心如秋水常涵月,身若菩提那有花。
西方寻找天城杭州的行动轰轰烈烈,找到天城的故事却悄无声息。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离别家乡诺瓦,从波斯湾乘船经印度由海路抵中国,经广州、泉州、福州到达杭州;此后,沿大运河北上来到北京,出河西走廊,沿“丝绸之路”达西亚,返回故乡。长途旅行累垮了他的身体,去世前,他在病榻上记录了沿途见闻,他是这样描述杭州的,“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城开十二座大门”,“城市位于静水的礁石上,像威尼斯一样有运河,它有一万二千多座桥”,“男人非常英俊,肤色苍白,有长而稀疏的胡须;至于女人,她们是世上最美者”。
历史常常会对史中行进的人文进行“历史定格”。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对创立于两千三百多年前的稷下学宫的“历史定格”是“齐王乐五帝之遐风,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在自由、开放、包容的稷下学宫,形形色色的门派、五花八门的思潮,从四面八方汇集交聚,知识分子们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景象,造就了人类文化政治景观的一座高峰。
历史定格之处往往有各种文化思想学说的汇聚、碰撞、交流与融合。思想的活跃,创造了稷下学宫的仪轨,打造了百家争鸣的舞台,营造了文化包容的氛围,形成了思想多元的格局。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所有学派,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在时间的深处,有这样一群人轰轰烈烈,衔命而出,用自己的智慧、立場、观点、方法,去观察,去思索,去判断。他们带来了人类文明的道道霞光,点燃了激情岁月的想象和期盼。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稷下学宫由此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互相争辩、诘难、吸收,成为真正体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正是天时、地利、人和,迎来了历史的定格。
(二)萦怀长相思,尽心忆长安
长相思,忆长安,忆唐诗故里,忆盛唐气象。
历史定格于长安建都一千四百年之际。《大春秋》是这样调遣文字的:夏末秋初的长安,刚刚从淋漓溽暑中走来,丰韵,成熟,美得雍容华贵,美得不可方物。红尘紫陌,斜阳暮草,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难得天高云淡,满城普天同庆。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这座城堪称是一个奇迹—它有红墙、碧瓦、金吾卫;也有霓裳、胭脂、堕马髻。它有宫阙九重,廊腰缦回;也有渊渟岳峙,马咽车阗。它有宫苑依傍着山明,也有夜弦追逐着朝歌。
凭借着过人的音乐天赋和一手好书画,王维十五岁时已名动长安。唐玄宗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天下慨然应者云集,李白也来到了心中的圣地—长安。杜甫、岑参、韦应物都有长安之忆。数十载之后,古文运动倡导者、被苏东坡评价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与元稹,被欧阳修赞为“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下”的柳宗元……也接踵而至。李贺、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刘禹锡……这些将要在中国文学长河中熠熠发光的名字,还都是漫天飘洒的尘埃。然而,在未来的两个多世纪里,他们将络绎不绝地聚集在同一个城市—长安。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艺术海报
无数的天才会聚到唐都长安。他们往来穿梭,尽情讴歌这座伟大的城市,礼赞这个伟大的时代。岑参写道,“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刘禹锡说,“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骆宾王则留下诗句,“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大唐长安,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国际大都市,而且城市面积超过八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六个巴格达、七个拜占庭、七个古罗马。这时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是中国精神的文化符号。开放的胸怀、开明的风尚、包容的气度,纵使今天的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都无法与之并肩。唐都长安不仅在当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积淀了自信自豪、开明开放、创新创优、卓越超越、求真务实的精神财富。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文化自信的时代,历史定格了这种“文化自信”。
(三)欢“吹笛鱼龙尽出”,醉“题诗日月俱新”
历史让城市浸润“春夜喜雨”,城市让生活更加充满诗意。
《大春秋》把读者带入了“诗歌成都”。成都外揽山清水秀,内胜人文丰赡,是一座“诗歌成都”。陆游在《风入松》中总结蜀中生涯:“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万金选胜莺花海,倚疏狂、驱使青春。吹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成都有着四千五百多年城市文明史,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以前。古蜀国开明王朝九世时(前367)将都城从广都樊乡(华阳)迁往成都,构筑城池。《太平寰宇记》记载,“成都”这个名词,是借用了西周建都的历史(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蜀都。在四川话里,“成都”两个字的读音就是“蜀都”的意思。所谓成者,毕也、终也。成都的含义,其实就是蜀国建完的都邑,或者说最后的都邑。
成都是中国文化的一块高地,是举世闻名的“诗歌之城”。成都具有丰厚的诗歌资源,是中国诗歌不可忽视的地标。历代文学巨匠大多游历过成都,留下了大量翰墨珍藏。杜甫草堂不仅是当代中国,更是整个世界范围内诗人祭拜的圣地。古诗人皆入蜀,入蜀必然入成都。唐代诗人杜甫写过《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蜀地诗歌风靡中国,杜甫功不可没。中唐诗人张籍极其崇拜杜甫,他曾经把杜甫诗集焚烧成灰烬,再以膏蜜相伴,全数吞下,之后抹嘴大叫,可以改换肝肠。张籍写下《送客游蜀》:“行尽青山到盖州,锦城楼下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白居易赞誉“诗家律手在成都”。在宋朝,更多的诗人、词人与成都结下深厚情谊和缘分,柳永初来成都,便被这里繁荣、壮丽的景象震住,填了一阕《一寸金·井络天开》的词,以赋体形式极力铺陈,将宋朝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描绘得淋漓尽致。柳永离开成都二十余年后,写出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到成都担任益州知州。苏家父子赴京师赶考,从成都出发,那时苏洵四十七岁,苏轼十九岁,苏辙十七岁。尽管苏轼在成都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对成都一直念念不忘,他在《临江仙·送王箴》词中写道:“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苏轼直到四十七岁,还追忆眉山老尼讲述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在摩诃池上夜间纳凉的故事,填词《洞仙歌》,留下“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的美妙辞章。南宋中期,著名诗人陆游与范成大相继入蜀,书写了宋代成都最夺目的篇章。范成大认为成都的繁华与扬州很相似,将成都万岁池与杭州的西湖相提并论。离开成都的范成大,心心念念总是成都的花事,他在词作《念奴娇》中倾诉衷肠:“十年旧事,醉京花蜀洒,万葩千萼。”陆游对于宋代成都的意义,堪比唐代杜甫。他热爱城市、园林、山水、民俗、物产、花草、饮食、文化,涉及世俗生活的所有方面。陆游四十七岁到成都,作《汉宫春》两阕,他初来已被成都的繁盛惊住了:“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敧帽垂鞭。”陆游还写了《成都行》:“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都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诗人在诗歌上的栖居地,成为文学家精神上的故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成都一直是一个在文学的繁荣史上从未有过低落、有过衰竭,甚至一直保持在高峰姿态的城市,这是文化的奇迹。

苏轼像
三、有四季的触摸和文学的呼吸
《大春秋》除了写大历史、大文化,还写大景观、大人文,其间充盈着读历史的叩问和观天下的感慨,在字里行间有四季的触摸和文学的呼吸。
(一)察无风中的狂浪,显漂泊中的永恒
如何感悟四季的触摸和文学的呼吸?可以读读李青松的《山与水的差别不是高度,而是情感》(《光明日报》2022年8月12日):
置身自然,作家产生什么樣的情感,创作的作品就会涌动什么样的情感。面对一棵树时,你看见树里的水了吗?没有。但树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水在树体里流动。谁说水是无形的?树长什么样水就长什么样。情感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将语言浸润在作品中,通过作品的品质来表现的。
唐代杨炯的《巫峡》中,就有文学的呼吸:“三峡七百里,惟言巫峡长。重岩窅不极,叠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莓苔烂锦章。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可以涉砥柱,可以浮吕梁。美人今何在,灵芝徒自芳。山空夜猿啸,征客泪沾裳。”《大春秋》把读者带入了“漂泊中的永恒”。西起奉节白帝城,东到宜昌南津关,三条大峡谷气势如虹,一路昂首东去。大自然用两百万年的耐心和伟力,打造出数不清的神秘与神奇,从而成就了长江三峡这幅迤逦诡谲的风情画卷。“放舟下巫峡,心在十二峰。”(清人许儒龙语)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季云雨,千年古镇,万年文明。在中国的历史版图上,从没有哪道山湾水景,像巫峡这般鼓荡旅人的情思、放纵行者的想象。长江裹挟岁月风尘,浩浩荡荡,呼啸而至,像一把利刃,切开了巫山坚实的腹地,造就了巫峡的壮美。
云锁巫山十二峰。连绵七十余公里,巫峡奇峰嵯峨,烟云氤氲缭绕,景色清幽迂回。巫峡阴晴雨雪各有其美。晴时,白雾悬浮于峰峦之巅,似烟非烟,似云非云,如雾非雾;雨时,宛若沧海巨流,云从天降,呼啸而至,铺天盖地;雨歇,云雾在峡谷间游弋,忽飘忽荡,忽升忽降,忽聚忽散。三峡是风和水的杰作,是美和真的童话,曾经有山与山绵绵不绝的心手相拥。而今却任由风的蹂躏、水的侵蚀,铺陈出这傲岸的嶙峋、巨大的坚硬。旷世的宁静之中,是生命的飘逝和人文的接续。三峡风格迥异。瞿塘山势雄峻,斧削而成,可是多了些悬陡的稚嫩、初生的鲁莽。西陵怪石横陈,滩多水急,可是多了些草率的刚愎、青春的犹疑。也许巫峡的幽深奇秀、峰峦跌宕最适合疲惫的诗人搁置桀骜的灵魂,所以才有了徐夔的放舟巫峡吧。杜甫有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漫卷诗书的喜悦,元稹有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悼念亡妻的哀伤,而今,流光散去,岁月渐老,漫卷诗书的愉悦定格为砥砺风雨的雷霆万钧,悼念亡妻的凄凉幻化为阅尽沧桑的悲歌传响。这是巫峡的至大至美、至幻至真、至柔至刚、至性至情,这才是真正的巫峡,这才是有四季触摸和文学呼吸的巫峡。
(二)思江春入旧年,叹宽简有大量
四季触摸和文学呼吸,在魏晋向秀的《思旧赋》中亦可感可叹:“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晋书·嵇康传》则写道:“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兄喜,有当世才,历太仆、宗正。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正始末年,嵇康居山阳,“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肆意酣畅,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也谓“竹林七贤”。

史载,嵇康曾经在洛阳西边游玩,晚上夜宿月华亭,引琴弹奏。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拜访,自称是古人,他与嵇康一起谈论音律,辞致清辩,于是索琴而弹,声调美妙绝伦。他把《广陵散》传授给嵇康,并让嵇康起誓不传给他人,他亦不言其姓字。《广陵散》歌颂了聂政对残暴的韩王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据《琴操》记载,战国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因延误日期而惨遭杀害,聂政立志为父亲报仇。他入山学琴十年,身怀绝技,扬名韩国。韩王召他进宫演奏,聂政终于实现了刺杀韩王的报仇夙愿。汉画像石《刺客聂政攻韩王》描绘的正是这个故事。《广陵散》最早见于汉末,又称《广陵止息》,或《止息》。“止息”为一佛教术语,转意为“吟”“叹”。《广陵散》是我国现存保留汉唐遗音的最重要琴曲,据北宋《止息序》称:“其怨恨凄恻,即如幽冥鬼神之声。邕邕容容,言语清泠;及其拂郁慷慨,又亦隐隐轰轰,风雨亭亭,纷披灿烂,戈矛纵横。”粗略言之,不能尽其美也。嵇康临刑前神情自若,调轸抚弦,弹奏《广陵散》,以宣泄满腔愤慨之情,更令此曲名扬天下。《广陵散》气势恢宏,悲怆动人,堪称琴曲之典范、武曲精品。嵇康的《琴赋》中有文学的呼吸:“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异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
(三)悟“山山记水程”,感“余特死有声”
“多少无名死,余特死有声”,这是明代李贽《答袁宏道〈别龙湖诗〉》中的诗句。在《大春秋》中,《山山记水程—李贽在晚明》一篇写得有温度,有分量。
《大春秋》中有撕心裂肺的文字:死神在不远处纵声大笑。李贽躺在冰冷的地面上,他用最后残余的力气凝视着死神,以及死神身后遥远的地方。巴掌大的窗口里,只有巴掌大的蓝天,枯索的双眸里,满是慈悲和傲岸。这不屈服的眼神,逼得死神偃旗息鼓,节节后退。死神怀着从未有过的惊恐向后张望,仿佛自己的身后,还站着一个死神。两天前,李贽要侍者取来剃刀为他剃头。花白的头发披散着,他要理一理这三千烦恼丝。可是,侍者未曾料到,稍不留意,李贽便抢过剃刀,用力割开了咽喉。他已经年逾古稀,狱中的粗茶淡饭、离群索居,耗尽了他最后的元气,包括力气,否则,他会一剑毙命,哪怕剑锋指向自己。颈上血流喷涌而出,整整两天,血流不止。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破暗夜沉沉的天际,倏尔陨落。
“山山记水程”,“余特死有声”。《藏书》不藏。《藏书》未经刊印,便在师友间广为传抄阅读,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南京公开刊印,更如巨石投水,波浪滔天,一时“金陵盛行”,洛阳纸贵,“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陈仁锡《无梦园集》)。尽管李贽自言:“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可是,天真的李贽不知道,这又怎么可能!《焚书》是李贽万历十八年以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论、诗歌等。他之所以不顾“逆耳者必杀”的危险,毅然决定在麻城刻行书稿,是因为他认定此书是“人人之心”,必将存之长久。而这些,会将那些宵小之徒照出原形的。李贽在千古流芳的作品—《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中,将人们供奉了几千年的圣人拉下圣坛,将人们遵守了几千年的道德准则放在审判台上。在他死后,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全部被烧毁。《明史》没有为李贽立传,只是在他相爱相杀的死敌耿定向的传记中提及他。时至今天,耿定向早已在浩瀚的历史里化为尘烟,每每被提及,却只有在李贽的传记中。“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嗟乎!才太高,气太豪……”(袁中道《李温陵传》)《大春秋》的引语也总是铿锵有力,有历史的温度,有文学的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