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之夕矣,彼黍彼稷
2022-05-30张定浩
张定浩
一
我在林庚先生的文集《唐诗综论》中,意外地见到几篇谈论《诗经》的短文,其中似乎只有《〈野有死麕〉》一篇注明发表在一九六五年的《文史》杂志上,其余《〈君子于役〉》《青青子衿》等数篇均无出处。这些一两千字的文章,被作者冠以“谈诗稿”之名,附在文集最后。作者在后记中自谦这些短文“大都是早年短篇的谈诗散文,上自风骚,下迄唐宋,多乃零星诗句的点滴体会,不足为论,不过是全书的余响而已”。说是早年,实则彼时作者也已过天命之年,而这些乱世中聊以遣兴的短文,因其出自诗人之心的体贴蕴藉,又携带着现代汉语发展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渐渐形成、随后又转瞬即逝的丰润、明净与婉转流荡,反倒能在时过境迁之后,仍葆有一种不灭的新鲜在,余响遂成了令人怀想的正音。
比如他讲《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才是真正的挂念,而此外便什么也不说。她之所以想念起远人,乃不由于悲哀,而由于暮色里一片的安息之感,才想起了辛苦在外的人,才想起要与那人分享这喜悦,所谓“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这便是一点的惋惜之情,也便是一点最平实的爱,因物及人,因人及物,古诗所谓“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物我之间有一点美善的关系,这所以不由于感伤而由于喜悦。黄昏的美感本来有浓厚的彩色,但是人偏偏又有了迟暮之感,这便是颓废的开始。从颓废之中而又生出一点爱来,这乃是人生的一点转机。所谓“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日之夕矣”自然没有这么分明的意思,却预先为后来不健康的人们留下了爱恋。
我觉得这里解得就比钱锺书总结的“暝色起愁”(参见《管锥编·毛诗正义·君子于役》)要更好一些。钱锺书是博采古今中外的诗句来证明“诗人体会,同心一理”,但林庚还看到古今情感在承续中隐伏的差异。而能够感知到《君子于役》一诗在哀愁忧思之外期待分享的安宁喜悦,就我所知,在这首诗的诠释史中,也是少有的。
诗学研究者试图追索一首诗的本事和缘由,但他们不晓得,一首诗虽然自有其特定和具体的写作缘由,但诗人写诗的过程,很多时候,却是要努力尝试忘记和克服这个缘由,乃至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尼采语)。“君子于役”,这四个字本身已经是一首诗。至于究竟具体是何种“役”,何等程度的“役”,诗人都不曾提及。或许他觉得这并不重要,甚至需要抛开烦琐的私人细节纠缠。“君子于役”,这是诗人所看到的、属于在世君子的普遍而恒久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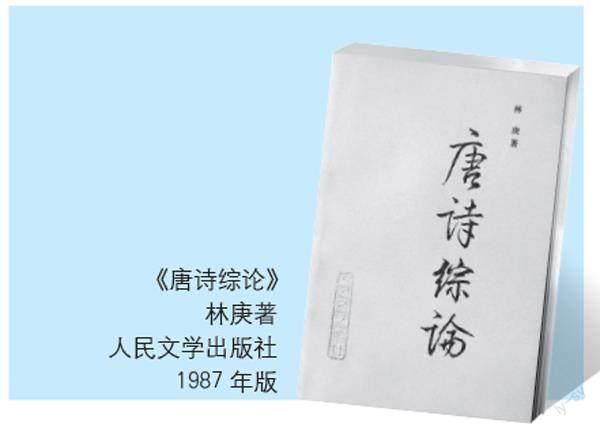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影印版
《说文·殳部》段玉裁注:“凡事劳皆曰役。”君子虽可努力做到不为物役,但在力所能及的内心自由之外,一个人只要去做事情,去参与社会生活,就仍然不得不为种种外力所劳烦,所驱使。古代之行役者,今日之打工人,就其本质而言未必有太大的差別。只不过,悲叹苦难的人往往并非置身苦难的人,言说与行动的分裂古今皆然,但诗歌的一个作用,或许正是弥合这种分裂,好的诗歌总是在暗暗调整和纠正我们对一些事情自以为是的情感判断,而非迎合。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这里面没有抱怨,因为抱怨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耐心和具体的关心。“曷至哉”,一直有两解,郑玄笺释为“何时当来至哉”,即“什么时候到家”;而朱熹则释为“且今亦何所至哉”,即“现在到哪里了”。我觉得后一种解释于诗意上更深一些,倘若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苦役,我们虽无法知道各自具体的期限,但依旧可以问一句,现在到哪里了。这是将时间的困惑转化成空间的确认。西西弗无止境地又徒劳地一次次推动巨石上山,“不知其期”,但加缪说,应该认为,回身走向巨石的西西弗是幸福的,“一开始就坚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是源于人的,西西弗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永远行进”,至少,西西弗知道此刻自己走到哪里了,而关心西西弗的人也想知道。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三句诗很美,有人甚至认为这就是中国田园诗的滥觞。于鬯《香草校书》:“今却‘日之夕矣一句在中间,则以中间一句义贯上下二句,诗法之变也。”这三句中有空间和时间的交错,并最终落脚在空间中。也还是林庚解得细密:
栖是鸟在巢上,而鸡是家禽,便又把这印象由巢上拖下,于是自然地落在短墙之上。“鸡栖于埘”,所以是情生文,也是文生情。那么这不正是一个黄昏的时分吗?下面“日之夕矣,羊牛下括”才因此不觉得那么唐突。如果我们没有这墙头的一瞥,则日之夕矣,如何能有一个那么亲切的落日?落日下山,而羊牛也自山坡走下,这里连带而来,正是一片当时的实感。原野的景色虽然没有说出,却已点缀于这个短墙之外。
因此,这种“中间一句义贯上下二句”的诗法,看似炫技,实则只是眼前所见的实录。那居家的妇人就是先看到回巢的鸡,随后目光沿着短墙看到了远处的夕阳,再看到夕阳下缓缓而归的牛羊。如果改成“日之夕矣,鸡栖于埘,羊牛下来”,意思虽然没有变,却显得有点呆板,因为那妇人由近处向着远方犹疑探望的目光不见了,就只成了局外人对乡村生活图景的空洞赞美。
再者,这三句居中的“日之夕矣”,恰好对应前面三句居中的“不知其期”,仿佛是一种自问自答,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归期,也不知道你如今身在何处,对这些我所不知道的,我只能保持沉默和耐心,但我可以努力讲述我所知道的一切,比如此刻我所看到的盛大的日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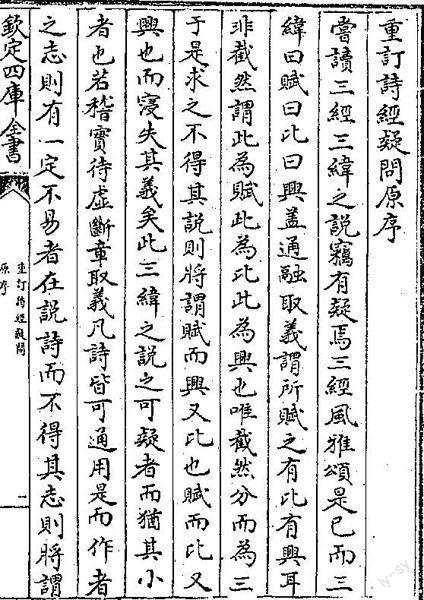
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四库本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如果说首章的前三句从彼处的君子讲起,中间三句回到此处的妇人,那么这最后两句,就是将此处和彼处勾连在一起。“如之何勿思”,这种曲折的句法也暗示了闺中人调伏其心的艰难。“如之何”,是先秦两汉一种特定的句法,其中每个字都是有意义的,即拿这个事情怎么办;“勿思”则是诗人希望达到的结果。它们合在一起,直译的意思大致会是,我该拿“君子于役”这件事怎么办才能做到不去思念?后来的阐释者,大多就将“如之何”等同于“如何”或“怎么样”,这意思大抵也没错,却少了一份那种一字一顿、往复回环的纠结,以及达臻自我平复时的安宁感,好比百炼钢如何一点点化成绕指柔。
于是这安宁并不意味着放弃思念。陶渊明《答庞参军》:“伊余怀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与汝乐之。乃陈好言,乃著新诗。一日不见,如何不思。”末句就是对《君子于役》的化用,而从中我们看不到悲哀,因为这思念已经化为了一种日常,成为生活本身,生活本身的方向就是要朝着和那个人一起分享的时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一个人外出久了,对在家中等待他的人而言,相应的计时工具也会慢慢发生变化,起初是以他离开的日子来计算,后来则以月计,再后来,或许就不再以日和月来计算了,是谓“不日不月”,这也谈不上感慨,只是如实的陈述。“佸”和后面“羊牛下括”的“括”,都是会聚的意思。“曷其有佸”,什么时候才能够再相会呢?但与其说她是在要一个答案和期限,不如说,她是在表达一种终有一天必将会重逢的决心。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这里可以说一说的,是鸡桀和鸡埘的区别。鸡埘,最早当是在矮墙上凿出的浅浅洞穴,主要是供母鸡生蛋和孵化小鸡所用,因其依附于墙,比较稳固,且在墙上相对比在地上安全。后世渐渐发展出专门制造的鸡窝,也依旧称为鸡埘。鸡桀,则是供鸡睡觉的横木架子,甚至也包括鸡所栖息的树枝。鸡本就有栖息在树枝上的习性,并且在架子上睡觉可以将粪便拉在地面,从而保持自身的干净,避免各种寄生虫的侵袭。现在农村养鸡依旧有搭栖息架的传统。有些流行的《诗经》注解,将鸡桀解释为拴在木桩上的鸡笼,或者竹木编的可折叠的鸡栅栏,恐怕都是不对的。
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埘必其苟栖处,桀必其稳栖处。”从回到鸡窝到最终上架睡觉,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从牛羊下山缓缓归来到最终会聚的时间,或者可以说,这个过程就是居家的妇人每日所目睹的黄昏。所谓“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其实只是后世男性文人几成惯例的抒情,而对于古往今来真正在乡村中日复一日生活着的妇人们来讲,家禽牲畜归来的黄昏,做好了晚饭的黄昏,首先意味的是紧张辛劳的一天的结束,意味着短暂安宁的到来。这也正是林庚所说的“暮色里的一片安息之感”。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这也正是居家晚饭时分自然会生出的对于缺席者的平实挂念。如果说首章末句“如之何勿思”是对自己而言,那么这一章末尾的“苟无饥渴”则是对远人而说。这两次祈语其实都是低聲的,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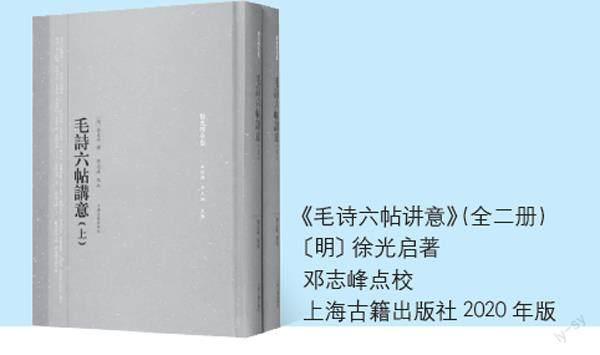
二
《君子于役》位列《王风》次篇,在它前面,作为《王风》开篇的,是那首著名的《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围绕这首《黍离》,已经有过很多精彩的疏解,再单独重讲一遍,似无必要。但如果把它和《君子于役》放在一起,这首次二篇之间倒是还有不少可以贯穿比较的东西。
和《诗经》中很多篇章一样,关于《黍离》的主旨,历代一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但最为主流和普遍的意见,是认为这首诗讲的是东周大夫行役至西周故国,见到原本的宗庙宫室所在之地如今已经成为禾黍丛生的庄稼地,“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毛诗小序和朱熹在这首诗上也达成了一次难得的共识。
我们前面讲到《君子于役》的作者只字不提令君子长年在外从事的是何种具体事务,诗人看到的是一种普遍的命运,随后他讲述的只是闺中人的即目所见和即景会心。而《黍离》亦有类似的笔法,我们现在见到那位行役的君子了,但我们依然不知道他具体的身世、际遇,我们依旧只能顺着他的目光看出去,看到一片如“日之夕矣”般不背负任何历史印记的自然景致,再听他坦陈此时此刻的心事。
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此诗详玩本文,不见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庙宫室等字。今俱就感黍稷而兴歌上言,不可露出宗周意思,亦不露出宗庙宫室,如此则有无限感慨之情,而于‘谓我心忧、‘谓我何求处自有含蓄,且不失诗人浑厚之旨。”
一首抒情诗的深度,往往来自那些它没有直接讲出来的部分。但这并不仅仅是后世所谓的“隐微之术”,在早期中国古典诗人那里,这种沉默自抑的笔法,更多源自性情和教养,以及对于“人的局限性”的更为诚恳的认知。而朱熹《诗集传》在这里引用前朝学者刘安世的话,我觉得也特别之好:“常人之情,于忧乐之事,初遇之则其心变焉,次遇之则其变少衰,三遇之则其心如常矣。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则不然,其行役往来,固非一见也。初见稷之苗矣,又见稷之穗矣,又见稷之实矣,而所感之心终始如一,不少变而愈深,此则诗人之意也。”
所谓“常人之情”,未必就是要被鄙弃的,因为那也是一种普通人的自我保全。某种程度上,《君子于役》讲述的就是一种常人之情,那居家的妇人面对变故之后的平静衬托着《黍离》中行役君子始终如一的忧愤,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两面,如水火之相济。而诗人,就是要同时理解和体贴这两种属人的珍贵情感:忽视常人之情,容易变得尖刻峻厉;而遗忘了君子之情,也会导致卑屈苟且。
《黍离》三章,“彼黍”一直“离离”,而“彼稷”则自苗而穗而实。前人对此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也都有各种各样的牵强。黍和稷同为上古最重要的两种粮食作物,考《诗经》中出现黍和稷的篇章,有六首诗有黍无稷,有八首黍稷并举,没有一首单独出现稷,也就是说,黍稷在《诗经》中构成的基本是一种同类合称关系,而非异类对比关系,没有理由认为《黍离》是个例外。因此,若将《黍离》中“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视为一种互文修辞,即“彼黍稷离离,彼黍稷之苗”(那些黍稷稀疏成行,长出新苗),或许会更为平实一些。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行迈靡靡,中心如醉”“行迈靡靡,中心如噎”。在《君子于役》中,夕阳西下,禽畜归巢,在这一片自然界的动态图景中我们看不到人的动作,那个妇人仿佛是静止的,恒定的,她成为家园的一部分;而在《黍离》中,一切颠倒过来,只有人持久地行走在静谧无声的大地上,而和那些扎根于废墟之上肆意生长的植物相比,他更像是一个被双重拔根的人,失去故国,也回不了家园。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凡君子之情,因其稍稍有别于常人,就会有人知有人不知。这两句忽然而起,仿佛诗人忽然分身于外,凝视那个正在如醉如噎的自己,也审视着那些在未来岁月中可能存在的知己或路人,进而仰天感慨道,“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此处的这个“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需要承担这一切。这种分身术,令过去、现在和未来浑然一体,再奇异地完全落实在此时此地这个独行君子的身上,只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何人哉”这句诗更为常见的解释,是“致此者何人”,即导致这一切亡国的是什么人啊,表示对祸国殃民者的斥责。但这种解释,一方面要增加一个本来没有的动词,另一方面,似乎也变成一种怨天尤人,有违君子“反身而诚”之本分。再从句法上讲,“此何人哉”与《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相仿,“彼”既为“他”,“此”自然应该是“我”。
《君子于役》中几乎没有“我”,即便有“我思”也要竭力遏止(“如之何勿思”);而《黍离》中满满当当的全都是“我”,忧思充塞鼓荡于天地之间。但这二者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后来王国维所区分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它们要比王国维拈出的诗境更浑厚一些。《黍离》之“有我”,不单单是“以我观物”,更是分出一个他者的目光来观“我”,“我”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行动者也是叙事者;而《君子于役》之“无我”,也并非由于“以物观物”,相反,《君子于役》中“我”的目光无处不在,但诗人有意识地后撤了一步,“我”既是一个等待者,同时也是一个见证这种等待的人。
《王风》收诗十首,据说皆为东周时期的作品。此刻煊赫一时的西周已经灭亡,华夏文明风雨飘摇,“我生之后,逢此百忧”(《王风·兔爰》),这既是个体生不逢时的哀嘆,却也是一种永久的哀叹,因为历史上的乱世远多于治世。能够“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的,毕竟只是幸运的少数人,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大的动荡或战乱,经历无可抗拒的离散和丧失。《王风》的编者,用开篇的两首诗,教我们如何“站在人这边”,怀抱无限的耐心,去承担和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