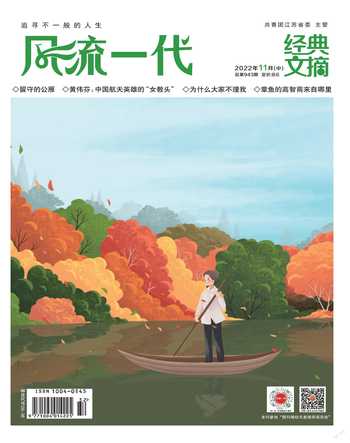大话中国艺术史
2022-05-30意公子
意公子

【内容简介】
热门艺术书籍《大话西方艺术史》姐妹篇,句句有梗,打破艺术高冷的刻板印象,一口气读完10000年中国艺术史。本书从原始社会的陶器说起,内容涵盖了青铜器、草书、山水画等多种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150件中华艺术品,45位艺术名家,32个让你意外的艺术故事,作者以独有的视角,带你走近文化自信的根源,解码中国艺术的深沉内涵,给你博物馆式沉浸體验,感受中国这片土地独有的艺术色彩。
3000年前的吃货太讲究了
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评出一个最会吃的朝代,那么非周朝莫属。周人以食、货、祀、司空(管理居民)、司徒(管理教育)、司寇(管理盗贼)、宾(管理朝觐)、师(治理军务)为国家施政的8个方面。其中,“食”被排在了第一位。
“民以食为天”,无论是原始时代,还是青铜时代,吃饭都是天大的事儿。
你一定想象不到,在吃这件事上,周朝人讲究到什么地步。光是蒸、煮、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已满足不了他们那颗吃货的心。每一样食材用什么煮,拿什么样的餐具盛放,甚至都有明确规定。
而他们的餐具不是别的什么,正是我们在历史书上读到过的国之重器——青铜器。
脑洞大开一下,假如你今天受邀参加某周代贵族的饭局,那场面很可能会是这样的:
入座以后,只见大厅中央一口大“鼎”正咕噜咕噜地煮着肉。肉香早已蔓延开来,有人从里头捞出煮好的肉,切成小块,分到你面前一口小的升鼎里,就像是单人小火锅一样。而边上的“豆”中,放着各种口味的酱料,甜的、咸的、辣的,统统都有。夹块肉再蘸点酱,颇有我们今天吃涮羊肉的感觉了。主食是“粟”,也就是小米。粟可蒸可煮,想吃干饭就用“甗(yǎn)”蒸,想吃稀饭就用“鬲(gé)”煮,一顿饭也能吃上满满一大“簋(guǐ)”。渴了的话,桌上的“斝(jiǎ)”和“壶”里已经装满了酒。如果你想喝点热的,斝还可以拿来温酒。吃饱喝足,让我们高举起“爵”为友谊干杯。
虽然想象中的场景可能远没有真实历史中贵族饭局的奢华,但这些青铜器却实实在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饭桌上从煮肉的鼎到当调料盘的豆,从煮饭的甗和鬲到装饭的簋,从装酒的斝和壶到酒杯爵……说白了,青铜器直接承包了古人的一整套餐具,跟我们今天用火锅涮肉、用电饭煲煮饭,有饭碗、有酒杯是一样一样的。
根据不同的烹饪方法、不同的食材,再配以专门的青铜餐具,这只不过是周代一个普通贵族的一顿饭而已。
那我们普通小老百姓能用什么呢?别说用青铜器吃饭了,水煮菜先了解一下。
青铜的出现是个意外,但把青铜铸造成器物却是个有意而为的大工程。
经过备料、洗泥、制模、夯范、雕刻花纹,还有制芯、焙烧、合范、浇铸、打磨修整等一系列工序,一个青铜器才算基本完成。乍一看除了工序多点,这青铜器的制作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啊?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就错了。
制作青铜器的每一个环节都不简单。单就雕刻花纹来说,那都是有讲究的。
哪怕只是一尊酒罐令方彝,都装饰了10只饕餮、16只凤鸟和4只虎头双身龙,再用整齐精细的回形底纹填满整个铜器平面,可以说是从头“武装”到了脚底,才算完成雕刻花纹这一步骤。而这还只是青铜器在外观上的小设计。
在青铜器上还藏有更大的“彩蛋”——铭文馈刻。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记录下这件青铜器所有者人生中的高光时刻:昨天被天子册封,今天出征打了场胜仗,还有两大家族联姻等各种大事记。对于那时候的贵族而言,青铜器就像是纪念碑一样。他们把重大事件或文书记录下来,并铸刻在青铜器上面,好像这样自己也能随着青铜器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数量众多的青铜器分类齐全,用料极其奢侈,带着一身繁复的花纹,用镌刻的铭文定格着一段段历史。这时候,你还觉得青铜器仅仅是周朝天子、贵族餐桌上的一个小小餐具吗?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国古代礼制的开始,就来自我们日常的一餐一饭。只有吃饱喝足了,礼仪礼节才会成为人们下一步的追求。
在3600多年前的商周,贵族们用一整套青铜器完成了在“吃”这件事上的仪式感。觥筹交错之间,开启了这个钟鸣鼎食的青铜时代。朝堂之上,鼎依旧咕噜咕噜地煮着肉,而有一种乐器也正在被敲响,它的名字叫,曾侯乙编钟。
这个黑科技产物,
是给上天听的声音
为了能够“有档次”地吃顿饭,古代贵族们可以说是极尽所能地“搞事情”,甚至不惜花重金打造了一整套豪华餐具。你以为,这已经够有仪式感了?不,他们还想来点音乐。
如果回到战国时期,曾国的宫廷之上,有这么一位叫作乙的诸侯王或许会在宴席上这样命令道:“来呀,接着奏乐接着舞。”
于是下一秒,曾侯乙编钟的金石之声响彻整座宫廷。
据说,这声音是演奏给上天听的。有人甚至说,如果音乐有鄙视链的话,那么编钟就应该在这鄙视链的顶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曾侯乙编钟就是顶端中的顶端,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举世无双的乐器。
2400多岁的曾侯乙编钟,有5吨重,两面墙这么大。在中国目前出土的编钟里头,它是众多纪录的保持者——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广、保存最好、音质最高、做工最精细……同时,曾侯乙编钟还被称为“镇国神器”。
它的出现直接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因为在以前,整个学界都以为中国的十二平均律,也就是C大调,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却告诉世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中国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十二平均律,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
整套曾侯乙编钟足足有65口之多,分成3层8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
即使放在今天来看,要制作完成这样数量庞大的编钟也是个不小的工程。它需要制作者掌握包括音乐、化学、物理学、铸造学、数学等学科的顶尖知识,同时还得有美学和艺术素养。
因为制作工艺太过精湛,有人甚至对曾侯乙编钟产生了怀疑:难道这是现代科学家穿越回去制作的?否则凭那时候的生产条件,怎么可能制作出如此气势恢宏的编钟呢?
对啊,曾侯乙编钟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首先,它是一组青铜器。青铜器非常讲究青铜合金的化学成分,制作非常复杂。而曾侯乙编钟作为乐器,每一口钟的构型、几何尺寸、音乐性能等的设计和安排对铸造技术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其中大点的编钟高度超过1.5米,光是制作這样一口大钟,就需要用136块陶制的模具组合成一个铸模,然后在里面灌上将近1000℃的铜水。一口钟就这么费劲了,更别提这一整套下来需要花费多少年。
关键是,曾侯乙编钟还不是普通的青铜器,它跟别的青铜器不一样,作为乐器它得发出乐声。所以在铸造过程中,工匠们需要严格把握好铜、锡、铅3种金属的配比,让它们达到一个黄金比例。
后世科学家们经过反复实验后发现,当含锡量在13%~16%、含铅量在1.2%~3%时,编钟发出的音色浑圆饱满,且钟声能快速衰减,声音和声音不会混杂在一起,是最适合进行演奏的。
想象一下,2400多年前的古人没有精密仪器,要让每一口大小不一的钟都能达到演奏水准的黄金比例,唯一能靠的也就是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了。
而且光是这样还不够。为什么说曾侯乙编钟了不起呢?
史料记载,在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其实都有过铸钟的实践,但它们所铸造出来的钟都是圆形的。无论你怎么敲,钟只能发出一个音,而且延音很长,根本不能做成乐器。
但是,中国古人却做到了让钟成为乐器。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曾侯乙编钟有的钟表面有些凸起的“疙瘩”。这些“疙瘩”的准确名字其实是“钟枚”。它的用处就在于减小声音的扩散,防止编钟扩音太久,发出更加浑厚的低音。这样,我们就能把钟当成乐器使用了。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地方。我们不仅让钟变成了乐器,而且可以让一口钟发两个音。
古人巧妙地把编钟做成了“合瓦形”,把钟分成瓦状的两块板拼在一起,这样敲击正面和敲击侧面时,就相当于敲击不同的板。并且,铸钟的工匠们为了能更好地区分一口钟的两个音,还把编钟的振动块分离开,在钟体里面挖隧道隔音。
一钟双音,这是中国先秦时期编钟的独门手艺。
不夸张地说,曾侯乙编钟称得上一件集音乐、美学和科技于一身的艺术品。当时制造编钟的难度之高,远超我们今天的想象。即便是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的1979年,我国考古、音乐、机械等方面的众多专家一起研究复刻“曾侯乙编钟”,也投入巨资,历时5年才最后成功。
“堂下之乐,以钟为重”,想象一下,在群山之巅的祭祀大典,在金戈铁马的出征现场,在国君宴请使臣的殿陛之间,乐师们手拿着敲钟槌撞向编钟。一时之间,钟鼓齐鸣,“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钥,似星辰日月”。天、地、人在这一刻浑然一体,这个声音仿佛就不是人间会有的……
有四方,才有中国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3100—4800年,比古希腊文明(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要早得多。这是一处古蜀国的文化遗址,是中国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各种青铜造像。
在它们身上,有太多的谜团至今难以破解——
在铜矿产量不多的四川,要制作数量这么多的青铜器,原料是从哪里来的?
如此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文化,是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外来之物……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得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入手,比如青铜神树——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三星堆遗址一共出土了8棵青铜神树,其中修复最完整的一棵有近4米高。要不是最上面的部件已经缺失,这棵青铜神树的高度能有5米左右,也就是快两层楼那么高了。
我们说过青铜器的冶炼制作过程,在商周时期,应用最广的青铜器铸造方法是范铸法,也就是先做模具,然后把液态的铜水浇注到模具里,等到冷却之后再扒掉模具进行修整。但这棵青铜神树,它有很多细细的枝杈,枝杈上还站着太阳神鸟。且不论这个模具制作有多么复杂,光是把铜水灌进模具这一步,就无法实现。因为铜水凝固速度太快了,倒进模具后还没等它流到枝杈末端就会凝固,更不用说枝杈上的太阳神鸟了。
那三星堆的古人是怎么做的呢?
科学家曾经研究过三星堆青铜器的成分,发现其中居然还有磷元素。这不仅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内部元素不同,也完全颠覆了世人的认知。
在大众的认知里,磷元素是1669年德国商人布朗特在尿液中提炼出来的,难道远古时期三星堆的先民们早就发现磷了吗?
更让人惊奇的是,他们居然还能精准地计算铜和磷的比例。因为铜的熔点在1000℃以上,而红磷的熔点只有590℃。在当时,主要燃烧材料还是木柴,木柴的燃烧温度在800℃上下。三星堆的先民把磷掺杂在铜里,就降低了金属的熔点,也降低了燃烧的难度,从而在浇注铜水的过程中让铜水在模具内能流得更快,顺利流到枝杈末端,流到太阳神鸟的部分再凝固。
太厉害了,你不得不佩服几千年前古蜀人高超的技艺!
除了青铜神树,三星堆还出土了众多的青铜造像。令考古学家好奇的是,从古至今,四川就不是盛产青铜的地方,那这些青铜原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金正耀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做了系统的铅同位素分析和研究,发现在这些青铜器中含有一种名“高放射成因铅”的物质。这个物质并不产自古蜀之地,而是与中原殷墟(今河南安阳)所用的主要青铜矿料来源相同。
那问题又来了,三星堆现在已经出土的青铜文物就已经达到一吨以上的重量。数量如此巨大的原料,究竟是怎么被运到古蜀国来的呢?
至今,人们也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这个问题,还不只是出现在青铜文物身上。
三星堆遗址里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部分象臼齿经过科学鉴定属于亚洲象。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雄性的亚洲象都有象牙,这么多的象牙,那得多少头大象。而这么大规模的象牙又是来自哪里,都是古蜀国本土的吗?有不少学者倾向于,三星堆的象牙是来自异域,比如缅甸、南亚或者印度。
在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非本地“出产”的象牙和青铜器,无一不在告诉我们,几千年前的古蜀国有着丰富的对外交流活动。
李白在《蜀道难》里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也许,在遥远的古蜀国,有着一条连李白都不知道的神秘通道。而就是这条古道把古蜀文明、中原文明甚至更遥远的异域文明连接在了一起。
今天我们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走进一个远古文明,更是走进一个个巨大的谜团。而一次次揭开谜底的过程,更是充满了惊喜,并且具有非凡的意义。
三星堆的存在,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化的。曾经,我们以为它的缘起是“站中国,雄踞四方”,但是三星堆文明告诉我们——有四方,才有中国。
中华文明,并不是发源于一地,然后传向四方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如点点繁星,在中华大地各处诞生、发展、绽放光辉。
(摘自海南出版社《大话中国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