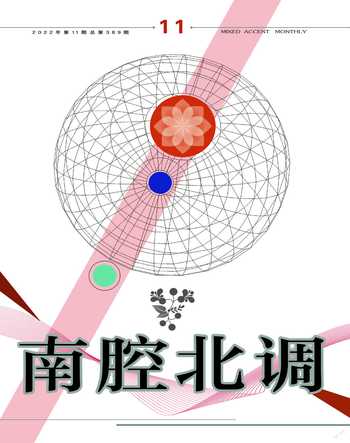青春的撕裂与涉渡
2022-05-30关羽
关羽
摘要:由白雪导演、田壮壮监制的青春电影《过春天》聚焦于往返深港之间的跨境女学童佩佩的成长遭遇和内心世界,在对主人公佩佩情感与身份的双重缺失的遭遇的叙述中,通过佩佩经历的青春破禁与涉渡成人,揭示当下一代人从经历成长迷思、遭遇困境,到无奈接受、达成身份和解的残酷青春主题。
关键词:青春电影;情感缺失;身份迷思;涉渡成长
一、灰色苦痛青春——情感的缺失与压抑
青春电影的主题,往往会结合青春成长来关注、探讨人物的情感问题。由于青春期的主人公处于从少年到成年的过渡阶段,情感需求日益旺盛,迫切需要更多的情感体验来填充成长撕裂带来的新空间,从幼稚无知到懵懂迷惑到渴求成熟;由于性意识觉醒渴求两性关注,个体意识的急速形成造成的对家庭亲情的矛盾心理,为青春期少男少女带来了在爱情、友情、亲情方面的诸多情感问题;青春电影便不可或缺地通过少男少女在爱情、友情和亲情方面上的情感遭遇,来探讨青春期主人公的情感主题。《过春天》的女主角佩佩出身和成长于不完整的家庭之中。来自香港已有家庭的父亲与外来务工的年轻母亲,在深圳非婚生下佩佩,这让佩佩一出生便作为非婚生子女,而无法在成长过程之中获得来自完整家庭的亲情情感体验。父亲返港回归原有家庭,造成了佩佩的父爱缺失,母亲幼稚可怜又纵情声色,也无法扮演好单亲母亲的角色。白天在香港上学、晚上返深圳生活,苦于奔波辗转的佩佩无法认同母亲,与母亲也处于失语的境地之中。在影像处理方面,深圳部分虽然多表现私密的家庭空间,但以固定机位拍摄固定镜头,表现出佩佩与母亲之间的情感疏离和佩佩的亲情缺失。在家里,她不愿和母亲产生过多的交流,甚至排斥母亲醉酒后的亲昵,只困缩于自己的小空间,更像是家中疏离的陌生租客,将自己与母亲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父亲也给不了她完整的父爱情感,在撞见父亲与原有家人聚餐时,佩佩只能装作陌生人默默地离开。
作为跨境学童,身份的尴尬、家庭亲情的缺位,也让佩佩无法释放青春天性结交朋友,来获取广泛或深刻的友情体验。唯有在天台与仅有的朋友JO一人一杯奶茶,畅想一起坐飞机去日本看雪,但少女间的情怀遐想,飘忽又短暂的情感经不起风浪考验。对于佩佩,这仅存的友情不久便因JO怀疑佩佩抢走其男友而如四月樱花般飘散而去。惊觉、冲动的友人,只能让青春友情更加脆弱短暂,进而走向枯萎死亡。在学校走廊上,JO对佩佩的推搡质问,一句“你和你妈一样都是鸡”的恶语相加、肆意诋毁伤害,暴露出多少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暴躁无知,这也使之后的佩佩更加压抑自己的情感诉求。
在当下的消费语境中,青春片制作已经把对情感和身体的浅薄表现作为取媚市场的一大法宝。国产青春电影常常会将青少年主人公正处于性意识萌发、个体走向性成熟的时间节点来对涉性情节、画面进行结合展示,如《万物生长》《匆匆那年》等。而在《过春天》中,情爱主题却被以一种朦胧压抑的方式表现着,佩佩与阿豪等人物没有随意地处置两性关系。因为有着同样的不愿诉说的经历,佩佩与阿豪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所以阿豪帮她摆脱困境,劝导她收手。在香港山顶,阿豪身体开始靠近佩佩,低头往她嘴巴凑过去,佩佩紧张局促,不安地静待着阿豪的靠近,最后只得一句:“好多蚊子。”俩人便离开了,情感到此戛然而止,朦胧的暧昧交织缠绕在夜色中,空留观众的无尽遐思。电影里最暧昧的一场戏——阿豪和佩佩互相帮对方缠水货手机。俩人在霓虹灯光下,互相撩起衣服,用胶带把手机一个一个地在对方身体上缠绕一圈又一圈,不经意地眼神对视,情愫溢于言表,在逼仄的空间里,只剩萦绕着的沉重呼吸声和缠贴带来的胶带撕扯声。这段最接近情欲的非性爱戏,被誉为华语青春电影最高级的情欲场面处理。青涩中透着欲望,却没有撕开最后的面纱,成为片中最有魅力的一场戏。然而青春萌动的欲望、压抑的情感、青春的叛逆等却被停留在这逼仄的红晕空间,正如导演白雪所说:“俩人的感情,我的理解是处于青春期的他们的荷尔蒙分泌,并不是真正的爱情。”[1]无论是处于青春期的佩佩、JO或阿豪,还是早已成年的父亲母亲,都处于情感缺失与残缺家庭的泥潭之中。
二、香港与深圳——从空间变换到身份迷思
电影艺术中的空间和时间共同组成了叙事,随着空间叙事和空间理论的发展,就有了艺术批评学者提出“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2]的观点,空间理论的影响逐渐渗透到电影创作中。电影《过春天》深港之间地理位置和地理空间的差距,也象征着城市发展的差异,此类地域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两地不同的生存环境之中居民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差别。佩佩作为跨境学童,辗转于深港之间,对于展现片中尖锐的社会现实矛盾和人物的境遇与精神困境,都起到了强烈的推动作用。
影片一开始,佩佩挤上从深圳驶往香港的城铁,夜里又匆匆赶回深圳,佩佩就这样每日往返于深港之间,带着两张面孔穿梭于两个空间。在香港上学,却居住在深圳,家庭破碎与情感缺失,让她自小缺乏安全感。“跨城”是她生活的常态,但是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海关的存在,让在地理意义上只有一河之隔的深港超出了一般城市之间的关系,虽同属国内,但进出往返还是行政层面的“跨境”,于是也出现了“跨境”群体与“跨境”学童。作为往返于“春天”两侧的“无家之人”,打工时,别人问她家在哪里,拿著香港身份证的佩佩闪烁其词,只说“很远”,因为她的家不在香港。但大陆对于她来说,就像是那个她鄙夷的母亲,还是没有给足她家庭的温暖。而父亲则代表了佩佩对香港的印象,情感上想要亲近,但在现实里却也疏远,并非真正的归属。也正是她既属于两边又疏离于任何一方的状态,不仅让她成为“过春天”水客的最佳人选,也造成佩佩的身份认同困境与身份迷思。
美国心理学家艾里克森在关于人的心理社会发展论述中,将人的青春期视为人生心理发展的关键中的关键。此阶段发展关键是完成“自我统合”(ego identity),容易产生的心理危机是“角色混乱”(confusion),发展顺利体现为自我观念明确,追寻方向肯定,能够多层面完成关于“自我”问题的思考;发展障碍则表现为彷徨、方向迷失,自我认同困惑,进而产生与年龄、角色不相符的行为等问题[3]。浩瀚的青春影像,业已深入表现或探讨过这些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描述依赖暴力与性获取成人身份感的残酷青春群像;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到陈果的《香港制造》,突出香港青年的青春迷惘;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分别探讨青少年地域身份认同与性别身份认同问题;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直接揭示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自我蜕变的苦痛;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少年依靠占有单车实现扭曲的身份诉求;《过春天》亦有讨论佩佩的身份迷思。在《过春天》的前半部分,佩佩更亲近香港的父亲,仅有的欢乐时光产生于香港校舍的天台。她在陷于困境时,也曾求助于父亲,但无论是因父亲的年迈还是困于原有家庭的无力,就像父女之间隔着的那面厚厚的玻璃墙,阻隔了佩佩,让佩佩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对方的生活,无法真正融入香港空间。佩佩也终究无法将自己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香港人,认同香港身份。与此同时,她也直接否认了自己大陆人的身份,这也与佩佩在电影前半部分跟母亲的疏离相一致。在深圳,佩佩与母亲较少出现在同一画面中,少有的同框画面也是俩人中间隔着厚重的墙,这样的镜头画面处理,直截了当地交代了母女关系的疏远与对立。在语言的使用上同样如此,佩佩常使用粤语(佩佩的父亲使用粤语)与他人交流,而面对母亲,佩佩则以“失语”的状态进行直接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