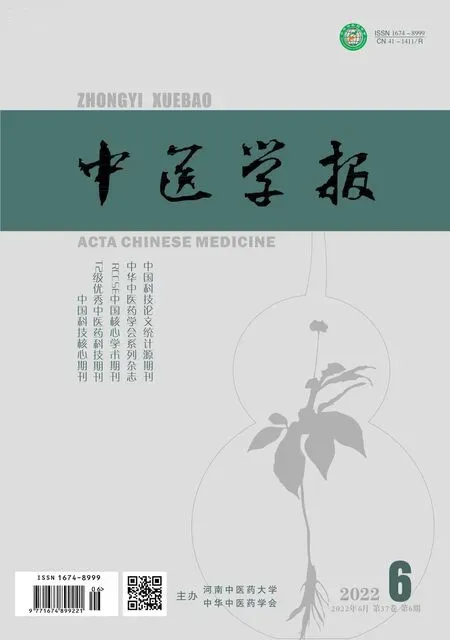《伤寒论》与《黄帝内经》关系研究*
2022-05-30屈杰陈丽名李小会
屈杰,陈丽名,李小会
陕西中医药大学,陕西 咸阳 712046
《伤寒论》与《黄帝内经》的关系十分复杂,不是简单的“有关”或者“无关”所能概括,无论何种结论,对于目前《伤寒论》的教学、临床、研究方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实事求是,以理性客观的角度去论证两者关系。
1 《伤寒论》存在误读的原因
《伤寒论》《金匮要略》年代久远,文辞简略,义理深奥,古今有别,加之传抄错误,即使不参考《黄帝内经》,本身就很难读懂。正如唐代医家孙思邈所言:“夫医方卜筮,艺之难精者也”。古典中医学深奥难懂是公认事实。在《伤寒论》的文本语句理解或者是研究方法(以经解论)方面,由于医家的价值取向、学术观点、临床经验、方法学的不同,很容易产生分歧。分歧不代表都是“误读”,若以自身立场、价值取向、学术流派来审视他人的观点、方法,就有可能认为别人在“误读”。这种情况在金元以后的中医学术发展中屡见不鲜。比如张景岳对朱丹溪养阴学说的批判、历史上的“寒温之争”以及伤寒学研究史上四大注本体系的辩论。至于是否是“误读”,笔者以为主要从结果、效验来分析,而不是单纯以方法学来衡量。清代医家俞昌认为[1]:“晋唐以来,代不乏贤,虽其聪敏,揣摩《黄帝内经》,各自成家,卒皆不入仲景堂奥,其所得于《黄帝内经》者浅耳”。显然,俞氏认为学习《黄帝内经》不够深入才导致了不能领悟《伤寒论》真谛。当今在伤寒学研究方面有影响力的专家如刘渡舟、李培生、李克绍、杜雨茂等十分推崇从《黄帝内经》解读《伤寒论》,且卓有成效。如刘渡舟以经络学说为基础[2],提出“六经是脏腑、经络、气化的统一体的六经实质论”,是应用《黄帝内经》解读六经的成果,也是对六经本质的透彻诠释。伤寒学的研究历史,实际就是与《黄帝内经》融会贯通,“以经解论”“以论证经”的历史,但也不可回避,立言愈多,争讼不断,若思考缺乏见地,反致其理愈涩。
2 《伤寒论序》是否张仲景所写
目前全国的大部分《伤寒论》教材、专著对《伤寒论序》未提出疑问,认为从序言中可以了解到仲景学术渊源[3]。冯世纶[4]认为,从“笔调韵律”角度分析,《伤寒论》序言前半部分“韵虽不高而清,调虽不古而雅,非骈非散,的是建安”,而后段从“天布五行”句开始,笔调韵律有所不同,得出了序言后半段是王叔和补撰写的观点。此观点看似正确,其实值得推敲。首先,从语言文字来讲,《伤寒论》采用汉代散文体为主,个别地方有骈偶文体。序言中前半段是以散文为主,夹杂少量骈偶文体;后半段(从天布五行开始)以骈偶文体为主。若以此认为后半段属后人补写,实际上是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语言文字不了解所致。序言中前半段叙事夹杂议论,故散文多,骈偶少;后半段议论多,故以骈偶为主,有利于抒发感情,这是表达需要,与所谓“晋音”关系不大。况且《金匮要略》中也有以骈偶为主的句式,如《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8条“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大量使用骈偶句。此外,所谓“晋音”考证也没有公认的标准,比如唐代的李白、韩愈也可以写古体诗,但不能认为他们生活在秦汉。唐代的文言文与明清文言文也没有本质区别。韩愈的《师说》能否从文字证明是唐代的而不是明清的?再者,出于对古人先贤的礼敬,受儒家思想影响,王叔和补写《伤寒论序》的概率不大。此外,“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腑腧,阴阳会通”句与《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中的“夫人禀无常……经络受邪,入脏腑……”也有相通之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伤寒论序》是后人补写的观点不成立。
3 《伤寒论》六经与《黄帝内经》六经的关系
六经以及六经辨证是《伤寒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六经即三阴三阳,具体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伤寒论》中没有六经名称,只有具体内容如“太阳病”“三阴”“阳明病”等。从现存古典医籍来看,“六经”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现代伤寒学家杜雨茂总结《黄帝内经》之“六经”有4种不同的含义:指代脏腑和经络、指脉、指气化、对热病证候的归类[5]。仲景书中的六经基本上也是《黄帝内经》六经含义的体现。比如《伤寒论》中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是对外感病的证候或者阶段的分类,但是其源流仍然与《素问·热论》一致。《伤寒论》中“太阳病”更多的是病理概念,是对疾病病位、病性、病情阶段的概括,但是病理与生理密切相关,离开了太阳经、阳明经的生理功能,不可能对太阳病、阳明病有深刻认识。《伤寒论》中的六经也常用于指代脏腑经络,如《伤寒论》第124条在解释太阳蓄血病成因时候提到了“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提示外邪不解,循经入里,瘀热内结下焦是其病因。此外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也是在应用经络理论解释疾病。仲景不但应用经络理论解释病情传变,还用于治疗疾病,如《伤寒论》第37条言“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因为胸满胁痛与足少阳胆经“过季胁,行身之两侧”的经络循行路线有关。此外,太阳病中的头痛、项强、腰痛以及少阴病中的咽痛、心烦等症状都可以较好地应用经络理论解读,而且千百年来也在指导临床实践。仲景还特别重视应用经络理论指导针刺治疗疾病,比如《伤寒论》中太阳病针刺风池、风腑;阳明蓄血刺期门;热入血室刺期门等。总之,仲景之六经具体所指与《黄帝内经》基本一致,说明仲景六经与《黄帝内经》有密切关系。
总之,《伤寒论》的六经以及六经辨证都与《黄帝内经》有千丝万缕联系。正如程门雪所言[6]:“六经本质必须承认经络学说,必须承认其与《素问·热论》六经的一致性”。黄飞[7]认为:“虽然不能肯定《伤寒论》之六经本质即为《黄帝内经》所论之六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黄帝内经》之六经是《伤寒论》六经之核心要素”。张仲景正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融合了医经派、经方派的经验,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
4 《伤寒论》“伤寒”与《黄帝内经》“伤寒”的概念
“伤寒”一词在《伤寒论》中主要是狭义外感风寒病的代名词,伤于寒邪,感而即发的病证。在《黄帝内经》中“伤寒”是伤于寒之意,是病因学的概念,与之对应的疾病名是“热病”“温病”。如《素问·热论》言:“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可见言伤寒,是从其病因;病温热,是从其病态[8]。仲景书之“伤寒”与《黄帝内经》“伤寒”侧重点不同,但含义没有本质区别。仲景所论述的暍病、痉病、湿病、温病、伤寒、中风都是外感热病具体分类。因此《伤寒论》中的“伤寒”也是多种外感病的统称。
5 《伤寒论》与《黄帝内经》诊疗方式比较
《伤寒论》属于中医临床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属于中医基础理论,不具有同质可比性,但是若干细节问题,可以有所讨论。《伤寒论》的诊疗方式是辨证论治。笔者认为,若从全篇来细看,至少有三种诊治模式:一是辨证论治;二是方证辨证;三是经验治疗。其中《伤寒论》中主导的是方证辨证,即通过患者脉象、症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称为“象”,采取对应的方剂治疗。《伤寒论》中提到的“桂枝汤证”“柴胡汤证”就是方证思维表现。但是方证思维中也蕴含着辨证论治思维,方证辨证是辨证论治早期的简化形式[9],二者并不冲突,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方证辨证中也包括《黄帝内经》的审因思维。比如《伤寒论》第51条言:“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结合仲景之“风令脉浮”观点,可以推断此条主要是风寒袭表,故用麻黄汤发汗祛邪。《金匮要略》中的“诸病在脏者,随其所得而攻之”也是审因治疗的体现。清代医家程钟龄从八纲辨证角度简化了对六经辨证的认识,但并不意味着《伤寒论》就不讲脏腑病机、气血、阴阳。比如仲景在解释桂枝汤证病机时提到了“阳浮阴弱”,治法提到了“调和营卫”,这是对《黄帝内经》阴阳、营卫理论的应用。在生姜泻心汤条文中提到“胃中不和、胁下有水气”;在小青龙汤条文中提到“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以及第277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都是脏腑病机的阐述。
近些年,关于《伤寒论》与《黄帝内经》所代表的学术流派成了研究的热点。任灵贤[10]根据《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医经”与“经方”家的记载与西晋针灸学家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言》中“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经》为十数卷,用之多验”以及现代出土文物《辅行诀》二旦四神方与仲景方剂比较,认为仲景经方源于《汤液经》古方。这一观点也逐渐被主流医家所接受,部分学者因此提出了经方学派与医经学派在理论实质上存在明显差异[11],继而为《伤寒论》与《黄帝内经》无关的论述埋下了伏笔。先秦古典中医学著作大量失传,仅仅根据上述观点就证明两者无关,理由不充分。况且从目前整理的《辅行诀》内容来看,其实际上是经方与《黄帝内经》脏腑辨证、五行学说相结合,说明经方与医经的相互融合是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
此外,《伤寒论》与《黄帝内经》都普遍运用了中医学阴阳、脏腑、经络,以及药性理论,显示了两者同源性,这一点在《金匮要略》中尤为明显。这里还需要界定两个概念,一是《伤寒论》;二是伤寒学。《伤寒论》强调的是仲景的文本内容,伤寒学是以《伤寒论》为载体,经后世医家不断发展形成的学问或者学科。从文本来看,《伤寒论》与《黄帝内经》关系更多的是内在的联系,不是直接的引用关系,这是因为两者性质不同。从方法学来看,后世医家如王叔和、成无己、朱肱等应用《黄帝内经》的经络理论、标本中气学说以及开阖枢学说来阐明《伤寒论》六经内涵或者六经辨证规律,丰富了伤寒学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从多角度理解《伤寒论》,但是客观上也导致了争论不休,引发了后学者莫衷一是的局面。但不能因此否定《黄帝内经》理论在《伤寒论》研究、应用方面的价值。任何一种学说、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完美地解释、解决所有问题,这是科学发展史基本的历史观。经络理论在解释外感病传变时,所遇到的“传足不传手”,便是其局限性的体现。正如此,后世才进一步引入“气化”学说、“标本中气”学说进一步来解释六经辨证。
总之,抛开《黄帝内经》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单纯从八纲辨证不能反映疾病本质,更不能动态地观察病情变化。比如里寒证代表的方药有桂枝汤、理中汤、四逆汤、真武汤等,完全抛开脏腑病机去“但见一证,不必悉俱”的选方治疗,难度会很大。况且,《伤寒论》条文十分简洁,离开了“以方测证”“以药测病”病机模式推断,也很难用好经方。
6 总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主,病分三阴三阳,治疗以方证相应为主,强调脉证并治,方证相应。无论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形成渊源、伤寒、六经的概念,抑或是扶阳气、保胃气、存津液的治疗思想以及方证辨证中所体现的辨证论治思想,无不与《黄帝内经》中阴阳、脏腑、经络、病机、治法理论有密切关系[12-13]。简而言之,两者是继承与发展关系,完全抛开《黄帝内经》学术理论去研究《伤寒论》是行不通的,或者说很有可能走上类似于日本汉方医学的道路。同时,机械地、不加选择地应用《黄帝内经》的理论去解读《伤寒论》同样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