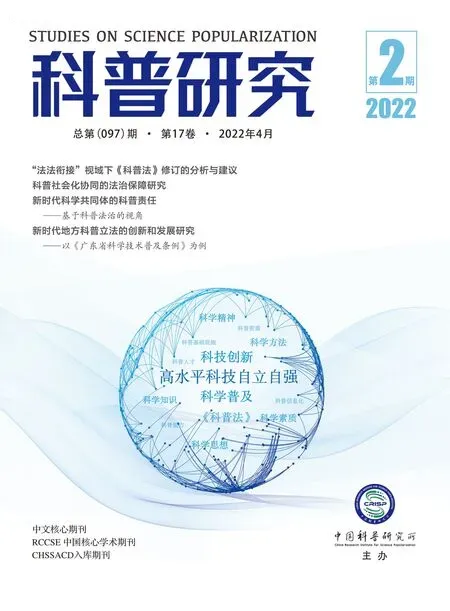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科普法》修订的理念与范式
2022-05-27胡印富
[摘 要] 新时代我国科普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一部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科普法》提供制度保障。韩国、日本、美国及欧盟各国虽无科普专门法律,但依照相关法律制度在依法推进科普工作方面,已有成熟经验。从比较视角和中国的科普国情来看,《科普法》的修订从基本理念上,应当采取纳入型模式,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立法;从目标立场上,将国家创新战略作为新的目标,增加体现公民的数字素养、信息素养等能动科学素质要素;从范式转变上,构建促进型立法结构的调整,发挥科协在协同科普中的优势功能。
[关键词]《科普法》 纳入型立法 创新战略 公民科学素质
[中图分类号] D908;N4 [文献标识码]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22.02.009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1]这一重要指示精神为新发展阶段的科普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作為我国科普领域的专门法律,为科普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科普法》实施已近20年,科普的内在构造、立法理念、治理体系、运行机制等在此期间均发生了深刻变化,根据实践发展变化对《科普法》进行全面修订,已经势在必行。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学界也不断呼吁修订《科普法》,“进一步明确其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形式、履行方式、承担的责任等”[2]。2021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修订《科普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科普法》修订迎来了新的机遇。修订《科普法》是对科普制度的顶层设计与系统完善,既需要主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也需要兼顾科普法律体系的自洽性与协调性。国外虽无专门的科普法,但在科学普及的宏观理念与具体制度方面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例如,韩国、日本形成了 “宪法—科技基本法—具体法” 的层级化科普制度体系,美国及欧盟各国通过分散式立法、集中型政策系统规定了科学普及的理念、目标与范式。当前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馆、科学教育、科普活动等内容的比较借鉴,尚未从科普法律角度切入。鉴于此,本研究以韩国、日本、美国及欧盟各国科普相关的法律制度为视角,从基本理念、目标立场、范式转变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探讨,以期为我国《科普法》的修订提供有益参考。
1《科普法》修订的基本理念
基本理念是探究法律理论和修正法律体系的出发点,黑格尔将法律理念定义为法的概念与现实化[3],美国法理学家霍菲尔德(W. N. Hohfeld)进一步将法律概念限定为法学领域中基本范畴。《科普法》修订的基本理念就是明确科学普及的法律调整范畴,为完善科普法律提供方向遵循。现行《科普法》第二条界定了科普构成的二要素:普及主体与普及内容(“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但是定义中没有明确《科普法》的调整范畴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通过第二章“组织管理”确定的行政机关与主要社会力量,可以推定现行《科普法》的调整范畴为自然科学。由此可知,我国《科普法》基本理念采取了单一模式。法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理性主义自然法体系与反思性实在法体系的博弈过程,最终回归到建立“体系性法学”[4]内在转变中。科学技术推动下的自然法学说促使现代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转变,重塑了法律世界观。毫无疑问,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的《科普法》在科技推广、技术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体系法学的角度看,建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科普法》同样有着时代使命。本部分以融合式立法的典型代表国家韩国与日本的科技法律制度为参照,阐释我国“大科普”立法理念的构建。韩国、日本关于科普的相关制度采取了分散立法模式,见诸“宪法—科技基本法—科技具体法”各类法律之中。分散式立法模式通过基本法体现科普立法的基本理念,以具体法贯彻理念要求。
1.1 基本理念的域外考察
1.1.1韩国《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均衡发展理念
在科技领域,韩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韩国以宪法为根本法,以《科学技术基本法》为基本法,以《技术开发促进法》《合作研究开发促进法》《技术师法》《科学财团法》等为具体法。2001年,结合科技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国内需求,韩国政府在对《科学技术振兴法》《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两部法律进行整合、吸收的基础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该法成为韩国在科技领域推动技术创新、科学普及的基本法。在此期间,经过28次修订的渐进积累,现行《科学技术基本法》共5章36条。
韩国通过基本法形式确立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衡发展理念,具体体现在《科学技术基本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二条规定了理念内涵,指出本法的基本理念是科技创新以人类的尊严为方向,实现自然环境和社会伦理价值的和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尊重科学技术人员的自由性和创造性,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联系和均衡发展。第三十条细化了科普内容,该条文共包括七项内容,从人才培育、学术振兴、财团保障等多方面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普及做了具体规定。《科学技术基本法》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政府为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建立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体制,设立韩国科学创新财团。为落实《科学技术基本法》的规定,韩国又专门制定了《科学财团法》,在第一条立法宗旨中明确了振兴科学文化教育的理念要求。这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普及创造了强有力的财团保障。
1.1.2 日本《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的和谐发展理念
日本于1995年制定了第一部科技领域的基本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该部法律成为指导科技法律体系的核心制度。2020年,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修正案,修订后的法案更名为《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确立了新的基本理念与基本框架,成为科技政策、科技法律的根本指引。日本对沿用了25年之久的《科学技术基本法》的修订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增加社会科学内容;二是提升创新能力。与此相应,在其指导下制定的基本计划,由“科技基本计划”更名为“科技创新基本计划”,增设振兴社会科学领域的内容。
《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第三条规定,“在振兴科学技术方面,要在广泛领域中均衡培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开发研究能力的协调发展,必须考虑国家试验研究机构、大学(包括大学院,下同)及民间团体的有机合作。同时,应当充分重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联系对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必须注意两者的和谐发展”。基于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社会伦理与制度层面的新问题,以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建立有韧性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新需要,社会科学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科学技术基本法》的修订旨在推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跨域融合发展[5]。修订后的《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第十七条要求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交流。为贯彻落实《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的和谐发展要求,《技术创新激活法》增加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独立行政机构。同时,日本内阁于2021年公布的《第6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中提出,要强化日本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e-CSTI)的政策制定功能,实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战略评价标准。
1.1.3 制度演进的规律借鉴
通过梳理韩国、日本科技法律制度的体系内容与制度变迁,提炼出以下两项值得我国《科普法》修订借鉴的规律。第一,建立科学普及的层级化制度。从法律文本体系看,韩国、日本在科技领域的法律文本形成了“宪法—法律”向“憲法—基本法—法律”的层级化科普制度体系的转化。宪法是科学普及的根本法,通过设置基本法表明科学普及的基本理念、基本方针与推进措施,基本法有引导行政政策的功能。行政部门在基本法发布、实施后,以基本法为导向制定更具体的行政法律规则体系。第二,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韩国、日本的基本法的修订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法律嵌套,凸显两者知识交叉、优势互补、理念共享的协同发展观。
1.2 我国《科普法》修订的理念建构
法律理念是形塑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基石,立法内容要尽量避免制定法律理念不确定的条文。《科普法》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规定的缺位,既制约了社会科学的有力普及,也影响了科学普及的整体效应。借鉴韩国、日本的科普法治经验,结合我国科普工作实践探索,建立有序的科普法律体系,实行“大科普”理念,在我国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本文主张以科普法秩序推进我国科普立法理念变革。科普法秩序是指按照科普法治精神和形成健全科普法律体系的要求,基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性,建立科学普及的共同法秩序。
1.2.1科普法秩序建立的可行性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根本要求。从与《宪法》的关系看,《宪法》是《科普法》的母法,《科普法》是《宪法》的具体实施法。《宪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宪法》对科学的界定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普法》作为指导科学普及行为、规范科学普及权利、约束科学普及义务、明确科学普及责任的统筹性法律,对科学普及起到固根本、稳预期的效果。因此,科学普及之“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宪法》的要求。这是科普法秩序建立的宪法依据。
第二,现行《科普法》的应然之意。现行《科普法》第二条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四科”作为科普内容,其中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社会科学普及的内容是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人文精神,现行《科普法》关于科普的内涵规定实际已经体现了对社会科学普及的要求。这是科普法秩序建立的法律依据。
第三,地方立法的实践探索。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普及的地方立法开展了较为丰富的实践探索[6]。截至2022年2月,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统计查证,目前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的现仍具有法律效力、单独规制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共计14部,单独规制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共计25部,地方性法规中融合立法的有5部(包括天津、辽宁、四川、浙江、重庆5个省级行政区)。地方性法规的探索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别立法为主流,成为其他地方开展科学普及立法的应然之选。但是分别立法模式呈现出严重的趋同化现象。趋同化现象是指自然科学普及与社会科学普及的地方性法规在总则、普及形式、组织管理、社会责任、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内容重合,除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和普及内容有所差异外,其他方面几乎无明显差别。同时,因《科普法》未明确社会科学普及事项,地方性立法依据采取抽象表述,即“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地方性融合立法模式为《科普法》修订提供了经验,单独立法的趋同化与立法依据抽象化问题,也亟待通过上位《科普法》的修订解决。这是科普法秩序建立的经验依据。
第四,学科研究的知识融合。科学研究最终要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共通之处。随着研究的深化,两者之间的交叉越来越多,自然科学的普及离不开社会科学方法,社会科学的研究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7]深刻论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根据重叠影响阈理论(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8],两者对科学普及产生了交互叠加的影响。这是科普法秩序建立的现实依据。
1.2.2科普法秩序建立的操作性
从内容体例上看,韩国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日本的《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类似于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以下简称《科技进步法》)。相较于韩国、日本分散的立法方式而言,我国具有专门的《科普法》作为《宪法》与《科技进步法》的衔接,这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但是相较于韩国、日本阶层化的立法体系而言,我国还缺乏对科普法律体系的明确定位。因此,在《科普法》修订中,首先要明确《科普法》作为引领科普工作的行政“母法”地位。“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法治化进程,已经日益成为社科普及领域治理的普遍共识”[9]。确立《科普法》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统筹指导,既有利于完善科普法律体系,也有利于地方社会科学立法制定有法可依。《科普法》修订完成后,一体化推进实施细则的制定,形成我国特有的“宪法—基本法—专门法—部门法(细则)”科普法律制度体系。就立法模式而言,本文否定二元立法论,主张采用纳入型立法模式,将社会科学普及事项纳入《科普法》调整范畴。在《科普法》中对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协同普及、经费保障、法律责任等内容做出系统规定。
2《科普法》修订的目标定位
根据马克思人类活动的目标理论,人类行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的”[10],确定立法修改的目标立场实质是人类有目的的理性行为。立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立法目标是国家治理目标的彰显。立法目标是动态发展的,会随着国家目标的调整而优化升级。2002年颁布的《科普法》第一条将立法目标定位于人的发展(公民科学素质)与国家发展(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两个方面,经过20年的发展,公民科学素质有了明显提升,国家在科技领域提出了新战略,这为我国修改立法目标提供了新定位。域外关于科普立法的目标也主要基于上述两个方面,这是与我国《科普法》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目标内容与具体实施方面。
2.1 科普目标的域外模式
2.1.1公民科学素质
英美等国作为科学技术领先的国家,在科学普及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英美等国以习惯法作为规范秩序的基本逻辑,没有专门科普法律。相关内容散见于各类制度文件中,本文将之作为英美等国科普法律的渊源。纵观英美等国科普法律的渊源,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始终是其制定、调整、变革的重要目标。
科学素质的内容是动态调整的,英美法系学者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1983 年,美国学者米勒(J.D.Miller)首次提出了科学素质的三维模式(科学本质、科学知识、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2 年,博尧德(S.BouJaoude)提出了科学素质的四要素:科学知识、科学本质、科学思维、科学和社会的互动[11]。后来,又有不同学者相继提出了对科学素质结构的不同认识,如鲁佛的“五要素说”、恩哲的“六要素说”、沙瓦尔特的“七要素说”[12]。
学界对科学素质的研究推动了科普与教育相关法律政策的发展。以美国为例,美国通过多元分散的法律模式突出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地位,强调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目标导向,推进科普与教育的融合发展。除了在联邦宪法中规定公民享有科学文化的权利外,各州依据其公共科技、文化服务机构等具体情况,制定相应州的宪法、行政法、判例法,细化公民科学文化权利的内容,明确对公民科学素质的培育。在培育方式上,美国高度重视科学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的作用。《新一代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是全美国科学界与教育界的精英制定的一部国家级科学教育标准。该标准为公民科学素质目标的实现提出了具体要求,重点聚焦公民科學素质实现的实践性、跨学科性与学科核心概念性的三维路径。以欧盟国家为例,欧盟国家的法律政策始终将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作为价值目标。《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中明确了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公民社会权利的重要组成。2019年,欧盟议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又发布了《作为教育挑战的科学和科学素养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科学素质的内涵进行了适时调整,强调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理性决策的能力。同时,建议欧盟各成员国在教育政策法律中进一步明确培养公民科学素质的目标要求,重视数字化转型、终身教育等背景下公民科学素质的内容调整。德国的《基本法》将科学素质视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组成,在《基本法》的指导下制定了《国家教育标准的开发》,又称为《Klieme框架》,作为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的纲领性文件。
2.1.2 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
域外国家将科学普及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分别提出了国家竞争力、国家创新等不同国家战略观。第一,国家竞争力战略。以美国为例,《2010年美国竞争再授权法》将科学传播教育视为国家竞争力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美国制定了落实国家竞争力的专门举措,例如,针对科学普及、科学教育制定了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法案。2018年,美国《STEM教育战略计划》提出,STEM教育与国家人才战略、工业4.0时代的需求、未来公民素质等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教育的普及事关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第二,国家创新战略。以欧盟为例,欧盟的法律政策以国家战略高位推动科学普及,例如,瑞典制定了《研究与创新法案》,指出科学普及是国家创新战略体系构成之一。丹麦科技、技术和创新部颁布《大学新法》,规定大学在国家创新战略中的传播作用,促进大学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以大学为载体的研究成果传播。德国作为公众参与科学的典型代表国家,在《公众科学战略2020》绿皮书中明确提出了公民参与科学的国家战略愿景。
2.1.3目标模式的域外借鉴
域外科普法律法制的目标定位以人的提升与国家发展两大要素为主导,既突显了科普的应然价值,也体现了对科普事业系统指导的实践价值。从域外目标模式发展来看,得出以下两点规律。第一,妥善处理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基于人的提升视角,也是《科普法》修订需要调整的关系。无论是科普方式的变化还是科学素质内涵的争论,本质是科技与社会关系的矛盾关系演绎。从知识灌输式科普到公众参与式科普的变迁,从认知科学素质到行动科学素质的转型,深刻镶嵌着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科技权利的追求。第二,提高科普目标定位。现代社会的竞争体现在综合国力上,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竞争力。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教育)对科技竞争力提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英美法系国家通过优化科学普及政策、加大STEM教育财政投入、建立社会团体协同普及机制等系列举措,最终实现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根本目标。
2.2 迈向国家战略的目标定位
相较于域外科普战略定位而言,我国同样提出了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我国《科技进步法》第二条明确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为《科普法》修订提供了本土经验。通过立法形式贯彻国家创新要求,以法律护航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要求,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内在遵循。对此本文主张,对《科普法》第一条做如下调整。
一方面,增加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世界各国对科技发展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科学”(science)、“科技”(science and technology)再到“科技创新”(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的演进,创新在科技领域的作用更加突出。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加快创新薄弱环节和领域的立法进程,修改不符合创新导向的法规文件,废除制约创新的制度规定”。科普立法的目标定位建立在对科技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13],因此应当把政策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从域外经验看,国家战略既要体现在立法目标中,也应贯彻于具体制度内容中。从立法目标中,增加创新发展的战略要求。以创新战略的高度,在具体内容中增加科普创新方式(如数字科普等)、创新力量(如新媒体等)、创新教育、创新投入等要素。
另一方面,丰富公民科学素质内涵。从域外科学素质研究的发展可知,素质具有变动性与决定性。科学素质的内涵与国情世情的变动相关联,同时科学素质决定了科学教育的内容。从我国科普立法看,当前《科普法》规定的科学素质“四科”内容,呈现出一定的平面性。平面性的科学素质是指重视科学知识单一性,忽视公众全面参与科普活动的主体作用。同时,科普与教育的融合程度还不够深入。现行《科普法》中只有一条内容强调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把科普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
鉴于此,需要在立法中进一步丰富科学素质的内涵。结合域外探索,本文认为,公民科学素质内涵的修改应当紧密结合《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要求,适度增加或体现公民处理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创新能力、符合时代要求的数字素养等内容。在立法修改中,增加科普与教育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丰富科普形式。
3《科普法》修订的范式转变
最早由美国哲学家库恩(Kuhn)在自然科学领域提出的范式理论,如今已经衍生至法学领域。“范式”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14],已经产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随着客观情势、主观认知的变化会产生新的范式,这就是范式转变。科普法律供需关系的认知变革: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主位场域到客位反思,推动了科普法律范式的转变。如何更好地让公众主动接受科普、推动综合科普、恰当发挥各方力量作用,是《科普法》修订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现行的《科普法》还存在稀释科普概念、弱化科普原则、泛化普及方式、柔性化法律责任等结构性不足。基于此,本部分借鉴域外促进型立法结构与协同科普体系等方面的经验,探究我国科普法律制度的范式转变。
3.1 管理型到促进型立法的结构调整
域外科学普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以促进型立法为主。促进型立法是指以推动与促进某一领域的发展为主要目的[15],以引导、鼓励、扶持、奖励为主要手段,采用倡导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的设范模式。以韩国立法为例,韩国《科学技术基本法》除总则内容外,其余四章分别为“科學技术政策的制定及促进体制”“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增加科学技术投入与人力资源”“增强科学技术基础及营造创新环境”,立法中的核心内容为“促进”与“增加”,更多地强调政府在科学普及中的服务保障职能。从财团制度上,《科学技术基本法》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政府为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建立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体制,设立韩国科学创新财团。明确财团性质为法人,规定政府在必要时可以不履行《国有产权法》的规定而按照总统令的规定向财团无偿转让国有资产或贷款。同时,韩国又专门制定了《科学财团法》,该法第五条规定财团的职能之一为促进科普与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十三条规定了财团的政府出资与无偿贷款方式。又如,日本法律制度为了促进科学普及,设定了《图书馆法》《博物馆法》《儿童福利法》等,通过福利型立法内容保障了公民享受科学权利。
管理型立法着眼于公权力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的调控管理效能,立法模式以任务配置、管理约束为主要内容,在权利保障与问责机制方面内容偏少。与域外促进型立法模式相比,我国现行《科普法》兼顾管理型与促进型立法,但主要不足是管理型内容多、促进型内容少。从现行立法框架看,管理型内容体现在组织管理、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等三章,以科普工作任务分配为立法表达方式。促进型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条,以国家鼓励、支持科普事业为立法表达方式。从法的功能看,《科普法》的重点是发挥对科普工作保障与促进的指引与评价功能,立法结构应当是促进型多,管理型少。因此,我国科普立法的修订应当侧重促进型立法范式。从立法内部看,要进一步丰富立法要素。增设科普标准、科普规划、素质评估等前置促进内容,细化财政投入、税收优惠等运行保障措施。从立法外部看,恰当做好制定立法与实施细则之间的衔接。在《科普法》实施细则中,具体化科普场所、科普主体、科学教育及保障机制。
3.2 公权中心论到公权主导下的科普协同体系
公权中心论以政府主体为中心推进科普工作,强调科普的供给本位。公权中心论过度发挥政府在科普工作中的单一力量,这种情形多体现于管理型立法结构中,各科普力量之间比较分散,呈现出“行政部门—社会力量”平行关系。公权主导下的科普协同体系,是发挥政府服务职能,通过整合社会力量推进科普工作。科普协同体系更侧重于公众教育需求,多体现于促进型立法结构中,各科普力量之间有机衔接,呈现“科技主管部门(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社会力量”交叉关系。随着政府的职能被不断分散或外包,公共机构越来越多地向外寻求合作[16]。加之公众对科普的质量、效率以及多样性需求,科普更需要公权主导下的协同科普体系。域外各国在科普协同体系上进行的制度探索,最突出的特征是以法律形式确立科普社会团体在科普工作中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以英国皇家学会为例,英国皇家宪章中明确了皇家学会的组织架构,于2012年由英国女王签署的补充宪章中,进一步更新了学会管理内容。再如,日本根据《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法》设立了国家级科技组织——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承担广泛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任务。
我国《科普法》第二章“组织管理”确立了“政府领导—科技部、行政部门分别负责—科协为主要力量”的科普工作体系,倾向于公权中心论,没有充分发挥科技部及科协主导作用。公权主导下的科普协同体系的本质是在新时代合作主义指导下推进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模式,强调政府、社会团体及社会力量在推进科学普及过程中能够对话、协商、共赢,从而实现科普事业发展的动态平衡[17]。
《科普法》的修订应当做出补强性规定,设置实定化的职责规定。可以进一步厘定科技部在科普工作中的牵头作用,明确科协作为衔接科技部与其他科普工作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中坚力量,赋予科协在协同体系中的中枢地位,从而发挥科普协同的功能优势。
4结语
立法者應当秉持前瞻性的立法理念,结合我国当前科普现状与工业4.0时代的发展要求,借鉴韩国、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和组织成熟的科学普及制度经验,特别是科技与教育(STEM教育)、社会科学、公众互动的关系,通过对科普立法价值的再思考,重新定位科普的立法目标问题。在立法技术上,明确科普法律制度的强制性规范与自治性规范的价值导向,突出《科普法》在科学普及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并对科普法律目标、范式、内容进行契合式修订。
参考文献
习近平.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任福君.新中国科普政策70年[J].科普研究,2019(5):13-1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
Wieacker F. 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unter besonderer Beru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Entwicklung[M]. Gottingen:Vandenhoeck&Ruprecht,2006:90.
鈴木,せいら. 科学技術·イノベーション基本法」へ:25 年ぶりとなる実質的改正の[J]. 研究技術計画,2021(3):345-355.
李涛.地方立法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J].理论月刊,2018(9):117-124.
新华社.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8)[2022-03-2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Epstein J L. School,Family,Community Partnerships:Caring for the Children We Share[J]. Kappan,2010,92(3):81-96.
刘宇.我国社会科学普及地方立法的动力、样态与趋向[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02.
冯翠典. 科学素养结构发展的国内外综述[J]. 教育科学研究,2013(6):62-64.
Showalter V. What is Unified Science Education?Program Objectives and Scientific Literacy[J]. Prism,1974(2):1-6.
贺德方,陈宝明,周华东.国际科技立法发展趋势分析及若干思考[J].中国软科学,2020(12):3-5.
郭晔.法理主题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2):55-57.
王晓.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文明行为地方立法现代化研究——以39 个设区的市文明行为促进型立法为样本[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21-23.
Hinings B,Gegenhuber T,Greenwood R. Digit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J].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2018,28(1):52-61.
李天民,潘雪婷,路欢欢.国外科普工作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传播,2021(13):17-20.
(编辑 颜 燕 袁 博)
收稿日期:2022-04-01
*作者简介:胡印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教育法治,E-mail:59793046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