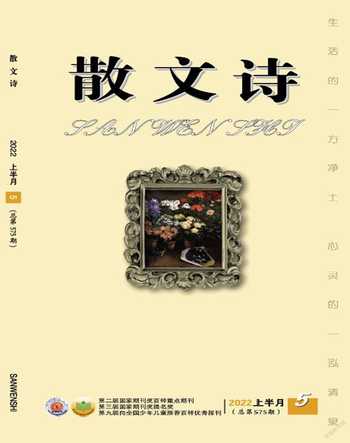无限的临终,或生命的组织可能性
2022-05-27师飞
师飞
评 论
1998年,苇岸在居所东边的田野上选取了一个标点。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在无限的临终之中,劳作已经不可追索,但可追索的是,从他踏进松软泥土的那一刻,从他感到肢体伸张、血液涌动的那一刻,他自身作为一个寓言化的标点已经显形;而那个让标点显形的肉身——那个无论自身晓得与否,都已经投身于临终状态的人——则开始着手为那些“一生从未踏上土地”的人,保存只可能在静默中熠熠生辉的“遗迹”。
一年之后,伴随着苇岸的离逝,那个闪烁的标点(在其中有一系列动作:观察、拍照、思想、记录)已脱离它借以显形的肉身,成为了一个等待点亮的寓言性触发机制—— 一处丰富的“遗迹”。不妨想想乔治·康吉莱姆,在他为“遗迹”供出的档案中,存在之物总是倾向于表达一种否定性,或者,存在总是倾向于在否定性中自我呈现。毋宁说,本真的生命本身就是以遗迹的形式存在的——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本真生存的人,他时刻能感受到自身的遗迹属性;他同时处于活着与死去的叠加状态之中,他同时居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他当然也因此能够记忆、体验和筹谋。而一个书写者——譬如苇岸,或譬如思之青——其行动在严格意义上就是在摹写这种遗迹。“遗迹”本身就是一种已逝之物的证明,一种因“无”而成其所是的“有”;无需从存在论意义上继续追溯就能看到“遗迹”本身在现象学维度的差异性结构。我们不仅在错误、病态、遗忘、告别、不安、叛逆之中感知这种否定性,也通过时间、天气这些外在因素确认其否定性。就此而言,主体是在与世界的相互指认中接纳否定性的—— 一个必死者(mortal)必然占据一席死亡(death)。
那么,生命的组织何以可能?如果说苇岸企图借《一九九八廿四节气》(以下简称《节气》)道出一个大地之子的生命低喃,一种基于连续性的对自然世界秩序的个体性收纳,那么,在《接近黄昏》中,“微小的死亡”则总是与不歇的黄昏意向性地达成耦合,将某种断裂的、更具人味儿(或许可以更准确、也可能更武断地将其界定为“女性气质”)的经验通过文字罗织于巨大无际的生命之流。
在体例上,我们基于“影响”一词就能轻松建构起《接近黄昏》对《节气》中所设机制的触发性继承。当然,一个有意识的写作者,总是致力于将自身纳入某种“影响的焦虑”之中,而这正是艾略特所主张的传统的力量。“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在创造一个作品,都是在源源不断地将一个作品进行不停息地复制、删削、改写、扩充、偏离、强化。”索性更直接一些,将《接近黄昏》视作对《节气》的一次致敬,这一致敬尽管依然遵循苇岸设置的体例,但它从根本上而言却又是异质性的。一方面,苇岸的定点(居所东边田野的一个恒点)、定时(上午9点)、定向(廿四节气)书写在思之青这里被改换为随机、随时、散射式书写;另一方面,生命的组织结构不再是连续而匀质的统一体,而是一个断裂的生发性指认过程——它总是在无限地临终之中涌现。
不妨稍作分析。随机在于,思之青的视线不是固定的,其意向性——我们在广义上使用这个现象学术语——不是指向某个点,而是随着一个幽灵般的主体在漫游,在变焦,在推拉;它几乎取代了作为作者的、本就建构而成的主体本身,进而投向可能的各处;譬如“融雪”、“墙壁”、“屋顶”、“浴室”、“顶灯”、“飞鸟”、“篓子”、“欲望”、“惊奇”、“胆怯”……我们完全可以跟随文本对此种意向性相关项划出一个巨大的范畴集合—— 一个充分个人化了的世界。在那里,一个主体得以被建构、被明确、被指认,而“她”——文本中的“她”——绝非作者本人,毋宁说是必死之人思之青(她究竟是谁?)的无限可能性标记。在这种书写的随机性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漫漶无极的意向性,而意向性背后是一个幽灵般的主体——“她”富含女性气质,是一个被建构的、处于瞬移之中的光标。至此,我们重新发现了之前我们提及苇岸时的那个标点—— 一个寓言化的触发机制。与其说思之青触发了那个被苇岸设置的寓言机制,不如说——更寓言性地——思之青借苇岸设置的寓言机制触发了自身;更直白地说,“她”在询问“她”是谁,她如何被语词编制,成为世界的一个节点。随时在于,与从容的苇岸所设定的“上午9点钟”相比,思之青则在一瓢一瓢地打捞世界的时间,据文本标记,每一次打捞都是一次筛选,“2020年2月17日下午4点:晴;2020年2月23日晚上9点:多云;2020年2月26日正午11点30分:阴,伴有短暂小雨……”这些不同的时刻俨然不具备统一性,但它们被罗织成网,这固然是因为同一个打捞主体,却更因为是同一个打捞主题——黄昏。时间因此同时成为主体和主题的一個索引,在同一个主题框架中,主体不停地变换身姿、变幻情绪,直至成为主题的一个构成性因素;同样地,在同一个主体支点下,同一个主题散落于不同的时刻,它们因为不具备连续性而成为一种象征性断裂,一种关乎话语本身和认知范式的提示。散射性就如同一种氛围弥漫于随机性和随时性之中。
那么,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散射性中究竟什么被揭示了?什么又同时被掩埋?当然是生命——作为“遗迹”的生命。
生命——无论它呈现为文本,还是具体的肉身——总是以偶发性单元的形式汇聚成死亡冲动。《接近黄昏》与其说是对黄昏意识的一个意向性投射过程,不如被视作一种生命体验和指认。“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不可捉摸的灵魂,它们隐于内部,也无时无刻不在向外部呈现。它们是流动的,扩张的,隐忍的,没有形态的,但同时也在含蓄中收拢起无限。”如果说这种对“存在”的体认同时标明了“缺席”,那么,对“缺席”的体验同样也标记了“存在”——“现在,正是向黄昏趋近的时候,如同某种带有色泽的水流、棕黄的流沙,或是碧绿的湖水,它们向生活的某个中心,不确定的中心部分蔓延,缓慢而幽深地灌入最浓郁的地方。”可以说,在存在本身的结构性差异之中,生命本身的结构被标记——它作为一种活力涌现的遗迹,不断经受着意识的投射。
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床上”,无论是“听鸟鸣”还是观街景,视阈始终被严格地限定在一个生死框架之中。作为经验主体的生命体乐此不疲地向失落的可能性敞开,只有在这种失落中,生命的活力(它当然可以被简化为作者的感受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一个失落者、一个行路人、一个听风者、一个打开黑夜者……归根结底,一个接近黄昏者,它本身就是一个疾病的幻影,它比常人——想象海德格尔所谓的查无此人、从无此人的常人,总是沦陷于闲谈和两可的常人——更负有对生命的责任。一个接近黄昏者当然也是一个深入生命内部——死亡根部——的人,死亡冲动和黄昏意识反逻辑地促成生命体认,这就是为什么生命的组织总是在它陷入自身困局之时才表现出来,并且也将不可避免地跌倒在——它注定隶属于其中也将永续轮回的——边界之上。如此则可以申言:生命的意义恰好就深深扎根于它的不安抗辩与临终关切之中,就潜伏于它的未完成状态之中。
经验世界中的主体是如此不稳定,如此易碎,以至于只有获得一个内在的根部才能立稳身形。一种生命的组织可能性出现了,生命的维持不是被外界规范,而是奠基于自身的不安和未竟。简言之,生命的组织可能性就在于生命本身的无限可能性——它总是在两极之间自我矫正、自我规范。于是也可以说,生命的完满之处恰好在于自身先天性的不完满,它犯错、生病、健忘、惶恐不安,它总是接近黄昏,并面临死亡的永久威胁,但它时刻都能自我修正、自我界定、自我规范、自我诞生。世界不是施加于人的巨大怪物,而是——恰好相反——人从自己身上奇迹般地创造了世界。
这种创造无疑是在对肉身性自我的抛掷和对黑暗——无论他是物质性的还是意识性的——领略中实现的,生命因而总是呈现出另一个维度,它不是在既定规范之中,而是在一种界限上涌现。“这世界,/依然有美好的事情。/黄昏。”(詹姆斯·赖特《试着祈祷》)是的,黄昏,它作为一个临界范畴,不只具备物理性,也——更要紧地——具备精神性;黄昏——作为一个词、一种氛围、一种视阈——始终在揭示一种临终状态,它同时包含着白天与黑夜、生命与死亡、存在与缺席。这种差异性结构的魅力在于它始终是一种召唤而非拒绝,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确定性,一种潜能而非现实。而“接近黄昏”就是接近召唤、接近可能性和接近潜能。
生命的意义是一种只有靠失去才能赢获的珍惜之物,而让其存在于一种永续的临终状态,一种无限濒临消失的状态,一种弹性十足的未完成状态,无疑便是唯一可能的胜利姿态——在据有之中丧失,在消逝之中存留。那正是黄昏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