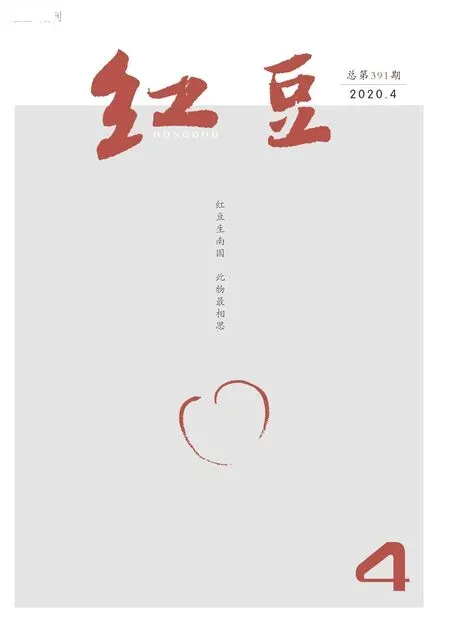货郎旦:九转太平二重奏
2022-05-26宋长征
宋长征
立秋死了。田野、屋瓦、枯草上落满白霜。驼子二叔坐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手拿着那只圆圆的拨浪鼓,鼓身是红色的,油漆斑驳,鼓面是黄白色的,透出一种牛皮的韧。别人的拨浪鼓只有一面小圆鼓,而驼子二叔的是特制的,特意在定制的作坊里要求人家在上面再加上一面小些的,这样摇起来声音更为丰富,像是鼓的二重奏。虚空或冷意,让驼子二叔打了一个寒战,面前闪过立秋灿烂的笑容。立秋笑起来很放肆,好像不把整个世界放在眼里,或者已经完全忽略了其他的存在。驼子二叔也不嫌,笑就笑嘛,为啥要绷着?皮笑肉不笑、嘴笑牙不笑都不是好笑。想到这里,驼子二叔也就笑了起来,好像原本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一边笑,一边摇着手中的拨浪鼓,慢三快五,拨浪鼓的二重奏响起,惊散了大雁南归的阵型;笑声苍凉,越过院墙,越过老河滩,好像那遍野的白霜都是被笑声震落下来的,落在枯草断茎上,还在簌簌发抖。
货郎这个营生,起源较早。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勾栏瓦肆、乡间里弄,会经常游走一些货郎身影。你不能说他们有多富,大富之家哪有做这种走街串巷小生意的?一定是身板太弱,像驼子二叔这样的人才做。驼子二叔从小身子骨就不好,大爷爷思来想去,干脆找木匠做了一辆木牛车,左边放一些乡间时兴的布料和针头线脑,右边放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日用品,前面放了一只分为两档的小木箱,一档里是小孩爱吃的米团、麻糖、螺丝糖,一档放乡间女子常用的胭脂水粉、手帕、木梳、小镜子,装扮后木牛车就成了流动的百货商店。
刚开始还不适应,驼子二叔说车有点重,推起来在乡间小路上侧不楞的。时间长了就好了,木牛车的车把就像跟手臂长在一起,甚至有时候,驼子二叔把襻带挂在脖子上,竟能一只手稳稳当当地推车,另一只手腾出来,没到村庄就摇起了拨浪鼓。这鼓好似催阵鼓,好似远方情人的心跳声,一点点接近,一声声越来越响亮,听得人心里毛毛躁躁的。居家女人听到了,就想起纳鞋底的线绳快没了,寻了平常积攒的破布烂麻团,拿去以物易物;大姑娘听到了,想着哪日跟后村的青年约好一起去镇街看电影,香香的雪花膏没了,不能不添置一包;小孩子听到了,他们这样的年纪,鼻子底下长个嘴,就知道吃,米团、麻糖、螺丝糖也能打打馋虫,再不济也要买上一包透明的糖精粒,再用汽水瓶子兑水、兑醋时放进几粒,就成了自制的土饮料。
立秋是后来才跟驼子二叔的。那时驼子二叔已不算年轻,小四十了,卖货走到梨花寨。梨花开得正浓,一片一片云样的梨花在树上飘。他走到梨树下停住木牛车,拿起手中的拨浪鼓,刚想摇,就听见一扇门里有弱弱的喊声:卖货郎的,你过来。驼子二叔就弓腰驼背走了过去,透过门缝,他看见立秋瘫在地上。立秋是个瘫子,她跟二叔早就认识,只不过是媒人带着匆匆见了一面,再没有了下文。这时立秋的父母已经故去,从她脱在地上的鞋子就能看出,布鞋头缀了一小块白布,说明老人刚走了没多少时日。父母走了,瘫子立秋没有人照应,驼子二叔自作主张,把一边的油盐酱醋挪到另一边,再把立秋放上去带回了家。
为了方便,驼子二叔又找木匠把木牛車改造了一下,独轮车变成了双轮车,前面钉了一块木板,当成座位,这样就可以和立秋面对面。两人一边行走,一边有头没尾地说着听来想来的闲事。走到村口,驼子二叔把车子放下。立秋腿脚不方便,但嗓音清脆,脸蛋长得也不差。往往是驼子二叔摇起拨浪鼓,立秋就开始清嗓子吆喝:“被子面绣红花,生儿养女能持家;油盐酱醋十三香,年年粮食装满仓;铅笔油笔写字本,学生能考一百分。”这些都是立秋想来的词,驼子二叔也佩服,心想若是立秋腿脚好,怎么也不会嫁给我这个驼子。这样吆喝着,流动的货摊前渐渐人多了起来,拨浪鼓在几个孩子的手里传来传去,鼓声零零碎碎散落一地。
这是老河滩上的货郎,穿过时间的光影从遥远的地平线走出,抖落一身尘埃,站在村庄的背景前。我所见过的货郎有那么几个,红胡子老李,多卖乡间农具、铁器,声音嘶哑,一嗓子能喊落天上的星辰;跛子老侉,从天寒地冻的关东回来,因一次煤矿塌方压住了他左腿,几天后他被挖了出来却成了跛子,所以摇起拨浪鼓来也一声轻一声重的,轻的像时光之羽,重的能震痛人的鼓膜;再就是驼子二叔了,那只拨浪鼓配上立秋清脆的嗓音,声音竟然变得叮咚透明起来,像被春风吹拂后破开的坚冰,脆裂着、推搡着远去,像节气与风的二重奏,四手联弹,恭迎春夏秋冬。
而《货郎旦》是一出遥远的戏剧。有的说是诞生于元末明初,有的说是诞生于金末元初。后者的证据就是里面“说唱货郎儿”的部分:“《货郎旦》将他(指货郎儿)作为剧中之一部分,其动机似在新颖特殊,犹如现今的话剧内,插演一段皮黄或大鼓,他本身便完全是违背了元剧的规律的。这种情形,在元杂剧盛行的初期及中期,也许就不会有。杂剧里用到以‘说唱货郎儿’来号召擅场,争取观众,实已象征地表示了杂剧的衰落。” (《杂剧〈货郎旦〉创作时间辩正——兼论北杂剧的早期创作》)货郎儿唱腔,原本就是指由“叫声”而来的一种歌曲和说唱艺术。《武林旧事》载:“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可见,一种艺术形式的起源,有着其曲折的历史线条。叫声从市井的深处、从民间的里弄里传出,渐渐形成了固有的唱腔。时间久了,沿途敲锣摇鼓、吆喝物品以招徕顾客的声音,就演变为货郎儿或货郎太平歌、转调货郎儿。
昆曲《货郎旦》最重要的是《女弹》一折。跟随张撇古流浪多年的张三姑也学会了说唱货郎儿,张撇古作古,张三姑恰好遇见落水被人救起的李彦和,主仆二人多年后相遇,结伴来到驿站。恰好落水那天被一纸文书卖给拈各千户的李春郎也在驿站,履任途中无趣,央人找来张三姑说唱一曲货郎儿。九转货郎儿,其时已发展为一种曲牌名称。现代戏剧理论家吴梅在《南北词简谱》中有记:“无名氏《货郎旦》剧第四折,有《九转货郎儿》九支,支支换韵,在元词中别开生面。而句法之多少长短,支支不同。”又说,“此套传至今日,只有三种:一为《货郎旦》,一为《义勇辞全》,一为《长生殿》(尚有《三国志·挑袍》折),《长生殿·弹祠》即徙此出。”可见货郎儿流传下来的曲目并不算多。
这时的货郎鼓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具,或曰作为一种乐器出现在荒村驿站。人是旧年的人,风已不是旧年的风,透过雕花的木格窗棂探听一折属于民间的传奇。技巧或者说唱的方式并不重要,张三姑在发觉年轻的千户大人酷似十三年前的李春郎时,偷偷告诉了李彦和。李彦和心中一惊,自己造下的孽岂能不知?只是尚且不能确定那是不是自己分离多年的骨肉。张三姑是李家的奶妈,也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风霜雪雨,一家人天涯别离,她最适合讲述人的身份。
转调货郎儿,相当于事件的起承转合,先从故事的开頭讲起。长安秀色,一派太平景象,车如流水马如龙,竟让千户大人听得如痴如醉。二转货郎儿,李秀才为色所迷,不顾夫人劝阻,一定要纳水性杨花的女子为妾。怎知张玉娥并无嫁到李家的真心,一时间大娘子也气得一口气没上来,魂飞瑶台。
我仔细听了《女弹》一折,张三姑唱到此时情绪已高昂,手中的货郎鼓紧摇一阵,仿佛临别时的凄风苦雨在眼前重现。张玉娥把李家的金银财物收拾交给了奸夫魏邦彦,且定下计谋,让魏邦彦在洛河边寻一艘小船,假做艄公。风雨在继续,惨剧在上演,魏邦彦摁住李彦和推落入水,又准备把张三姑也推进水里,这时岸上来了一些人,原来是拈各千户大人路过,一家人被救。张玉娥和魏邦彦撑船落荒而逃。
命运的起承转合往往也有潜藏的行迹。平日里驼子二叔和立秋大多在乡间行走,田里的庄稼青了黄,黄了又青,似乎今天和昨天没什么不同,但细微处肯定不一样。昨天路过老河滩,一只灰灰的野兔站在河岸上,身后是几只怯生生的小野兔,驼子二叔想要去撵,被立秋努努嘴止住了。下一次再遇见时,身后的几只野兔已经是少年模样,散落在兔子母亲周围。驼子二叔能看见立秋眼中的暖意,故意打趣说要不要也生一只小兔子。立秋属兔,驼子二叔也属兔,只是大了十二岁。当年他跟着媒人去立秋家相亲,立秋娘倒没说啥,立秋爹看一眼就下了逐客令。立秋知道,爹是为她好。不曾想过了几年立秋爹娘害了痨病,爹前脚走娘后脚跟,只剩下立秋一个人,眼看日子就要过不下去了,还是驼子二叔照顾她。
驼子二叔待立秋好,他间或用货品换一些鸡蛋、鸭蛋给立秋补身子,立秋身上的衣衫也干净利索。有了立秋,驼子二叔好像也有了奔头,往往天不亮就从县城上货归来,然后再把立秋抱到推车上,一人摇鼓,一人唱:“被子面绣红花,生儿养女能持家;油盐酱醋十三香,年年粮食装满仓;铅笔油笔写字本,学生能考一百分。”
《九转货郎儿》中李春郎似有发觉。原来十三年梦中见过的亲人就在眼前,那一场烧红半个长安城的大火,一直作为背景在梦中出现,眼看着父亲被佯装艄公的魏邦彦推进河里,却不敢大声哭号。一张文书一张纸,命运就寄托在拈各千户的手里。老千户死去,李春郎承袭了恩情也承袭了千户之名。东方戏曲中似乎总有一种通病,就是所有人期待的大团圆结局。《货郎旦》也未能免俗,但未尝不是一种温暖与抚慰,让流离安居,让失散重聚,让因有果,让悲伤化为欢喜。
洛河图,河图洛书,洛河是黄河的支流之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是对于河图洛书的最早记载,冥冥之中是否也有天意,织成了符合天人合一的玄机天书,体现出宇宙和人之间缥缈却真实的紧密关系?一只货郎鼓紧紧慢慢,摇落满天星辰,也摇响了属于老河滩独有的歌谣。
十几年恍然而过,驼子二叔鬓角生出浓密的白发,立秋也从一个还算标致的姑娘变成了妇人。临走时,妇人立秋握着驼子二叔的手,眼睛里汪着一团暖意。立秋是满足的,看遍了老河滩上的景色、老河滩上的人,熟悉了大地上的每一种事物。驼子二叔就是立秋的腿,立秋就是驼子二叔的眼,立秋只要一听见叮咚的鼓声眉眼就飞了起来,驼子二叔一听见立秋唱清脆的《货郎谣》浑身就充满了力量。
驼子二叔在摇手中的货郎鼓,紧一阵慢一阵,好像在等立秋的节奏。须臾,一阵苍凉的笑,惊落田野、屋瓦、枯草上的霜。秋天到了。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