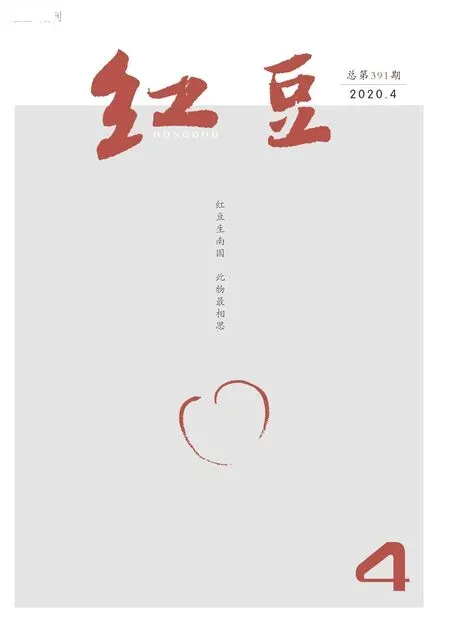岁月可期许
2022-05-26胡笑兰
胡笑兰
人生就是一个个句子、一个个章节,它的路径没有谁能预见。天赋、志趣、努力……数十年来,我辗转各地,无论是住所还是单位,我舍下了一些东西,也守住了一些东西,比如书。我拿出其中的两本杂志。这是两本《红豆》杂志,紙都有点发黄了,甚至有些脆。我小心地抚摸它们,就像抚摸我生命中走过的那些章回。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七月,我高中毕业,刚刚参加完高考。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好像是心灵的引领,我走到了那一排法国梧桐树下。树下摆了很多摊位,除了服装和杂货,还有一个小书摊。我在书摊前定住了脚步。那天,我用三毛钱又为自己买下了一本《红豆》杂志。我口袋里的几毛钱,是母亲给我的零花钱,三毛钱可以买三碗馄饨,那漂着猪油花和小葱花的鲜香混沌,一直是我的心头爱。但是谁让我看见了《红豆》呢!封面上,一辆自行车载着一对年轻人,像我邻家的国哥带着他心爱的姑娘梅。
我翻了翻书页,一缕好闻的墨香直入鼻孔,内容吸引了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我使劲摁下对馄饨的欲望。
其实读书是我打小就有的爱好。在我年少时,窑街常常来一个说书人,说书人走了,父亲还会给我说书。这样的浸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年少的我有了读书的兴趣。我的阅读从哥哥的书箱开始,里面有四大名著、鲁迅全集、苏联小说,甚至还有一些手抄本。鲁迅的书最多,是我的“三味书屋”……
于是,我心中的门被踹开了。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毫无悬念,我这个严重偏科的文科生,落榜了,我成了待业青年。那是一段非常苦闷的日子,是情绪与情感的灰色地带。我的心里像是缺了一个口,又像塞进了一团乱麻。恰巧父亲的工厂有几个招工名额,科长把待业证和招工表同时交给了我。是复读还是参加厂里的待业青年统招?我彷徨了。我坐在乱石嶙峋的山脚下,面对浣河清澈的水面,不知道心归何处。
《红豆》似乎是上天派来安慰我的使者,它让我暂时忘记了一切烦恼。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触摸杂志,给了我以往所不曾有的阅读体验。我熬过了这段从虚空到现实的时光以后,在心里由衷地感谢文学。
杂志内容也完全吸引了我。它和我之前看过的一些书,比如《红旗谱》《金光大道》等小说完全不一样。《红豆》里面有几篇写青工的小说,在我看来,就如在写我邻家的小哥哥小姐姐们。这样的文字是在寻常的生活中煮出来的。伴随作品中的人物,我了解到那些熟悉的或者新颖的东西,还了解到作品是和人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
王蒙在《漫谈小说创作》中的许多观点一直到现在都有教化的作用,于我后来的写作多有启迪。“一个人越是精通、熟悉某种东西,她的苦功往往正藏在她的轻松里。一个会跳舞的人,别人看上去她一点也不费劲,实际上她是花了很大功夫的。”
那年,我爱人从部队转业,工作落地于宜城,我也随调成功,来到了宜城。我上班报到的第一天就发现了公司大门前有间报刊亭。十字路口,车流人流如织,报刊亭的小小的窗口,一根细绳夹着几本杂志在窗口上方摇晃,我推着车上坡的时候,眼光就被它们牢牢地牵引住了。这个方寸之地,外面是铁皮和木板的组合,尖顶,围起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但报刊亭内里浩瀚,因为有《大众电影》《青春》《知音》……《红豆》落进了我眼里,我最终选了一九九四年第六期《红豆》。杂志里面的作品《特区舞女》让我知道了千里之外的南国深圳,看见了另一种不为自己所知的生活。我打开那本杂志,沉浸其中,瞥见人生无限的可能、人世间的诸多风景。我和书中人物交谈,触摸他们的心灵与生活,我为他们的苦恼而苦恼、幸福而幸福。阅读后,即便忧伤也换得一番滋味在心头。
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我和《红豆》有了交集。我携带着自己,把人生的章回重重地落在深圳。深圳的图书馆自然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二〇一八年底我知道了投稿纸媒的方式,我的散文《台风》便在《深圳晚报》上发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我的一颗文学心宛如南国的芭蕉树迎风生长。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何不给自己向往已久并热爱着的《红豆》投稿呢?这样想着的时候,我心里激动了。半个月后,我接到了用稿通知,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红豆》样刊,那上面印着我的散文《大地珍馐》。仿佛是一种定数,或者说是倾心的胜果,在南国,我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活。无数个日子被创作填满,被突如其来的灵感触动,我的心似有了归处,灵魂也有了安放之所。
文学,我心灵的应许之地,我会一直和你相依相偎。
责任编辑 谢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