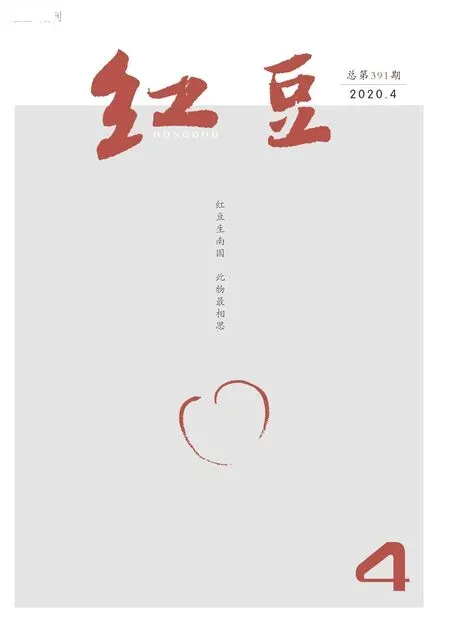看坟
2022-05-26无为
无为
一大早牛娃来到炕头前,一脸认真地对牛玉堂说:“爹,为冲冲晦气,就先看一下坟吧,这是老一辈的讲究。”牛玉堂没有说话,微微出了口长气,意味着他既不反对给他看坟,也明白自己的死期实实在在地要到了。
办理出院手续时大夫对他说,回家好好养养,缓一缓就好了。牛玉堂听到这话就已经知道个七八分了。可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些犯嘀咕,胸闷也减轻了,身子也不疼不痒的了,还有了一点食欲,脑子还很灵光,就算是回光返照也持续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吧?自己还不满六十五岁,社会发展得这么好,现在就去见阎王爷,真的不甘心。其实牛玉堂并不知道,他得的是肺癌,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了。
牛玉堂是昨天半夜被从西安拉回来的。大约过了午后,牛玉堂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村里来探望他的人。他已吃不了什么东西了,但村里人却拿了些好吃好喝的来。他的身体只剩下皮包骨了,脸也变成了鬼样子,来人却说些言不由衷的夸奖话,看来是给他送行来了。窗外有牛家族人的身影在闪动,还有搬动东西的声音,这分明是给他张罗着后事了。
牛玉堂开了一辈子砖瓦厂,是方圆百里的有钱人。以前他放个响屁,都会震得牛家山哆嗦,这会儿行将就木,唯一能够让他说了算的就是给自己看坟。这是陇庄原上的风俗,据说如果违背了死者的意愿,子孙会遭到报应。子孙若遇不顺心的事情,都会认为是这个原因而被迫迁坟,有些甚至会迁来迁去,痛苦不堪。
太阳落山的时候,文老先生来了。文老先生是从几十里外请来的,七十多岁,长眉白须挂满露水珠子,显得仙气十足。白露前后的陇东山区多雾,早晨雾从山涧沟壑里升腾起来,慢慢淹没村庄,随后就遮天蔽日,打湿人们的衣服。须发上有露水是常事,牛玉堂是知道的。可太阳都快落山了雾还没散,这就很奇怪了,这辈子头一回看到这种鬼天气。缕缕雾气也跟着进了屋里,牛玉堂的后背立刻感受到了寒意。他不由得连连咳嗽,嘴里的痰还来不及吐出又倒灌进了食道里。
文老先生远远地就抱拳作揖,看牛玉堂咳喘不止,走过去幫着扶翻身子,用手掌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牛老善人不要动。”算是打了招呼。牛玉堂平静下来后,回了一句:“老神仙来了。”说得有气无力。
客套完后,文老先生开始往屋墙上挂太上老君像,往桌子上摆香炉上香,三跪九拜,诵经祷告,肃穆而庄严。香烟缭绕起来后,他的目光也凛冽了起来,显得神气十足。他起身手执拂尘,迈起方步在屋里、院里四处走动。
看坟是有讲究的。夫妻合葬选鸳鸯坟,光棍选青龙坟,寡妇选白虎坟。牛玉堂的老婆死了二十多年,牛玉堂百年后肯定要和老婆合葬,顶多选个风水更好的地方,把他老婆的坟迁来合葬。
文老先生转了一圈后,回到老君像前又祷告了一番,才言归正传,摆手让跪在地上的牛娃和其他儿女以及围观的亲戚、邻居都退到了门外。他俯下身子小声问牛玉堂:“牛老善人的意思是?”牛玉堂气若游丝地说:“青龙坟。”文老先生愣了半天才说:“儿孙满堂,龙凤呈祥,百年后也该鸳鸯相伴才好。”牛玉堂面有难色地说:“老婆死了二十多年了,在阴间那边还会等我?”“这个……”文老先生皱了一下眉头说,“牛老善人,你报一下她的生辰八字,我查询一下,不过天机不可泄露。”说完取过布褡裢,从中拿出一本旧线装书翻开看了看,抖了抖稀疏的山羊胡子,嘴巴伸到牛玉堂的耳边小声说:“还真是没等,转世托生多年了。”
牛玉堂听清楚后,灰黄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他慢慢抬起一条枯瘦的手臂微微晃了晃,示意文老先生靠近他,又说了一个人的生辰八字。文老先生以为病人刚才没说准确,就按新告诉他的生辰八字仔细查对,可总觉得不大对头,说:“这个妇道人家尚在人世,五十三岁,生性风流,百年后将有二夫争妻惨剧上演于阴曹地府,似乎在劫难逃啊。”
“啊呀——”牛玉堂听清楚后,脸色突然变成了茄子色,嘴唇哆嗦个不停,脑袋向炕边上一歪,一大口血就喷到了地上。
文老先生见状大声冲门外喊,院子里的人闻声都跑进来。有人猛掐牛玉堂的人中,半天了牛玉堂还是昏迷不醒。大家以为他要咽气了,就赶紧给他穿上寿衣。牛玉堂却渐渐有了回气,算是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又回来了。
大家抢救牛玉堂时,牛娃媳妇悄悄把牛娃拉到隔壁房里嘀咕,说她觉得公爹的相思病犯了,理由是公爹吐血前,她听到他喊了那个骚狐狸的名字。牛娃还没听完就把一口茶水笑喷到了墙上。他骂媳妇是老狗记起了陈干屎,都十来年前的事了,还扯出来玷污他家活祖宗。
文老先生离开时,两口子把他送出大门。牛娃悄悄打听刚才屋里的事情,得知他爹确实问过一个女人的生辰八字,这才相信爹的确是犯病了。不过对于这事儿的看法,两口子还是有分歧。牛娃觉得他爹只剩一口气了,就算犯这病也不算是一回事,不影响他老人家进坟墓。媳妇却认为,只要没咽气,这病迟早都会生出祸端。
牛玉堂的相思病,得了有些年头了。起因是当年在路上与村里陈家刚娶来的新娘子铃子相遇。据说牛玉堂当时在路边一棵杏树上摘杏子吃,路过的铃子说她也要吃。牛玉堂伸手递杏子给她她不接,要他喂到她嘴里。天哪,牛玉堂当时就吓傻了。铃子见他不动,就给他抛了几个媚眼,半眯起眼睛,把噘起的嘴巴伸了过去。牛玉堂浑身一阵躁热,见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就壮着胆子把杏子喂进铃子的小嘴里。
一个山里的庄稼汉,老婆死了那么多年,孤独难耐。他一直很羡慕电视里的人谈恋爱,不由得认为铃子这样一定是爱上他了,回到家就得了相思病。
没过两年,铃子的男人死于车祸,家里没人去处理后事,陈家老汉求牛玉堂出一趟远门。牛玉堂带着几个汉子去处理后事,弄回尸首和十来万元赔偿款,小寡妇铃子也变成了他嘴边一块香喷喷的肉。好事就要成双时,陈家老汉却跑来给牛玉堂下跪,说铃子不能嫁给别人,只能嫁给她家小叔子。理由是家穷,小叔子讨不上媳妇,赔偿的钱也不能进别人家的腰包。陈家老汉还发动陈家整个家族来阻挠这件事。一口嫩肉溜进了别人的嘴里,牛玉堂气了个半死,就气出了相思病。每次犯病都神情恍惚,胡诌一通。十里八村的人都说铃子是个转世狐狸,狐骚味进了骨髓,无法医治。后来牛玉堂开砖厂挣的钱,都无怨无悔地填进了铃子的家里。十多年前,娶了铃子的那个小叔子暴病身亡,村里人都说牛玉堂没白痴一场,终于等到了这一口肉。丧事期间,牛玉堂亲自出马料理,显得踌躇满志。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以父亲的口气教训铃子的儿子堂堂。堂堂是铃子与小叔子生的,大学毕业落脚到省城。他年轻气盛,听牛玉堂的话不顺耳,翻脸就问牛玉堂算哪根葱,并当场扇了他一个嘴巴子。铃子脸上挂不住,张口要呵斥儿子,结果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儿子一把扯进旁边的屋里上了锁,任凭她怎么哭喊也不搭理。烧完头七纸,儿子扯着母亲的胳膊,一起去省城生活了。
吐血昏迷一天一夜之后,牛玉堂醒过来了。
看坟之事一刻也不能再耽搁,病人自己动不了,就抬着走。文老先生摇着铃铛在前边带路,他们出了门直奔牛玉堂老婆的坟墓去。到了坟前,吹唢呐,烧纸钱,作揖跪拜……仪式很完整。这些都是做给牛玉堂看的,希望他能深受感动,同意与老婆合葬成鸳鸯坟。
文老先生拿着罗盘测来量去,忙活半天,感慨地说:“前朝朱雀,后靠玄武,左右抱穴,是风水行当里公认的‘三星一’结构啊!怪不得儿女发财,人丁兴旺。”牛玉堂听得清楚,闭着眼睛不吭声。
牛玉堂的一个妻弟也被请来了。妻弟有些急,走过去拍了拍担架的手柄,直截了当地说:“我姐给你生儿育女,没享你一天福就走了,你百年后去陪陪她天经地义啊!”旁边有人附和说:“牛娃他娘人虽丑点,可生的都是有本事的俊儿俊女。”牛玉堂就是不开口。有人小声嘀咕说:“是不是人不行了?”儿媳妇说:“出院时大夫交代过,要看眼珠子动不动,如果不动就快往棺材跟前抬。”牛娃就跑过去伸手翻他爹的眼皮子。牛玉堂是装睡着,耳朵一直听着的。眼皮被翻开后,面对十几张俯视着他的脸面,他把眼珠子很用力地转了几圈。“老姐夫哎——同不同意你给个准话吧,大雾已经从沟里头起身了。”妻弟有些沉不住气了。
牛玉堂没法再装了,嘟哝了一句没人能听得懂的话。小孙子闹闹和他爷爷最亲,跑过去趴在担架前给大家当起了翻译:“我爷爷说了,我奶奶早托生了,没有在阴间等他。”有人接了话茬,说:“给你爷爷说说,他腿脚麻利,比兔子跑得都快,让他过去了好好追你奶奶。”“我奶奶已经托生成驴了,追上有啥用呢?”闹闹没说完自己先大笑不止,笑够了又补充一句,“我爷爷说是文老先生掐算出来的。”
大伙儿一时愣了起来。牛娃舅舅走过去对他耳语:“看来这事情还得跟文老先生合计合计才行。”牛娃手一挥,担架又往别处抬了。
现在谁家死了人只能埋到自家的承包地里。牛玉堂和儿子两家的田地,分别在几个山头上的四五块梯田里,一群人抬着牛玉堂去了几个地方,他都闭目摇头。到了最后一块梯田,是一块荒草地,顾名思义就是给牛羊种草的地,种粮食不会有什么收成。梯田像一条带鱼,最宽处不足两丈。这个地方叫雀儿湾,两条山梁夹一块滩地,有些像一张有圆形靠背的椅子。这块带鱼状梯田,就在椅子左边扶手的位置上。文老先生还没说话,众人却嘀咕起来,都说这地方不好。理由是过去年月里经常往这埋夭折的小娃娃,这里阴森诡异,夜里经常有怪叫声,野狗大白天都不敢到这里来。
已是午饭时间了,大雾还没有散去。有人骂骂咧咧道:“今年的天气真怪得很。”这时东南方的大雾忽然裂开一个口子,太阳的笑脸显露了出来,万丈光芒直射大地,四周的山梁沟壑都渐渐探出了头,梯田、秋禾似隐似显,牛家庄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被冷落在担架上的牛玉堂忽然呜哩哇啦地叫,把其他人都惊得不轻。回过头看到牛玉堂竟然掀掉身上的被子,坐了起来,眼睛死盯着天空,蜡黄的脸上瞬间有了血色,有了温柔和羞澀。
没人听得明白牛玉堂说的是什么。孙子急忙跑过去当翻译,说:“爷爷说在云彩里看到了铃子奶奶,他是喊铃子奶奶等他。”
“相思病又犯了。”不知谁小声嘀咕了一句。大家很吃惊,一个要断气的人,竟然还能犯这个病,有人就捂着嘴低着头笑。牛娃难堪至极,挥手说:“回家!”要抬担架的时候,牛玉堂伸出一只胳膊揽住旁边的一棵槐树,死抱住不放。另一只手指向树下,意思明白无误,就是死了要埋在这里。
文老先生始终法相庄严,不轻易说话。牛娃再也沉不住气了,可能觉得太丢面子,随手扔掉端着的香盘,大声喊道:“这儿就这儿,爱埋哪里就埋哪里。”
文老先生手中的铃铛适时响了起来,显得很急促。伴着铃声他指手画脚,扯起嗓门拉起高腔,冲着跪在地上的牛娃说:“榆树改种松柏,冤魂小鬼打醮超度,此处不失为一方宝地,子孙必将兴旺发达——”
夜幕下院子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叮叮当当一声急过一声,这是木工打制棺材的声音。一头猪被牵进了院子,叫声凄惨,似乎知道自己马上要挨刀。牛玉堂明白大家在给他筹备葬礼,有些与死亡赛跑的意思。
闹闹推门进来了。白天跟着看坟,玩耍了一路还不过瘾,夜里不睡觉还要来找爷爷逗乐。牛玉堂刚小睡了一会儿,睁开眼看到孙子瞅着自己发呆,就伸手去摸。手哆嗦着伸到半空时,被孙子的小手捏住了。
“爷爷你真要死了?”孙子眼里充满了惊恐。“是的,爷爷快要死了。”牛玉堂说完笑呵呵的。他明白自己在亲人们的眼里早已是个死人了,唯独在这个孙子的眼里还活着。“爷爷,炕这么热,热得烫人,你不嫌烫人吗?”牛玉堂说:“爷爷感觉不出来了。”闹闹哇的一声就哭了,牛玉堂伸出颤颤巍巍的手给孙子擦去眼泪。
闹闹这孩子脑瓜子灵光,很会摆弄手机。牛玉堂住院时学会了用微信,可不够老练,就是跟铃子的微信连不上。闹闹接过手机,三下五除二就连上了。视频里看到的是一位漂亮奶奶的白嫩脸蛋。没等对方说话,闹闹就哭喊说:“铃子奶奶,我爷爷要死了。”同时把手机镜头转向了睡在炕上的牛玉堂。牛玉堂恍恍惚惚地还没看清楚,微信就断线了,再拨几次也没人接。闹闹说掉线前,奶奶身后冒出个爷爷。
闹闹要回去睡觉的时候,牛玉堂把准备好的一沓钱递给孙子。闹闹却坚决不接,说:“我以前要你的钱,现在不要了。以前我把你说的话告诉爸爸妈妈,现在我不告诉他们了。”说完哭着出门去了。牛玉堂想小孙子长大懂事了,而自己却要死了,不免有些伤感。
服药之后,牛玉堂渐渐入眠。夜深人静时分,卧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了。门缝里进来一股白雾,被灯光一照,地上出现了滚动的白影。天还没亮就起雾了,怪事。门又吱吱嘎嘎地被推开,走进来一个女人,是铃子。一身大红色旗袍,披麻戴孝,哭丧着脸扑倒在炕前,跪着伸手扯住牛玉堂干枯的胳膊大哭。牛玉堂这时候又兴奋又生气,不知哪里来的力气,胳膊肘往炕上一用力,竟然坐了起来。他用深情和哀怨的语气指责她:“我还没死,你哭什么丧啊!”玲子哭着说:“村里人都知道你要死了,微信朋友圈都发了。”牛玉堂叹了一口气就沉默了。“快给我看看死亡证明,现在城里人都流行看这个。”铃子从地上爬起来,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那我就让你看看。”牛玉堂拿出病历,不慌不忙地递了过去。铃子看完就笑了,笑得前仰后合,气喘吁吁,旗袍领口的扣子都被绷开了一枚。牛玉堂似乎没了病痛,也跟着咯咯地傻笑。
“怎么回的?为什么半夜三更回?”“赶马车回来的,马拴在山后的大槐树下,怕村里人看到丢人现眼。”这么一问一答,牛玉堂又幸福又伤感,觉得到了生死离别的时候,该诉衷肠才是。门外的雾一股股扑进屋里,遮蔽了挂在屋顶的那盏幽黄的灯。铃子身上的旗袍渐渐变成了深红,缠在额头上的白纱,也变成了米黄。那双眼睛还是水汪汪的,她歪着脑袋用狐媚的目光深情地看着他。铃子看了一会儿,又伸手摸他的额头,妖声妖气地说:“真像个男人。”说完话又很妩媚地噘起了小嘴,就像二十多年前在路边让他喂杏子时的表情一样,似乎比那时候还要好看。
牛玉堂问:“你是先看上我,还是先看上你小叔子的?”她摇摇头又点点头,表情更迷人,就是不说话。牛玉堂又问:“有一天夜里我去找你,和你商量着要怎么娶你,睡到半夜突然有个人悄悄从门外进来爬上了炕。碰到我脑袋后,就伸手在我的脑门上摸,摸来摸去,可能觉得是一个男人的脑袋,他就很慌张地跳下炕跑出去了。那天夜里摸我头的是不是他?”铃子还是又摇头又点头,一脸的狐媚。牛玉堂再问:“你的宝贝儿子堂堂,这些年来一直是我供养的,为啥这么恨我?”铃子伸手抚摸了一下牛玉堂干瘪的脑门说:“好几次你半夜出门去了,我都在睡着的儿子手中摸到菜刀,还有学校里的娃娃欺负他时,让他喊‘牛玉堂是我爹’。你亏欠他的不少。”
这时候门缝里不断地涌进白雾,快淹没了铃子的身体。牛玉堂忽然想起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没说,刚想张口,门外响起了马嘶声。铃子从地上爬起来就往外跑,嘴里唠叨说不能让村里人看到。
牛玉堂又昏睡了一天一夜,在一阵唢呐声中苏醒过来。睁眼看到自己已经穿上了寿衣,家人开始给他办丧事了。
窗外有白纸条在晃动,屋里地上跪着许多披麻戴孝的人,没怎么有哭声,只有个女儿在干号。牛玉堂看着心里就来气了,很愤怒地咳嗽了一声,伸出一只手朝炕边晃动了一下。他还活着的情况立刻被棺材旁的文老先生看到了,文老先生怒气冲冲地对牛玉堂的亲人说:“牛老善人咽没咽气都没弄清,真是不肖子孙。”“没人敢去摸鼻子听呼吸,眼睛是他自己紧闭上的。”跪在地上的人说话了,都显得很冤枉。牛娃气呼呼地站起来,伸手摘掉头上的孝帽扔在地上,一阵风似的出了门。其他孝子都起身悻悻而去,仿佛牛玉堂没死是一种罪过。
牛玉堂活了过来,屋里却是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来打针、喂药、喂饭,牛玉堂身体竟然异常平静,连胸闷气短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牛玉堂觉得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进来,就心急火燎地拿出手机用微信给铃子发语音。
“昨晚你回家天快亮了,儿子没发现吧?”
“你说什么呀老牛?昨晚我早睡了,今早六点就去公园跳舞了。”
“你的马车不是拴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吗?”
“还牛车呢,你是不是做了噩梦?”
“你是穿大红色旗袍吗?”
“是啊。我最近跳廣场舞都穿这个。有啥快说,我在厕所里快被臭死了。”
“我快死了,我有急事给你交代。”
“你又撒娇了,待会再说,都臭死了。”
昨晚难道是做梦?牛玉堂拖着哭腔,语音留言给铃子,是急着要告诉她这样一些事情:嫁过两个男人的女人,尤其是长得漂亮的,将来到了阴间两个男人会争抢。阎王爷没办法判,就会用锯子把女人锯成两截,一人一截。这是文老先生亲口说的。让铃子尽快回来在雀儿湾选坟头定下……说了一两句,又觉得人家毕竟才五十出头,活着的日子还长着呢,说这样的晦气话有点不合适,就删掉了。只请求她尽快回牛家庄一趟,有急事要当面说。
天已经很黑了。牛玉堂醒来了,着急地打开微信,看到了铃子发来的语音。铃子一腔的委屈和无奈,说她儿子堂堂的生意资金周转出了问题,差几十万元,逼着她天天出门借钱,想回牛家庄看他,可一时半会儿动不了身。牛玉堂自己要咽气是分分钟的事情,有天大的事情要告诉她,她怎么能让几个臭钱耽搁了呢?不行,还是打钱给她救急吧。有了这样的想法后,牛玉堂还是纠结了老半天。这些年他往铃子的钱坑里不知填进去了多少,临死了还往里填?想来想去觉得大半辈子都能扛住,别最后犯糊涂,伤了下辈子的感情。想通之后就打开微信,给铃子转钱。一次最多只能转五千元,转到五万元时受限了,咬着牙等过了零点再转,直到又受限了,支付总额显示为十万元,才合眼入睡了。鸡叫惊醒他时,他猛然想起夜里打的款,本来是留给孙子闹闹的。赶忙打开微信,看到款已经全收了,铃子回过来一个笑脸。应该有几个笑脸,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符号吧?想再留言说这钱是留给闹闹的,得及时还给他,又不好意思开口,觉得等见了面说更好。
一阵急促的嘈杂声传来。门哐当一声被推开,儿子牛娃带着文老先生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人和一团散乱的雾气,他们进屋后在文老先生的指挥下,都哗啦啦跪在了地下。
“我还没咽气——”牛玉堂有些发急了。
没有人理睬他。
跪在地上的人都没戴孝帽,儿子也没穿孝服,唢呐也没响动,只有文老先生手里的铃铛叮叮当当。牛玉堂看清这些后,停止了叫喊。
文老先生挂好老君像,燃起香火,甩了甩拂尘,吟诵了几句,迈着方步走到炕头,双手合十口称“牛老善人”,作了好几个揖,伏下身去,嘴对着牛玉堂的耳朵小声说:“我见了铃子女善人,你把她的生辰八字搞错了,没分清阴庚阳庚。她的阳寿很长,阳世还有姻缘未了……”说话的同时,文老先生从道袍的宽袖里拿出一张纸片,递到了牛玉堂的手里,那是一张铃子近日再婚的婚纱照。
牛玉堂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文老先生捣的什么鬼或使的什么妖术,就颤抖着把一根食指指向了文老先生的鼻子。
“孝子贤孙们,听神仙谕令:‘牛老善人同意他百年之后与原配合葬。’你们看他伸这个指头的意思是一言为定。”文老先生喊道。
一口黑红的鲜血,从牛玉堂的嘴里直喷了出来。没折腾几分钟,人就不行了。
出院时大夫说,他应该能坚持到重阳节,实际上只熬到了九月初五。
责任编辑 符支宏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