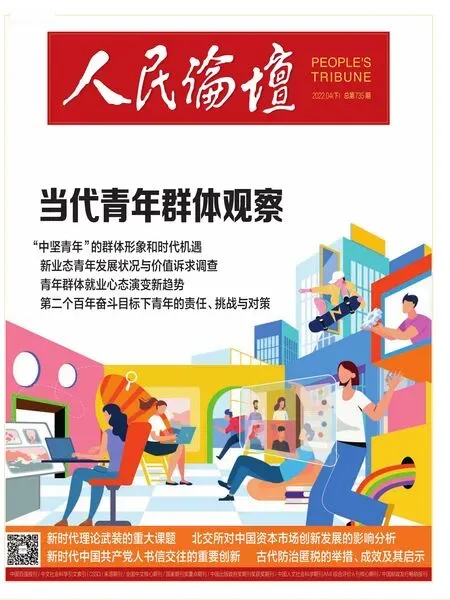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综合应对
2022-05-26陆杰华
陆杰华
【关键词】青年群体 婚育推迟 表现形式 潜在影响
【中图分类号】D669.1 【文献标识码】A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这不仅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率的国家行列之中,而且也预示着未来生育水平下行或将成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最新人口基本情况数据还表明,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人口净增长仅为48万,人口出生率为7.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出生人口再创新低,人口增长模式开启了零增长时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和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总和生育率30年来呈持续下降趋势,其中的原因既有外生性的生育政策影响,同时还有经济、社会、文化等内生性因素的驱动。但近年来生育率下降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则与不同时期育龄人群的婚育推迟密切相关,尤其是近年来各方数据均显示,21世纪青年群体的平均初婚年龄和平均初育年龄都比以往呈现明显推迟的态势。据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2006年—2016年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6.3岁,十年间推迟了2.7岁;与此同时,同期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则从24.3岁上升到26.9岁,十年间推迟2.6岁。为此,2022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毋庸置疑,“90后”“00后”既是当下婚育群体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提振当下和未来生育水平的重要主体。因此,有必要充分认识当下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主要表现形式,深入剖析这一特殊群体婚育推迟的主客观原因与潜在影响,对于今后我国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典的人口学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与以往社会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等观念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婚育文化相比,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恋爱观、婚姻观和生育观势必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最终将形成以晚婚晚育、少生甚至不育为鲜明特征的现代社会婚育文化。从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更加深入人心,中国的婚育文化也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正成为当代婚育主体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早期队列相比,推迟婚育年龄不仅成为当下青年群体的基本共识,而且也成为多数青年人的一种行为准则。综合而言,当代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表现形式突出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分性别初婚年龄呈现稳中有升的鲜明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十多年间我国的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基于官方统计数据计算得出,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由1990年的23.57岁上升至2010年的25.86岁,20年间累计上升2.29岁;女性初婚年龄则由1990年时的22.02岁上升至2010年时的23.89 岁,20年间累计上升1.87岁,2016年更是上升到26.9岁。与此同时,三十多年间城镇居民平均初婚年龄上升速度更快,如2010年城镇男性初婚年龄为26.92岁,比20年前上升了2.56岁。此外,一些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上升更为明显,如2021年南京市不分性别的初婚登记平均年龄为27.9岁,比2020年上升0.3岁。更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中的女性初婚年龄的持续延迟势必将导致大龄单身群体不断增加。
二是不同队列的女性初育年龄保持着持续延迟的态势。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计算,“60后”“70后”“80后”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分别为23.46岁、24.35岁、24.49岁,这也从一个侧面动态地反映出不同时期队列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同一数据还显示,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延迟现象更为明显。基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经测算显示,我国不分城乡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27.2岁,比2016年上升了0.3岁,再次证明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将推迟初次生育作为她们的现实选择。
三是随着时间推移,不同队列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测算,我国15岁—49岁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仅为1.86个,大大低于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如2018年美国为3.59个和2011年英国为2.37个。此外,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也显示,“60后”“70后”“80后”“90后”育龄妇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其中越是处于年轻队列的平均理想子女数相对更少。例如,“90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仅为1.86个,比“60后”“70后”“80后”分别减少0.22个、0.15个、0.10个。
四是婚前同居比例大幅攀升,而女性在婚比例却明显下降。一方面,有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青年群体的婚前同居比例一直在个位数下,20世纪90年代之后提前进入同居生活来体验婚姻的青年群体成为“试婚族”的比例呈现大幅度增加的态势,婚前同居的比例从1990年—1999年的10%上升至2010年—2014年的35%左右。另一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岁—34岁处于生育高峰期的育龄妇女在婚比例却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0岁—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2006年的75%下降到2016 年的67%,十年间下降了八个百分点。
青年群体婚育推迟的多重原因
纵观全球,青年群体婚育推迟与各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其青年人的恋爱观、婚姻观和生育观转变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婚育推迟毫无疑问是大势所趋,一定程度上寓意着快速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迁,同时更折射出转型期青年群体的文化观念锐变。与其他国家相比,当下中国“90后”“00后”婚育推迟主要原因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
从经济层面上看,婚育成本持续上升是当下“90后”“00后”婚育年龄推迟的显性原因。一方面,今天的絕大多数青年人在步入社会的初期,就需要面临着成家与个人发展,尤其是与职业发展的冲突,加上婚恋成本的上升、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等主客观原因使很多青年人对婚姻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即使步入婚姻“围城”之后,年轻夫妇还要直面下一代生育、养育、教育等成本上升的压力和挑战,导致他们中很多人不敢生。除此之外,生育、养育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年轻夫妇就业和职业晋升的机会成本。
从文化层面上看,婚育推迟折射出“90后”“00后”婚育观的深层次变化。传统社会中,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最基本组织形式之一,由此形成了家庭高于个人且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家庭利益的“家本位”文化。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嬗变,以家庭为圆心的“家本位”逐步让位于以个体自由发展为主体的“人本位”。今天的“90后”“00后”的思想更独立、观念更多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未必将结婚和生育作为他们人生的必选项。这些直接导致形成了当下晚婚少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意愿性、选择性、内生性、稳定性、持续性和内卷性的低生育率现象。
从教育层面上看,受教育水平稳步提高客观上延迟青年群体的婚育年龄。改革开放之后最直接的红利之一是年轻人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早期青年队列通常是在18岁之后就直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他们的成家和生育年龄势必比较早。据统计,“80后”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6.7%,但是随着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90后”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高达35.7%,而18岁就进入社会工作的“90后”人口比例降低至64%,预计“00后”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会更高。个体受教育周期延长直接导致青年群体婚育年龄的推迟。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90后”“00后”婚育年龄推迟将带来不容忽视的中长期潜在影响:
其一,婚育年龄推迟直接和间接地拉低时期生育水平。婚育年龄影响着低生育社会背景下总和生育率的稳步提升,而初婚年龄推迟直接导致生育年龄推迟。以往研究发现,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大概会影响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 此外,初育年龄的推迟由于生育间隔期的影响还间接波及到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概率,并影响到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子女数。
其二,初婚年龄推迟直接导致在婚比例的下降。如前所述,青年群体初婚年龄的持续上升程度不同地导致生育旺盛期育龄人群在婚人口比例的下降,不仅客观上使已经很低的生育水平“雪上加霜”,导致生育水平下滑,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女性终身不婚人口比例的持续增加。
其三,婚育年龄推迟还可能带来生殖健康的负面影响。从医学上看,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25岁—29岁,过度晚婚晚育不仅会增加胎儿畸形等出生缺陷问题,也可能会引发女性生殖健康问题。因此,从宏观层面上看,适龄结婚和生育不仅关系到育龄人群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关系到人口素质的稳步提高。
破解“90后”“00后”婚育推迟现象需要从长计议、内外兼顾、标本兼治
首先,降低婚恋生育成本,有效释放生育势能。调查数据显示,“90后”“00后”这部分青年群体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仍然高于1.8。因此,短期内要促进他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育行为、释放生育势能的最有效措施是多措并举降低他们在恋爱、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一系列方面的成本,最大限度缓解因为婚育成本上升引发的婚育年龄推迟现象。
其次,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实行家庭自主生育。全面放开生育数量限制,让有意愿且有条件的青年群体自主且负责任地生育子女,不仅是将生育还权于民,而且有利于促进国家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长期来看,放开生育数量限制不仅有利于生育势能的最大限度释放,更重要的是改变以往社会视少生就是一切的价值取向。
再次,构建生育友好环境,保持适度生育水平。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环境就是重构婚恋、育儿、住房、就业、教育、税收、医疗保健等方面公共政策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生育旺盛期育龄人群结婚前“想不想结婚”、结婚后“想不想生”和“敢不敢生”的矛盾,使生育友好环境的构建真正成为推动适度生育水平的稳定阀。
最后,重塑适龄婚育价值观,促进人口均衡发展。重塑适龄结婚和生育对于个体及其家庭的深远意义。在包容、尊重和理解“90后”“00后”婚育观的基础上,注重从内生的婚育文化入手,通过引导和激励措施,让青年群体重视和尊重婚育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1ZDA10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李月:《鼓励适龄婚育应成为重要的政策着力点》,《人口与健康》,2019年第2期。
②於嘉、谢宇:《我国居民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17年第2期。
③刘佳、徐阳:《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探讨》,《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8年第7期。
责编/谢帅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