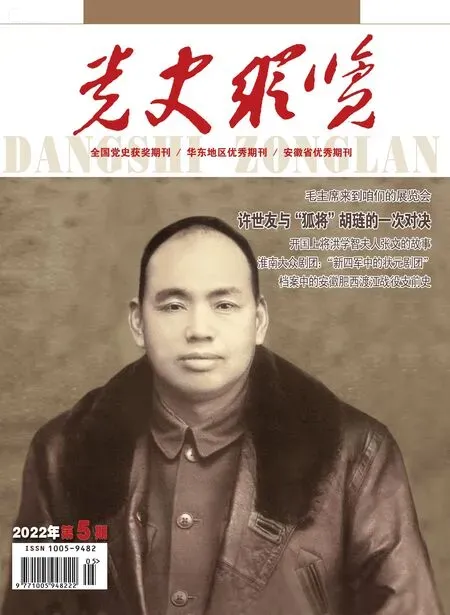“两膺上将”洪学智的传奇人生(五)
2022-05-26张子影廖天琪
张子影 廖天琪



苏家埠战役 死里逃生
1932年5月7日,苏家埠战役结束的前一天,二十九团从七里橋攻上去,战斗异常激烈。洪学智率领着重机枪连边打边冲,刚刚冲到一个小坟头跟前,忽然觉得胸前剧烈一震,一颗子弹“叭”地打进了他的左胸。他一头倒在地上。
紧跟在后面的团政委曾传六看得真切,马上跑过来抱起洪学智,伸手一摸,一股热乎乎的鲜血呼地涌出来。
曾传六一下子热泪汹涌,他声嘶力竭地大吼了一声:“担架……”
立刻有两个小伙子跑过来,放下担架,小心地将洪学智搁上。曾传六大吼:“快抬走,送医院……快……”
小伙子们抬起担架就跑。
身后的曾传六挥着枪再次连声大喊:“快送医院……快!”
此时,躺在担架上的洪学智意识已经模糊,他的手无力地从担架边上滑落,跳出他脑海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回完了……不过,够本了!
一路上,血不停地顺着担架流淌。两个担架队队员知道自己抬着的是二十九团最能打的重机枪连的连长,看着洪学智的脸色从惨白变成黑色,两个人一边狂奔一边喊:
“挺住啊!洪连长,一定要挺住!”
“马上到了,洪连长,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很多年里,洪学智一直都在试图寻找这两位分秒必争地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担架员,希望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希望能当面见到他们,不管何时,也不管他身居何位,都要向他们深深地鞠上一躬。
担架队在路上遇到了敌人的飞机。
敌机发现了送伤员的担架队,追着担架队低空扫射,子弹接二连三地打下来,担架队队员们一边迈大步伐一边绕着弯子躲避敌机的追击。子弹打出的一串烟雾,遮蔽了敌机的视线。等烟雾稍散,担架队又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了。
敌机恼了,丢下两颗炸弹。
一颗落在担架队的后方,一颗在另一个担架边炸开,两个重伤员当场牺牲。
炸弹爆炸后,队员们立刻起身,清点一下队伍,又带着伤员继续向红军医院飞奔。
在苏家埠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各医院积极开展战地救护。因为战场形势恶劣,敌我绞杀激烈,伤员太多,担架队一时间送不下来,加上一些伤员轻伤不下火线,所以许多医护人员都靠上前去实施阵地抢救,红四军后勤总医院政委周时禹在前线抢救伤员时中弹牺牲。
抬下来的轻伤员先包扎治疗,危重伤员急救后转送后方医院。
洪学智的伤势很重,血都流到胸腔里,形成了黑血块,昏迷中的他被送到红军医院。
红军医院设在篓子窝村离麻埠街三四公里的一个地主的大宅院子里。
剪开鲜血浸透的军衣,伤口令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子弹从洪学智的前胸正面进入,洞穿左肺叶后又从背部穿出,肺部大量鲜血倒灌进胸腔、腹腔,压迫心脏,引起多部位感染和呼吸障碍。红军医院缺医少药,即使开刀排出脓血,也无法控制感染。
连续高烧加上呼吸障碍,洪学智陷入了长久的昏迷中。
洪学智奄奄一息。医护人员心急如焚。
这一天,洪学智似乎有了点动静,护士们赶紧把他抬出了房间,放在门口草地上,希望在通风的地方能稍微缓解一下他的痛苦。
洪学智却再没有动静,呼吸声渐小,胸部的起伏也渐弱,乌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任人怎么喊他摇他,都没有回应。
“可能不行了,也许熬不过今天了。”医生难过地说。
几个年轻的护士大哭起来,几天前他们还在方面军的表扬大会上听过这个年轻的连长生动有趣的发言,可现在,由于缺医少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才19岁的年轻人就这样离去。
哭声惊动了旁边正走过来的一行人,他们是苏家埠战役结束后送来的俘虏。其中一个穿着敌军制式衬衣的中年人停了下来,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洪学智,走过去,然后,又停下,向押送的红军战士说:“报告……”
红军战士把枪一横:“干什么?”
“让我看看他的伤。”
守在洪学智身边的女护士立刻用身体挡在洪学智床前,用警惕的眼神瞪了他一眼:“你想干什么?”
穿衬衣的摊了下双手:“我没有武器,我只是想看一下他的伤。”
押送俘虏的红军战士说:“哦,他是几天前从被围的苏家埠城里逃出来投降的,是个医生。”
这名医生先用水仔细地洗了洗手,然后伸出细长白晳的手指,用手指尖轻轻解开绷带,仔细地检查着。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人终于直起身,他已经重新把伤口做了处理,并且包扎好了。准备离开时,他又站住了脚,垂头不语像在下一个决心,然后从口袋内里掏出一个黄油纸纸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有几粒白色的小药片。他用手指拈出两颗,递给流泪不止的护士:“给他吃了。要快。”
护士睁大了眼睛,疑惑地看着他。
“这是我给自己留着保命的。仗打完了,我也不会再当兵了。”
那医生把剩下的几片药重新小心地包好,交给护士:“不多了,就这几片,算他幸运。”
那名医生对伤口的处理以及留下的药真是管用,当天夜里,洪学智就睁开了眼睛。天亮后他觉得清醒了不少。接连几天吃下另外几颗药,洪学智的烧开始退了,咳嗽减弱,吐出的血块逐渐减少,后来就没有再吐血了。护士医生们奔走相告,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都来看他。洪学智忍着伤痛坚持每天清洗伤口,咬牙努力吃东西。也是因为他年轻身体好,一些日子后,伤口开始愈合,人也有力气坐起来了。
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洪学智靠在树下打盹,蒙昽中仿佛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他睁开眼睛,面前站着的是余推子和连里的另一名战友,只见他们睁大着眼睛,一脸惊异地看着自己。
余推子上前扶住他,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连长,真是你,你还活着?”
原来,团里派余推子来红军医院慰问伤员,余推子以为洪学智早就牺牲了,不承想,刚进门就看到洪学智居然好端端地自己靠着大树坐着,虽然瘦了大大的一圈,身上还缠着绷带,但是人已经有了精气神。
大喜过望的余推子又号啕大哭了一阵子。
余推子带回的消息让二十九团特别是重机枪连上上下下欢腾不已。新任团长专门从前线派人来到医院,通知洪学智伤好后不能到别处去,一定要回到二十九团。
大难不死的洪学智得到的到底是什么药,他一直不清楚,红军医院的医生们也说不上来,后来分析,可能是特效抗生素一类的药品。洪学智对这名医生也一直心存感激。
苏家埠战役后,红四方面军率第十、十一、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回师豫东南商城地区,与红十二师会合。不久,红二十五军成立七十五师,七十五师动员洪学智去当营长。洪学智记着团领导的话,没有同意。
近乡情怯 “我还活着”
洪学智在医院一共住了38天,伤口总算基本痊愈。他听说二十九团又回到潢川,就再也待不住了,要求出院。医生起初不同意,可经不住他软磨硬泡,只好放他离开。考虑到他身体还很弱,路途遥远脚力不及,医院找了副担架,送洪学智回部队。
归心似箭的洪学智坐着担架,从麻埠的红军医院出发,翻山越岭往潢川追赶部队。从麻埠到潢川正好要从双河过,洪学智顺便回了一趟家。
离开的时候,医院给了他两块钱的苏区票。这是发给每个出院伤员的补助,也算是路费。洪学智花一块钱买了包盐,装进背包里。
近乡情怯。这一路走来,所到之处,但见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经年战火,原本青葱一般的家乡被蹂躏得不像样子了,根据地人民饱受敌人“围剿”的惨状,令洪学智痛苦万分。
快要到双河了,远远地看得到双河大庙金红色的屋顶尖了。洪学智不想让家里人看到自己受伤的样子,就支撑着下了担架,说:“我自己走,你们回去吧。”
告别了一路照应他的两个小伙子,洪学智慢慢地走着。双脚踏在家乡的土地上,洪学智的内心禁不住激烈翻腾起来。
村子的变化不大,只是房子更破旧,也稀少了许多。初夏正是插秧时节,田野间却池塘干涸,只偶尔看到有一小块水洼地,几小片绿色。因为人烟稀少,四下里静悄悄的。
一缕烟尘飘过,洪学智看得出是从稻场上飘过来的。场上有四五个人,正在打豌豆。洪学智一步一步挪过去,隔着十几米站下,他一眼就认出了大爷洪金财。
洪學智声音颤抖地叫了一声:“大爷……”
几个人一齐停了手,望着他,洪金财两眼发直,直愣愣地盯着他好久没吭声。
洪学智又叫了一声:“大爷,是我啊!”
洪金财嗫嚅道:“你……你不是……你不是死了吗?”
洪学智明白了,一定是他伤重的消息传回来了,他挥拳抡着胳膊,说:“我这不是好好的,你们看看。”
洪金财走近跟前,先小心地伸过一只手摸了摸洪学智脸,再又摸摸他的胳膊:“没错,热乎的。”
其他几个人也走近来,个个伸手摸摸他的身体:“是活人,不是鬼。”
洪学智哇地哭出来,抱住了大爷:“大爷,我活着,我还活着……”
这时,村里人告诉他,他有一个老乡,也是从双河同他一起参军的,打苏家埠的时候亲眼见到洪学智中弹倒下,一身是血,以为他牺牲了。后来老乡也负伤住进红军医院。他出院回双河时,洪金财向他打听洪学智的情况。他无法隐瞒,只好说洪学智在苏家埠前线带头冲锋时,被敌人一枪打倒。
老实巴交的洪金财哆嗦地问:“打倒……后……怎么样?”
老乡叹了口气,悲痛地说:“唉,胸口中弹,还能怎么样?肯定牺牲了啊!”
洪金财一路呜呜地哭回家,到了家,全家人跟着大哭了一场。
眼见洪学智好端端地站在眼前,大家破涕为笑,簇拥着洪学智回到家里。乡亲们听说“牺牲”了的学智伢子又活着回来了,便都来看望,挤了满满一院子。洪学智打开背包,把带的盐分给了大家。
正在大家感叹唏嘘时,一个高个子女人匆匆地挤进来,喊了一声“小弟……”上来搂着洪学智就哭起来。
“姐姐……”
姐弟二人紧紧拥抱。日夜思念的姐姐就在面前,洪学智觉得仿佛在做梦。
天快黑了,姐姐执意要带弟弟走。洪学智看得出大爷家实在太可怜了,因为找不出啥东西来招待自己,大娘愁得揪着衣襟抹眼泪。于是姐弟俩辞别了大爷大娘,走出村子。
洪学智对姐姐的婆家很熟悉,母亲去世后,是姐姐一直带着他,姐姐婚后不久就把年幼的洪学智带到婆家一起生活。姐夫家是个大家族,姐夫是老小,作为小儿媳妇的姐姐温和漂亮又贤惠能干,深得公婆及众姑嫂的喜爱。洪学智也聪明懂事,在这个家里度过了童年时少有的一段快乐时光。这里的里里外外他都十分熟悉,也很有感情。
但如今姐姐的婆家大不如前了,被连年的战火所累,原本殷实的大家庭现在已是捉襟见肘,生活难以为继。晚饭是菜粥,来回走了几十里山路的姐姐肯定早就饿了,可还是把小半碗底干些的菜粥倒进弟弟的碗里。
姐姐的房间有一架织布机,姐姐回到房间就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一边和弟弟说话。天都黑透了,姐姐还舍不得点亮旁边的半碗油灯。
洪学智见状心里酸酸的,他拿出另一块钱,交给姐姐道:“队伍上发的,姐你拿着。”
姐姐推辞说:“不行,姐不要,你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
洪学智硬塞给姐姐:“姐,我老不在家,这个家大大小小的事我都帮不上,你拿着,队伍上啥都管,我用不着。”
姐姐想了想:“好吧,我先拿着,你这次回来别走了,这钱,留着给你娶媳妇。”
一点温暖的光晕下,坐在门槛上的洪学智手托下巴,出神地看着姐姐。姐姐一下一下地踩着织布机,一缕头发弯弯地垂在了面颊一侧,跟着她的动作一晃一晃地拂动。面庞依旧美丽的姐姐不时地抬起头来,用两根手指拂开头发,冲着亲爱的弟弟轻轻一笑。
这是洪学智参加革命后,与姐姐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洪学智和姐姐相守的最后一个夜晚。
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夜。
姐姐家如今只剩下窄小的两间房,洪学智不便久留,天一亮就回到大爷家。
几天里,洪金财对洪学智这棵兄弟留下的独苗格外疼爱,想尽办法给他弄点好吃的。他让老婆翻遍了谷仓,把用作烧锅的稻草又仔细过了一遍,筛出大半捧谷粒,细细地磨了,煮了一大碗香喷喷的米糊,看着侄子吃下去。
周围邻居们也络绎不绝地过来看望。这家送块红薯,那家给个菜饼子,有几位婶婶实在没什么送的,就带着针线和布头片来,给洪学智缝补破得露洞的衣服。几个婶子们坐在一起,一边飞针走线,一边嘘寒问暖,说到没娘没爹的孩子,她们一边劝慰,一边自己唏嘘落泪。
此情此景深深地刻印在洪学智的脑海里,乡亲们对革命、对红军的一片深情,洪学智终生铭记在心。
洪学智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家乡和乡亲们。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关心家乡建设。身居高位的他先后7次回到故乡,每次都事无巨细地了解各种情况,并且用各种办法帮助和支持家乡的生产发展及文化建设,帮助家乡脱贫致富。
在家住了几天,洪学智体力恢复了些。他惦记着部队正在打仗,想尽快归队。可他不知道怎么对大爷开口。他知道大爷舍不得、也无论如何不会放自己走。
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起来,洪学智拿了两块红薯揣在口袋里对大爷讲:“爷,姐说让我待几天再去看她呢,今天我去一趟。”
洪金财问:“那你好久回转来呢?”
洪学智硬起心肠面对大爷的殷殷目光:“下晌午就回来。”
大爷说:“那就快去快回,我已托人给你提亲了。说不定人家什么时候就来看你呢!”
洪学智说:“那我去去就回。”
洪学智没有去姐姐家,他出了家门后转个弯,顺着岩崖中的羊肠小路,向着潢川方向找部队去了。
回望家的方向,洪学智心里难过极了,他没有和家人告别,甚至没有告诉亲爱的姐姐一声,就这么走了。他不敢向亲人告别,也无法面对亲人们的眼泪。他趴在山头上,冲着父母的坟头、大爷和姐姐家的方向,分别磕了三个头,然后放声大哭了一场。
哭声响彻原野。
空无一人的山坡,陽光静静地照着这个悲伤的年轻人。
哭完,他擦擦泪,紧紧腰带,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天后,洪学智赶到潢川,却扑了个空,一打听,才知道部队已调到新集了。他又连夜赶路,到了新集,总算找到了部队。安顿好后,洪学智马上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又回到了部队,要家里不要惦记。
在信的最后,洪学智写道:我作为一名红军,反动派一天不消灭干净,我就一天不能回家。
洪学智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顺利送达家乡亲人们的手中,当然也不知道他瞒着亲人悄悄离开家后,亲人们是如何寻找无果而伤心凄惶的。直到1937年,洪学智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进入抗大后,才又给家中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还活着,望家里不要惦记。
但没有接到回信。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30万兵力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面对强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终因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人,特别是身为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的错误估计,接连在战略方针上失误,而屡遭挫折,陷入险境。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川、陕,汤家汇红军主力转移,卫立煌遂率部尾随,乘虚占领了金家寨。
这天夜里,冷风扑面,星光暗淡,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四姑墩地区集结完毕。转向外线的部队共计13个团,其中洪学智所在的十师有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此外还有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红七十三师、少共国际团等部共计2万余人,分左右两路纵队向西进发。(待续)
(责任编辑:章雨舟)